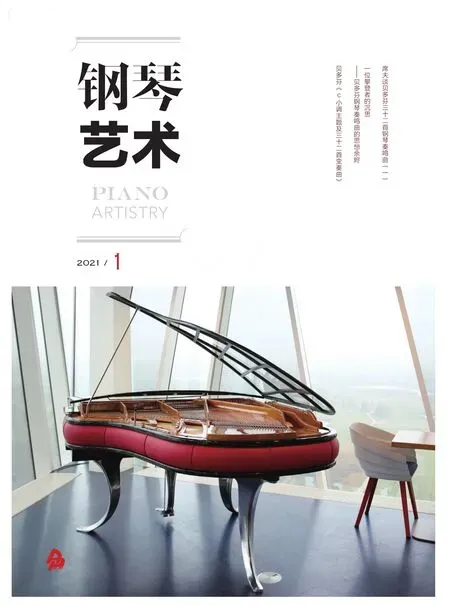深度解析《c 小調主題及三十二首變奏曲》
文/ 孫鵬杰 校譯/ 李穗榮

古典主義時期最盛行的三種主要曲式中,“主題與變奏”在鋼琴領域里占據了最獨特且矛盾的地位。從莫扎特的《媽媽我要對你說》(俗稱《小星星變奏曲》)到貝多芬以當時家喻戶曉的詠嘆調(雖然都早已被歲月遺忘)為題材所作的多首變奏曲,這種體裁具有較為寬容靈活的曲式結構要求和運用即興演奏概念的創作性質,使變奏曲成為最適合普羅大眾娛樂消遣的曲式種類。正是基于這種大受歡迎的親民特點,眾多作曲家們都應市場所需而創作了海量的變奏曲。就貝多芬而言,他出版的大部分變奏曲都沒有作品號,幾乎像是作者在暗示這些“小玩意兒”并不能跟自己其余曠古爍今的巨作相提并論。可是歷史卻偏偏證明了,當變奏曲這個始于平民的體裁在升華為最高境界時,是能成就出如巴赫《哥德堡變奏曲》、貝多芬《迪亞貝利變奏曲》或者勃拉姆斯《亨德爾變奏曲》等曠世神作的。
相比之下,我們很難想象可以把古典主義時期其余兩種最重要的曲式體裁稱之為“具有大師風范的”回旋曲或者“僅限于娛樂消遣的”奏鳴曲。嚴謹的結構和具體的組成部分都是這兩種體裁不可缺少的根基,只有這樣,才能允許作者在史詩般長度的奏鳴曲中條理清晰地編織出哲理深奧的豐富內容;又或者把題材簡單重復性強的回旋曲變成情節緊湊并組織有序的精彩音樂小品,甚至成為奏鳴曲套曲的其中一個樂章。而這些嚴謹的整體結構組織方式,不但奠定了奏鳴曲和回旋曲的地位,也給演奏者提供了如何解剖及還原作品音響的范本。譬如,當我們在學習一首奏鳴曲時,帶著對呈示部(介紹主要調性以及主題)、展開部(闡述主題們的發展)和再現部(讓這次音樂之旅踏上歸途回到主調)的清楚認知,就能更圓滿地完成練習計劃及最終的演繹。
相反地,正因為變奏曲的整體結構組織沒有上述例子中的各種嚴謹規矩,反而能引起觀眾更大好奇心和想象力:親愛的路德維希在下一個變奏又會有些什么操作呢?那么,我們到底應不應該總結出一個常規方式來理解變奏曲曲式,還是僅僅每次都消遣娛樂一下,任由作曲家擺布呢?
實際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種能相對舒適地把變奏曲曲式中的秩序與方向整理好的途徑,否則這篇文章寫到這里就可以收工了。自開始紀念貝多芬250周年誕辰以來,涌現出無數篇關于他那永垂不朽的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的出色文章,精彩不斷。在臨近尾聲之際,我們何不把紀念活動進行到底,來關心一下他的變奏曲呢?于是,我就很順手地以這首《c小調主題及三十二首變奏曲》(WoO.80)為例,找到理解變奏曲曲式的最佳途徑。
第一種途徑就是找出每一個塑造主題性格的決定性特征(見例1)。
例1

這看起來非常簡單,其實內里容納了豐裕、充分的主題材料(見例2)。
例2

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主題成分:(1)下行的低音旋律線條和相對應的和聲進行;(2)織體密度較高的和弦;(3)一直被強調的第二拍;(4)左右手之間的反向進行;(5)左右手同時形成的琶音;(6)多變豐富的運音法標記;(7)一個奇特的五連音;(8)不斷出現的反復音;(9)一個令人驚嘆的sf 記號;(10)f和p 之間的鮮明音量對比;(11)齊奏的八度;(12)一個低調的結尾。
以上被發現的都是主題最關鍵的特征,雖然看起來有些無關痛癢,但實際上,接下來的三十二段變奏和尾聲的形成都是靠它們的發揮了。這就等同于每個人的某種顏值特征(美人痣、胡子、雙眼皮、健壯的腹肌、高挑的身材)或者性格特點(風度翩翩、急性子、喜歡冒險、深謀遠慮)都會成為眾人對他/她的“標簽化”印象。
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我們去耐心觀察某一個人的急性子是如何在一生中不同階段起到各種變化和影響的,就會發現一個易怒的寶寶會逐漸長大成為一位浮躁的少年,繼而從魯莽沖動的青蔥歲月走到了頑固不化的垂暮之年。如果用同樣的方式去觀察某一個關鍵的音樂動機或者樂思材料是如何在每一個變奏中相繼變化和發展的,相信是同樣有趣的過程。為了能用最短時間去體驗這個過程,我們就來跟蹤主題中尤其顯著的一個動機吧:sforzando !
猶如一位對你人生起了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一樣,sforzando第一次在第6小節登場時,就讓大家拜服這是一位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將是決定余下所有變奏成敗的關鍵因素。在第一變奏中,它以原型第二次出現在了第6小節。到了第二變奏,與第一變奏同樣材料的琶音跑動只是改變了進行方向,致使我們覺得還會在第6小節遇上同樣的sforzandos。可是貝多芬已經開始吊大家胃口,他把sf 換成了fp;然后緊接著在第三變奏sf的記號仿佛已經一去不返,不過卻仍然以雙手的連音小連線來強調了一下第6小節。
劇情到了這一步,相信各位聰慧機智的觀眾們已經盯上了這個sf,隨后的一切發展都會是“貓和老鼠”的游戲,到底貝多芬在下一個變奏又會讓這個動機出什么新花樣呢?在第四變奏,它是一個sfp。在第五變奏,它一分為二,變成兩個sforzando。然后到了第六變奏,我們突然被一連串強拍上的sforzando連環襲擊!以下的列表總結了整首變奏曲中這個狂躁又機智善變的sforzando的每一次活動蹤跡(見表1)。

表1
從以上列表我們能觀察到,隨著樂曲(歲月)的進展(流逝),這個sforzandos(狠角色)現身的痕跡越來越少,這意味著什么呢?為了尋求答案,我們需要啟動第二套可行方案——分段。
在練習變奏曲的時候,我們可以用歸類的方式把數個變奏分成不同的大段落。例如,貝多芬從第一變奏就開始運用的“輕巧琶音跑動”和“重復音輪指”是源自主題中的琶音動機和重復音動機。這個考驗技術的棘手組合在第一變奏由右手開啟,然后由左手在第二變奏接力,最后在第三變奏以雙龍出海的架勢,兩只手反向進行同時耍起來,似乎貝多芬逐漸開始熱身、熱腦,再熱一熱情緒。然后到了第四變奏,音樂仿佛被按下了重置鍵,之前的十六分音符材料突然換成了三連音,不過保留了琶音材料。而這個“重置”正有效地劃分了下一個新段落的開始(見例3)。
例3


如果我們用同樣的歸類方法來把整首變奏曲分段,就會得出以下的組合排序(見表2)。

表2
很明顯,把原本34段的音樂(主題+三十二個變奏+尾聲)精簡成八段的“化零為整大法”讓我們對整首變奏曲的宏觀結構一目了然,從而可以一氣呵成地演奏作品,而不是像流水賬那樣一個一個變奏地接著彈。更奇妙的是,如果我們把同樣的“物以類聚大法”運用在每個變奏的平均音量的變化,會得出以下的列表(見表3)。

表3
從以上列表中,我們不但能看到八個段落的長度和關聯,還可以看到每個段落中的力度變化如何主導著音樂的劇情發展。
在我們對關鍵主題動機做出明察秋毫的提煉,并以其為歸類標準把作品分為八個段落之后,接下來可以進行第三個,也就是最后一個演奏準備步驟了——總結出每一段的戲劇性發展規律。如果觀察一下前面的段落,會發現第一段的使命就是“啟動”這首作品。緊接著,之前提到過的“重置按鈕”開啟了第二段之后,音樂就進入了“探索”已有材料的階段了。然后第三段再次被“重啟”,先是發人深省的醞釀,接著就是第一次高潮的爆發。擁有連續五個C大調變奏的第四段成為了整首作品的“綠洲”,而隨后的第五和第六段分別重復并激烈化了第三段所呈現的“深思與爆發”。最終,第七段和第八段有效率地先后把整個故事“鋪墊結局”和“大結局”了。有了以上總結出來的發展規律,現在就可以用鷹眼視角來清晰透視這首蔓延滋長的大作了(見表4)。

表4
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把主題中的關鍵動機總結出各自的個性特點,盡管結論可以非常的個性化。如同任何一部文學著作或歌劇中的主角和主題,所有決定性的特征都會保持著各自獨有的特點來貫穿整部作品。只要我們對這首變奏曲的主題做一次簡單的“主題動機個性”檢測,立刻能感受到貝多芬的音樂是如何與人生哲理緊密相聯的(見例4)。
例4

主題前六個小節中的堅持與斗爭,終究在最后兩個冷漠的小節中落得了一個憤世嫉俗后的凄涼收場。這種突然被世界拋棄了的落寞感并沒有在余下的變奏中出現,直到整首作品尾聲的最后兩個小節,于落寞中結束(見例5)。
例5

貝多芬仿佛在說,你可以用盡畢生之力去籌謀、掙扎、追求、和斗爭,但是到了最后,就算你擁有了全世界的sforzando都不可以改變你的命運。正如當這首作品中本來桀驁不馴、藐視群雄的sforzandos相繼離去之后,我們也只能啜泣抱怨一聲,默默接受命運。
當掌握了界定動機的特點、結構整體性和感情含義傳譯這三種分析手段之后,就能頓悟“主題與變奏”這個貌似謙虛低調的體裁是如何能成就如《哥德堡變奏曲》或《迪亞貝利變奏曲》般結構宏偉的音樂巨作的。當然,這不代表其余大部分的小型變奏曲就不能運用這三種手段去理解。
在平日的教學中,我經常會把一些小型變奏曲布置給初級學生,不但能掌握豐富的觸鍵及個性變化,還能趁機讓他們從探索中發現音樂作品中的結構原理。所以,如果下一次你發現自己正在彈威武的勃拉姆斯《帕格尼尼變奏曲》、幽默的貝多芬《天佑吾皇變奏曲》,甚至是舒曼的《狂歡節》,請花一些時間去實踐一下我們今天做過的這步。你會發現,即使在看似最謙卑、渺小的簡單變奏曲里,也蘊藏著令你愛不釋手的無價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