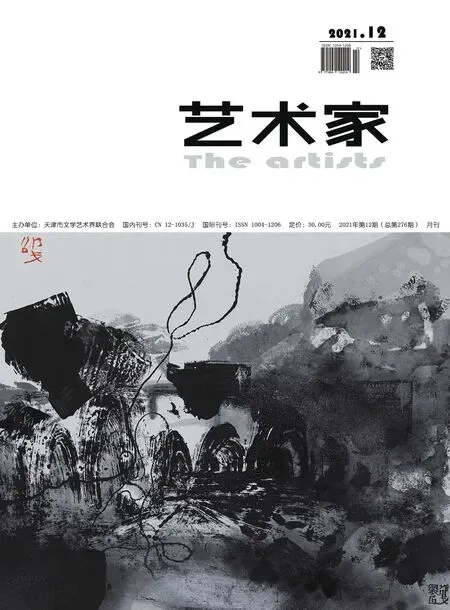淺談當代女性藝術的困境與思考
□劉 佳 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19 世紀出現在挪威的偉大的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創作出的《玩偶之家》是一部經典社會劇。這部戲劇為大眾塑造出一位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她的名字叫娜拉。娜拉一直被人們譽為追求女性獨立的“勇士”。隨著劇情的變化,娜拉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從一個溫婉且順從的家庭婦女到最后逐漸變為一個冷靜獨立、渴望平等與自由、為追求真理而奮斗的女性形象。這場特殊的經歷甚至被稱為女性解放的“獨立宣言”。在當時女性地位較低甚至將女性視為“玩偶”的社會背景下,娜拉這樣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女性,真的能尋求解放和獨立嗎?魯迅先生曾在《娜拉出走后怎么樣》中提到,從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其實也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由此不難看出,娜拉的“出走”是現代女性向前邁進的一大步,這不僅代表了現代女性要求獨立的勇氣,也為“出走”之后該何去何從埋下了伏筆。
《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預示著女性意識的覺醒,也是婦女解放史上反叛他者地位、爭取主體地位的典型代表。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清晰。當代女性藝術萌芽的顯現,標志著父系歷史結構和權力制度逐漸褪色。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娜拉“出走”之后,娜拉與其“藝術”的經歷又發生了什么呢?“出走”雖有其自身人格解放的意義,但也無法避免其孤獨的命運。
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生活敘事和審美敘事已經逐步瓦解了激進主義觀念下的現代行動主義革命的敘事結構。社會現實中的矛盾與對立將改變當下社會的兩性關系,與此同時,也會對藝術的意識形態結構有所突破,進而產生新的創作。由此看來,娜拉的這次“出走”,在女性藝術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同時也是嶄新的現當代女性藝術史的敘事建構。
20 世紀70 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術理論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研究女性藝術,揭示了女性在男性話語權下是受到壓制的。娜拉的“出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女性正在逐漸擺脫傳統藝術史觀念的束縛。然而,由于早期激進女權主義的刻板印象與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大眾的批判,甚至到了提其色變的地步。
這種社會背景下的年輕女性藝術家或文學家都害怕自己被定義為“刻板”的女權主義者,并且把她們與早期激進主義聯系起來。不容置疑的是,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加了解其本身的感官世界與心理世界,并且能夠更直接地理解女性自身對藝術創作的感受,甚至是對生活的理解。女性主義為當代女性藝術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促使人們對藝術表達和理論批評表現出女性的真情實感。這使得女性問題研究視角更加多樣化。我們對視覺藝術的關注已經不單單是研究其藝術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畢竟這也只能作為一種表現和解釋的形式來豐富我們對視覺藝術的關注,并在這個基礎上引發新的思考。在紛繁復雜的社會背景下,兩性之間關系的內在問題表現在方方面面。女性主義只是其中單一的觀點,假設我們只是用這個片面的研究方法來解讀藝術史,就會造成視域的狹隘,理論內容也相對單薄。同時,父權制度下的藝術批評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不能全面地、系統地看問題。這會阻礙我們正確客觀地看到事物的發展變化。近些年來,女性藝術研究者也一直在試圖去解決此類問題。不同的研究方法對藝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兩性交織的社會中要更加理性地去研究問題的本質。
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女性意識在中國女性藝術中開始了全面覺醒。這是一個現代啟蒙思想開始傳播的時期,也是現代性敘事推進建構的新時期。作為一種特殊的思想萌芽,女性意識也逐漸加入了思想解放的浪潮。20 世紀80 年代對意識形態的探索啟發了藝術家們對于自我意識的認識,將自我意識與自我存在從集體意識認知中剝離。對于女性而言,只有實現了人權的自由和平等,女性才能站在一個追求自我的平臺上實現權利自由。而個體的自由是當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女性藝術在社會學意義中的獨特性正是由其本身的性別來闡釋的。正是在這個階段,在大眾視野中出現了一批極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藝術家。然而,在藝術家的群體里,女性藝術對女性主義的感知并不涉及廣泛性。在我國的社會結構中,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不同時期內,在同一線性空間中的女性問題多呈線性分布。具體而言,在女性的藝術領域里并沒有明確地表達女性獨立意識,在女性的藝術理解中也沒有特殊的意義。她們對藝術的理解和判斷仍然是對藝術本身的判斷,并未質疑過其中有不合理性的設定。她們默許了藝術史的合法性,甚至擔心自己的藝術被誤解為基于女性而不是藝術,這時候,她們基本還屬于前女性主義階段。對她們而言,女性只是一種性別認同,而不具備藝術的身份。同時,這個階段也出現了具有藝術語言意識的女性藝術家的自我肯定,主動強調和探索先前存在的女性審美的特征。語言自覺意識是基于主體自覺意識的,主體一旦有了意識,第一個釋放的就是語言霸權中的父權結構。回歸到女性自身上,本能地表達才是女性最真實的性別特征。審美的范疇中包括語言的表達,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又使女性自身的審美陷入語言霸權之中。

圖1
隨著經濟的日益增長,女性逐漸獲得了經濟獨立。這不光是經濟時代賦予了女性經濟上的自由,同時也是女性精神自由的開端。女性藝術集中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根植于西方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闡述了父權制度與女性之間關系的破裂和抵抗;另一個方面是在當今消費主義話語體系中,女性的形象被勾勒出對欲望的渴望。它被放置于消費主義話語的懷抱中,勾勒出在狂歡欲望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主義來源于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慣性邏輯。”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義在中國歷史上遇到的困境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激進的背景下對女性的不信任,仍然存有傳統的思想。另一方面是缺乏女性的發聲。所謂女性藝術理所當然被歸屬于娛樂性活動,而且很難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在人權缺乏的現實面前,女性藝術需要回歸到自由人權的基礎上,以女性主義的方式實現藝術民主和爭取人權自由,這樣才能構建其新的與大眾社會的有機聯系。
在后現代社會的圖景中,呈現出欲望和狂歡的,是所謂消費主義的女性藝術。在經濟獨立的支持下,女性可以成功從玩偶之家“出走”,彰顯出自己獨立的特殊身份。所以,女性藝術的主要內容就是女性形象,不難看出“女為悅己者容”也不會因為女性的“出走”而失去意義。“由于女性在身體上獨有的特點,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差異性讓她們擁有不同于男性的身體體驗,這種體驗造成了女性特殊的視角和視點,創造著她們自己審美趣味的能力”,所以,呈現在圖像中的女性形象不僅僅是男性視角下的所想所看所畫,更是女性藝術家的所思所想所感所畫,女性的自戀自畫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當下盛行的“對鏡貼花黃”。“鏡子充當了女性認識自身軀體獨立于男性的價值(內在欲望)的重要工具,只有借助鏡子,女性才會真正面對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自我軀體的真實”,而女性所謂“出走”所追求的自由,貌似只能在自我的幻想中實現。這便又成為另一種困境,且在這種自戀之后,隱藏孤獨的悲傷難以掩飾。
我們所說的女性的獨立與“出走”應建立在人權的基礎上,而不是將兩性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離。性別的維度是最基本的關系,這也是在世界關系的建構中必不可少的,但這僅僅是其中之一。人類之始,男性與女性就存在于人性的同一緯度中。因此,女權主義抵制父權制度的壓制,并不是歧視和抵制男性,而是借用這個反對來表達女性對于存在男女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質疑,是弱勢群體女性遭受社會霸凌時無助的吶喊。此時的男性也只是某一時段權力的代表。身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弱勢群體不光包括女性,還包括老弱病殘等。因此,研究藝術史不應該單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這不是給予女性的特權,而是需要結合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實際情況。女性主義是一種向往自由和尊重、渴望平等和純凈的精神。性別之間的關系紐帶和情感狀態并不應該被打破,而是應該在實際生活中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兩性之間要同一緯度尋求自由,以愛之名相融。只有平等和諧看待女性的兩難和性別之間的差異,才能改變所處的困境,脫離聒噪的激進思想和縹緲的虛無主義,才能全面地看待當代女性藝術的困境,以發展的眼光看待藝術史的發展,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將兩性的內在思想和邏輯相融合,更好地解決問題。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說,如果婦女要成為自我,主體,她必須像男人一樣超越所有限定她存在的定義、標簽和本質。她必須努力成為她所希望的人。“脫離傳統觀念束縛,追求女性人格獨立和藝術風格獨立是女性藝術發展的唯一出路。”在藝術實踐中,女性需要超越性別和自我意識,運用獨特的語言風格,深入地表達雙性社會中個體的自我愉悅、自我痛苦、自我理想,拋棄激進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欲望來看待世界,從兩性平等的視域出發,客觀地看待藝術、社會及自我之間的聯系。
女性藝術家在藝術史中的歷史沉積和杰出創造成就了“女性藝術”。中國當代女性藝術更是受到了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啟迪,有屬于自己本土化的特點。其中不缺乏女性藝術家情感的表達和質樸的創作。她們打破了建立的規矩與標準,創作狀態正如“隨心所欲,不逾矩”。這也是當代藝術正面臨的一個轉折點,同時,女性藝術也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和機遇。這就需要注入新的價值觀,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同時,女性藝術家要不斷進行反思,包括自身的本土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發展,要開闊跨文化的視野,有選擇地汲取經驗。更重要的是,類似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運動反映了女性意識的覺醒,這也使女性將個人價值和社會背景的歷史語境相結合,從而通過藝術實踐獲得更多的創新和突破。當代女性藝術實踐對社會文化產生了影響,同時也建構了獨立的女性話語體系,為女性開辟了一條自我探索和跨越之路。只有在藝術實踐中不斷思考,在審美維度上正視性別觀念,才能通過藝術的方式引導大眾跨越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