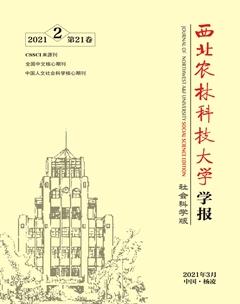供應鏈金融對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緩解效應








摘 要:中小農業企業為促進我國農業產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農業天然弱質性且生產周期長,生產規模小、財務規范性差及抵押資產不足等原因導致中小農業企業具有較高的融資約束。農業供應鏈金融可以彌補中小農業企業的信用缺失,降低銀企的信息不對稱,從而緩解其面臨的融資困境。在對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因素及緩解效應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以2012-2018年A股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中涉農中小企業數據為研究對象構建回歸模型并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受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因素的影響,供應鏈金融能顯著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并通過降低企業間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來增強這種緩解效應。
關鍵詞:供應鏈金融;融資約束;中小農業企業;信息不對稱;信用風險
中圖分類號:F30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1)02-0140-12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671054);國家留學基金項目(201808230348);惠州學院教授、博士科研基金項目
作者簡介:付瑋瓊,女,哈爾濱商業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供應鏈金融。
引 言
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黨和政府多年持續聚焦“三農”問題,將農業問題列為日常工作之重。現代農業的發展不僅需要科學技術創新,更需要金融支持與創新。目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金融支持匱乏,主要表現為中小農業企業和農戶融資難,而供應鏈金融的出現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近年農業農村部陸續發文表明農業經濟的發展應依賴于農產品和金融的高度融合,即建立以農業為主體的金融架構。利用本地農業的優勢和特有的農產品,以農業供應鏈的龍頭企業為融資核心,聯合其他中小型企業、個體農戶和消費者等參與主體,通過有效信息整合,調整生產滿足供應鏈各個環節的金融需求,共同獲利。在政府的重視和推動下,農業供應鏈金融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戶和涉農中小企業資金缺乏的問題。但是相對于大企業,涉農中小企業技術含量偏低、同構性較大,貸款意識落后,難于獲得股票和債券的融資;有效擔保和抵押資產受限、支農貸款挪為他用的現象層出不窮,再加上農業本身受自然災害和價格波動影響較大,中小農業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弱,難于從金融機構籌借資金。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給諸多中小企業帶來的重創遠高于大型企業,農資中小企業儲備明顯不足,疫情下人員無法復工、運輸停滯、原材料上游企業停產造成農資企業生產能力大幅下降;禽類養殖和生產企業也由于疫情禁止銷售活禽,各地紛紛關閉了交易市場;農產品銷售企業由于“封城封路”導致保質期較短的農產品配送艱難、腐壞嚴重、損失巨大。這讓原本就資金短缺的農業中小企業更加捉襟見肘[1]。資料顯示,目前涉農中小企業融資狀況依然嚴峻,不良貸款率高居各行業前三位,信用風險堪憂。盡管疫情下依靠國家出臺的各種政策福利能得到一定貸款風險補償,擴展融資渠道,但是農業中小企業固有的信息不對稱、財務管理混亂、盈利能力低下等風險才是限制企業發展、無法抵御外來環境變化風險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從根本上解決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問題仍是推動我國農業發展的關鍵。
自2014年國務院正式提出創新供應鏈金融模式緩解中小農業企業融資難以來,我國涉農貸款余額平均每年提高16.5%。截止2018年末,貸款余額比2017年增加了5.3倍,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也有較快發展(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2018)》),說明供應鏈金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改善中小農業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根據農業經營主體不同可將涉農主體分為農戶、農村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龍頭企業及中小農業企業,其中農戶及農村合作社的融資主要依靠從私人手中或民間借貸機構的直接融資和參與地方政府投資項目、政府協調的國內外貸款項目等間接融資;農業龍頭企業和中小農業企業主要通過信貸和非信貸的方式獲得融資,其中大型企業可以依托大型金融機構及資本市場較容易地獲得直接融資[2],而中小農業企業由于弱質性等特征鮮少從非信貸渠道獲得融資,存在較大的融資約束,主要依靠供應鏈金融以農業供應鏈中的核心企業為依托緩解融資約束。在農業產業化政策的指引下,為了實現傳統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的現代農業轉變,需要培育農業龍頭企業,大力扶持中小農業企業,從而帶動農戶,推進農業產業一體化進程。因此,本文以如何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為研究對象,對于解決農業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及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有重要的意義。此外,在現有多層次資本市場中,可以為中小板農業中小企業緩解融資約束提供理論及數據支撐。
根據億歐智庫的統計發現,目前資本市場上農業融資企業主要包括:農資研發、農業信息科技、農業種植、畜禽養殖、農業金融、農業服務、農機植保、土地整合、食品安全、生態農業、綜合企業、農業環保、農機生產,而中小農業企業主要集中在農業種植、養殖、生態農業、農產品加工和零售等,遍布于農業供應鏈的上中下游各環節,其融資模式更貼切供應鏈金融的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模式。本文以2012-2018年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創業板及中小企業板涉農中小企業為樣本,研究可以代表供應鏈金融中各環節的涉農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為中小農業企業開展金融服務、提高融資效率提供實證依據。
一、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文獻回顧及機理分析
(一)文獻回顧
由于中小農業企業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弱,信用較差,因此信用貸款比例較少,加劇了融資難度。周敏等認為,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銀企的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違約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3]。我國金融制度的微調導致銀行貸款審批層層把關嚴控,使得這種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擴大[4]。中小企業的融資窘境同樣適用于中小農業企業,并且農業企業自帶生產周期長、抗風險能力弱的天然屬性,使得信貸難度更大。此外,中小農業企業或者農戶缺乏與金融機構的長期的良性互動關系,無法彌補由于自身財務報表失真、經營規模小、抵押農產品不穩定等中小企業的“固有缺陷”,導致面臨較高的融資成本[5]。顯然,信息透明度低的中小農業企業獲得銀行借款的難度可能會加大,或者需要付出更高的貸款成本。
信用風險是金融機構衡量是否給中小企業融資貸款的重要指標。根據2017年全國細分行業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占比統計,繼制造業(32.12%)、批發零售業(27.17%)之后農林牧漁業位列第三(6.18%),而在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中有不少涉及農業制造業和銷售的中小農業企業,證明中小農業企業的不良貸款率偏高,信用風險堪憂,這與我國中小企業的特點及農產品特有的自然屬性不無關聯。農產品生產周期長容易滯銷導致虧損,引發中小農企的內部違約動機[6];同時,環境的變化、突發事件的出現及市場的波動都會引起外在違約動機,比如新冠疫情下中小農企的困境遠高于龍頭企業。金融機構難以根據中小企業的信息披露情況監控其行為,因此銀行會提供較高的貸款利率保證自身資金安全;而高利率會促使中小企業通過投資高風險項目以還貸,從而加劇了自身的信用風險[7],這也是我國中小農業企業不良貸款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農業供應鏈金融源自金融服務與供應鏈結合的的一種創新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因而大多數學者都集中于農業供應鏈金融概念及模式的研究。以楊進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農業供應鏈金融基于供應鏈管理思想是以核心農業企業為主,通過契約和利益與上下游的農業中小企業形成密切合作關系,以供應鏈的整體授信提高農業中小企業的信用,從而提高融資效率[8]。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供應鏈金融的應用有效地緩解了農業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境,并為農業產業化進程做出積極貢獻[9]。由于農業中小企業的產業特點、生長和生產周期相似,有利于實現農業供應鏈金融服務的標準化、流程化操作,實現農業供應鏈的規模效益。因此,一些學者在實踐中開始研究農業供應鏈金融模式,根據農業中小企業處于供應鏈中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的不同節點,可以將農業供應鏈金融模式分為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及存貨質押模式[10-11],并陸續以龍江銀行的金融項目“惠農鏈”[12]、馬王堆蔬菜批發大市場批發中心模式[13]、農業銀行的蔬菜供應鏈金融模式等驗證了農業供應鏈金融模式的可實操性。究其根本原因,農業供應鏈金融模式主要通過農業核心企業的實力降低中小農業企業的信用風險和違約風險,依賴供應鏈的整體協調性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化,并保障交易的穩定發展,從而改善中小農業企業融資困境。
國內關于供應鏈金融和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研究中,多數用實證的方式驗證這種融資約束的存在性,對其原因和影響因素的分析并不全面,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數據是否適用于中小農企也有待進一步考證。事實上,信息不對稱和信用風險的疊加效應對于中小農企的影響更為深遠,值得深入研究。
(二)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1.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機理分析。融資約束是當企業對外融資成本過高,使得投資回報與融資成本不成正比,從而限制了企業對外融資的機會。對外融資渠道主要包括向金融機構的抵押貸款或上市融資,大多數中小農業企業由于農產品加工銷售利潤低,股本總額小,達不到上市準入門檻要求,無法進入證券市場直接融資,只能通過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實現間接融資[14]。同時,涉農中小企業經營不穩定、信用風險高、信息披露質量不高,金融機構對其信用評級低,在融資中需要提供相應的質押物實現抵押貸款,而大企業憑借其商業信用就能獲得銀行的信用貸款。相較之下,缺乏融資擔保的中小農業企業融資難度更大。此外,農產品具有自然和季節性風險,生產流程簡單,比較利益低,使得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比其他行業更為嚴峻。中小農業企業面臨融資約束的主要因素如圖1所示。
在傳統中小企業融資中,銀企形成單一的委托-代理關系,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銀行只能根據中小企業披露的部分盈利和負債等財務信息確定貸款利率,易產生“逆向選擇”,迫使穩健型的中小企業退出,高風險的中小企業進入,提高了銀行的風險概率。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可知,在商品市場上,掌握充分信息的“代理人”和信息掌握不充分的“委托人”存在逆向選擇和違約風險的可能[14],從而提高融資成本。在借貸市場上,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保證借貸安全,需要根據中小農業企業披露的財務等信息進行信用評估,而披露的信息往往不真實或不全面,使得金融機構只能剔除信息披露質量較低的企業,或者對中小農業企業提出高于大企業的抵押擔保要求,以彌補潛在的融資風險,無形中加大了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的成本和難度。因此,信息是否對稱是金融機構貸款決策的重要參考,也是中小農業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因素之一。
信用風險即違約風險,是指在信貸中,中小企業獲得銀行授信后,違背合同改變貸款用途,或者企業缺乏償還貸款能力而故意違約的行為[3]。融資契約雙方的信息存在“孤島現象”,銀行不可能完全了解借款人的履約能力,以及借款投資項目的風險水平,只能根據平均風險狀況和盈利能力確定貸款利率,導致資金流向低信用者,致使商業銀行貸款平均風險提高[15]。銀行面對違約風險高的中小農業企業時,最優策略是拒絕授信,因此造成了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困境。同時,農業的天然弱質性加劇了中小農企的經營和違約風險,影響其授信能力。國外學者對美國公開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量的決定因素研究發現,信用風險與企業現金持有量成反比[16],而現金持有量反映了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因此認為信用風險是影響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供應鏈金融緩解融資約束的機理分析。供應鏈金融緩解融資約束的作用機理在于依托農業產供銷一體化的供應鏈交易背景,降低金融機構與融資企業間的融資成本、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幫助中小農業企業順利獲得金融資源。供應鏈金融模式下,中小農業企業將應收賬款或預購的農產品質押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依托核心企業的信用擔保或者將農產品交給第三方物流企業監管,將與中小農業企業的單方合同關系擴大為多方合作,分散了中小農業企業的信用風險,降低了融資成本。譚喻縈等從博弈的角度認為供應鏈金融模式是中小企業、金融機構、核心企業多方博弈降低信用風險的惟一均衡決策[17]。
第一,供應鏈金融可以降低融資成本。企業融資成本屬于交易成本理論范疇,影響交易成本的三要素為資產專用性、交易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15]。傳統融資下,中小農業企業和金融機構很難做到完全理性,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出現的欺騙、違約等行為必然增加融資成本。而供應鏈金融模式下,金融機構憑借農業核心企業的信用擔保對整條供應鏈提供金融服務,降低交易頻率;利用核心企業掌握中小企業的財務、信用狀況等信息,快速甄別優質企業,降低信用風險的調查成本,提高交易的穩定性[18];利用第三方物流企業控制農產品儲存和質押的權限,在融資中后期監控中小農業企業的資金使用和還款去向,消除融資資產的不確定性,降低融資管理成本。
第二,供應鏈金融可以實現信息共享。為了保證供應鏈金融整體運營的有效性,核心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及中小農業企業必須以信息共享為前提,保持穩定而長期的合作關系。這就給金融機構傳遞了一種信號,即只要是進入供應鏈中的中小農業企業,其信息透明度相對較高。同時,核心企業、物流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會對中小農業企業的規模、償貸能力、資信狀況全面評估,這增強了中小農業企業的信息共享程度,極大地提高融資效率。在農業金融服務中,第三方物流協助銀行看管農產品等質押物,提供相關信息,改善了銀企的信息不對稱。或者通過供應商回購模式以分擔風險、提升流動性溢價[19]。通過供應鏈金融模式可以顯著降低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提高融資效率[20];融資效率與融資約束成反向變動,也可以初步判斷在供應鏈金融模式下,信息共享程度較高的中小農業企業會更快突破融資約束的困境。在貸款前期,農業核心企業與中小企業通過穩定合作關系實現利益捆綁,打通信息孤島,憑借自身優勢充分掌握中小農業企業的經營狀況、財務風險等信息,并以自身信用能力為擔保,提供充足信息給金融機構作為甄別優質貸款企業的依據,規避逆向選擇問題[21]。
第三,農業供應鏈金融可以降低融資風險。農業供應鏈金融本質是通過上下游企業間信譽共享,將中小農業企業的信譽度提高到與核心企業同等水平,從而降低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風險,形成可靠的信譽體系[22]。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核心企業的信譽及第三方物流企業對農產品的質押監管,監督融資企業的交易信息,嚴格控制信貸資金的用途,防止企業逃避償貸責任,降低中小農業企業的道德風險。國內學者從相反角度證明了企業的商業信用可以緩解企業融資約束,而商業信用與信用風險成反比,意味著降低信用風險可以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緩解融資約束[23]。在貸款中后期,核心企業、物流企業均可以作為中小農業企業的委托人和金融機構的代理人,通過控制整個供應鏈中的金融鏈,監控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資金及使用,最大程度地實現透明化,降低了道德風險的發生率,提高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可得率和信用程度,降低由于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風險[24]。
供應鏈金融正是基于供應鏈網絡化特點,實現核心企業和第三方的多重監管以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大大提高融資效率[25]。隨著金融區塊鏈技術、物聯網、云計算等廣泛的應用和農業供應鏈金融信息平臺的使用,農業中小企業信用風險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24]。基于以上分析,構建本文分析的邏輯框架(見圖2)。
本文的研究假設如下:
H1:中小農業企業面臨較明顯的融資約束;
H2: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受信息不對稱程度影響,即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中小農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大,反之則越小;
H3: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受信用風險水平影響,信用風險越大,中小農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大;
H4:供應鏈金融可以降低中小農業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
H5:供應鏈金融可以降低中小農業企業的信用風險;
H6:供應鏈金融可以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
H7:供應鏈金融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來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
H8:供應鏈金融通過降低信用風險來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
二、變量選擇及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選擇
本文數據來源有兩部分:(1)查詢CSMAR國泰安和RESSET數據庫,參照《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以2012-2018年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布的A股農林牧漁業及與農業相關的制造業、零售業等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2)查詢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公布的中小農業企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評并統計。為了確保數據測試的有效性,收集數據時剔除同時在主板上市的大型企業;剔除被ST、*ST的公司;剔除財務數據不全和信息披露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金融類公司;根據收集數據及手動計算并進行排序,剔除嚴重偏離度超過30%以上的異常值[11],最終得到2012年52家、2013年54家、2014年58家、2015年65家、2016年71家、2017年77家、2018年77家,共454家企業數據,2 694個樣本觀測值。運用EXEL及SPSS24.0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
(二)變量選取
1.主要變量的選取。被解釋變量:用C表示現金持有量的變動額,衡量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用當期的貨幣資金及現金等價物相對于上一年的變動額除以當期公司總資產計算得出[12]。
自變量的選取:(1)用CF表示當期現金流量,即用當期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除以當期的公司總資產計算得出[11]。(2)供應鏈金融發展水平用S表示,即用企業的短期貸款和應付票據之和的均值來表示供應鏈金融發展水平[23]。短期貸款額代表企業為了緩解短期資金需求,向金融機構借入的為期一年內的貸款,可以視作中小農業企業采用存貨融資和應收賬款融資的兩種供應鏈融資模式的代理變量;應付票據是采用商業承兌和銀行承兌匯票,視作中小農業企業預付賬款的供應鏈融資模式的代理變量,兩者的加和可以全面反映中小農業企業不同供應鏈融資模式的發展水平。(3)中小農業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選取兩種表示方法:第一,用D表示股票分析師的預測準確度,參考董秀良的做法并做了一些調整[26],D值越大,表明分析師預測準確度越高,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小。第二,用I表示信息披露水平,以深圳交易所公布上市企業信息披露結果為準,分為A、B、C、D四個等級,對應信息披露質量由高到低,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中小農業企業與貸款銀行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低。(4)中小農業企業的信用風險用RK表示,梳理文獻發現,經典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包括信用評級模型、判別模型等。考慮到該模型的行業適用性和計算可得性,本文參考史雪明的做法采用巴薩利模型來計算信用風險,計算公式見表1。計算結果稱為巴薩利值,該值越大,表示信用風險越小,反之,則信用風險越大[20]。
2.其他變量選取。其他控制變量主要選取能反映公司規模、負債、盈利、投資機會等財務數據,本文使用的所有變量的解釋及計算見表1。
(三)回歸模型構建
1.融資約束基本模型及擴展。受融資約束的中小農業企業相對大企業很難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不得不從企業內部的現金流中提取資金,累計以作為未來投資和自身發展的需求,此時,中小農業企業會存在一定現金-現金流敏感度。國內外學者進一步驗證了融資約束與現金-現金流敏感性存在著正的相關性[10、27]。基于此,本文構建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基本模型為:
由于中小農業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較大,同時信用風險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企業融資約束,為了說明融資約束的影響因素,根據H2、H3,對模型(1)進行拓展,增加D、I、RK及與現金流CF的交乘項,形成如下擴展模型:
為了驗證H1,模型(1)預期β1為正,且顯著,說明中小農業企業存在明顯的現金-現金流敏感性;為了驗證H2、H3,模型(2)當F2=I,預期β3顯著為負;當F3=RK,預期β3顯著為負。
2.信息不對稱程度及信用風險的模型。中小農業企業存在較為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及信用風險,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其信用評分較低,而供應鏈金融模式可以依托核心企業資信水平,緩解其信息不對稱程度及信用風險。根據本文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構建和發展出信用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的模型如下:
為了檢驗H4、H5考察供應鏈金融是否可以降低中小農業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及信用風險,在模型(3)~(5)中分別加入衡量供應鏈金融發展水平的變量S,得到模型(6)~(8),預期模型(6)~(8)β1顯著為正。公式如下:
3.供應鏈金融對融資約束的緩解效應模型供應鏈金融通過改善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和交易環境,憑借與核心企業的契約關系提升中小企業的信用水平,降低信用風險和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供應鏈金融緩解融資約束的模型(9),同時為了檢驗供應鏈金融是否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來緩解融資約束的效應,參考周卉等的做法[28],在模型(9)的基礎上增加S×CF×Fi交互項構建緩解效應模型(10)。如下:
為檢驗H6,引入供應鏈金融S與現金流CF的交乘項系數β3,預期β3為負,說明供應鏈金融能緩解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為檢驗H7,引入信息不對稱程度變量,該變量可以用D和I兩個變量衡量,預期β5顯著為正;為了檢驗H8,引入信用風險變量,用R衡量,預期β5顯著為正。說明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或信用風險越高的企業,供應鏈金融緩解融資約束效應越明顯。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1.描述性分析。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結果表明:不同企業分析師預測準確度D、信用風險水平RK及信息披露結果I標準差較大,說明不同企業的信息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都有較大差異,二者變化相似,也反映所選取變量的穩健性。公司規模SZ的標準差為0.8,說明中小農業企業,相互之間規模差異不大;資產負債率RI均值為0.32,小于0.5,說明中小農業企業的負債能力低,融資需求和能力之間不匹配;資產收益率Ro最小值為1.83,最大值為2.17,表明中小農業企業盈利能力相差很多。
2.變量相關性分析。表3為主要變量的相關性結果分析。結果表明:現金變動、現金流量、供應鏈發展水平、分析師預測準確度、信息披露水平、信用風險各指標顯著相關;現金流量CF與現金變動ΔC相關系數顯著為正,可以初步證明假設1的合理性;同時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lt;0.5,說明變量之間并無顯著多重共線性。
(二)回歸結果分析
1.融資約束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在回歸式(1)中CF現金流系數為0.171,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中小農業企業存在明顯的現金-現金流敏感性,即存在融資約束,且該系數越大,融資約束程度越高,驗證了H1,這與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在融資約束影響因素回歸式(2)中,為了解釋現金流CF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受到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的影響,分別引入表示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兩個變量:D和I及與CF的交互項:D*CF/I*CF/RK*CF,回歸結果表明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16和-0.345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根據交互項的原理[15]說明D的加入使CF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力度為:0.153-0.16*D,當D值越小,即預測準確度越低的時候,CF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力越大;同理,I的加入使CF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力度為:0.105-0.345*I,I值越小,即企業信息披露結果越差的時候,CF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力越大。最終得出結論:中小農業企業與銀行的信息對稱程度越高,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低,這與姚王信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回歸分析結果相同,驗證了H2;引入表示信用風險的變量RK及RK與CF的交乘項。結果表明,交乘項系數為0.230,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中小農業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越低,其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反之,融資約束程度越低,驗證了H3。
2.信息不對稱程度、信用風險水平與供應鏈金融。回歸結果見表4,當引入供應鏈金融發展水平變量S后,回歸模型(3)~(5)中其他變量的結果顯著未發生明顯變化,回歸模型(6)~(8)中S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53、0.141、0.095,分別在1%、5%、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S對被解釋變量D、I、RK有正向的作用。即當供應鏈金融水平提高1%,分析師預測準確度D會提高0.153%,信息披露質量I會提高0.141%,從而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同理,信用風險水平RK會提高0.095%,從而降低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因而,中小農業企業供應鏈金融發展水平越高,信息不對稱程度越低,信用風險越小,驗證H4、H5。
3.供應鏈金融對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緩解效應分析。進一步分析,供應鏈金融對中小農業企業是否有緩解作用,這種緩解作用是否可以通過調節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信用風險實現。為了驗證H6,在基本回歸式(1)中引入供應鏈金融發展水平變量S,及S與CF的交乘項,結果見表5。S*CF的系數為-0.268,顯著,表明供應鏈金融確實對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有較強的緩解作用。為了驗證H7、H8,在回歸式(9)的基礎上分別引入信息不對稱程度D/I和信用風險RK變量,以及S*CF*D、S*CF*I、S*CF*RK的交互項,通過三者的交互項系數是否顯著判斷新變量的加入是否具備調節作用。表6回歸式(10)的結果表明,S*CF*D、S*CF*I的系數分別為-0.222和-0.662,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當引入D和I時,S*CF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回歸式的斜率分別為0.222和0.662,即D或I的加入對供應鏈金融對融資約束的緩解作用是正向調節,即隨著D/I值變大,這種緩解效應增強,這與周卉等引入盈余管理程度、分析師關注度和股價非同步性衡量企業信息透明度與供應鏈金融的調節效應分析結果一致[21]。同理,引入信用風險RK及S*RK*CF的交互項,回歸結果表明S*RK*CF系數為0.068,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對供應鏈金融的緩解效應有正向調節作用。最終得出結論:對于信息不對稱程度較大或信用風險較大的中小農業企業,供應鏈金融的緩解效應更明顯,驗證了H7和H8。
(三)穩健性分析
參照以往研究成果中提供的穩健性分析方法,用托賓Q值代替GR,對上述主要回歸模型進行檢驗(限于篇幅,不再報告檢驗結果)。穩健性檢驗表明:模型(1)、(3)~(10)的回歸結果無實質性改變,說明本研究結果是穩健的。
四、結論及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分析供應鏈金融對中小農業企業融資約束的緩解機理,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主要結論:(1)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方式多為向金融機構貸款,由于同金融機構間信息不對稱及本身具有較高的信用風險及融資成本,導致中小農業企業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2)通過引入供應鏈金融模式可以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3)通過降低中小農業企業與金融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及減小中小農業企業的信用風險,供應鏈金融模式能顯著緩解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4)在收集的數據中發現信息披露水平整體偏高,披露結果較差的企業僅占11.1%,對分析結果有一定影響,在引入I分析S對融資約束影響力度變化的回歸分析中,I的加入使得S*CF的系數出現不顯著的結果,雖然不影響本研究,但是信息披露質量的合理性有待考究,至少可以判斷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能單憑借企業信息披露質量的好壞,判斷該企業的信用程度以及其是否可以得到貸款等。
(二)相關建議
根據本文的實證分析,建議從三個方面更好地完善供應鏈金融模式,解決中小農業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
1.從國家政策協調角度。(1)政府需要有效的干預和引導,引入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技術,創建中小農業企業、核心企業、物流企業、金融機構的信息共享平臺或協調機制,具體可以落實到鄉鎮政府、農業銀行及龍頭企業共同出資并監督管理信息平臺。(2)完善農業金融貸款制度。通過立法擴大農產品質押范圍,提供標準化的農產品存貨、預付和應收賬款的信息制度,制定中小農業企業及農戶的抵押資產評估體系和特定的法律規章;重新構建信息披露指標的衡量標準和制度,盡量能充分體現中小農業企業披露的財務數據,以降低金融機構的放貸風險。
2.從金融服務創新角度。(1)金融機構要結合中小農業企業的特點,大力推進應收和預付賬款融資模式的發展,創新與農業企業利率、盈利能力、還款時限相匹配的金融創新產品,如設置農業專項借貸項目,評估中小農業企業借貸風險;與核心企業保持長期的戰略合作,激發其擔保、協調、監管的功能,防止核心企業和中小農業企業聯合騙貸。(2)通過與保險公司或其他擔保機構合作分散信貸風險;完善金融機構內部的貸款審批體系,嚴控準入資格,利用人民銀行查詢中小農業企業和核心企業的購銷記錄、應收賬款的轉讓、質押等情況,提高一線業務人員的職業素養,避免操作風險,保障資金的良好流動率。
3.從中小農業企業自身管理角度。(1)中小農業企業應以龍頭企業為標桿建立規范的財務管理制度,以符合金融機構的信貸評估標準;保持與核心企業的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以獲得核心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的融資擔保,提升信貸能力。(2)轉變企業傳統形象,向綠色農業、有機農業的政策方向靠攏,堅持產融結合的思想,在農村金融戰略的基礎上,實現“融資+保險+龍頭企業+中小農業企業”協同發展的新思路。
參考文獻:
[1] 黃慶華,周志波,周密.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應對策略[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6(3):56-68.
[2] 華中昱,林萬龍.貧困地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需求狀況分析——基于甘肅、貴州及安徽3省的6個貧困縣調查[J].農村經濟,2016(9):66-71.
[3] 葛永波,張萌萌.企業融資偏好解析——基于農業上市公司的實證數據[J].華東經濟管理,2008,22(6):42-48.
[4] 張捷,王霄.中小企業金融成長周期與融資結構變化[J].世界經濟,2002(9):63-70.
[5] 盧強,劉貝妮,宋華.中小企業能力對供應鏈融資績效的影響:基于信息的視角[J].南開管理評論,2019,22(3):122-136.
[6] 張玉明,趙瑞瑞.共享金融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機制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9(6):58-65.
[7] 何自云.不良貸款容忍度與中小企業貸款[J].中國金融,2010(14):94.
[8] 楊進先.農業供應鏈金融模式探索[J].中國金融,2012(22):85-86.
[9] CHRISTIN M.Supply Chain Differentiation,Contract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Marketing Preferences[J].Food Policy,2014,10:667-677.
[10] 姚王信,夏娟,孫婷婷.供應鏈金融視角下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及其緩解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34(4):105-110.
[11] 朱秋華,楊毅,楊婷.信息披露質量、供應鏈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企業經濟,2019(6):89-96.
[12] 曾青福.“惠農鏈”農業供應鏈金融體系的設計與實現[J].金融電子化,2014(3):67-69.
[13] 邵嫻.農業供應鏈金融模式創新——以馬王堆蔬菜批發大市場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13,34(8):62-68.
[14] 周敏,雷國平,匡兵.信息不對稱下的農地流轉“檸檬”市場困境——以黑龍江省西城村例證[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118-123.
[15] WILIAMSON O E.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87(3):548-577.
[16] OPLER T,PINKOWITZ L,STULZ R,et al.Th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Cash Holding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52(1):3-46.
[17] 譚喻縈,楊箏.基于收益共享機制的線上供應鏈金融最優均衡策略研究[J].管理評論,2019,31(9):241-254.
[18] 羅正英,張雪芬,陶凌云,等.信譽鏈: 中小企業融資的關聯策略[J].會計研究,2003(7):50-52.
[19] 周月書,王雨露,彭媛媛.農業產業鏈組織、信貸交易成本與規模農戶信貸可得性[J].中國農村經濟,2019(4):41-54.
[20] 史雪明,張志林,許立新.信用風險, 融資約束與投資行為——基于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實證分析[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48-54.
[21] 楊軍,房姿含.供應鏈金融視角下農業中小企業融資模式及信用風險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7(9):95-104.
[22] 鄭建明,王萬軍,白霄.制度環境,現金持有與信用風險[J]. 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7(5):104-119.
[23] 王立清,胡瀅.供應鏈金融與企業融資約束改善——基于產融結合與戰略承諾的調節作用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8,32(6):122-128.
[24] 申云,陳慧,陳曉娟,等.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實證分析[J].世界農業,2020(2):59-69.
[25] 宋華,楊璇,喻開.信息不對稱下中小企業如何獲得融資績效——基于供應鏈金融的實證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7,31(9):89-99.
[26] 董秀良,張婷,孫佳輝.中國企業跨境交叉上市改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嗎?——基于分析師預測準確度的實證檢驗[J].中國軟科學,2016(9):99-111.
[27] OOTHAKER L E .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J].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1994,45(1):119.
[28] BURRILLl D F.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in Multiple Regression[J].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Toronto,Ontario Canada,1997:777-789.
[29] 周卉,譚躍,鄢波.供應鏈金融與企業融資約束:效果,作用機理及調節因素[J].商業研究,2017(9):163-169.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