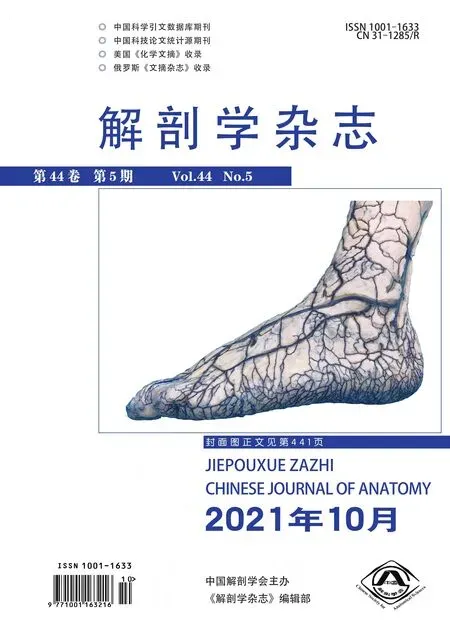脂肪干細胞在皮膚損傷再生及組織工程中的應用及進展*
朱 亮 林享玉 何 晶
(同濟大學醫學院病理和病理生理學系,上海 200092)
皮膚作為人體最大的器官,是隔離外界環境的天然屏障。燒傷感染、外科手術及放射性損傷等都可導致皮膚損傷[1]。尤其是大面積皮膚缺損,雖然臨床上多采取自體皮膚移植,但供體來源不足及二次損傷等都限制了其應用,而同種異體移植又面臨免疫排斥而難以獲得更好療效。干細胞技術和組織工程的飛速發展,為組織器官損傷修復、重構再生提供了更具優勢的新途徑,成為再生醫學領域最具潛力的發展方向之一,也為大面積皮膚缺損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2]。種子細胞是皮膚組織工程的關鍵要素之一,而干細胞因增殖能力強、多向分化潛能被認為是理想的種子細胞來源。干細胞包括胚胎干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ESCs)、誘導多能干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和成體干細胞等,其中ESCs 存在倫理學方面的爭議,而iPSCs涉及安全性、效率和再分化機制等方面的問題,目前均難以用于臨床;成體干細胞是從成體組織中獲得,例如脂肪干細胞(adipose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ASCs)、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BMSCs)、牙髓干細胞(dental pulp stem cells,DPSCs)等,近年來在再生醫學領域開展了大量的研究[3]。其中,ASCs是2001年Zuk等[4]首次從脂肪組織中提取,其具有來源豐富、損傷小、獲得量大、增殖能力強且免疫原性低等獨特優勢,被認為是組織工程理想的種子細胞之一。現主要從ASCs的獲取培養、生物學特性及其在皮膚再生及組織工程中的應用及相關研究進展展開論述。
1 ASCs的獲取和體外培養
1.1 ASCs的獲取、分離
ASCs多通過腹部或臀部等部位抽脂、吸脂術獲取。無論是人或者動物,ASCs分離方法和其他間充質干細胞類似,均可通過酶消化法或者非酶促分離法來獲得。酶消化法最為常用,主要通過膠原酶消化細胞間的膠原組織,使細胞彼此分離,再經過過濾、洗滌和離心等操作等后獲得單細胞狀態的ASCs,速度快,但成本稍高。而非酶促分離法包括組織塊貼壁法、梯度離心法等。組織塊貼壁法存在細胞貼壁難,漂浮在液體中容易在換液過程中丟失;而梯度離心雖然操作簡單,但仍有損失大、獲得量有限的問題,因此非酶促分離法在實踐中較少采用。
1.2 ASCs的純化
脂肪屬于中胚層,類似于骨髓擁有豐富的基質,包含有多種組織成分。酶消化法所獲得的是一個混雜的細胞群,又稱為血管基質部分(stromal vascular fraction,SVF)。SVF除了具有多向分化能力的ASCs,還含有分化在不同階段的脂肪系細胞,如成熟的脂肪細胞、前脂肪細胞及脂肪祖細胞等,另外還包括成纖維細胞、周細胞、內皮細胞、內皮祖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免疫細胞和造血干細胞等多種細胞成分[5-6]。有研究顯示,ASCs作為SVF的干性成分,實際上主要分布在白色脂肪組織中血管周圍[7]。而通常人ASCs可通過多次傳代培養,逐漸提高ASCs的純度,干細胞表面標志鑒定顯示純度可達95%以上。也有學者通過免疫磁珠或流式分選等方法進一步純化ASCs。
1.3 ASCs的體外培養
ASCs的培養方式、培養體系及氧濃度[8]等均是影響ASCs體外培養的重要因素。相較于傳統的2D培養,3D培養方式可以促進細胞增殖和特異性蛋白表達[9]。而無血清培養液可以增強ASCs增殖能力,有效減小其倍增時間,并促進其向脂肪和骨的方向分化[10]。低氧環境不但促進ASCs增殖及干性維持[11],也促進多種可溶性因子的合成和分泌[12],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同時有利于血管化[13]。
2 ASCs的生物學特性
2.1 ASCs的分化能力
與BMSCs相似,ASCs在特定的誘導條件下具有分化為脂肪細胞、軟骨細胞、骨細胞、內皮細胞、角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神經細胞、尿路上皮細胞、心肌細胞等的多向分化能力[14-16]。而與BMSCs相較,ASCs具有損傷小、獲得量大及異位骨化可能性小的獨特優勢,使其在臨床治療的應用中具有更大的潛力。同時,供者年齡、組織類型、取材部位、手術方式、培養條件及細胞密度等都可能影響到ASCs的活力、增殖和多向分化能力。
2.2 ASCs的分泌功能
ASCs具有強大的分泌功能,例如其可分泌多種血管生長因子,包括VEGF、胰島素樣生長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肝細胞生長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和血管生成素等,有助于血管內皮化及微血管形成。ASCs還可合成及分泌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類、集落刺激因子類、干擾素類、趨化因子類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17],參與脂代謝、食欲及胰島素敏感性等的調節。同時,ASCs分泌如外泌體等細胞外囊泡,囊泡內帶有大量蛋白質、RNA和脂質分子等生物活性物質,參與到周圍細胞發育和功能的調節中[18]。
2.3 ASCs的細胞表型
目前分離獲取的ASCs經過體外傳代培養后可獲得純化,其細胞表面可表達特征性受體和黏附分子[19]。與其他成體間充質干細胞的表型類似,ASCs具有如CD73、CD90、CD105等多種間充質干細胞的特異性表面抗原[20]。
3 ASCs在皮膚組織工程及再生中的應用
3.1 促進皮膚創面愈合
3.1.1 調節炎癥反應促進修復 ASCs在創面炎癥初期遷移至局部創面部位發揮重要作用[21]。有研究表明,ASCs促進炎癥局部血管生成和上皮細胞增殖再生,同時通過促進巨噬細胞等炎性細胞及內皮祖細胞的遷移,從而促使局部創面成纖維細胞增殖遷移和肉芽組織增生調節炎癥反應,該作用相比于BMSCs更具優勢[22]。ASCs分泌多種生長因子調控成纖維細胞和內皮祖細胞等的生長、分化,促進血管化和膠原合成,為局部創面修復奠定基礎。另外,分泌含有蛋白、脂質和RNA等的外泌體也是ASCs參與創面組織的修復和再生的重要作用機制。Li等[23]的研究顯示過表達Nrf2的ASCs分泌的外泌體可以有效下調局部創面IL-1β、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參與炎癥反應相關細胞因子的水平,從而有效抑制炎癥反應,輔助創面修復。
3.1.2 ASCs促進一般創面愈合 創面愈合是一個涉及上皮形成、新生血管生成以及膠原沉積,并伴有炎癥反應的復雜生理過程,其關鍵因素是局部炎性細胞釋放的細胞因子和新血管形成的數量。研究表明,ASCs可通過分泌多種生物因子促進纖維化,旁分泌相關細胞因子加速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和血管化[24],同時ASCs可以減少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和I型膠原的含量,改善真皮組織空間結構,從而有效抑制創面愈合過程中的瘢痕形成[25-26]。黃敏等[27]將ASCs聯合富血小板纖維蛋白復合物用于治療小鼠全層皮膚缺損,結果顯示可顯著提高創面愈合率,并抑制炎癥反應。
3.1.3 促進難愈性創面愈合 而臨床上一些年老體弱、極度營養不良患者,或者某些具有基礎疾病的患者,其皮膚創面的愈合往往非常困難,例如糖尿病足部創面愈合、放射性損傷皮膚創面等。趙月強等[28]通過自體ASCs局部注射的治療方法,顯示實驗組創面愈合面積顯著高于對照組,創面感染率和平均住院時間顯著低于對照組。這主要依賴于ASCs通過增殖分化為不同類型的組織細胞及分泌VEGF、bFGF等促進成纖維細胞和血管內皮細胞的遷移,增加局部毛細血管和側支循環來促進皮膚愈合[29-30]。另外,Horton等[31]報道ASCs能夠通過下調IL-1等促炎因子、增加IL-4等抗炎因子的分泌調節免疫細胞的數量和功能,從而調節炎癥反應,這對放射性損傷引起的難愈性創面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32]。同時ASCs還可以直接分化為表皮細胞,上述生物因子也可促進表皮角化細胞的增殖和遷移,從而加速創面的再上皮化[33]。
3.2 抑制瘢痕疙瘩
瘢痕形成是創面愈合的自然過程,病理性瘢痕是膠原沉積和重塑異常導致真皮細胞外基質產生過多及降解不足從而形成的,尤其瘢痕疙瘩是皮膚損傷愈合后所形成的過度生長的病理性瘢痕[34]。瘢痕會給患者帶來疼痛、痙攣及功能障礙等,影響患者身心健康。ASCs可以有效降低成纖維細胞和肥大細胞的活性,從而調節膠原沉積,刺激血管再生,可在治療瘢痕疙瘩中發揮作用[35]。
有研究表明,異常瘢痕形成與TGF-β1/Smad信號通路密切相關[36]。Penn等[37]將ASCs和成纖維細胞共培養,顯示ASCs可以顯著降低該通路中的轉化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磷酸化Smad2/3以及Ⅰ型、Ⅲ型膠原蛋白等關鍵成分,防止TGF-β1刺激成纖維細胞從而降低其增殖能力,可以有效抑制瘢痕形成。李響等[38]通過共培養ASCs與瘢痕疙瘩成纖維細胞,24 h后檢測成纖維細胞相關指標,結果顯示ASCs可以顯著抑制成纖維細胞的增殖、遷移和膠原合成能力,并且作用效果可隨ASCs的比例升高而增強。同時,ASCs還可以有效降低病理性瘢痕中成纖維細胞的侵襲性,抑制成纖維細胞向肌成纖維細胞轉化,促進成纖維細胞凋亡。Li等[39]報道ASCs可通過P38/MAPK信號通路促進α-SMA陽性的成纖維細胞數量凋亡及磷酸化p38下調,從而降低膠原沉積,減小瘢痕形成。
3.3 ASCs參與構建組織工程化皮膚
ASCs具有多向分化潛能,例如直接分化為脂肪細胞而填充組織;分化為內皮細胞等促進新生血管形成,為移植組織提供營養,提高成活率;并且可旁分泌VEGF、HGF等多種細胞因子,促進周圍組織修復再生[40]。而新興支架材料等[41]輔助新技術的出現進一步提高了ASCs促進皮膚創面愈合的能力,而且也為其在皮膚組織工程的應用提供新的可能。支架材料可為ASCs的增殖和分化提供適宜的微環境,從而顯著提高創面修復效果、減少瘢痕增生。Machula等[42]以電紡絲彈性蛋白原作為ASCs的遞送載體以評價其在小鼠皮膚切口模型中的傷口愈合效果,顯示ASCs處理組與對照組相比,傷口閉合速度和上皮厚度顯著改善。Wang等[43]以基于多肽的FHE水凝膠(F127/OHA-EPL)作為支架材料結合ASCs外泌體修復大鼠皮膚損傷創面,與對照組相比,顯著加快了創面愈合。Zonari等[44]在3-羥基丁酸-co-3-羥基戊酸共聚物(PHBV)結構上培養ASCs,并將其移植到小鼠背側全層損傷模型中,與對照組相比,PHBV組的VEGF、bFGF和血管密度表達較高。這提示新生血管的形成,并可通過減少TGF-β1和α-SMA,上調TGF-β3的表達,從而修復皮膚缺損,減少傷口疤痕。
ASCs因可增殖分化為皮膚創面修復所需要的各種細胞,以及通過旁分泌作用分泌VEGF等各種生物活性物質的能力,從而調控參與皮膚修復的各種生理機能。因此,ASCs被認為是修復皮膚損傷及構建組織工程皮膚重要的細胞來源,不但在燒傷、慢性難愈性創面等諸多疾病的治療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其作為種子細胞聯合新型生物材料構建組織工程化皮膚,用于將來的大面積皮膚缺損修復也具有明顯優勢。但其向皮膚組織定向分化的誘導方案尚不完善,以及ASCs的混雜性等,都是ASCs應用于再生研究及臨床轉化的難題,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