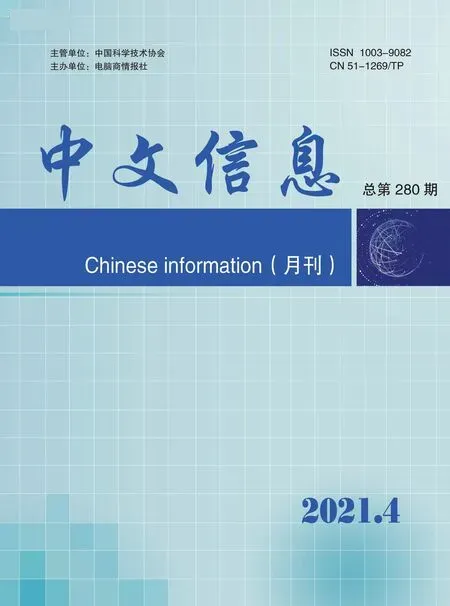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主體與實踐意義探尋
王蘭花
(劍河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貴州 黔東南 556499)
自2004年8月份,我國正式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之后,我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也越來越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是一個民族最為古老的記憶喚醒,也是我們向世界展現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徑,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大背景下,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四大文明當中唯一一個發展至今的文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因此,為了能夠促進我們的基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本文中,作者將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基層主體群眾與實踐意義進行分析。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國基層進行教育傳承的內涵分析
在現如今人類已經擁有的精神文化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內涵的核心內容,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時間、經驗上的積累以及技術上的改進與創新,是最為絢爛的藝術表現形式。簡而言之,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能夠證明人類歷史的證據手段。也正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難以再次出現的歷史文化,所以更加需要我們進行教育傳承,否則將為我們帶來了永久的損失與遺憾。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手段中,傳承的方法多種多樣,傳承的途徑也不再單一,其中,教育傳承就是一個十分有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手段。當前我國基層類似于縣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方式,主要是利用一些公共設施,進行適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活動,或是通過舉辦民俗節慶活動,使基層群眾廣泛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主體;近年來,縣級職業技術學校陸續設置民族文化相關專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滲透到教材中,使學生都能夠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主體。
由此可見,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不同于一些基本的文化傳承,其更加傾向于傳承受眾的廣泛性,并且在影響范圍以及力度上都有明顯的增強。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國基層的教育傳承主體分析
在我國,基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已經區別于傳統的單一的學徒個人傳承,而是向著多方向的傳承受眾主體發展。
首先,就是一些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徒個人。究其根本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得以傳承,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某些個體的積極促進而成的。例如:“苗族剪紙”代表性國家級傳承人姜文英說:“從當前發展來看,我想苗族剪紙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作為‘苗族剪紙’代表性傳承人,傳到我這是第八代,希望在我身上,在傳承、創新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績。”由此可見,姜文英不論是作為師傅,還是作為苗族剪紙的學徒來說,都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傳承個體[1]。
其次,就是社會上的基層,類似對于村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社會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是具有導向作用的,并且這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教育傳承的受眾主體,因此,我國政府要加強對廣大村民群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講座,讓每一個村民都能夠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
最后,就是學校方面對于學生的教育傳承。不論是在以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當中,還是現如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學校都是一個最有效的教育傳承平臺,由于其影響范圍極大,受眾學生群體眾多,所以在校園內開展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活動,或者是將這種思想滲透進學校的教材中,可以更好地讓學生們認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方式,以及傳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三、教育傳承是我國基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手段
之所以說教育傳承是我國基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要手段,主要是因為通過教育,能夠讓廣大群眾感受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所在,尤其是學生群體,讓我國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受眾群體能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發揮著重要的主導地位。在2006年,我國第一屆非物質文化遺產討論大會上,重慶文化遺產學院的專家教授提出了“走進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代”這一關鍵理念,由此我國拉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熱潮,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已經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2]。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在縣級基層的實踐意義分析
首先,就是能夠培養基層村民們的文化自覺性。通過各種途徑的社會宣傳,讓每個村民都能夠了解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具體內容,了解其真正的文化魅力,由此,才能夠提高他們的文化認同感,進而培養他們的文化自覺性,使廣大的村民群眾能夠真正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體。
其次,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還能夠實現教育傳承的社會意義以及提高縣級及以下基層人民的精神文明質量,陶冶人們的情操、豐富人們的文化知識,讓璀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被歷史的長河所淹沒。
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的主體研究,是我們當代進行文化傳承工作當中的重點內容,真正地了解教育傳承的主體,實現傳承的意義,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任務的關鍵。對此,本文中,作者分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國基層進行教育傳承的內涵、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國基層的教育傳承主體以及具體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