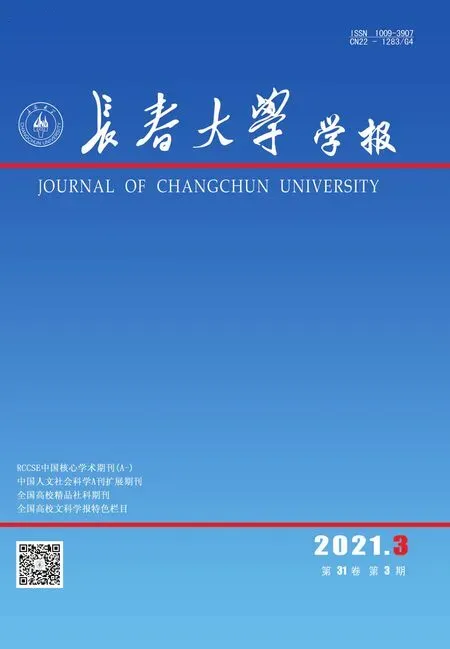從邏輯分析哲學(xué)向心智哲學(xué)的轉(zhuǎn)向
——格賴斯意向性意義理論新解讀
劉景珍
(吉林大學(xué) 公共外語(yǔ)教育學(xué)院,長(zhǎng)春 130012;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 中國(guó)外語(yǔ)與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格賴斯(H. P. Grice)的意向性意義觀萌生于分析哲學(xué)盛行的年代。當(dāng)以賴爾、奧斯汀、斯特勞森等人為代表的日常語(yǔ)言學(xué)派對(duì)弗雷格、羅素等人的邏輯分析傳統(tǒng)提出挑戰(zhàn)之時(shí),格賴斯另辟蹊徑從“說(shuō)話人意圖”的視角出發(fā),展開(kāi)了對(duì)“意義”的另一場(chǎng)哲學(xué)思辨。在格賴斯畢生的語(yǔ)言哲學(xué)探究中,無(wú)論是解釋語(yǔ)言表達(dá)在特定場(chǎng)合傳達(dá)的意義,還是解釋語(yǔ)言表達(dá)本身的意義,“說(shuō)話人意圖”都完美地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1]。本文以“說(shuō)話人意圖”為切入點(diǎn),首先點(diǎn)明了格賴斯意義理論的意向性取向,接著梳理出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哲學(xué)起源、“說(shuō)話人意圖”對(duì)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的劃分,會(huì)話含義推導(dǎo)的重要性以及格賴斯意義理論的貢獻(xiàn)與局限性。
一、說(shuō)話人意圖——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靈魂
(一)意向性之溯源
意向性(intentionality)這個(gè)詞來(lái)自中世紀(jì)拉丁語(yǔ)intentio,意為“延長(zhǎng)”,13、14世紀(jì)經(jīng)院哲學(xué)家用它來(lái)指稱“概念”。intentio被譯成英文intention后,作為術(shù)語(yǔ)仍沿襲拉丁語(yǔ)指稱“概念”這個(gè)用法,而intention用來(lái)指“意圖”則見(jiàn)于日常話語(yǔ)[2]331。意向性就是指“人的意向與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意向性的哲學(xué)思辨就起源于中世紀(jì)的經(jīng)院哲學(xué)。德國(guó)哲學(xué)家弗朗茲·布倫塔諾(Franz Clemens Brentano)在討論真理問(wèn)題中將“意向性”引入現(xiàn)代哲學(xué)。此后,人們把有關(guān)“意向”的議題也稱作“布倫塔諾的論旨”(Brentano’s thesis)[3]。奧地利哲學(xué)家、現(xiàn)象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以及后來(lái)的語(yǔ)言哲學(xué)家格賴斯和賽爾(J. R. Searle)都強(qiáng)調(diào)意義的意向性,他們?nèi)艘脖徽J(rèn)為是意向論的主要代表人物[4]。
(二)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緣起
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觀是以他對(duì)語(yǔ)言、思維和現(xiàn)實(shí)之間關(guān)系的理解為基礎(chǔ)的。在這一點(diǎn)上,他受到了洛克哲學(xué)思想的影響。洛克相信人類理性的能力,強(qiáng)調(diào)理性探究的必要性[5]。洛克在《人類理解論》(1690)專辟一個(gè)章節(jié)對(duì)語(yǔ)言問(wèn)題進(jìn)行了剖析。洛克認(rèn)為,觀念是構(gòu)架人類知識(shí)的基本單位,各種觀念則存貯在人的大腦(mind)里,而思維則是對(duì)這些存儲(chǔ)的觀念根據(jù)需要進(jìn)行的心理操作(mental manipulation)。觀念是客觀事物在心理的標(biāo)示(mental sign),而文字則是觀念的有聲標(biāo)示(vocal sign)[6]。格賴斯秉承了洛克的哲學(xué)思想,認(rèn)為:意義并不是靜態(tài)存在的,言語(yǔ)只是承載了意義的物化形式;意義是需要言語(yǔ)來(lái)表達(dá)的思想,是動(dòng)態(tài)而可變化的;語(yǔ)言表達(dá)了說(shuō)話人的思想,若沒(méi)有這些思想,語(yǔ)言就沒(méi)有了意義,如同鸚鵡學(xué)舌一般[7]24。

圖1 思維、現(xiàn)實(shí)和語(yǔ)言的關(guān)系
格賴斯在《言辭用法研究》的第18章“Meaning Revisited”(再談意義) 開(kāi)篇里探討了思維、現(xiàn)實(shí)和語(yǔ)言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8]284(見(jiàn)圖1)。
如圖1所示,現(xiàn)實(shí)與語(yǔ)言的關(guān)系是間接的,但是無(wú)論是現(xiàn)實(shí)還是語(yǔ)言都與說(shuō)話人的思維有直接的關(guān)系。格賴斯強(qiáng)調(diào)這是他意義分析的理論支撐[8]28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被很多格賴斯研究者忽視了[9]。來(lái)自洛克關(guān)于語(yǔ)言哲學(xué)的影響是促成格賴斯從“說(shuō)話人意圖”的角度去探討意義的重要理論基礎(chǔ)。
(三)格賴斯在分析哲學(xué)流派中的立場(chǎng)
分析哲學(xué)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gè)主要階段:第一個(gè)階段為早期形成階段(也稱為邏輯主義階段),主要以維也納學(xué)派為代表;第二個(gè)階段是日常語(yǔ)言哲學(xué)階段,主要以牛津日常語(yǔ)言哲學(xué)學(xué)派為代表;第三個(gè)階段是自然主義階段,主要以蒯因的自然主義認(rèn)識(shí)論、塞拉斯對(duì)經(jīng)驗(yàn)主義的批判、戴維森的變異一元論和達(dá)米特的反實(shí)在論為代表[10]。
第一階段的邏輯分析學(xué)派認(rèn)為:哲學(xué)思辨只能使用邏輯符號(hào)(&,v,?,? x,? x等),并通過(guò)邏輯推算的方式來(lái)進(jìn)行,因?yàn)槿粘UZ(yǔ)言充滿歧義,缺乏精確性,對(duì)語(yǔ)言哲學(xué)學(xué)術(shù)研究來(lái)講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們又被稱為理想/人工語(yǔ)言學(xué)派或形式語(yǔ)言學(xué)派。第二階段的日常語(yǔ)言學(xué)派對(duì)用符號(hào)邏輯來(lái)分析語(yǔ)言在使用中的情況持質(zhì)疑態(tài)度,他們認(rèn)為,日常語(yǔ)言完全可以應(yīng)用于學(xué)術(shù)分析,語(yǔ)言不僅能對(duì)客觀世界進(jìn)行描寫,還能用來(lái)發(fā)布命令、提出請(qǐng)求、表達(dá)感情等學(xué)術(shù)研究和哲學(xué)論證,因此又被稱為自然語(yǔ)言學(xué)派或非形式語(yǔ)言學(xué)派。馮光武指出,兩派的核心分歧是:前者將語(yǔ)言與人(語(yǔ)言使用者)分離,認(rèn)為語(yǔ)言哲學(xué)的任務(wù)就是解釋語(yǔ)言形式與客觀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后者則把語(yǔ)言使用者置于中心地位,認(rèn)為語(yǔ)言哲學(xué)需要揭示語(yǔ)言與其使用者之間的關(guān)系[7]24。
格賴斯在《邏輯與會(huì)話》(1975)一文的開(kāi)篇中提出了形式語(yǔ)言學(xué)派和非形式語(yǔ)言學(xué)派對(duì)立的事實(shí),并明確表達(dá)了自己的哲學(xué)立場(chǎng):并無(wú)意于加入其中的任何一派;有這種對(duì)立關(guān)系的想法本身就是一個(gè)錯(cuò)誤,而這個(gè)錯(cuò)誤就源于對(duì)制約會(huì)話的那些條件的本質(zhì)和重要性缺少認(rèn)識(shí)[8]306。格賴斯認(rèn)為,羅素的邏輯分析思想可以保留,對(duì)于羅素的限定摹狀詞理論列出的那些“問(wèn)題詞”(如but和or),會(huì)話含義理論提供了一條更好的解釋路徑。這種路徑有助于建立一種更加完善的會(huì)話邏輯,這種會(huì)話邏輯雖然可以得到形式邏輯的輔助,但不能被它所取代[11]。可見(jiàn),格賴斯是想調(diào)和邏輯分析學(xué)派和日常語(yǔ)言學(xué)派之間的矛盾。然而他本人的研究仍然以日常話語(yǔ)為研究基礎(chǔ)并非純邏輯符號(hào)的演繹,而且他將語(yǔ)言使用者的意圖作為研究意義解讀的核心,因此仍然被后人劃歸為日常語(yǔ)言學(xué)派。
二、說(shuō)話人意圖——意義的分類與實(shí)現(xiàn)
格賴斯在邏輯分析學(xué)派以及真值條件語(yǔ)義理論(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受到日常語(yǔ)言學(xué)派的挑戰(zhàn)之時(shí),以人的心理意圖為出發(fā)點(diǎn)探討意義的本質(zhì),將意義分為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
(一)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
格賴斯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的劃分受到了皮爾斯(C.S. Peirce)符號(hào)理論的影響。皮爾斯(1867)指出,符號(hào)與被表征的對(duì)象之間有的是象似關(guān)系(icon),有些是指示關(guān)系(index),還有的是象征關(guān)系(symbol)[12]。格賴斯在研究意義時(shí)沒(méi)有關(guān)注象似關(guān)系,而指示關(guān)系和象征關(guān)系則成為他劃分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的參照。格賴斯沒(méi)有明確給出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的定義,而是通過(guò)例證的方式進(jìn)行了解析。最經(jīng)典的例句“那些斑點(diǎn)意味著麻疹”中,斑點(diǎn)就是麻疹的癥狀,是有自然聯(lián)系的物理特征,即為自然意義。這種表達(dá)的字面意義即為說(shuō)話人要表述的意思,反映的是事物的內(nèi)在特征,不需要通過(guò)解讀說(shuō)話人意圖,沒(méi)有更深的含義,無(wú)需推斷就能理解其意。而在例句“公交車的三聲響鈴意味著車滿員了”中,“公交車的三聲響鈴”和“汽車滿員”之間并不存在自然的因果聯(lián)系,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是人為的約定,因此表達(dá)的是非自然意義。在日常交際中,人們之間的信息傳遞往往不是在自然意義層面上進(jìn)行的,更多時(shí)候是利用言語(yǔ)的非自然意義來(lái)表達(dá)意圖的。
(二)說(shuō)話人意圖與聽(tīng)話人辨識(shí)
格賴斯在“意義”一文中雖然是在談意義的分類,但實(shí)際上他意在突出“說(shuō)話人意圖”才是核心靈魂。這種思想在《說(shuō)話人的意義與意圖》(1969)一文中再次得到重申。在這篇文章中,格賴斯提出,說(shuō)話人意義的表達(dá)始于說(shuō)話人意圖,成于聽(tīng)話人辨識(shí)。格賴斯將其總結(jié)如下:
說(shuō)者U通過(guò)說(shuō)x產(chǎn)生某用意,當(dāng)且僅當(dāng)滿足以下條件:
對(duì)某聽(tīng)者A而言,說(shuō)者發(fā)出x時(shí),其意圖包括
(1)A作出某個(gè)反應(yīng)r;
(2)A想到(或辨識(shí)到)說(shuō)者有意圖(1);
(3)A作出反應(yīng)(1)是在(2)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2]336-337
說(shuō)話人意義的實(shí)現(xiàn)不僅要求由說(shuō)話人表達(dá)“意圖”(intention)從而引發(fā)某個(gè)“信念”(belief),而且說(shuō)話人還想要通過(guò)這個(gè)“信念”使聽(tīng)話人能辨識(shí)到這種表達(dá)背后的“意圖”從而作出相應(yīng)的反應(yīng)。
(三)首要意圖
在聽(tīng)話人意圖辨識(shí)的過(guò)程中可能會(huì)出現(xiàn)不同的情況,對(duì)此,格賴斯在“意義”一文中對(duì)如何辨識(shí)說(shuō)話人意圖作了較為清楚的交代。在聽(tīng)話人辨識(shí)說(shuō)話人意圖的過(guò)程中,只有說(shuō)話人的首要意圖與該話語(yǔ)的非自然意義相關(guān)。當(dāng)對(duì)說(shuō)話人兩個(gè)或多個(gè)意圖的辨識(shí)存在疑慮時(shí),則借助于該話語(yǔ)的語(yǔ)境(語(yǔ)言的或其他方面的)[13]。這一點(diǎn)也是語(yǔ)境介入格賴斯意義理論的重要接口。學(xué)界雖認(rèn)可格賴斯對(duì)語(yǔ)境的重視,但鮮有文章提及說(shuō)話人意圖與語(yǔ)境之間的關(guān)系,而這一層關(guān)系的表述也為他之后用語(yǔ)境來(lái)解讀會(huì)話含義奠定了基礎(chǔ)。
(四)說(shuō)話人意圖的實(shí)現(xiàn)
在區(qū)分了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之后,格賴斯又提出了意義理論的另一個(gè)重要部分——會(huì)話含義和合作原則及其準(zhǔn)則。格賴斯認(rèn)為,人們?cè)诶硇缘慕浑H中是普遍遵守合作原則的,當(dāng)違反合作原則中的一條或幾條準(zhǔn)則時(shí),便產(chǎn)生會(huì)話含義。會(huì)話含義的推導(dǎo),則是結(jié)合語(yǔ)境對(duì)說(shuō)話人意圖的辨識(shí)而實(shí)現(xiàn)的。格賴斯將合作原則細(xì)化成四條準(zhǔn)則:數(shù)量準(zhǔn)則、質(zhì)量準(zhǔn)則、關(guān)系準(zhǔn)則和方式準(zhǔn)則。數(shù)量準(zhǔn)則是根據(jù)交際需要來(lái)提供信息,在數(shù)量上應(yīng)恰到好處,不多不少;質(zhì)量準(zhǔn)則用來(lái)約束提供的信息要真實(shí)、可靠;關(guān)系準(zhǔn)則用來(lái)確保說(shuō)話人提供的信息與當(dāng)前的話題相關(guān);而方式準(zhǔn)則是指信息的表達(dá)要以清楚、明白的渠道實(shí)現(xiàn)。
三、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貢獻(xiàn)
(一)說(shuō)話人意圖——格賴斯理性思想的載體
格賴斯意向意義理論中的“意圖”概念與理性有著重要聯(lián)系,即人類的意圖是以理性為基礎(chǔ)的,人類進(jìn)行判斷、推理、決定等思維活動(dòng)都是在理性的參與指導(dǎo)下完成的。因此,格賴斯在其意義分析模式中對(duì)“說(shuō)話人意圖”的解讀離不開(kāi)理性這個(gè)基礎(chǔ)。對(duì)理性的依賴,也揭示出格賴斯意義理論對(duì)人本身的關(guān)注,即以反映說(shuō)話人意圖的意義為中心。會(huì)話過(guò)程中的意圖傳遞和意圖辨識(shí)都離不開(kāi)人的理性判斷和推理。格賴斯在《邏輯與會(huì)話》一文中提出合作原則時(shí)也表明,他把說(shuō)話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有目的的,而且著實(shí)是理性的行為”,因此,合作原則不僅適用于人們的會(huì)話交際,也適用于人類其他的理性行為,例如修車、做蛋糕等[14]。這樣的理念一直貫穿格賴斯生命的始終,在他畢生各個(gè)時(shí)期的著作中都有關(guān)于理性的討論。因此,格賴斯提出會(huì)話含義理論的終極目標(biāo)不是探討或解決語(yǔ)言問(wèn)題,而是通過(guò)對(duì)語(yǔ)言的哲學(xué)思辨探討人的理性的本質(zhì)以及相關(guān)的哲學(xué)研究方法[15]。
(二)從“說(shuō)話人意圖”到“社會(huì)意圖”
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理論還為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dòng)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提供了理論來(lái)源和靈感。哈貝馬斯在自己的交往行動(dòng)論中拓展了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理論,將其放入更廣泛的社會(huì)意圖框架,從個(gè)體走向社會(huì),同時(shí)將交往理論置于更大的行為理論框架之中[16]。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dòng)論中,說(shuō)話人意圖或經(jīng)驗(yàn)、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事態(tài)以及對(duì)話雙方的關(guān)系相互關(guān)聯(lián)構(gòu)成了一個(gè)更寬泛的交際網(wǎng)絡(luò)。與格賴斯一樣,哈貝馬斯也同樣關(guān)注理性,并在自己的交往行動(dòng)理論中提出了“交往理性”。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與格賴斯理性思想的不同之處在于:交往理性是在生活世界視域內(nèi)運(yùn)行的,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考察交往理性不能脫離生活世界的概念;哈貝馬斯從交往理性范式中引出了交往行動(dòng)的概念,闡述了交往理性的準(zhǔn)則,并批判了工具理性(他認(rèn)為格賴斯的理性即是工具理性的一種),使哲學(xué)研究從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范式走向了以交往為中心的理性范式[17]。從“說(shuō)話人意圖”到“社會(huì)意圖”的發(fā)展和傳承,也意味著對(duì)哲學(xué)的思考從語(yǔ)言領(lǐng)域到社會(huì)領(lǐng)域的過(guò)渡,擴(kuò)充了“意圖”在更多外延下對(duì)我們生活的哲學(xué)闡釋。這是哲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也是哲學(xué)對(duì)生活的反哺。
(三)語(yǔ)言哲學(xué)向心智哲學(xué)的轉(zhuǎn)向
語(yǔ)言哲學(xué)作為哲學(xué)的第三次轉(zhuǎn)向,把語(yǔ)言本身看作是哲學(xué)研究的本質(zhì)問(wèn)題,而在心智哲學(xué)中,語(yǔ)言本身不再是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在言語(yǔ)活動(dòng)中反映出來(lái)的心智活動(dòng)才是研究的直接對(duì)象[18]。格賴斯以“說(shuō)話人意圖”為基礎(chǔ)構(gòu)建的意義理論,開(kāi)啟了心智哲學(xué)的探究轉(zhuǎn)向。格賴斯的意向性意義觀秉承了既傳承又開(kāi)拓的研究思想。他在自己的意義理論中將邏輯分析和自然預(yù)料中的語(yǔ)言結(jié)合起來(lái)進(jìn)行分析,成為利用邏輯學(xué)分析日常話語(yǔ)的第一人。同時(shí),他又借助一些心理概念,比如“意圖”和“信念”等,對(duì)說(shuō)話人的意義進(jìn)行哲學(xué)思辨。可以說(shuō),他既傳承了邏輯分析對(duì)語(yǔ)言哲學(xué)的貢獻(xiàn),也進(jìn)一步開(kāi)拓了從心智哲學(xué)視角對(duì)意義進(jìn)行探究的道路。著名哲學(xué)家賽爾(Searle)認(rèn)為,如果20世紀(jì)的第一哲學(xué)是語(yǔ)言哲學(xué),那么21世紀(jì)的第一哲學(xué)則應(yīng)當(dāng)是心智哲學(xué)(philosophy of mind,也被譯為心靈哲學(xué))[19]。意向性是人眾多的心智特征之一[20],也是心智哲學(xué)探討的核心話題之一[21]。心智哲學(xué)作為認(rèn)知科學(xué)的六大核心領(lǐng)域之一,勢(shì)必將給我們?cè)谛率兰o(jì)里有關(guān)哲學(xué)的思考和討論帶來(lái)新的認(rèn)識(shí)和啟發(fā)。
四、格賴斯意向性意義觀的局限性
(一)格賴斯循環(huán)的困擾
格賴斯的意義理論具有相當(dāng)大的影響力,也正因?yàn)槿绱耍瑢W(xué)術(shù)界偏重對(duì)語(yǔ)言含義的探究而忽視了語(yǔ)言規(guī)約基礎(chǔ)而重要的地位。近年來(lái),無(wú)論是在理論語(yǔ)用學(xué)還是實(shí)驗(yàn)語(yǔ)用學(xué)領(lǐng)域,“所言”和“所含”的劃分以及這種劃分的可行性研究成為研究熱點(diǎn)之一[22]。對(duì)于“格賴斯循環(huán)”這一現(xiàn)象,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紛紛作了相關(guān)探討。Bach提出了介于“所言”和“所含”之間的“中間區(qū)”(middle ground)[23];關(guān)聯(lián)理論也提出了話語(yǔ)意義的三分法——所言、明含(explicature) 和所含[24];Levinson提出了插入(interleave)法[25]等。然而,有關(guān)“格賴斯循環(huán)”的爭(zhēng)論仍在繼續(xù),因?yàn)椤八浴焙汀八钡姆诸惻c關(guān)系的界定,作為格賴斯含義分類的主要分支,直接影響了整個(gè)含義系統(tǒng)其他次分類的相關(guān)解讀,是一項(xiàng)不小的工程。毋庸置疑,格賴斯對(duì)“所言”與“所含”的劃分確實(shí)給人們對(duì)意義的研究帶來(lái)了革命性的認(rèn)識(shí),引導(dǎo)人們開(kāi)始關(guān)注詞/句子背后的含義,只是在處理“所言”和“所含”的關(guān)系這一點(diǎn)上是值得進(jìn)一步探究的。“所言”以言語(yǔ)或字面表達(dá)呈現(xiàn),是顯性的;“所含”是“說(shuō)話人意圖”的傳遞與辨識(shí),是心智層面的、隱性的。在將來(lái)的研究中以依存互補(bǔ)的角度去理解和研究它們,也許會(huì)有更多積極的發(fā)現(xiàn)。
(二)意向性的相關(guān)闡述缺乏具體性
格賴斯的意義理論以“說(shuō)話人意圖”為出發(fā)點(diǎn)構(gòu)建會(huì)話含義理論,雖提出了“合作原則”及其準(zhǔn)則作為分析的理論框架并強(qiáng)調(diào)語(yǔ)境的重要性,成為影響語(yǔ)用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支撐,但是在闡述“說(shuō)話人意圖”和“聽(tīng)話人識(shí)別”時(shí)缺乏具體性。會(huì)話含義的推導(dǎo)主要是聽(tīng)話人對(duì)說(shuō)話人意圖進(jìn)行辨識(shí)的過(guò)程。在這一過(guò)程中,格賴斯提出了一個(gè)重要的概念——“首要意圖”,并指出會(huì)話含義的推導(dǎo)實(shí)則是聽(tīng)話人對(duì)說(shuō)話人首要意圖的辨識(shí)。那么,怎樣根據(jù)語(yǔ)境來(lái)辨識(shí)首要意圖?如果在交際中沒(méi)有辨識(shí)到說(shuō)話人的首要意圖,會(huì)發(fā)生什么情況?其實(shí),在日常交際中,我們有的時(shí)候會(huì)誤解對(duì)方的意思,造成誤會(huì)的產(chǎn)生。這是否就是格賴斯所說(shuō)的“首要意圖”辨識(shí)失敗的結(jié)果?然而,這雖然與格賴斯提出的“說(shuō)話人意圖”密切相關(guān),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有清晰的闡釋。因此,有關(guān)意向性和這些會(huì)話現(xiàn)象仍值得進(jìn)一步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