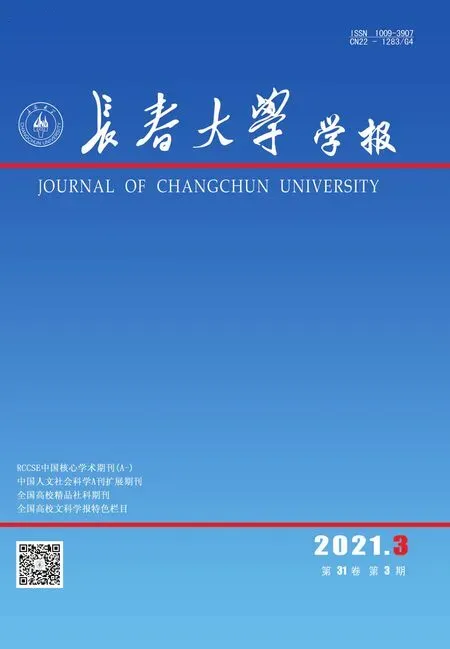論西方音樂肖像作品的創作特征及演變
李云潔
(閩南師范大學 藝術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肖像在藝術作品中一般是指對具體的人或集體的描繪。最初,肖像出現在美術作品中,之后發展到文學、音樂以及電影電視藝術中。肖像的創作目的是表達人物的外貌特征,如人物的姿勢、手勢及面部表情。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露,綜合展現出人物復雜的生理與心理特征[1]。我國東晉顧愷之也提出“以形寫神”的“形神論”,為我國肖像繪畫藝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在音樂中,肖像一般是指在標題音樂作品中或者在作品的某一樂章中,其主要音樂主題是描寫的人物[3]。其創作對象是具體的人。一般外貌特征的表現有姿勢、手勢、行為及語言特點等,另外還可以表現人物的性格、氣質、精神面貌或思想感情,從而達到神似[4]。這些人物形象的所有特征都是通過音樂手段(音樂語言、體裁及風格)重新創造而來,而這些人物形象創作的方法,其歷史發展和風格的變化在音樂學中研究還需要更加的系統。所以明確18—19世紀作曲家作品中音樂肖像風格的特征,闡述其基本音樂創作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音樂肖像的誕生——弗朗索瓦·庫普蘭的作品
肖像從雕塑、素描與色彩的藝術形式延伸至不同的藝術作品領域當中,而肖像出現在音樂作品中已經若干個世紀,且所有的音樂特征都屬于新時期的音樂藝術,其藝術觀點是“基于對外部和具體事物的關注,以及對人類情感多樣性的關注”[5]。最早的音樂肖像出現在17—18世紀英國維它琴和法國大鍵琴的作品中,以法國作曲家弗朗索瓦·庫普蘭的作品最為突出,其總共創作了幾十個器樂肖像作品。他說:“創作作品時,我始終牢記某個對象:它是由各種不同的情節展現給我。并且,這些作品的標題符合我的意圖……當他們在我的手指下演奏時,發現他們很相似。”[6]
(一)題材豐富的庫普蘭音樂肖像作品
在庫普蘭的音樂肖像中,有許多不同的典型形象出現,比如貴族形象:獻給波旁公爵的年輕女兒的作品《波旁公主》;獻給路易十四的女兒,同時也是庫普蘭的學生的《無與倫比的風度》或《孔蒂公主》;有為紀念路易十五的新娘,波蘭斯坦尼斯洛斯一世的女兒《瑪利亞公主》;也有紀念摩納哥一世親王安東尼·格里馬爾迪的小女兒《摩納哥的繆斯》;還有描繪公爵夫人拉·費特的女兒《拉梅內圖》等。
有些肖像作品并不是庫普蘭專門為人而創作的,只是描繪其對周圍人的印象。如描寫皇家管風琴家加布里埃爾·加尼爾的妻子《拉加尼爾》;有為紀念作曲家朋友讓·巴蒂斯特·馬雷的女兒而創作的《拉瑪麗列特》;還有對作曲家安托萬·福克雷的妻子創作的《華麗的福克雷》等。庫普蘭還在作品中刻畫了自己的家人,如獻給作曲家兩個女兒中最小的瑪格麗塔·安托瓦內特的《拉克魯伊,或拉庫佩里內特》《莫妮卡姐妹》和自己的妻子《拉庫普蘭》。
有些肖像只以女性名字命名,因此無法確定其原型,如《娜內塔》《咪咪》《馬尼翁》《貝比》;有些作品名有明確的人物性格特征,如《美麗溫柔的娜內塔》《溫柔的芳淑》。
作曲家還在一些作品中忽視人物的內心情感,只展示人物的職業身份。這個特點體現在庫普蘭的集體肖像作品中,如樂曲《年輕的修女》《朝圣者》《見習修女》《葡萄采集人》等。這些作品并沒有刻畫單獨的人,而是以集體的特征進行展示,具有一種普遍的情感,但這個情感沒有明顯的人物差別。如展現高貴氣度的《哀歌或三個寡婦》,展示內斂與悲傷的《老者》等。
在神話題材的肖像作品中,作曲家同樣刻畫了單人肖像與集體肖像,如樂曲《戴安娜》《忒耳普西科瑞》《花神芙羅拉》《希爾瓦娜斯》。也有描寫具有國家和民族特點的肖像,如作品《佛羅倫薩人》《西班牙女人》《巴斯克人》和《中國人》。但是,這些作品表現人物民族性的程度并沒有很高,我們只注意到作品《佛羅倫薩人》的旋律中帶有升六級音極具意大利風格;而《瑪麗公主》第三部分中帶有波蘭舞曲的節奏,表明瑪麗亞·萊什欽斯基具有波蘭人的血統。最有意思的是,作曲家庫普蘭還創作了一首鋼琴小品《中國人》,但作品旋律的色彩較為中性,沒有明顯的中國民族音樂特點。
(二)弗朗索瓦·庫普蘭音樂肖像的體裁及創作方式
庫普蘭的大多數音樂肖像的體裁都屬于“小型樂曲”,其標題反映了所描繪的人物原型的鮮明特征。如《胡鬧的女人》《危險》《嫵媚》《深情》和《丑角》等。庫普蘭在創作這些作品時,試圖通過其特有的情感狀態來描繪人的性格。在描寫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上,作曲家需要構思作品的體裁、速度、節拍、情緒以及音樂主題和表現手法。這些人物性格特征通常是借助一個或兩個細節來體現,如《西爾瓦諾斯》通過跛行的節奏變化,展現他山羊蹄的步態;通過命令式的切分節奏作為動機來展現《女巫》;用大量跳動的旋律來展示《調皮的女孩》;還有通過低音區的多聲部來描繪公爵夫人拉·費特的女兒《拉梅內圖》。另外,在一些集體肖像作品中,庫普蘭通過兩種調性的運用作為人物情緒的對比(莊重和無憂無慮);或是通過大小調的變化來進行創作,使一個形象同時具有不同色彩,如《年輕的修女》和《雙胞胎姐妹》。
庫普蘭還做了較多的譜面標記,如“溫柔”“天真”“優雅”“活潑”“高貴”“莊重”“強調”,有的標記更加細致,如“非常溫柔”“稍微溫柔”等。這些標記在作品中并沒有打算展現角色的內在情感,而只是記錄所描繪人物的性格特征。庫普蘭甚至在作品《貝比》中較為罕見的運用“粗心、懶惰、冷漠”標記,讓人印象深刻。
不同的角色性格決定其相應的創作方式,在《娜內塔》中,運用了顫音與倚音來體現天真而樸素的帶有r口音的女性形象。作曲家也常常用輔助標題來定義舞曲。如《獨一無二》《雄偉輝煌》《憂愁的》薩拉班德舞曲,《勤奮的》阿萊芒德舞曲,《精致的》《陰郁的》《親密的》的庫朗特舞曲等。很多肖像作品常常具有舞蹈的特征,具體表現在作品風格、節奏形態、和聲和曲式,還包括明確的平行樂段結構,也包括對稱的帶再現樂段的完整結構。特別重要的是庫普蘭的回旋曲,在作品《查貝公主》和《莫妮卡姐妹》中,短小的主題動機在作品中多次出現,而這種由舞曲發展出來的回旋曲形式,也是展示歌舞音樂的主要特點。
在庫普蘭的音樂中,刻畫的情緒缺乏極端表現,如“快樂”“頑皮”“惡作劇般的”情緒永遠不會變得興奮;而憂郁、悲傷也不會變成沮喪和悲觀。如作品《頑皮的女孩》刻畫的并非快速與躁動,而是優雅高貴,而作品《憂傷》相對于戲劇性描寫,作曲家更注重莊嚴與肅穆。這一時期的音樂所描繪的人物感情還僅僅出現在諧和的、合理的音樂色彩框架里,反映出庫普蘭所創作的肖像作品具有宮廷藝術美學思想,是古典主義理性與情感和諧統一的思想特征。
總的來說,在庫普蘭創作的音樂肖像中,大多數描繪的是女性形象。而且,她們的原型主要是作曲家周圍的真實人物。其音樂形象是擬人化的情感、人格化的情緒。每個肖像作品通常是一種情緒,一種情感,而這些情感的描寫是通過簡單的方式體現,即通過體裁、調性和節奏等手法來體現人物一種或兩種性格。庫普蘭作品另一個特點是標題非常簡短,他認為僅借助這些幫助即足夠。簡短的標題能將聽眾的感知引導到正確的方向,無須進行詳盡的闡述,而所被創作的人物情感、情緒和性格特征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些特征是由作曲家來展示的,而并非是主人公的個人經歷。
二、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期音樂肖像的繁榮
音樂肖像真正的綻放出現在19世紀的浪漫主義時期,這一時期許多作曲家都創作了大量的音樂肖像作品,其中以舒曼、格里格與穆索爾斯基的作品更為典型。
(一)羅伯特·舒曼浪漫主義音樂肖像的作品特征及創作方式
19世紀最精彩的音樂肖像作品是羅伯特·舒曼的鋼琴套曲《狂歡節》。其音樂充滿了印象畫的特點,類似于人物寫生畫。作品展現出在舞會的背景下,每個人都戴著面具,各自都有著自己的角色,包含若隱若現的臉龐和片刻交談的節日場景。作品描繪了一系列的核心人物肖像,有約瑟比烏斯、弗洛里斯坦、基阿琳娜、埃斯特雷拉、肖邦和帕格尼尼。其中第一對夫婦是埃斯比斯和弗洛里斯坦,一個是憂郁的、沉思的,夢幻般的,另一個是活潑的、充滿激情和活力的。這兩個作品矛盾的性格特征其實是舒曼對于自己“我”的認知。所以在作品《弗洛雷斯坦》和《約瑟比烏斯》中,舒曼明確了自己內心性格的矛盾與對立。根據作者的說法,它們在舒曼的音樂和文學作品中不斷地“出現”,是作曲家本人的個性,表達其性格的兩個方面。弗洛雷斯坦“沖向天空”的主題體現了浪漫般的熱情,對未來的渴望。但他脾氣暴躁,有著自相矛盾的思想隨意性。作品中有舒曼的表演特征標記“激情的”,表達了他的激情和任性的感受,但其主要音樂形象是急躁的、焦慮和不安的。這不僅體現了人物的內心狀態和肢體語言,還展現因激動而感到窒息的語言節奏等。弗洛雷斯坦的叛逆性格通過旋律而迅速上升,并在弱音上靜止而展現。這與從作品《蝴蝶》借來的“柔板的”抒情主題形成了鮮明對比。音樂中的張力因不和諧的和聲、不穩定的功能以及在突然停頓的節奏中擴張。與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弗洛雷斯坦》的結尾打亂了旋律的節奏,將占主導地位的動機進行分裂,并在結束后,毫不停頓地出現作品《妖艷的女子》。這一微妙的細節說明了不知疲倦的渴望是舒曼肖像的本質。
相反,在《約瑟比烏斯》中,節奏的感受幾乎不存在,悠揚的旋律,充滿了夢幻和與現實世界的分離,這種效果是由“連綿而有呼吸”的旋律來產生。婉轉的七連音好像“脫離”了雙聲部的伴奏,左手透明般的兩個聲部增加了內心的清澈印象,這個形象通過復調音樂結構逐漸顯示出其內心世界的豐富,并且作曲家認為這個作品應該“低聲地”演奏。與《弗洛雷斯坦》一樣,在《約瑟比烏斯》中,不僅描繪了人物性格,還描繪了人物形象特征:一個夢想家、沉思者;一個有著輕盈的動作、溫柔的語調和動作緩慢的人。
作品《帕格尼尼》和《肖邦》的對比方式與《弗洛雷斯坦》和《約瑟比烏斯》非常相似。舒曼模仿了肖邦鋼琴作品中歌唱般的旋律,也模仿帕格尼尼高超的小提琴技巧。帕格尼尼的音樂模仿了他著名的《惡魔的撥奏》,在這里,一切都突出了藝術家驚人的技巧和惡魔般的氣質:難以置信的跳躍節奏(不匹配左右的聲音)和難以置信的左手強弱的動態對比,這種快速的運動正變得越來越大膽和古怪。而作品《肖邦》的形象通過柔和的旋律來表達,透明般的琶音織體背景,仿佛他鋼琴作品《夜曲》的抒情風格再現。舒曼精確運用“風格模擬”來反映肖邦旋律創作的一個微妙細節,即在第一個音符之后停頓呼吸,給旋律帶來了特別輕盈的空氣流動感,如同肖邦的《夜曲Op.9 No.3》。
通過體現作曲家的風格來刻畫人物是舒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創造性發現,可以稱為“舒曼的肖像”,是全新的音樂創作方式。
另外,浪漫的華爾茲《基阿琳娜》和《埃斯特蕾拉》代表了一對反差較大的女性形象——克拉拉·維克和恩尼斯汀·馮·弗里肯的面具。首先是真誠,內心的魅力,其次是熱情。克拉拉的本質是“尋找”,她的熱情和心態通過“尋找溫暖”而展現出來;而后者被深厚的人性和渴望的語調圍繞,是一種緊張而虛幻的節奏,抒情的語調被強烈的節奏抑制,并融合成一個擴張的旋律。
《嬌艷的女子》的膚淺本性則是通過“輕浮”的語調來刻畫,時而活潑,時而狡猾。它們都來自一個聽起來像笑聲的開場白——銀色的鈴聲和寒冷般的笑聲。如果說《弗洛雷斯坦》和《嬌艷的女子》傾向于人物內心的獨白,那《約瑟比烏斯》和《肖邦》則傾向于展現“歌”或“舞”曲(輕快的抒情短歌或器樂曲)。而在《嬌艷的女子》中,我們又清楚地“看”到了舞蹈,作品通過兩個小節的引子仿佛展現芭蕾舞的入場,優美的芭蕾女舞者的身影劃過舞臺,為舞蹈做好站立姿態的準備。
舒曼在《狂歡節》中不僅刻畫了人物,還巧妙地結合背景,就像是有畫框的繪畫作品一樣。背景中的舞會場景與華爾茲舞蹈已經成為這個套曲的核心元素,為作品建造了一個完整而動態的舞會背景。這不僅僅是非人格化的戲劇“背景”如《變奏的序言》《高貴的圓舞曲》《德國圓舞曲》,而是滲入了人物的音樂形象:弗洛雷斯坦、基阿麗娜和埃斯特雷拉,成為“圓舞曲—肖像”;《肖邦》的“夜曲肖像”及《嬌艷的女子》“圓舞曲—諧謔曲肖像”。與圓舞曲體裁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也出現了帕格尼尼的弦樂《練習曲》風格和充滿幻想的抒情輕快短小的器樂曲《約瑟比烏斯》。舒曼的音樂肖像作品特點是小型的“音樂人物寫生畫”,作曲家具備在音樂中探尋對于場景、情緒的生動印象,具備對人物肖像的音樂寫生能力。但他并不尋求大篇幅的創作,而是把它們限制在多個“音樂小品”中,并將之組成一個完整的套曲形式。
(二)格里格夢幻般的音樂肖像作品特征及創作方式
格里格的音樂創作對象也較為豐富,且差異較大。其《抒情小品》創作的內容來源于生活所見所聞,但不局限于抒發情感和描述心境[7]。有描寫動物的《小鳥》和《蝴蝶》;有描寫挪威民間傳說中虛構的角色《風之精靈》《精靈之舞》《侏儒進行曲》;也有以作曲家為對象的作品如《海頓》《向肖邦致敬》等。以上所有的音樂作品都屬于“鋼琴小型曲”。但不同的是,格里格并沒有將作品創作為類似《狂歡節》的鋼琴套曲形式,而是將所有獨立的音樂作品匯編成了曲集,形成《格里格抒情小品集》。
《風之精靈》選自格里格《抒情小品》第七冊,它描繪了一個夢幻般的音樂形象。在中世紀的信仰中,它是風元素的精靈,有男女兩個性別,具有空氣的形態,是具有人格化的神話形象。從外文對這部作品的命名來看,這部作品描繪的是女版的風元素精靈,她叫作希爾菲德。該作品的主題旋律是輕盈的,具有較明顯的空間移動感,頻繁出現的休止符展現了精靈飛翔時較多的懸空停頓,旋律由較小的動機發展而成,以鮮明的節奏輪廓、優雅的旋律和“神秘不可捉摸”的動作為特點。作品的旋律大部分出現在高音聲區,“跳動”的音調和快速的色彩變化營造出輕盈與廣闊。作曲家的“輕快的”標記和斷奏的演奏方式也印證了這一點,作品中頻繁的速度變化,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這些創作手法都為創造優美的空中精靈,展示出了令人信服的童話般音樂形象。
格里格另一個神話人物是《抒情小品》第十冊中的第三首《精靈之舞》(又稱狗頭人)。小巨魔的形象以神秘的地下活力為特征,使人感知身影在黑暗光線下迅捷地移動。這部作品基于運動的特征,體現出角色的神秘感,具有極強的壓迫感。本曲節奏迅猛,旋律的力量對比強烈(由很弱變為突強),通過和弦的奇妙運用增加了神秘感和不可預測性。在本曲B段,運用和弦組成的樂句具有遞進關系,呈現出遞增的音樂感受,具有強烈的入侵和危險感。B段末尾在左手的二度下行跑動下,生動地展示出了地下精靈的神秘與詭異。這個樂段是作曲家對于聲音與和聲運用的經典之一,特別是和弦進行時的突然停頓,類似一種號角。這種創作方式,韋伯與里姆斯基·柯薩科夫在有關森林童話的音樂作品中也使用過,為童話人物創造了非常逼真的音樂背景。
除了童話肖像的作品外,格里格也創作了大量的人物系列,這些作品創作的都是真實的人,其作品風格取決于作曲家與挪威民間音樂的深厚淵源。在這些作品中,普通挪威人民的民族性與職業特征表現得尤為突出,較為典型的有《抒情小品》第五冊作品《牧羊少年》,其旋律讓人聯想到挪威牧羊人的歌聲“洛克”(又被稱為“牧牛”),一般是由管樂演奏(長笛或牧羊人的牛角)。作曲家再現了挪威民間音樂的典型特征:小調色彩主題中增IV度的運用,通過“牧牛”本身特有的即興演奏特征展現短小的三聲部旋律。旋律的開端源于簡短的民謠,簡單易懂,能夠引起明確的畫面聯想。長笛動機通過變奏成了旋律發展的基礎,復調在作品的中間部分出現,仿佛聽到了牧羊人號角的“呼喚”。最后,“卡農”出現在再現段中,仿佛是對牧羊人的回應。之后旋律進入到低聲部,表明牧羊男孩的離去與之后的寂靜。
具有極簡主義特點的人物形象出現在格里格《抒情小品》的第三組《孤獨的流浪者》。一個孤獨的旅行者的形象:他表現出對生命的無助與希望的喪失。“嘆息”音調以幾乎不變的弱起節奏彌漫在整部作品中,給人留下非常疲憊的印象。鋼琴中聲部感情色彩豐富,悅耳動聽的旋律是作品的主要表現因素。旋律以飽滿的六度音程構成兩個聲部,沒有宏偉的構造。它以中聲部中的持續延長音作為背景,使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身上。結尾出現漸慢的主題,更是凸顯和強調了嘆息與無奈的心理。這是一種表達精神狀態的創作技巧,描寫了孤獨與悲傷的心理,在之后的作品尾聲上,旋律穩定結束在小調主音上,又留給了人們一點點幸福的幻想。b小調的調性音色更是加深了流浪者孤獨的印象。該流浪者的音樂形象幾乎沒有描繪出他的外貌特征,只是重現了他的情緒和心情,這樣的肖像可以被稱為“心理肖像”,只突出人物的內心特征而非外在。
格里格創作的音樂作品中,格里格的絕大多數音樂作品都描繪神話人物,較少涉及真實的人物肖像。而真實的人物肖像出現在《抒情小品》第六冊,是以丹麥作曲家的人名來命名的——《加德》。這是一個非常溫暖、抒情和浪漫的音樂小品,是專門紀念丹麥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尼爾·加德(格里格的老師)。第二部作品來自格里格鋼琴組曲《心情》之練習曲《向肖邦致敬》。
(三)穆索爾斯基人物性格音樂肖像作品及創作方式
在19世紀的俄國,音樂迎來了新的發展。在穆索斯基的鋼琴作品中出現了較為典型的肖像作品。作曲家通過參觀他的畫家朋友維克多·哈爾特曼作品的印象,創作了一系列的音樂肖像作品——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作品以其鮮明而生動的“音樂畫像”而著稱,在音樂肖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侏儒》描繪的是一個相貌丑陋、內心敏感、具有惡劣態度與警惕目光的侏儒人。這個作品有一些描寫外形的音樂元素,但整體是屬于描寫人物的心理。快速的六連音在低聲區跑動,非常突兀的主題動機展示出了人物刻薄的形象,刻畫了一個矮小、跳躍、動作笨拙的侏儒形象。其動機也反映了角色破碎的內心世界。作曲家通過音樂的創作手法刻畫了一個性格怪異的、行為難測的形象,并確立了角色的性格和行為。作品以八度音階重復的單音作為旋律,最初出現在低音區中,突然被急劇的八度跳音打斷,仿佛瞬間的空間移動(旋律橫跨兩個八度)。而隨后主題出現的非常清晰的連接,短促與延長音的動機顯露出侏儒特有的步態——“跛子”,顯現了逼真的視覺效果:在這里,他“跳躍—停頓—跳躍”,如此高的運動能力和敏捷的動作給人以特殊的緊張感和原始不安的氣質。低音區的顫音增強了音樂的陰郁的特征,類似牙齒在上下抖動,它們似乎模仿了這種非人類痛苦與悲傷的聲音,最后以一段非常快速的段落“消失”。
“富裕和貧窮的兩個猶太人”——具有社會心理特征的人物場景對話。該作品屬于雙人肖像,兩個角色鮮明而準確的進行對等描繪。富人的主題帶有命令式的語調,表達了鄙夷和傲慢的態度。它通過相鄰八度的同旋律音的形式呈現,具有人物的權威性。斷斷續續的語句,沒有任何的伴奏,只是獨立的敘述角色本身的語言。第二個主題具有哀號的特點,這個窮人的主題是仿佛在向富人懇求某事,其主題是基于抽泣的語調,展現其委屈與討好的狀態。這個窮人著急地提出他的要求,而富人并沒有打斷他,但也沒有仔細聆聽他。富有表現力的高音旋律描寫了窮人顫抖的內心,“顫抖”主題是一種驚慌的語調,通過較多的三連音與帶附點的節奏型與低音背景的音程同步演繹。這里的富人主題與窮人主題交織在一起,直到結尾處出現了窮人的乞求聲,但最終被富人粗暴地打斷而結束。
穆索爾斯基也創作了童話音樂人物形象——《雞腿上的小屋》。作品描繪的是俄國童話故事中著名的妖婆,她叫“巴巴亞伽巫婆”。她擁有怪異、狡詐與惡毒的外表,并在木屋里快速地飛行。她的房子也有兩只腳,類似某種生物。作曲家利用托卡塔舞曲的韻律、奇怪的音調與參差不齊的重音精準地進行展現。特別在曲目的B段落,右手聲部的顫音仿佛巫婆在飛行,低聲區類似房子生物的“腳步”,充滿了神秘怪異景象。
穆索爾斯基的鋼琴組曲《圖畫展覽會》所描繪的人物是從真實藝術品中汲取的靈感,這種創作方式較為罕見。但是穆索爾斯基對于人物角色富有感情和表現力的創作,明顯比該作品的標題更為驚艷。特別是將哈爾特曼的繪畫《雞腿上的小屋》與穆索爾斯基的創作來進行比較的話,更為明顯。哈爾特曼的這個繪畫作品展現了俄羅斯的民族內涵:一個像童話小木屋一樣的鐘表;巴巴亞伽巫婆卻不在這里,但作曲家穆索爾斯基給作品增加了場景的時間與空間,讓這個小木屋與巴巴亞伽一起飛行與著陸。
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里的音樂肖像幾乎都是屬于人物性格的描寫,在肖像人物中,被描繪的人或童話形象的性格決定其表現形式,包含性情、行為、運動方式與語言風格。穆索爾斯基擅長精準的通過旋律來刻畫角色的語言,而且還能補充角色的社會屬性,如《兩個猶太人,富人和窮人》《利摩日市場》;有年齡特征的《未孵化出來的小雞舞蹈》和《杜伊勒里宮花園》。穆索爾斯基創作的人物肖像是對原本形象作了深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展現其性格與精神世界,同時也具有典型的社會和民族特征。
三、結語
18世紀作曲家的肖像作品最初的情感印象是得到更多的關注,而19世紀的音樂肖像作品是為了尋求更深、更全面的人物描寫。肖像藝術本質是展現人物的外貌特點,包括姿勢、手勢、步態與語言方式,更深刻表達人物個性特征,如氣質與情緒。因此,用音樂來展現人的綜合特征是非常可行的,并不亞于其他藝術形式。但音樂肖像并不是通過某些音樂技術來實現的,而是通過音樂語言,其中最主要的是富有表現的主題,精準的音色、節奏、風格以及正確的和聲色彩來綜合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