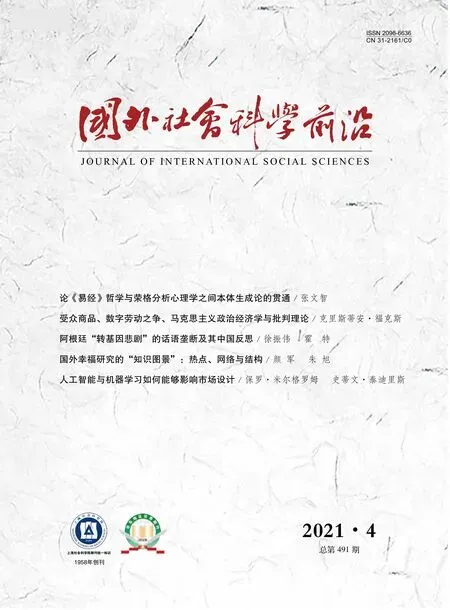受眾商品、數字勞動之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批判理論 *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 汪金漢 潘璟玲/譯
代編者按
受眾商品理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其提出者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是加拿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被公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斯麥茲認為,在資本主義商業傳播體制下,媒介機構、受眾和廣告商之間存在著一種隱秘的三角關系,即媒介機構生產大量優良的電視節目來吸引受眾,并將它們售賣給廣告商,從而獲取利潤。也就是說,在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媒介機構生產的真正商品不是其提供的優良的電視節目,也不是標價出售的廣告時段,而是受眾的注意力。因此,媒介經濟的本質在于培養和強化受眾對廣告商的忠誠度。
正如本文的作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述,很多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拓展和完善了這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如蘇特?加利(Sut Jhally)和比爾?李凡特(Bill Livant)提出的“觀看即勞動”的觀點、艾琳?米漢(Eileen Meehan)提出的“受眾分級”(ratings)概念,以及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提出的“控制性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概念,等等。
如果說,受眾商品理論的價值在于揭示出,在大眾傳播時代,媒介機構將受眾及其閑暇時間全部納入勞動的范疇,資本完成了對人類勞動全方位剝削的最后一道工序,體現出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顯著的“工作閑暇一體化”“工作時間碎片化”“工作空間任意化”的一般特征,那么福克斯在本文中的論述可以視為對這一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發展與更新。
福克斯認為,在新媒體環境下,對于受眾而言,媒介機構不僅是內容的提供者,也是生產內容的平臺。換言之,受眾既是媒介內容的消費者,同時也是媒介信息的生產者,因此其價值的形成模式與大眾傳播時代相比,更為多元化。一方面,受眾有意識地上傳圖文和音視頻,這些成為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內容;另一方面,受眾的瀏覽習慣、社交網絡甚至是個人消費信息等數據,有助于企業獲取更為精準的受眾畫像,有效地引導市場消費,從而謀取更多的利潤。
當前,國內外與受眾商品理論相關的著述已十分豐富。這一理論也是筆者長期關注的學術領域,故此在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與讀者分享三點思考。
其一,如上所述,受眾的價值在于其在使用新媒體技術過程中產生的數據,這些數據根據受眾特點通過算法進行分層和歸類之后形成龐大的數據庫資源,成為廣告商實現有的放矢、精準營銷的“利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當前媒介機構生產的真正商品是受眾的注意力與數據。基于此,對于報社這樣的媒體機構來說,它們在新聞生產的過程中往往遵循“流量至上”的邏輯,這將對新聞的“真實性”構成莫大的挑戰。
其二,即使在大眾傳播時代,受眾也并非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他們手中的遙控器賦予了他們在廣告時段切換頻道的權利。而在新媒體時代,受眾的能動性表現得更為明顯。以在社交平臺上為其偶像應援的粉絲為例,他們自發地、群體地通過發帖、轉載、點贊等行為為明星“做數據”,使其在網絡中獲得曝光度、話題度和討論度。粉絲的數據勞動不僅增加了明星的知名度,為他們爭取到更多品牌代言、節目通告和出演影視劇的機會,而且還為明星的唱片公司帶來了銷量,為綜藝節目帶來了收視率,為廣告主帶來了銷售額,但粉絲如工蟻般的辛勞與忙碌并未獲得任何經濟回報。在此,從受眾商品理論的視角出發,資本和社交平臺對粉絲勞動的剝削清晰可見,但如果將受眾商品理論與文化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分析粉絲參與無酬勞動的動因、深描他們在應援偶像過程中的個體經驗,探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青年(亞)文化的變遷過程,將極大地有益于拓寬研究者視野,激發理論創新。
其三,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受眾不僅是對商品有需求的消費者,而更應該是公民。因此,在此背景下,媒體機構(尤其是公共媒體)如何擔負起培育公民公眾意識的社會責任,讓他們便利地獲取參與社會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各類信息,為其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創造各種條件就變得尤為關鍵。當前,并未有太多研究者關注到這一點,這或許可以成為受眾商品理論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
——姚建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1977年,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一文。在文中,斯麥茲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沒有給予傳播在資本主義中的復雜作用以足夠的重視。這篇論文的發表直接引發了一場媒介社會學的奠基性爭論,也就是后來所謂的“盲點之爭”。如今30多年過去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使得人們不再關注階級與資本主義,進而導致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和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盲點。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認為,全球經濟危機重燃了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趣。1Slavoj ?i?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Verso, 2010.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主張,為了能夠在全球范圍內理解當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危機、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現象,“我們必須問馬克思一些問題。”2Eric Hobsbawm,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1,p. 419.鑒于馬克思主義在理解、闡釋和改變當代社會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應該接納斯麥茲的建議,大力發展馬克思主義媒介和傳播理論。如果我們想要一個服務于人類整體利益的社會與媒體,我們亟需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
一、達拉斯?斯麥茲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批判理論的貢獻
斯麥茲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他開設了第一門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并強調用一種批判性、非行政性(non-administrative)的方法來研究媒介和傳播的重要性。他在《關于傳播政治經濟學》(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一文中論述道: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根據傳播機構的組織和運作政策來評估它們的傳播效果,并分析其在社會環境中的結構和政策”。1Dallas Smyth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37, no. 4, 1960, pp. 563-572.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指出:“雖然斯麥茲的討論并未采用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主張與當時大眾傳播研究的主流范式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在20世紀70年代,“他使傳播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再次得到了明確的定義。”2
1981年,斯麥茲明確提出了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他主張,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和批判理論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或者類馬克思主義理論”(Marxist or quasi-Marxist theory)。在此基礎上,他確定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八大核心議題:物質性;壟斷資本主義;受眾商品化與廣告;作為資本主義基礎的媒介傳播;勞動力;技術決定論批判;對意識的辯證分析;藝術和科學的辯證法。3Dallas Smythe,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1981.
斯麥茲認為,了解馬克思的作品對于批判性地理解和認知資本主義社會中媒體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他看來,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對于意識形態、意識和霸權這些概念的討論充滿了主觀主義和實證主義色彩。與法蘭克福學派相反,斯麥茲沒有將意識形態理解為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而是將它理解為一套信念、態度和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工業的任務是驅使人們去購買商品并支付稅費,更深層次的任務則是推動有益于資本主義和財產私有制的價值觀念。
法蘭克福學派應該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實現互補。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概念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技術合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概念構筑了法蘭克福學派和傳播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連通之路。這兩個概念都源自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ács)的物化概念。物化概念是對馬克思拜物教這一概念的重新闡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一種物的特性,從而獲得了一種‘虛幻的客觀性’(phantom objectivity),即一種看來十分合理的和包羅一切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掩蓋了商品的基本性質,即人與人關系的一切痕跡。”4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23/1972, p. 83.
資本主義媒介的物化形式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一,商業媒體使個體成為廣告的消費者。其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很大程度上與商品形式掛鉤。消費者和受眾購買文化商品,媒體消費者和互聯網產消者成為了商品。其三,為了復制其存在,資本主義不得不將自己塑造為最好的社會系統,并且利用媒體來維持其信息霸權。其中,前兩方面構成了工具理性中的經濟維度,而最后一方面構成了工具理性的意識形態維度。
斯麥茲強調,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的出發點是商品交換論。1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發現,“交換概念是連接社會批判理論和建構整體社會概念的一個鏈條。”2Theodor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p. 32.商品和商品交換是批判理論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由于“商品”這個概念與資本積累和意識形態緊密關聯,所以這兩條研究路徑都應該以媒體商品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為其研究起點。
部分學者認為,法蘭克福學派和傳播政治經濟學具有一種悲觀與精英主義傾向,且忽視受眾。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批評盧卡奇時說道:“虛假意識這個概念充斥著簡化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色彩。”3Stuart Hall,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35-73.同時,霍爾提出了與法蘭克福學派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概念。在受眾的觀點上,霍爾認為:“普通人不是傻瓜,他們完全有能力認識到工人階級生活的現實是可以通過他們在《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中的(媒介)再現來進行重組、重構和重塑的。”4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edited by John Storey and Hemel Herpstead, UK: Prentice Hall, 1981/1988, pp. 442-453.《加冕街》是一部英國經典肥皂劇,它是英國電視史上播放時間最長的電視劇集和收視最高的劇集。——譯者注而在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看來,法蘭克福學派和政治經濟學都存在一個簡單的統治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受眾被認為是被動操縱的“文化傻瓜”,而“文化更像是一種商品和意識形態的操縱手段”。5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 12, no. 1, 1995, pp. 72-81.與這種論斷相反,斯麥茲對于受眾有一個相對平衡的觀點:資本嘗試去控制受眾,但受眾具有抵抗的潛力。“人們不斷承受著意識工業的壓力,他們被大量的消費品和服務所包圍;他們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但是他們絕不是被動或者無能為力的。”6Dallas Smythe,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1981, p. 270.
斯麥茲對在傳播領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很感興趣,所以不能僅僅把他的研究局限于批判的傳播研究,而應該對其進行超越,將他的研究界定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這就意味著需要整合媒介和傳播領域中的所有理論的/哲學的、實證的和倫理的研究,重點分析與媒介和傳播相關的矛盾、結構以及與統治、剝削、斗爭、意識形態和可替代性相關的實踐。我們不能否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對斯麥茲的重要性,也不能認為斯麥茲構建的只是一種批判性的經驗研究的方法論。
二、關于受眾商品之爭及其復興
根據斯麥茲自己的講述,他在1951年的《廣播電視中消費者的利益》(The Consumer’s Stak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一文中第一次形成“受眾為廣告商工作”這個觀點。在這篇論文中,斯麥茲回答了廣播電視真正的產品是什么。1977年,斯麥茲提出:“壟斷資本主義之下無休閑,大多數人非睡眠以外的時間都是工作時間……職業之外的工作時間,最大的一部分是售賣給廣告商的受眾時間……在這些時間中,受眾一方面為消費者商品的生產者履行基本的營銷職能,另一方面,在工作的同時完成了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1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1, no. 3, 1977, pp. 1-27. 中譯文參見達拉斯?斯麥茲,劉曉紅譯:《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傳播政治經濟學經典文獻選讀》(姚建華主編),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7~40頁。——譯者注斯麥茲在分析媒體廣告模式的時候引入了“受眾商品”這個概念,他認為:受眾作為一種商品售賣給了廣告商,“由于受眾被生產、購買和消費,它是一種商品就需要價格……受眾貢獻了他們的無償工作時間,作為交換,他們可以觀看電視節目和特定的廣告。”2Dallas Smythe,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1981, p. 26, p. 233.
在艾琳?米漢(Eileen Meehan)的研究中,她發現:商業媒體的商品不僅只有信息和受眾,還有收視率。在她看來,回答“電視收視率的評級以及評級行業是如何適應信息商品的生產”這個問題,比回答“大眾傳播生產的商品是什么”更為重要。收視率的測量根據受眾規模的大小而采取不同強度的測量技術。收視率行業是高度壟斷的,并且占據壟斷地位的資本家會制定測量的標準。收視率評級行業傾向于選擇那些購買率和消費率高的特定受眾來進行測量,這說明:一方面,受眾商品和收視率完全是人為制造的 ;3Eileen Meehan, Commodity Audience, Actual Audience: The Blindspot Debate,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edited by Janet Wasko, Vincent Mosco and Manjunath Pendakur, Norwood, NJ: Ablex, 1993, pp.378-397.另一方面,受眾商品并不具有相同的價值。4Eileen Meehan, Understanding How the Popular Becomes Popular: The Rol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tudy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Popular Communication, vol. 5, no. 3, 2007, pp. 161-170.
蘇特?加利(Sut Jhally)認為,斯麥茲的受眾商品概念是不準確的,廣告商購買的商品是受眾的觀看時間。他的核心假設是,我們應該將“觀看時間視為媒介商品”,“當受眾觀看商業性電視節目的時候,他們是在為媒體工作,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5Sut Jhally,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p. 76.電視臺購買的是受眾的觀看力。加利和比爾?李凡特(Bill Livant)認為,受眾的觀看時間是節目時間,而觀看廣告時間是剩余時間。“電視節目,即觀看力的價值,是受眾的工資,這是傳媒工業的可變資本。”6Sut Jhally and Bill Livant,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6, 1986, pp. 124-143. 中譯文參見蘇特?加利、比爾?李凡特,陳玉佩譯:《“觀看即工作”:受眾意識的價值增殖》,《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0年第6期,第25~34頁。——譯者注
布雷特?卡拉韋(Brett Caraway)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受眾不是商品,因為“受眾的活動不受資本家的直接控制,并且也不清楚受眾的勞動成果是否發生了異化”。1Brett Caraway,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3, no. 5, 2011, pp. 693-708.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利用市場的力量強迫工人出售他們的勞動力,如果不工作,他們就不能生存。與這種有償勞動受到對身體的直接暴力威脅不同,受眾的勞動則受到意識形態的(間接)脅迫。換言之,受眾受到資本家的意識形態控制,這些資本家控制著傳播手段。如果人們停止使用臉書(Facebook)和其他社交軟件,就會失去與社會聯系的機會。用戶可以拒絕為臉書“打工”,就像工人拒絕為工資而工作一樣,但是他們有可能因此遭到社會上不利因素的影響。商業媒體擁有的壟斷權越大,就越容易對媒體消費者和用戶施加這種脅迫。
卡拉韋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評態度與他對新媒體環境中創造性力量的擁護態度相契合,這使他的分析與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社交媒體決定論者異曲同工。詹金斯認為,“網絡已經成為消費者參與的網絡”,2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p. 137.并且當今的媒體已經成為參與性文化的“沃土”。提出這些批評(指代卡拉韋和詹金斯的觀點)的根源在于對斯麥茲的無知或者故意選擇性的閱讀,因而忽視了斯麥茲對可替代性媒體中受眾商品的關注。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討論斯麥茲對“受眾商品”的闡述時說道:“現在出現了一種能夠準確測量和監視每一條信息交換的數字系統,以此來完善向廣告商輸送觀眾、聽眾、讀者、影迷以及電話、電腦使用者的過程。這是對早期受眾傳輸系統的一項重大改進,且已經被廣泛應用到當今幾乎所有的媒體中,包括互聯網中那些像臉書一樣提供用戶詳細信息的社交網站。”3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p. 137.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也發現:“由谷歌等商業平臺構建的‘互聯網禮物經濟’表明,當禮物關系更普遍地融入商品經濟中時,剝削就加劇了”;“文化和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現在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維護數字時代的公共文化共同體”。4Graham Murdock,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pp. 13-40.
在尼克?迪爾—維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看來,“斯麥茲的分析如今已獲得公信力,因為家庭中的監視力度慢慢接近于我們在工作環境中受到監視的力度,并且馬克思描述的工廠中有償工作的‘看守者’活動已經與無酬的觀看時間混為一體了。”5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 119.他批評斯麥茲太過于絕對化地認為資本對于受眾力的剝削是完全成功的,并提出:捍衛網絡隱私以及使用可替代性媒體等做法是在嘗試打破資本的統治地位。
馬克?安德列耶維奇(Mark Andrejevic)運用加利和李凡特的分析結論來對電視、互聯網、社交網站和互動媒體進行探討,指出:資本積累的策略不是基于對觀看時間的剝削,而是基于被觀看的內容。安德列耶維奇進一步洞察到:在網絡世界中,馬克思的剝削概念需要更新到剝削2.0版本。因為在臉書或者谷歌這樣的平臺上,“對于直接付費網站和用戶生產內容這類間接付費的網站來說,監視成為在線價值鏈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Mark Andrejevic, Exploitation in the Data Mine,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s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edited by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71-88.
2012年,筆者和莫斯可策劃了一個特別專題:《馬克思歸來——馬克思理論與傳播學批判研究的重要性》,這一專題的論文發表在期刊《3C: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上。2這些論文已被翻譯,并在國內出版,具體參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主編,傳播驛站工作坊譯:《馬克思歸來》(上下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譯者注超過500頁的專題內容說明了當下馬克思的作品對于批判性地理解媒介和傳播的重要性,同時也彰顯了學者們對于斯麥茲作品的濃厚興趣。特別是在“數字勞動之爭”這部分中,一些學者主張斯麥茲的受眾商品理論在對諸如臉書或油管(YouTube)等平臺進行分析時,仍具有很強的闡釋性和穿透力。
這些討論說明斯麥茲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數字勞動之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現有的討論都是基于數字勞動受資本剝削的邏輯。數字勞動的剝削包括三個動態過程:首先是脅迫(coercion)。在意識形態上,用戶被迫使用商業平臺來進行交流、共享以及建立和維持社會關系;否則,他們的生活就會變得沒有意義。其次是異化(alienation)。公司擁有平臺并且創造利潤,而非用戶。最后是侵占(appropriation)。用戶在平臺上花費時間,而這些時間就是他們無酬的數字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用戶的數字勞動創造了社會關系、數據資料、內容、互動數據等——這是互聯網企業售賣給廣告商的數據商品,并且廣告商可以選擇他們想要關注的某類特定的用戶。剝削行為通過用戶生產數據商品就已經產生了。在這種情況下,用戶的在線工作時間被客體化,他們自己不擁有這些數據,而互聯網企業在使用條款和隱私條款的幫助下享有了數據的所有權。互聯網平臺將這些數據商品提供給廣告商。價值實現的過程(即價值轉化為利潤的過程)在目標用戶觀看廣告或者點擊廣告的時候就發生了。不是所有的數據商品隨時都在被售賣,一些特殊群體的數據商品比其他群體的數據商品更受歡迎。剝削在商品的生產和占有過程中就已經存在,它先于商品的售賣。
三、數字勞動:資本積累與社交媒體的商品化
許多社交平臺的資本積累都依賴用戶個人數據和根據用戶行為量身定制的定向廣告。資本主義的核心就是資本的積累過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資本家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或者提高生產率。提高生產率就意味著資本家可以在相同的時間內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1根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資本家有兩種途徑來賺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一是強迫工人延長勞動時間,或者強迫工人提高勞動強度,即產生“絕對剩余價值”;二是通過技術進步,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即產生“相對剩余價值”。——譯者注
在八邊形式密碼中,折線經過的點數為4有2208種情況,點數為5有10464種,點數為6有40512種,點數為7有119232種,點數為8和9均有236544種。可得,八邊形圖形的密碼排列情況共645504種。
隨著用戶生成內容、社交平臺和其他通過在線廣告獲利的免費平臺的興起,網絡上的資本積累方式越來越接近電視、廣播這類傳統媒體。用戶上傳照片和圖像、撰寫帖子和評論、發送郵件給聯系人、添加好友或者瀏覽臉書上其他用戶的資料,這些活動都構成了互聯網平臺售賣給廣告商的受眾商品。傳統媒體與互聯網的受眾商品之間的區別在于:在互聯網中,用戶(作為內容消費者)同時也是內容生產者。用戶從事的是傳播、社區建設和內容生產等不間斷的創意活動。由于互聯網是一種“多對多”傳播的“去中心化”結構,這就使得互聯網用戶相較于電視和廣播受眾更加主動。由于受眾持續性的創造活動和產消者的地位,我們可以說:社交媒體的受眾商品實際上是互聯網產消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
社交媒體的用戶是商品化過程中的雙重客體: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商品;另一方面,通過商品化過程,用戶的意識受廣告商品化邏輯的支配。在社交媒體上,定向廣告充分利用用戶的個人數據、興趣、互動、信息行為等。當人們在使用臉書、油管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平臺時,或者當人們與他人進行交流或者瀏覽資料時,所有這些行為深受推送給他們的廣告的影響,這些廣告的出現是基于對人們上網行為的長期監視。
如果互聯網用戶成為生產性的產消者,那么根據馬克思的勞動理論,這就意味著用戶成為了生產性勞動者,他們生產的剩余價值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馬克思認為,生產性勞動創造剩余價值。所以,不僅僅是那些被互聯網企業雇傭,用來編程、更新和維護軟硬件、市場營銷的工作人員的剩余價值被剝削了,生產內容的用戶和產消者也同樣被剝削了。新媒體公司不會或者很少會為用戶生產的內容支付報酬。這些公司給用戶提供免費的服務和平臺,讓用戶生產內容并且吸引更多數量的產消者,然后將他們售賣給第三方廣告商。這構成了新媒體公司最為重要的資本積累方式。一個平臺擁有的用戶越多,廣告費用自然也就越高。
互聯網產消者的勞動被資本無限地剝削。換言之,資本主義產消形式是一種極端的剝削形式,在這個過程中,產消者的勞動完全是無酬的。無限的剝削意味著所有的或者幾乎所有的在線活動和時間都成為商品的一部分,并且這些活動和時間都沒有被支付報酬。斯麥茲將受眾商品描述為“思維奴隸”(mind slaves)2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 297.,我們也可以將社交媒體的用戶稱為“在線奴隸”(online slaves)。馬克思區分了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勞動時間中用于生產維持勞動者自身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那部分時間;剩余勞動時間則是額外的勞動時間。用戶的勞動時間沒有被支付,所以他們沒有錢來購買生存的必需品。也就是說,花費在谷歌、臉書、油管或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時間都是剩余勞動時間。
加利和李凡特主張,“觀看(電視)是工廠勞動的延伸”,1Sut Jhally and Bill Livant,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6, 1986, pp. 124-143.并且今天的起居室已經成為工廠之一。也就是說,工廠是有償勞動的空間,但是在起居室中,有償勞動同樣存在,且今天,有償勞動無處不在,甚至整個地球都成為了資本主義工廠。在這其中,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使網絡成為了一個生產受眾商品的重要工廠。不可否認,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模糊了全球工廠的圍墻,社會已經變成了工廠。為了反映這一發展現狀,馬里奧?特隆蒂(Mario Tronti)提出了“社會工廠”的概念:“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水平,社會關系成為了生產關系,并且整個社會成了生產的紐帶,簡而言之,整個社會像工廠一樣運作,工廠將其統治權擴展到整個社會。”2Harry Cleaver,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Open Marxism, Volume II, edited by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and Kosmos Psychopedis, London: Pluto, 1992, pp. 106-144.
莫斯可和凱瑟琳?麥克切爾(Catherine McKercher)強調,斯麥茲“通過描述人們向廣告商出售注意力來考察受眾在家中的勞動”,從而為自愿、低薪或者無酬勞動的研究奠定了基礎。3Vincent Mosco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近年來,資本主義、父權制和種族主義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這種聯系,并且這種聯系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剝削群體之間團結的基礎。哈利?克利弗(Harry Cleaver)指出:“資本試圖以自己的利益形塑所有休閑或者空余時間的活動,并將其整合至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中,而不是將無酬的非勞動時間自動視為空閑時間或者與資本完全對立的時間……換句話說,資本試圖通過創建社會工廠將‘個人消費’轉變為‘生產性消費’。”4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UK: Anti/Theses, 2000.資本主義社會的媒體和文化受到全球生產方式的影響,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家庭工作者和消費者購買商品,積極地進行勞動力的再生產,并成為媒體的受眾;用戶在互聯網上生產數據商品;貧窮國家的奴隸工人提取礦物用于數字產品的生產;制造企業中的低薪兒童、婦女等在極其艱苦和危險的工作條件下組裝計算機、手機和打印機等硬件設備;高薪但高工作強度的軟件工程師為谷歌、微軟等企業工作;發展中國家的低薪知識勞動者為西方媒體和通訊公司的分公司創建、轉換、傳輸或者編輯文化內容或者軟件;女性低薪勞動力負責呼叫中心和其他服務公司的信息服務。全球價值鏈中傳播工作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帶來了一個問題:“世界知識勞動者會團結起來嗎?”5Vincent Mosco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特雷伯爾?肖爾茨(Trebor Scholz)認為,與社交媒體相關的種種現象表明:互聯網既是游樂場,又是工廠。互聯網用戶商品化是一切事物商品化趨勢的組成部分,這種趨勢導致了工廠和剝削的普遍化。在社交媒體中,用戶創造和瀏覽內容,通過交流與他人建立和維護關系并且更新個人資料。他們花費在這些平臺上的時間都是工作時間。廣告商在臉書、谷歌等平臺上購買的互聯網產消者商品是基于人口統計數據(年齡、地點、教育程度、社會性別、工作地等)和個人興趣(谷歌上的關鍵詞搜索)的。所以,某一個興趣小組可以被識別為目標小組,該小組成員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所有時間(工作時間)構成了特定互聯網產消者商品的價值。因此,我們需要反思一下媒體經濟價值的創造過程是如何與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性資本聯系起來的。用戶之所以使用社交媒體,是因為他們想在一定程度上去努力實現布爾迪厄所提出的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的積累)、文化資本(資格、教育、知識的積累)和象征性資本(聲譽的積累)。用戶花費在社交媒體上用于生產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性資本的時間包含在產消者商品轉變為經濟資本的過程中。社交媒體上的勞動時間是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性資本向馬克思的價值和經濟資本的轉變。
馬克思在探討價值規律時,闡述道:“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長,它的價值就越大。”1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1867, p. 131.在社交媒體中,價值規律同樣適用:用戶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越長,那么關于用戶興趣和活動的數據也就越多,推送給他們的廣告也就越多。用戶在線時間越長,創造的數據和價值也就越多,這些價值可轉化的利潤也就越豐厚。社交媒體的價值定律也可以通過以下情況來考察:與谷歌上頻繁搜索的關鍵詞有關的廣告,往往價格相對較高。許多用戶將他們的工作時間花費在搜索這些關鍵詞上,這就使得搜索這些關鍵詞的用戶商品更具有價值,因此可以獲得更高的定價。
總之,資本的積累過程離不開對勞動力剩余價值的攫取。在社交媒體中,創造剩余價值的主體是產消者,假如產消者停止使用臉書或推特,那么這些新媒體平臺的用戶數量就會驟減,廣告商也會因沒有廣告對象或者潛在產品消費者數量的驟減而停止投資,相關公司的利潤將會下降,甚至破產。如果這種操作大規模發生,會帶來新一輪的經濟危機。
四、意識形態、游戲與數字勞工
進入21世紀,臉書(2004)、領英(LinkedIn,2003)、油管(2005)、推特(2006)和新浪微博(2009)等社交平臺紛紛出現。這些互聯網平臺提供在線服務,是當今世界上訪問次數最多的互聯網平臺,它們的涌現伴隨著一種意識形態——頌揚這些服務是新鮮事物——以及經濟民主和參與文化的興起。阿克塞爾?布倫斯(Axel Bruns)認為,臉書、油管和我的空間(MySpace)積極營造了“公眾參與”的環境,并產生了“基于生產使用的民主模式”(produsage-based democratic model)。1Axel Bruns,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p.372.約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提出了“傳播的對話模式”,每個人在這個模式中都是生產者。他的觀點是,隨著支持社交網絡和用戶生成內容的生產和傳播的互聯網平臺的興起,大學、大眾媒體、檔案館和其他機構變得更加民主,因為“人們在生產和消費方面具有更多的發言權”。2John Hartley, 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Chic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p. 2.克萊?史基(Clay Shirky)提出,“Web 2.0”意味著“生產民主化”。3Clay Shirky,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London: Penguin, 2008, p. 297.唐?泰普司各特(Don Tapscott)和安東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則發現了一種新的經濟形式的崛起,即“維基經濟”(wikinomics),從而孕育出“新經濟民主”。4Don Tapscott and Anthony Williams,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London: Penguin,2006.
所謂社交媒體的力量,不僅是為了吸引商業投資,也是為了在用戶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喬迪?迪恩(Jodi Dean)認為,在互聯網被盲目崇拜的情境下,假定互聯網本質上是政治的,并且“Web 2.0”本身是一種政治形式,這種假定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然而,意識形態不僅表現為夸大“社交媒體”的民主含義,同時也存在于媒介生產過程本身之中,并且作為社會關系的剝削往往隱藏在社交媒體“玩樂”的結構中。2005年,尤里安?庫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首次引入了“玩工”(playbour)這個概念。5Julian Kücklich,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no. 5, 2005.中譯文參見姚建華、倪安妮譯:《不穩定的玩工:游戲模組愛好者和數字游戲產業》,《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第196~206頁。——譯者注對數字玩工的剝削瓦解了工作時間與玩樂之間的差別。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玩樂和勞動、愛欲和死亡、享樂至上和死亡驅力(death drive)已經部分地融合在一起:工人們被期望在工作時間內得到快樂,并且他們的娛樂時間能夠和工作一樣變得富有效率。娛樂時間和工作時間相互交織,導致人類所有的生存時間都被剝削,深深嵌入到資本的積累機制中。
馬爾庫塞辯證地認為,異化的勞動、統治和資本積累已將現實原則變成了壓制性現實原則,即績效原則(performance principle):異化勞動構成了對愛欲的剩余壓抑。對快樂原則的壓抑超過了文化上必要的壓抑。同時,馬爾庫塞將馬克思關于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剩余價值的概念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論中人的驅力結構(drive structure of humans)聯系起來,并提出驅力水平上的必要勞動相當于基本壓抑,剩余勞動相當于剩余壓抑。這意味著,為了生存,一個社會需要一定數量的必要勞動(以工作小時數為單位),因此也需要相應數量的對快樂原則的壓抑(也以小時數為單位)。對剩余價值(無酬勞動和產生利潤的勞動)的剝削不僅導致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迫為資本免費工作,而且導致了快樂原則必然被進一步壓抑的境況。
如今,有償創意產業的工作越來越像游戲,大衛?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和薩拉?貝克(Sarah Baker)揭示了許多創意產業工作中的矛盾性,這些工作雖不穩定,但因其可能包含的樂趣、人脈、聲譽、創造力和自我決定權而備受大眾的青睞。勞動就像游戲,娛樂和剝削因此變得密不可分。游戲和勞動在今天的某些情況下別無二致,也就是說,愛欲已經完全被吸納到壓抑的現實原則中。游戲基本是商品化的,不被資本利用的空間和自由時間幾乎蕩然無存,它們很難被創造和捍衛。當前,游戲是生產性的、被資本剝削的、不停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所以包括游戲在內的人類所有活動都趨向于被資本所吸吶和利用。作為愛欲表達的游戲也被破壞了,人類的自由和生產力被削弱了。因此,互聯網企業代表著時間被完全地商品化與剝削——所有的人類時間都趨向于成為被資本剝削的創造剩余價值的時間。
五、對數字勞動批判的批判
在赫斯蒙德夫看來,由于社會上很多的文化工作都是無酬的,所以互聯網勞動沒有被剝削。赫斯蒙德夫進一步闡述道:“在臉書上聯系朋友并上傳照片是某種受剝削的勞動這一主張更像是在爭論:我們應該要求向所有業余足球教練支付費用,因為他們奉獻了寶貴的業余時間。”在他看來,上述主張存在一種危險,即它有可能商品化那些我們想將其遠離市場原則的活動形式。1David Hesmondhalgh, User-Generated Content, Free Labour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Ephemera, vol. 10, no. 3/4,2010, pp. 276-284.
受眾和數字勞工受社交媒體剝削有三個條件:其一,積累的利潤剝奪了受眾和用戶的物質利益;其二,受眾和用戶被排除在媒體組織的所有權和利潤積累的范圍之外;其三,資本侵占了利潤。在馬特奧?帕斯奎內里(Matteo Pasquinelli)看來,谷歌是通過網頁排名算法來創造和積累價值的。谷歌的利潤以認知租金(cognitive rent)的形式存在。2Matteo Pasquinelli, Google’s PageRank Algorithm: A Diagram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the Rentier of the Common Intellect, Deep Search: The Politics of Search beyond Google, edited by Konrad Becker and Felix Stalder,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卡拉韋從更普遍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并強調:“斯麥茲描述的經濟交易就是租金。媒體所有者將媒體的使用權出租給那些希望獲得受眾的產業資本家。租金可以是時間,也可以是空間。創造一個有利于特定受眾形成的環境是媒體所有者的工作。”1Brett Caraway, Audience Lab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 Marxian Revisiting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3, no. 5, 2011, pp. 693-708.互聯網的租金理論用租金這個概念替代了階級、剩余價值和剝削等概念。
馬克思認為,租金是用土地交換的,并指出商品價值的三個方面:利潤、租金和工資。利潤與資本相關,租金則對應著土地,工資則與有償勞動相關。這三種收入與商品、土地和勞動力的售賣緊密聯系在一起。租金是通過借地或者房產獲得的,并不是剩余價值和人類勞動的直接結果,在出租過程中沒有生產新的產品。租金間接地來源于剩余價值,因為資本家通過攫取勞動力的剩余價值而得以購買房產。所以,如果使用租金概念來描述商業媒體、互聯網實踐及其結果,那就意味著在媒體和互聯網平臺上的活動,如瀏覽谷歌頁面、在臉書或油管上創建內容是不受剝削的,也不是一種勞動形式。理解和使用租金概念對媒體和互聯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沒有幫助。反之,由被剝削的知識勞動者所創造的互聯網產消者商品這一概念更為可行。
亞當?阿維德森(Adam Arvidsson)對數字勞動假說和斯麥茲的受眾商品理論提出了批評。作為一種結論,勞動價值理論只能在勞動具有價格以及勞動轉化為商品,并在市場上進行買賣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很明顯的是,我們很難將勞動價值理論運用于沒有定價以及在工資關系之外展開的生產實踐中……數字勞動沒有價格,并且也無法區分生產時間與非生產時間。正如阿維德森、馬克?科特(Mark Coté)、詹妮弗?皮布斯(Jennifer Pybus)和筆者所研究的那樣,馬克思的剝削概念應該應用在消費者聯合生產(customer co-production)這個過程中。但是由于無酬勞動是免費的,它沒有價格,所以也不能作為價值的來源。2Adam Arvidsson, Ethics and Value in Customer Co-Production, Marketing Theory, vol. 11, no. 3, 2011, pp. 261-278.阿維德森的結論是,數字勞動沒有被剝削,因為它沒有價格。
數字勞動不僅僅只是歷史上的那些無酬工作,如家政勞動或者奴隸勞動。在奴隸、家政工作者以及互聯網用戶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奴隸受到肉體的壓迫,家政工作者部分受到暴力以及愛與感情的壓迫,而互聯網用戶是一種思想上的壓迫。但是這三種勞動形式都生產了價值,并被別人侵占。他們沒有獲得報酬,即他們的勞動時間被剝削。阿維德森假設只有支付工資才會出現剝削,這種錯誤假設低估了剝削的可怕現實,同時也暗示著奴隸和家政勞動者未受到剝削。因此,在種族主義生產模式和父權制的社會背景下,他的假設很難站住腳。
蘋果手機、平板電腦、電腦以及諾基亞手機等都是“血淋淋”的。許多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電子照相機、mp3等是由金屬材料制作而成的,而這些金屬材料是工人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從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礦井中提取出來的。互聯網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信息與通信工具,它的存在基于多種勞動:相對高工資的軟件工程師的勞動、互聯網企業低薪工作者的勞動、用戶的無酬勞動,以及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硬件以及提取金屬材料的高度被剝削的體力勞動。不難發現,阿維德森對勞動價值理論的理解是一種理想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價值觀念——倫理價值被理解為“創造各種有意義的情感關系的能力”。1Adam Arvidsson, Brand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vol. 5, no. 2, 2005, pp. 235-258.這就忽視了物質的不平等、勞動力的不穩定和貧富差距這一客觀的現實。
六、結 語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帶來了新自由主義的缺陷、漏洞和一切事物商品化的邏輯。在這個階段中,馬克思的著作、批判理論、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資本主義批判重新點燃了人們的興趣。
為了分析媒體的商品化,斯麥茲提出了受眾商品理論,加利與李凡特提出了“觀看即工作”的觀點。媒體和互聯網上的看、讀、聽、用都是一種價值生產勞動,而受眾商品和互聯網產消者商品就是由以上這些勞動創造的。受眾生產了作為商品的自身,其工作將觀眾和用戶創造為商品。
我們將本文的重點總結如下:其一,斯麥茲提醒我們,馬克思的著作對批判性地研究資本主義媒體至關重要。其二,部分學者認為,批判理論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被認為是單方面的。這種觀點主要是基于選擇性的閱讀,它忽視了上述兩條路徑對媒介商品化、受眾、意識形態和可替代性的不同關注程度。批判理論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互補的,并且應該與媒介和傳播的批判性研究結合起來。其三,斯麥茲的受眾商品概念在數字勞動是否受互聯網企業剝削的爭論中獲得了新的關注。數字勞動的剝削涉及脅迫、異化和侵占三個動態過程。其四,社交媒體企業使用資本積累模式,該模式的基礎是:對互聯網用戶無酬勞動的剝削、對用戶生產的數據的商品化,以及對用戶行為數據的商品化。其五,定向廣告和經濟監督是資本積累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交媒體中,受眾商品已經轉變為互聯網產消者商品。其六,社交媒體和“Web 2.0”并不意味著經濟和文化的民主化,而是意識形態。它是一種新型的資本積累模式,從而有助于吸引投資者。其七,對互聯網產消者的剝削是資本主義階段性的具體表現。在這個階段,游戲和勞動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對“玩工”的剝削成為一種新的剝削方式。剝削在玩樂中進行,并成為休閑的一部分。其八,對數字勞動進行批評的學者將不同的工作混為一談,他們傾向于淡化剝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誤解了剩余價值、價值、價格和租金等核心概念。
資本主義在今天矛盾重重,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客觀矛盾的體現。對于經濟危機的反應也是充滿著矛盾的:從超新自由主義(hyper-neoliberalism)到騷動、抗議、示威、占領以及革命。這些抗爭和政治形式反映了危機時刻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今天,批判學者參與學術和政治斗爭的任務是為了建立包括傳播在內的公共設施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