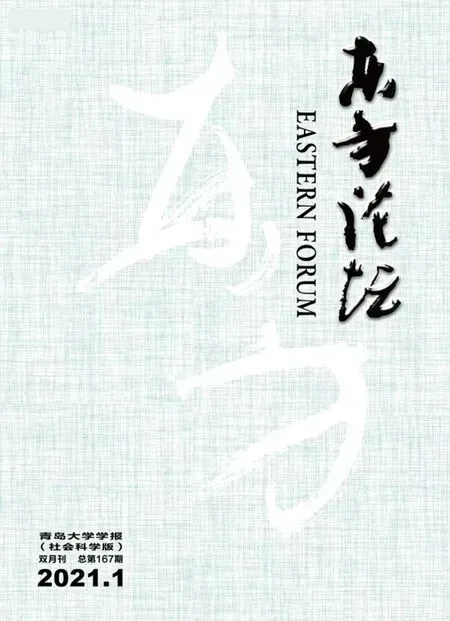“將真實(shí)深深地藏在心的創(chuàng)傷中”
——魯迅《傷逝》的創(chuàng)作心理
張龍福
青島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山東 青島 266071
雖然魯迅的小說幾乎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主觀抒情色彩,但像《傷逝》這樣抒情極為濃烈的作品仍然使人感到在魯迅的所有小說創(chuàng)作中似乎顯得頗為奇異。即便在整個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也因而顯得有些“另類”而十分引人注目。這就不能不激發(fā)人們深入探究造成《傷逝》這一特殊風(fēng)貌的內(nèi)在奧秘,而對其創(chuàng)作心理的研究自應(yīng)更加受到推重。
然而,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原本就幽深復(fù)雜,而魯迅《傷逝》之堂奧尤為難測。早在《傷逝》最初面世時,就有人猜測其創(chuàng)作可能和作者本人的婚戀生活不無關(guān)系,但魯迅在1926年12月29日致韋素園的信中說:“我還聽到一種傳說,說《傷逝》是我自己的事,因?yàn)闆]有經(jīng)驗(yàn),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難了。”①魯迅:《261228 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第520頁。魯迅看似否定的一聲“哈哈”之嘆,使得后來研究者的思路不再向這方面延展。新中國成立后很多年,我們的魯迅研究極度偏重于挖掘作家作品的社會思想政治內(nèi)涵,而對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作家的個人婚戀生活及其創(chuàng)作心理的探索卻頗多避諱,幾成空白,因而有關(guān)《傷逝》的研究成果雖然數(shù)量眾多,實(shí)則內(nèi)容雷同、結(jié)論單一。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傷逝》的題旨是要揭示個性解放、婚戀自由是不能離開整個社會的解放而單獨(dú)解決的,這也正顯示了魯迅思想卓然超拔于其所處的時代。新時期以來,學(xué)界思想日漸解放,人本思潮尤趨盛大,魯迅也被從神壇拉回到人間,不少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魯迅的婚戀生活對其創(chuàng)作心理的深刻影響,并著力開掘其作品中所潛隱的個人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