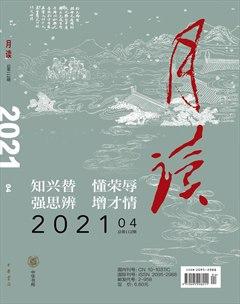中國哲學的主要論題與核心范疇
王杰
學術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紀的殷周時期,也就是傳說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時期,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哲學稱為傳統哲學,歷時長達三千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特別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思想空前活躍;這一時期,按照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說法,被稱為軸心時代。在人類文明的幼年時期,世界不同的文明點上,如古希臘羅馬、古印度、古巴比倫、古代中國等,相繼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群體,這些思想家群體不約而同地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生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提出了人類永遠不可能繞過的一系列核心問題,甚至可以說我們今天的思考,從本質上說并沒有超越軸心時代思想家們提出的范圍,是對古人思考的一種延續。
在軸心時代的思考中,古希臘側重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由此產生的思想具有科學性、實證性特征;古印度、希伯來文明側重于對人與神關系的探討,由此產生的思想就具有宗教性特征;而古代中國則側重于對人與社會、人生關系的探討,由此產生的思想就具有道德性、倫理性、人文性特征。
在夏商時期大約一千年間,社會的總體特征是先鬼而后禮、率民而事神,任何事都要問于鬼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與戰爭,是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情,這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周易》卦爻辭中,都有鮮明的體現。如果中國社會按照“先鬼而后禮、率民而事神”這條道路走下去,很可能會變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宗教社會。但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立以后,打破了延續千余年的天命觀,開始推行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制禮作樂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推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靡常”“天命轉移”的價值觀,開啟了中國文化遠神權重道德、遠鬼神重人倫的大門,由此奠定了中國文化三千年的基本走向和格局。
那么,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哲學在對人與自然、社會、人生、人性等問題的探討中,究竟對哪些問題感興趣呢?這都是些什么問題呢?
通過對春秋戰國五百多年思想爭論問題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思想家們最關注和感興趣的問題是什么。這里不妨舉幾個例子:
首先是天人關系問題。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首先面對的就是與大自然的關系,一切問題,可以說都是由天人關系衍生而來,中國古代哲學的產生與發展同天人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天人關系,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與人的關系如何。歷朝歷代的思想家們都站在天人關系的視角,探討天與人之間的關系,把天人關系看作自己理論的出發點,如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人通過反觀內求,就能夠認識天,孟子的這個天人合一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以后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司馬遷提出了“天人之際”說,劉禹錫、柳宗元提出了“天人相交”說,程顥提出了“天人同體”說,張載更是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提出了“天人·理”說,陸象山、王陽明提出了“天人一心”說,王夫之提出了“天人一氣”說,等等。這些思想家都是把天人關系看作自己思想的出發點。在中國文化系統中,天人關系及其所蘊含的智慧始終被中國哲學家看作最重要的哲學問題,是中國哲學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
其次是人性善惡問題。中國哲學的特點是,既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關注道德,又關注人性問題。孔子最早提出了“性相近,習相遠”這一人性問題,但他沒有展開論述,從而為后人探討這個問題留下了諸多思考空間。此后,關于人性的爭論,戰國時期主要有三種觀點,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以及荀子的性惡論。到后世,又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理論,如漢代揚雄的善惡混,董仲舒、韓愈的性三品說,張載的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等。
第三是王霸義利問題。所謂王霸,就是指王道和霸道,是就如何治理一個國家而言的,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方略。王道的基本特征是“以德服人”,霸道的基本特征是“以力服人”。這個問題,也可以看作儒家與法家之間爭論是以德治國還是依法治國的問題。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孟子把治國之道明確劃分為“王道”和“霸道”,荀子不再把王道和霸道決然對立起來,認為王霸兩種方式都可以治國強國,強調王霸并用。
如果說王霸學說是如何治理國家的,那么義利則回到了個人,是圍繞個人問題而展開的。孔子最早對義利關系進行了定位,提出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基本原則。主張義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要以義制利,見利思義,欲而不貪。孟子在義利關系上,更強調義的價值優先原則。在義利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孟子堅決主張先義后利,要毫不猶豫地放棄“利”,甚至是“舍生取義”。在義利問題上,荀子同樣主張先義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同樣秉持道德價值優先的原則。
第四是夷夏之辨問題。從其本質而言,其實就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夷夏”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說文解字》云:“夏,中國之人也”;“夷,東方之人也”。至春秋時期,隨著華夏與夷狄地緣關系被打破,“夷夏”觀念開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圍,被賦予了文化的意義,主要用于區別尊卑上下、文明野蠻。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夏”代表著正統、先進、文明,“夷”則代表著非正統、落后、野蠻,孔子在其思想體系中就力倡夷夏之辨。自孔子之后,夷夏之辨成為儒家正統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孟子與孔子一樣,也嚴倡夷夏之辨,認為“用夏變夷”是天經地義的,而“用夷變夏”則是不可思議的。從孔孟的夷夏之辨來看,他們的思想具有濃厚的華夏中心論傾向,現在看來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還有民貴君輕問題、天下國家關系問題、仁愛兼愛關系問題、德治法治問題、有為無為問題、古今名實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早期中國思想家們感興趣且始終追問探尋的問題;這些問題,見仁見智,有的有答案,有的可能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但中國哲學家幾千年仍然在不斷追尋和探索,試圖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就是中國哲學的魅力所在。
漢代以后,中國哲學在繼續探討先秦時期提出來的問題的同時,還探討了天人感應問題,語言與思想的關系問題,精神與肉體的關系問題,一多、動靜、本末、有無問題,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問題,天理與人欲的關系問題,心性性命問題,無極太極、理氣關系問題,等等,限于篇幅,我們就不一一贅述了。一句話,中國哲學探討的所有問題都是圍繞著人,圍繞著社會,圍繞著現實展開的,所以,有學者把中國哲學的特點概括為“人學”,是有一定道理的。思想家們無論是談論過去還是談論天道,都不是為過去而談論過去,不是為談論天道而談論天道,其目的是為現在、為當下、為人,這就是荀子說的“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白居易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知古一定是為了鑒今,推天道一定是為了盡人事。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為邏輯而邏輯的學問,在中國思想史上不是沒有出現過,但絕大多數都是曇花一現、難以長久,譬如先秦時期的名家學說,無論是惠施的“合同異”,還是公孫龍的“離堅白”,都是從概念本身出發,經由邏輯的思辨,達到最后的結論。名家在闡釋這些觀點時,僅僅是出于與別人辯論的需要,而不像儒、墨那樣立足于實際,服務于現實,因而遭到了儒、道等思想派別的譏諷和批判,也遭到了當時執政者的冷漠和反感,認為名家既不能定國安邦,也不能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名家在秦朝以后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后世名家傳人的影響均不及儒、墨、道、釋、兵、法諸家影響面廣。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特點,與西方哲學重天人兩分、重思辨、重知識、重分析、重邏輯推演、重探求客觀世界的真相相比,中國哲學表現出了重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平衡,重理想人格的追求,重內圣與外王的統一,重人的生命價值,重辯證思維,重道德實踐,重生態環境保護等特點。也正是這些特點,使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哲學的智慧也正是在與西方哲學的比較中體現出來的。
任何一個哲學思想體系必然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疇)、判斷(命題)、推理組成的。大家知道,西方哲學的核心范疇主要有理念、存在、對象、本質、精神實體、形而上學,等等。中國傳統哲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構筑了一個環環相扣、相互聯系的哲學范疇體系。這一范疇體系是中國傳統哲學在自身內在邏輯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反映了中華民族理論思維和認識外部世界水平逐漸深化的過程。
這些范疇體系可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宇宙論方面的范疇,如天人、天道、乾坤、陰陽、五行、道器、理氣、無極、太極等;二是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如有無、本末、動靜、體用、一多、形神、因果、虛實等;三是知識論方面的范疇,如名實、言意、知行、能所等;四是社會政治歷史方面的范疇,如古今、王霸、義利、名教與自然、理勢、理欲等;五是人生道德方面的范疇,如仁、義、禮、智、信、誠、心、性、情、欲等。
中國哲學的這些概念和范疇凝結著中國人的智慧,是偉大的思想寶庫。在中國傳統哲學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這些概念和范疇被不斷地運用、充實、豐富,并被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使中國傳統哲學具有了博大精深、包羅萬象的特點。這些概念大部分仍“活”在現實生活中,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陰陽五行學說仍是中醫理論的主要概念;還有一些成語、俗語仍是人們平時常用的語言,如扭轉乾坤、天道酬勤、本末倒置、避實就虛、言簡意賅、形神兼備、仁至義盡、名實相副等;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更是當今社會大力提倡的傳統美德。
再如,傳統哲學中的以人為本、天人和諧、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和為貴、和而不同、民貴君輕、與時偕行、變易維新、求同存異、民胞物與、協和萬邦、經世致用、重德重教重孝等思想,以及榮辱觀、廉恥觀、節儉觀、正義觀等,都已融入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中,成為我們今天制定治國方略的重要歷史資源和思想資源,成為當今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對于今天的社會仍具有巨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