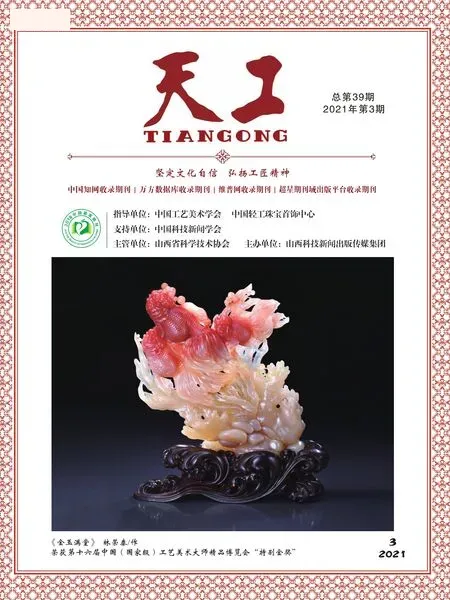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新疆傳統手工藝創新設計初探
——以喀什木雕為例
文 王丹陽 許 倩 周靈燕
木雕作為一種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的載體,是我國古代長期使用的一種裝飾手法[1],國際研討會將這一現象稱為木文化。廣義的木文化將所有與木有關的物質精神文化都統稱為木文化,狹義的木文化以木為載體來反映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思想文化,是社會精神文化中重要的文化構成之一。
一、喀什木雕手工藝發展概述
喀什位于我國最西端,是古絲綢之路的要沖,是我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西部門戶。喀什木雕作為我國民族地區傳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喀什木雕是新疆,特別是南疆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當地木材和人的生活實踐密切結合的產物、人文與自然相融合的載體。喀什木雕技藝作為新疆地區獨特的藝術載體,匯聚了當地人民的傳統文化和地域特征,映射著這個地區獨特的民族風情和審美,成為南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
木雕作為一種新疆傳統技藝,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雕刻耗費時間久、成本較高且缺乏紋飾、樣式上的創新已經難以在當今市場經濟體制下繼續存在并延續下去,許多喀什傳統家庭使用成本更低、更容易造型的密度板、刨花板進行室內裝飾,市場需求減弱,加上沒有政策性指導及缺乏統一的行業規范,多方面因素導致木雕工藝傳承困難,隨之逐漸沒落。
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談及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價值體系并表達了自己對此的認同和推崇,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將文化潤疆工程作為新疆文化建設的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向。喀什木雕工藝作為新疆非物質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探討如何保護和傳承,已成為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新的重要課題。
二、喀什木雕的藝術風格和構成特色分析
(一)藝術風格
喀什木雕的裝飾風格是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融合了我國中原地區及中西亞地區、歐洲地區的習俗、藝術、經濟、審美等多方面的內容而形成的,具有獨特的審美與地域特色,充分體現了“來源于生活,又回饋于生活”的表現方式。
雕刻藝術以紋樣、圖案為基礎,以平面的雕刻形式出現,在古代新疆地區草原巖畫是最早的雕刻藝術、當地人的生產方式從游牧轉變為農耕后,在繼承了原有的雕刻技藝的基礎上,充分吸收絲綢之路貿易各國的雕刻技藝,如印度木雕、希臘浮雕技術、犍陀羅藝術等,雕刻藝術不斷得到升華,隨著中亞地區文化傳入,喀什雕刻藝術再次得到了發展,雕刻種類更加多樣,有木雕、磚雕、石膏雕刻等,其中木雕的使用極其廣泛,包括民居建筑的任何部位,如院落門、屋頂、木柱等。

圖1

圖2

圖3
(二)構成特色
1.類型
木雕藝術應用廣泛,喀什木雕裝飾應用在不同的木雕構件上,例如民居中的廊柱(圖1)、木欞花格窗(圖2)、歐式拱形門(圖3)、配飾掛件、桌椅板凳等。新疆喀什的人們受地域影響一直使用木制器具,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裝飾品大都是以木制雕刻為載體來實現的。
2.雕刻手法
喀什木雕雕刻工藝具有多元化特點,包括深圓刀雕、浮雕、淺雕、圓雕、透雕等。圓刀雕由于刀法不肯定,刻出的輪廓比較含糊,但產生的凹凸感又比較清晰,所以一般表現各種物體的質感和肌理,作為浮雕的底面處理。浮雕是在木料上將所要表現的圖案形象凸起,分層次地表現出裝飾題材的立體感。淺雕適合于裝飾屏風、大型室內壁畫、隔堂板等大面積的板面。圓雕是一種完全立體的雕刻,前、后、左、右四面都要雕刻出具體的形象來,實際上是一種具有三維空間藝術感的雕塑藝術。透雕是將花板底子鏤空的一種工藝手法,它通常只雕刻器物的外表面,建筑木雕應用較多。不同的雕刻技法應用在不同的裝飾部分,形成獨具特色的木雕工藝品。
3.材質
喀什處于南疆西南部,氣候干燥,植物對生活在喀什的人們來說象征著生命,對其有著特殊的意義。在喀什這片地質疏松的土壤中,誕生了很多特殊的植被,例如新疆的白楊樹、核桃樹、沙棗樹、石榴樹、梨樹、杏樹等。其中楊樹的干又高又直、樹冠小,生長快速、生命力頑強,是當地首選的裝修和建筑木材。還有一些富有的家庭會選擇核桃木,核桃木做工比較復雜,但干燥后的核桃木不易變形干裂,還可以很好地粘接。
喀什木雕對材質的選用十分重視木材的自然原色美,有一部分是保留了木材原有的顏色,只涂一遍清漆保護木材,防止損害,在具體的處理手法中,以材質本身的花紋特性,體現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追求“天人合一”的效果;或通過巧妙組合不同材質的木雕作品,在保留木材原始之美的基礎上,通過不同花紋的相互對比,形成反差,突出雕刻之美,提升作品的魅力和表現張力。這種力求呈現樸實自然的原色美的做法是喀什木雕特色的存在。另一部分會為彌補某些木質的缺陷、豐富木材的質感而著色。
4.紋樣
民族紋樣是喀什木雕主要的表現題材,喀什本土“木雕的題材紋樣是將中華傳統的人本思想,深入圖案在文化層面的美育作用,貫穿于圖案的觀點與設計中,把圖案設計與人民的生活綁在一起”[2]。喀什木雕的特色最主要在于繁復的木雕裝飾紋樣、獨特的木材和精湛的雕刻技法。喀什木雕的裝飾紋樣表現出了獨特的民族審美,人們常用比較復雜的圖案進行裝飾,就逐漸形成了繁復華麗的裝飾紋樣。在喀什木雕中,紋樣大多以用植物花卉紋樣、幾何紋樣和工藝品類紋樣等來進行裝飾。植物類紋樣有石榴花紋、牡丹花紋、巴旦木花紋、菊花紋、雞冠花紋、葡萄花紋、葵花紋等。幾何紋樣有三角形花紋、菱形花紋、方形花紋、圓形花紋、扇形花紋、曲線型花紋、星形花紋等。工藝類紋樣有花瓶花紋、水壺花紋、壇子花紋、爐子花紋等。紋樣的變換與應用是當地人民將其作為美好寓意的載體。
三、喀什木雕工藝創新方法初探
(一)加工方式創新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往簡單粗加工已經難以在現在市場繼續存在延續下去,從而使很多粗雕制作人放棄粗雕制作,深入內容進行精細的雕刻制作,然而精細的雕刻耗費時間久、成本較高,對雕刻的加工方式進行創新是必要的。隨著社會的進步,如今的一些半自動化、全自動化機械已經被運用于木雕產業。
加工雕刻時,紋樣圖案的雕刻調整是最耗時的,因此利用電腦軟件對建筑、服飾、地毯上的紋樣進行提取創新、拆分重組,匯總形成數據庫,將現代工業技術和科學技術相結合應用到木雕上。在基本紋樣的基礎上進行旋轉、連接、變形,進行有效的組合,尤其是應用于比較大區域的雕刻上,紋樣的合理組合尤為重要。還可以通過電腦技術對紋樣的組合進行多次調整,防止出現紋樣單調、搭配失調和構圖邏輯混亂的問題。對于基本紋樣而言,每一個都是可以組合排列的,也可以作為單獨的來使用,是最基本的元素。利用機械速度快、完工周期時間短、雕刻精細等優勢,加上手工對細節的打磨雕刻,以精美、實用促進木雕的傳承,使其誕生更多的、符合時代審美的、突出民族特色的作品。
(二)木雕制品種類的創新
喀什木雕工藝的使用幾乎涵蓋了民居、家具、裝潢等,新材料新技術的出現對傳統技藝的沖擊,導致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木雕工藝主要集中在民居的雕刻中,但是隨著近幾年人工成本的攀升、居住觀念的改變,木質材料被更多廉價材料所代替。喀什木雕技藝的傳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要將喀什精湛的木雕技藝繼續保留下去,木雕產品的種類就必將更為豐富。
(三)喀什木雕技藝傳承觀念的創新
目前,我國很多傳統手工藝面臨失傳危險,究其原因,大多數都受到傳統傳承方式的影響。傳統手工藝的傳承主要靠手工藝人的言傳身教或者家庭內部的流傳,落后的傳播方式是手工藝沒落的重要原因。據調查,喀什木雕的傳承方式大多以師徒、家庭式的方式傳承,顯然這種模式已不適合現代經濟體制的發展,喀什大學等南疆高校也開始逐步重視手工藝的發展,開始設置相關課程,目的就是對喀什木雕藝術這樣的中國優秀傳統技藝進行研究、傳承,從而促進喀什木雕手工藝的發展。目前,喀什木雕的生產方式依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進行小規模加工,除了室內裝潢或外墻木雕改造,木雕工藝品的制作工期都普遍偏短,木雕成品的創新度也較差,真正能夠體現喀什木雕精湛工藝的作品為數不多,古城所售賣的木雕作品都大同小異。
對于喀什木雕技藝的傳承,在保證技藝傳承后繼有人的基礎上,首先要正視現代社會觀念變遷對木雕工藝的影響和改變。其次是要對喀什木雕技藝進行多角度的創新,要正視木雕工藝,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傳統的手工藝方式也需要進行取舍,明確創新與傳承的關系。在喀什木雕技藝的傳承發展中,應該著重思考木雕的創作手法、題材、結構,把握喀什木雕的文化精髓,傳遞木雕的細膩美學,在傳承的基礎上賦予木雕新的意義。
(四)提高喀什木雕的文化附加值
德國作家瓦爾特曾說:“機械復制時代如何辨別藝術品的不可復制的部分,這就是藝術品所獨一無二的地方。”賦予工藝品最大的特色,是承載在工藝品上不可替代的時代環境,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背景,在進行喀什木雕的創新時,應以此角度出發,挖掘手工藝產品的獨特性,然后表現出來,這樣不僅能夠更好地保護喀什本土手工藝,而且有助于提升喀什手工藝品的市場競爭力。
具體來說,喀什木雕的文化附加值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提升,其一,地域性的符號認同;其二,文化意義的情感認同。
地域性的符號認同:喀什地處絲綢之路要沖,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地,從古至今有多種文化在喀什進行著廣泛傳播,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喀什木雕藝術不同于我國其他地方的木雕藝術。正因如此,為喀什木雕藝術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素材和創作材料。地域性符號是指通過對喀什特色景觀、歷史文化等進行提取并巧妙地運用到產品中的創作方式,目的以給人帶來明確的辨識度,將對喀什地域的文化情感轉移到工藝品上,形成文化認同感。喀什本土地域符號可以從人文景觀、自然景觀兩個方面進行提取。人文景觀有喀什香妃墓、喀什古城、克孜爾石窟等,自然景觀有白沙湖、塔縣等可供素材選取,在未來的喀什木雕產品中,可以充分對以上喀什特色景觀進行元素提取和加工,形成具有喀什典型特征的木雕新作品。
四、小結
喀什木雕的出現、發展得益于喀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環境,位于交通樞紐的喀什,創作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承載著絲路精神的獨特內涵,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導致喀什木雕也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本文以一帶一路為背景,淺析了喀什傳統木雕工藝的保護策略。但對于龐大的喀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仍是杯水車薪。希望有關保護單位能夠加強對喀什木雕文物的保護,從而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