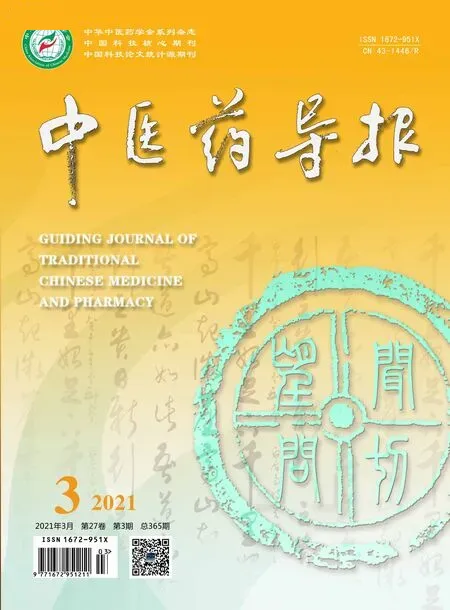孫申田針藥并用治療中風失語癥的臨床思維與經驗*
王 陸,姜德友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全國名中醫孫申田教授工作站,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中風失語癥主要的失語類型可分為外側裂周圍失語(Broca、Wernicke及傳導性失語)、經皮質性失語(經皮質運動性、感覺性及混合性失語)、完全性失語、命名性失語、皮質下失語(丘腦性、內囊、基底核損害所致失語)[1]。西醫治療一般在按照缺血性、出血性腦血管病的治療原則上結合語言康復訓練。雖然可體現一定療效,但結果仍無法令人滿意。也有研究[2]報道多巴胺能藥、安非他明、膽堿能藥、腦保護藥、唑吡坦、去氧腎上腺素、5-羥色胺等治療失語癥的藥物,但臨床療效尚待考究。中醫在針藥治療中風失語癥方面有獨特優勢,臨床療效較為顯著。診斷分型以風陽上擾、風痰阻絡、痰熱腑實、氣虛血瘀、陰虛風動等為主[3]。治療上以針刺[4](頭針、體針)結合方藥(天麻鉤藤飲、半夏白術天麻湯、星蔞承氣湯、補陽還五湯、鎮肝息風湯等)為主,也有灸法治療本病的記載[4],如《普濟方》:“治風失音不語,穴合谷,各灸三壯。”
孫申田(以下尊稱孫師),全國名老中醫,多年來致力于中風病的臨床研究,因療效顯著而聞名,現仍堅守臨床一線,診病針刺日均80余人。筆者有幸跟孫師學習,現從其對中風病失語癥的辨證診斷到針藥治療等方面進行分析整理,總結其中西互參、審病求因的辨治診斷思維,以及以神智調節為基礎,針刺大腦功能相應分區投影區并通過手法達到治療預期刺激量,與精準辨證前提下應用經典方藥相結合的治療舉措。
1 診斷思維
1.1 中西互參 孫師善于學習和整合醫療,在中風病失語癥的診斷上,不僅重視中醫的辨證分型,也結合參考西醫神經系統知識與實驗室診斷,匯通中西,每診患者時,必須先進行中醫病證診斷,又要明確現代醫學的確切病名及相關實驗室診斷,在充分的科學依據基礎上進行辨證施治[5]。每診時根據患者的表現結合家屬的主訴,不難辨病;再據四診所收集到的信息進行辨證,明確證。同時通過患者的影像學檢查,確定大腦病損區域及損傷程度,再結合患者已知實驗室檢查。中西互參全面了解患者當前狀態,不僅可以為接下來的針藥治療方案提供依據,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預判患者的預后恢復程度及治療周期。臨床中往往有患者的影像學檢查與實際患者表現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情況,有一些患者大腦左側顳葉影像檢查顯示損傷面積較大,右側肢體出現偏癱表現,但是言語功能未受到影響,此時治療以偏癱為主;抑或是左側顳葉影像未有明顯病灶,而患者表現出語言功能的完全或部分喪失,此時應以中風失語及偏癱為出發點提出治療方案。
1.2 審病求因 中風一病古有中經絡、中臟腑之分,而中臟腑中又有閉證、脫證之別[6]。現代醫學的進步,現實中往往急性發病者,首選西醫急救,待患者選擇中醫治療時,往往處于疾病相對穩定的恢復期,故臨床中多以中經絡者和恢復期患者為主。而失語一癥是中風病常見的并發癥之一,且臨床較為難治,孫師臨床中審病必求因,認為本病的主要致病因素為飲食不節、情志不暢及勞欲過度或年高體衰導致的正氣虧損,外邪侵襲。發作先期多以標實為主,恢復期則多以本虛為主并伴有氣、血、痰瘀于經絡,虛實可以互為因果又可相互影響。故臨床中應辨清“虛”為何虛、“瘀”為何瘀。故能精準的辨證施治指導施針、遣方用藥。恰如“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7]。
1.2.1 病在臟《張氏醫通·中風》[8]云:“舌強不能言,病在臟腑,先入陰后入陽。”說明中風失語與臟腑關系密切,且主要責之于臟。《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7]云:“邪入于臟,舌即難言,口吐涎。”同樣表明臟病和中風失語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且病既可在一臟,也可受多臟之影響。
單臟者,《靈樞·五閱五使》[9]云:“舌者,心之官也,心病者,舌卷短。”舌的正常功能發揮與心有密切關系,而舌的功能正常又是語言功能的根本,故而中風失語一病,首當重視此臟。《靈樞·九針》[9]云:“肝主語”。表明肝臟不病是言語功能正常的保障,患者情志平素易怒、脈弦等為中風失語是否與此臟相關提供依據。《丹溪心法·中風》[10]云:“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脾虛失于運化,水濕凝聚成痰,痰日久生熱,熱久生風,風痰竄犯清竅。脾主病患者多表現為痰濕、痰熱,舌滑苔膩,可伴齒痕,脈象多滑、滑數或弦數。
多臟者,《中藏經》[11]云:“心脾俱中風,則舌強不能言也。”表明心、脾二臟與語言的功能關系密切。《素問·生氣通天論篇》[12]云:“陽氣者,煩勞則張。”煩勞傷及肝腎之陰,陰虛陽亢氣血隨陽上逆,蒙阻神竅,腦竅受阻可導致本病,患者多有舌紅、脈弦細數等陰虛表現。臨床中中風失語一病多兼臟而為病。
1.2.2 病在經絡 肝、心、脾、腎四經的經絡主干或分支別絡皆與舌聯通。《靈樞·經別》[9]言:“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故在此若臟有疾必然影響其經絡絡屬失去溝通、運行、感應、調節及功能從而影響舌的正常功能;若邪犯四經,同樣影響臟和舌發揮正常功能。《靈樞·憂恚無言》[9]言:“舌者,音聲之機也。”故舌病,則其在語言發聲方面的功能也會收到影響。
1.2.3 病虛實 《素問·調經論篇》[12]云:“百病之生,皆有虛實。”探討疾病的虛實對于指導本病的治療極其關鍵。中風失語病初發以標實為主,氣、血、痰瘀阻腦絡。實者,或情緒易怒,或聲高氣粗,或面紅目赤;舌紅,或舌暗,或有瘀斑瘀點,或有齒痕;苔膩或黃或白;脈或弦而有力,或弦滑,或滑數。恢復期以及年高體弱者,多以虛(氣虛、陰虛等)為主,兼有實邪。或聲音低微,或乏力氣短或易汗出;舌淡暗或有瘀點,苔薄白或膩;脈沉細或弦細。或面色潮紅,或腰膝酸軟或耳鳴目干;舌紅或暗紅,苔少或無,脈弦細或弦細數。
1.2.4 病分型 中風失語癥可分為運動性失語(即患者保留理解語言的功能,能聽懂他人的話語,但失去組合語言的功能)、感覺性失語(即患者失去了理解語言的能力,所答非所問,當醫生檢查時不能按醫生的要求完成指定的動作)、命名性失語(即患者不能講出物體的名稱,但能講出該物的應用方法)和混合性失語(出現上述語言分析器的多處病變而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功能障礙)[1]。
2 治療思路
2.1 選穴配方是取得療效的根基
2.1.1 頭針 孫師治療中風一病尤擅從頭針入手,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探索研究頭針療法在腦部疾病治療過程中的機理,從多角度多層次對頭針治療中風一病的治療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最終得出臨床行之確效的中風病頭針治療方案,并應用于臨床至今。其將大腦功能區域的定位及行針手法結合的治療理念,不僅在臨床中切實有效而且也為本病的治療提供了理論依據。
頭針分區定位[13]:(1)運動區:上點在前后正中線中點后0.5 cm處;下點位于眉枕線和鬢角發際前緣相交處(顴弓中點向上引垂線與眉枕線交點向前移0.5 cm)。此區上1/5是下肢、軀干運動區;中2/5是上肢運動區,下2/5是頭面運動區。(2)感覺區:自運動區向后1.5cm的平行線。同樣分上1/5、中2/5、與下2/5。(3)情感區:第一針位于神庭與印堂穴之間,左右兩針位于目內眥直上平行于第一針,共3針。(4)足運感區:前后正中線重點旁開0.5~1 cm,向后引平行于正中線的3 cm長直線。(5)言語一區:運動區下1/5。(6)言語二區:耳尖直上1.5 cm向后引4 cm的水平線。(7)言語三區:頂骨結節后下方2 cm處引一平行于前后正中線的直線,向下取3 cm長直線。
2.1.1.1 調神 因本病患者多因語言障礙不能與他人互相溝通,而產生情緒障礙,患者或抑郁不語,悶悶不樂,或急躁易怒,孫師認為調節情感是疾病取得良好療效的首要,故在治療失語癥時,先以此作為切入點并貫穿整個療程。
取穴:百會、情感區(額區)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法”(針刺入相應頭部分區后,高速捻轉3~5 min,200次/min以上)。經絡取穴配以太沖,調暢肝氣,改善額葉功能,緩解抑郁狀態。
2.1.1.2 運動性失語 取穴:運動區(中央前回區)、感覺區(中央后回區)、言語一區(運動區下1/5)、配以(金津/玉液)、廉泉、地倉(患側)、迎香(患側)、風池(雙)、完骨(雙)、通里(雙),伴有中風其他癥狀臨癥加減取穴。
手法:運動區、感覺區、運動區下1/5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法,高速捻轉3~5 min,間隔10 min捻轉1次,共捻轉2~3次。其余穴位得氣為度,配合電針儀(疏波20 min),舌中穴點刺不留針,金津、玉液二者交替針刺。
2.1.1.3 感覺性失語 取穴:運動區(中央前回區)、感覺區(中央后回區)、言語二區(大腦顳葉顳下回后部感覺性語言分析器在頭皮表面的投影,配以舌中(金津、玉液)、廉泉、地倉(患側)、迎香(患側)、風池(雙)、完骨(雙)、通里(雙)。
手法:同上,并配合電針。
2.1.1.4 命名性失語(頂葉角回后部) 取穴:運動區(中央前回區)、感覺區(中央后回區)、言語三區(大腦頂葉角回在頭皮表面的投影)、配以地倉(患側)、迎香(患側)、風池(雙)、完骨(雙)、通里(雙)。
手法:同上,并配合電針。
2.1.1.5混合型失語 除運動區(中央前回區)、感覺區(中央后回區)外、選穴治療時將上述各類語言障礙取穴組合在一起,其余穴位不變;操作同上。
2.1.2 體針選穴
2.1.2.1 遵臟腑經絡配穴 本病主要責之于心、肝、脾、腎。故應選此四臟本經,及相關表里經配穴為主。心經:通里。肝經:肝俞、太沖、行間等。膽經:風池、完骨,陽陵泉、丘墟等。脾經:脾俞、三陰交、陰陵泉等。胃經:胃俞、地倉、足三里、豐隆等。腎經:腎俞、太溪、照海等。任脈:廉泉、關元、氣海等。經外奇穴:金津、玉液。
2.1.2.2 遵常見病機配穴 氣虛:百會、氣海、關元、足三里、三陰交、神闕(灸)等。陰虛:太溪、照海、陰陵泉、三陰交等。氣郁:風池、太沖、支溝等。痰阻:豐隆、足三里、三陰交等。
2.2 行針手法是取得顯著療效的關鍵 孫師尤重行針手法。清·李守先也曾在《針灸易學》[14]中說:“難不在穴,在手法耳。”孫師經過幾十年的臨床研究,以經顱電、磁刺激理論假說結合傳統針刺手法探索得出經顱重復針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acupuncture stimulation,rTAS)療法[15],通過快速的反復捻轉手法(200 r/min以上,連續捻轉3~5 min。)在施針處產生的場強,當刺激量達到一定程度時(此種刺激量強度與捻針速度、持續時間以及重復施術間隔有關)可以透過顱骨的高阻抗直接作用于相應的大腦分區皮層,刺激大腦細胞,通過影響相應區域的膜電位、離子等調整了相關生理、病理過程促進大腦受損區域恢復,從而到達恢復大腦相關功能的作用。體針行針手法易輕,稍加捻轉得氣即可。
中醫傳統針刺補瀉手法認為,捻轉角度大、頻率快、用力重為瀉法[6]。由此可見孫師頭針手法貼近于瀉法,應用此種手法,意在瀉除腦部實邪。中醫認為中風一病多屬本虛標實,即:全身正氣不足為虛,病損腦脈受阻為實。且西醫認為無論是出血或梗死,最終也都為瘀血留阻于腦,仍可歸屬中醫之實邪,治療以活血為主,恰能說明本種手法瀉實祛瘀、通經絡、活氣血的科學性。符合“泄其有余”[9]的中醫理論。捻轉角度小、頻率慢、用力輕為補法[6]。體針上,孫師選擇補氣補血的陽經為主,運用補法也正符合“補其不足”[9]的理論。簡而言之,孫師的行針手法,既符傳統中醫學理論,又有現代醫學相關治療體系的支撐,是同具科學性和可行性的操作手法。
2.3 方藥論治 孫師認為中風恢復期患者多屬本虛標實,虛者為氣血虧虛、正氣不足、下元虛損,實者為風、痰、氣、瘀留滯經絡,氣血運行不暢。故在臨床中以扶正祛邪、標本兼顧為則。孫師臨床針對此病常以肝陽上擾、痰濁阻竅、氣虛血阻及乙癸虧虛等分型為主并結合患者實際情況臨證加減論治,且尤重視活血藥的應用。其常說:“提出常用分型是為了在臨床中更高效率更精準的治療,但是切不可拘泥,中風病患者在年齡、性別、體質、飲食起居、既往病史等方面多有不同,且每個患者求診斷時所處的時期不盡相同,又或者在治療過程中癥型有變,故臨癥應在常見分型基礎上精雕細琢,加減變化,力求為每一位患者開出最精準的方藥,以求療效。”臨床常用方有天麻鉤藤飲、溫膽湯、補陽還五湯、通竅活血湯、地黃飲子等,臨證常加減或合方。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12]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偏枯。”肝陽亢盛者,以清肝息風為主,理氣通瘀為輔。治療以天麻鉤藤飲為主方,清瀉肝火,潛陽息風,再和能改善受損腦絡的活血之品,如川芎、三七、郁金、丹參、紅花、水蛭等,活血不傷正,止血不留瘀。
《中風斠詮·論昏瞀猝仆之中風》[16]云:“肥甘太過,釀痰蘊濕,積熱生風致為暴仆偏枯。”痰濕夾風,痰濕蘊熱,皆為發病病機。風痰者,化痰息風;痰熱者,清熱滌痰。再和活血之品。治療以溫膽湯為主方加減:風痰者,去竹茹,加天麻、白術、遠志,取和半夏白術天麻湯息風化痰之意,再加川芎、丹參、紅花、桃仁活血通瘀;痰熱者,加瓜蔞、膽南星增強清豁熱痰之功,也蘊通腹泄熱,使邪從下出之意,再加桃仁、紅花、川芎、丹參,活血通下。
《景岳全書·非風》[17]云:“即時人所謂中風證也……皆內傷積損頹敗而然。”虛損為本病的另一大病機:氣虛血瘀者,以補陽還五湯加黨參、水蛭,增強補氣祛瘀之力;下元虛損:雙補陰陽,化痰通絡,以地黃飲子為主方,滋補陰陽,化痰開竅,再加川芎、當歸、土鱉蟲等疏通受損腦絡。
孫師臨床常用活血藥。川芎:開郁行血,行頭目,腦梗死患者多加川芎。三七:血證良藥,止血通絡,不傷正、不留邪。郁金:通絡疏肝。丹參:破瘕止煩。紅花:量大破血,量少養血,“治口噤不語”[18]。桃仁:治血結,破蓄血,性散泄。當歸:血中氣藥,補血、行血,補中有行、行中蘊補。土鱉蟲:破瘀通絡,“善化淤血,最補損傷”[18]。水蛭:主惡血、瘀血,善治腦出血顱內水腫。
3 預 后
中風失語癥臨床治療難度較大,除針藥治療外,還需配合嚴格持續的語言訓練,更能提高療效,在常見的3種失語(運動性失語,感覺性失語,命名性失語)中,恢復難易程度為感覺性失語>運動性失語>命名性失語,即命名性失語最難恢復,通過現有臨床經驗分析:積極的治療可使感覺性和運動性失語多在發病2個月內明顯改善甚之恢復,而命名性失語的治療周期多在3個月以上,且部分患者終身不能恢復,或不能完全恢復。連續治療1個月無任何語言功能改善者,提示預后不良。
4 驗案舉隅
4.1 驗案1患者,女,64歲,2019年5月3日初診。曾因突發肢體活動不利,語言不清,被家屬送至哈爾濱某院神經內科治療14 d,出院后,癥狀未有明顯改善,為求中醫治療,故來孫師處。刻診:患者意識尚可,但不能明確自我表達,也不能進行跟讀,對檢查者所提出的問題或指示不能不能完全理解,右側上下肢,隨意運動尚可,肌力4+級;舌紅,脈弦細。結合其理化檢查,中醫診斷:中風病伴失語癥(肝腎陰虛證)。西醫診斷:腦梗死合并混合性失語。治法:滋補腎陰腎陽,化痰活血開竅。予針刺和中藥治療。取穴:病灶側運動、感覺區上1/5,病灶對側運動區上1/5,言語一、二、三區,配以(金津/玉液)、廉泉、地倉(患側)、迎香(患側)、風池(雙)、完骨(雙)、通里(雙)再和腎俞(雙)、命門、關元、氣海、太溪(雙)、三陰交(雙)。孫師針刺前先囑患者跟讀“1”“2”“3”“4”“你好”“謝謝”“再見”等簡單詞語,待針刺頭針分區,并對于主要3個語言區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捻轉5 min左右后,再次問詢,進行前后比較,該患者能較清晰地部分跟讀。孫師云:“有較大機會可愈。”其余穴位常規針刺得氣為度,后通以電針疏波30 min。電針結束后再次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再次捻轉1~2次,頭針可延長留針時間至2~3 h。方藥治療:熟地黃30 g,山萸肉20 g,肉蓯蓉10 g,枸杞子10 g,麥冬10 g,茯苓15 g,當歸15 g,桃仁15 g,紅花15 g,石斛10 g,石菖蒲10 g,遠志10 g,川芎10 g,三七粉10 g(沖服),炙甘草5 g。20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19年5月23日,上下肢肌力恢復至5級,肢體運動基本正常。語言功能較治療前有明顯改善,可清晰跟讀,能理解他人話語意思,但不能用語言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表述時以2~3個字為一組,不能連貫),也不能說出生活中常見物體的名稱。孫師囑效不更方,繼服原方10劑后停服,針刺處置同前。
3診:2019年8月1日,患者可對生活中常見物品進行命名,主觀表達也有明顯進步,但仍顯晦澀,時而忘詞,跟讀表述基本如常人。治療增加頭針言語區的捻轉頻次為4次,每次5 min,在針刺治療的初起、通電針后每間隔10 min捻轉一次。
4診:2019年10月4日,患者主動話語變多,能滿足基本生活交流,后停止治療。
2019年11月5日隨訪,患者狀態良好,家屬自覺患者語言溝通表述更流利一些。
按語:根據患者的年齡、舌脈、主訴及癥狀等,不難診斷為肝腎陰虛證,患者年高,肝腎不足,虛火夾痰上犯腦竅,痰阻絡瘀,發為本病。治療上,先以滋補肝腎為基,而后化痰活血通絡。取穴首選病損大腦功能分區體表投影區:病灶側運動、感覺區上1/5,病灶對側運動區上1/5,言語一、二、三區,所謂“穴位所在主治所及”。孫師針刺前先囑患者跟讀簡單詞語,待針刺頭針分區,并對于主要3個語言區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后,再次問詢,進行前后比較。此種方法利于臨床中快速操作,可以一定程度上對患者預后及恢復程度做出判斷。風池、完骨平肝息風,合用可改善大腦血液循環,增強神經營養代謝,促進病損腦絡恢復。金津/玉液、廉泉主治舌強不語,乃臨床治療失語常用穴。地倉、迎香治療中風患者口歪不正,利于語言表達。且陽明經乃多氣多血之經,補養氣血,適于中風患者本虛標實的病理狀態。通里為心經絡穴,且有“心經連舌本,散舌下”,主治舌強不語,即“經脈所過,主治所及”。因患者年長,素體陰虛為主,故加腎俞、命門、關元、氣海、太溪、三陰交。滋補其陰。方藥以地黃飲子為主方化裁。原方滋腎陰,補腎陽,開竅化痰。此患者陰虛明顯,無明顯陽虛表現,故去除原方溫陽之品,只取滋陰開竅之功,加入當歸、川芎、三七等活血藥,增強通絡之功。縱觀針藥處方,共奏滋陰化痰、開竅通絡之效。2診時患者肢體功能及運動、感覺性失語情況恢復較好,服中藥時間尚不長,針力、藥力尚處優勢,效不更方保證患者療效的穩定性。3診時患者已周期性規律針刺治療近3個月,患者運動、感覺性失語情況進一步改善,命名性失語情況也有明顯進步,但其自身厭棄中藥口感不愿再服,孫師考慮其發病時間已長,恐針效未有起初發病時明顯,故而增加針刺效力,增加捻轉頻次,以期提高療效。4診時患者已經規律治療近5個月,結合患者及其家屬對療效的滿意度,以及自身意愿,故而未有后續處置。綜合2診、3診、4診時患者的癥狀改善情況表明運動性失語和感覺性失語較命名性失語恢復周期短。積極連續的治療后,3種失語情況可得到不同成度的改善。
4.2 案例2患者,男,44歲,2019年5月15日初診。半月前,患者因突然摔倒,被家屬送至當地醫院,醫院以腦出血收入神經內科病房,出院后,為求中醫診治,來孫師處就診。刻診:右側上肢肌力1+級,下肢2級,不能自發言語,但能聽懂檢查者提出的指令;舌紅苔厚膩,脈弦滑數。平素脾氣暴躁,既往高血壓、高血脂、前列腺炎病史。結合其理化檢查,中醫診斷:中風病伴失語癥(痰火瘀阻證)。西醫診斷:腦出血合并運動性失語。治法:清化熱痰,息風活血。予針刺和中藥治療。取穴:病灶側運動、感覺區上1/5、病灶對側運動區上1/5、足運感(中央旁小葉區)(雙側)、言語一區,配以(金津/玉液)、廉泉、地倉(患側)、迎香(患側)、風池(雙)、完骨(雙)、通里(雙)、三陰交(雙)、豐隆(雙)、三里(雙)、陰陵泉(雙)、太沖(雙)、足臨泣(雙)。孫師針刺前先囑患者跟讀簡單詞語,患者搖頭無應答,待針刺頭針分區,并對于語言區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捻轉5 min左右后,再次問詢,患者仍不能表述。孫師云:“視其病情本輕重,其失語有較大機會恢復,但針刺即刻效應不明顯,須進一步觀察。”其余穴位常規針刺得氣為度,后通以電針疏波30 min。電針結束后再次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再次捻轉1~2次,頭針可延長留針時間至2~3 h。方藥治療:法半夏20 g,竹茹15 g,梔子15 g,陳皮15 g,天麻12 g,川芎12 g,丹參12 g,鉤藤10 g,麩炒白術10 g,茯苓10 g,石菖蒲10 g,遠志10 g,山楂10 g,葛根10 g,地龍8 g,全蝎8 g,僵蠶8 g,川芎15 g,郁金10 g,炙甘草5 g。14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19年5月30日,患者上肢肌力2級,下肢肌力2+級,仍不能主動進行語言表達。苔膩不退,口臭,便黏。原方麩炒白術改為生白術,加瓜蔞、枳實各10 g。
3診:2019年6月15日,患者晨起突然能進行清晰語言表達,便不黏,口臭明顯改善。查體:上肢肌力4級,下肢肌力3級。瓜蔞、枳實藥量減半,1周后停中藥,繼續針刺治療并囑每日針刺后,訓練患者站立。
4診:2019年7月2日,患者可在家屬適當攙扶保護下行走,上肢肌力5級,各項功能基本如常。后因家庭原因決定回當地繼續中醫治療,故治療流程至此。
2019年8月3日隨訪,患者可在拐杖輔助下行走,語言流利,精神佳。
按語:根據患者的年齡、舌脈、主訴及癥狀等,診斷為痰火瘀阻證,患者既往高血壓,高血脂,血管壁長期受到高壓刺激,彈性減弱,血液黏稠度高,故易發出血,平素脾氣暴躁,舌紅苔厚膩,脈弦滑數,肝氣夾痰火上沖腦絡,發為本病。治療上清化熱痰,息風活血。取穴首選病損大腦功能分區體表投影區:病灶側運動、感覺區上1/5、病灶對側運動區上1/5、言語一區,因患者素有前列腺炎病史,故增加足運感(中央旁小葉區)調節尿便中樞,風池、完骨平肝熄風,合用可改善大腦血液循環,增強神經營養代謝,促進病損腦絡恢復。金津/玉液、廉泉主治舌強不語,乃臨床治療失語常用穴。地倉、迎香治療中風患者口歪不正,利于語言表達。通里主治舌強不語。三陰、三里,補氣健脾,配豐隆,陰陵泉可滌化痰邪,太沖平肝降逆,足臨泣為膽經滎穴,清瀉膽火,二者合用增強清肝瀉火之力。方藥以溫膽湯主方清化痰濁熱邪,合半夏、白術、天麻,取半夏白術天麻湯的平肝息風化痰之功。半夏白術天麻湯未用全方,因姜、棗過于溫補,防助火增邪,故而不用,只取其息風化痰之力。加山楂以降血脂,郁金以疏肝氣,助血行。加葛根、地龍、全蝎、僵蠶、川芎等活血藥,增強通絡之效。縱觀針藥處方,合奏清化痰熱、息風活血之功。2診時,患者痰濁熱邪較重,腑氣不通,麩炒白術改為生白術,因生白術通力較麩炒白術強,且有調節血壓血脂的功效,瓜蔞、枳實合用,從上至下驅逐痰邪,祛痰的同時還可助降氣,使邪氣從肛門排出。3診時,患者突然能進行表達,表明失語癥的治療過程并非全是感覺、運動、命名這一線性恢復過程,且語言功能的恢復和上肢功能的恢復有一定的聯系。
4.3 案例3患者,男,47歲,2019年10月7日初診。患者發病時以“腦梗死”收入韓國首爾大學醫院,治療3周后,患者失語情況未見改善,為求中醫治療,來孫師處就診。刻診:上、下肢肌力5級,能理解語言指令,但不能用語言表述;舌質紅,脈弦數。既往高血壓病史。結合其理化檢查,中醫診斷:中風病失語癥(氣滯血瘀證)。西醫診斷:腦梗死合并運動性失語。治法:理氣通瘀。取穴首選病灶側運動、感覺區上1/5、病灶對側運動區上1/5、言語一區,配以(金津/玉液)、廉泉、地倉(患側)、迎香(患側)、風池(雙)、完骨(雙)、通里(雙)、太沖(雙)、俠溪(雙)。孫師針刺前同樣先囑患者跟讀簡單詞語,患者搖頭無應答,待針刺頭針分區,并對于語言區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捻轉5 min左右后,再次問詢,患者仍不能表述。孫師云:“難治矣。”其余穴位常規針刺得氣為度,后通以電針疏波30 min。電針結束后再次應用“經顱重復針刺激法”,再次捻轉1~2次,頭針延長留針時間至2~3 h。因家屬表示不想吃中藥,故未處以方藥。
2診:2019年11月13日,肢體活動較就診前改善,患者仍不能表述,受損語言功能未見改善。治療針刺方案同上,增加頭針言語區的捻轉頻次為4次,每次5 min,在針刺治療的初起、通電針后每間隔10 min捻轉1次。治療5 d后語言仍未有明顯改善,患者家屬主動放棄治療。
2019年12月12日隨訪,語言功能未有改善。
按語:根據患者的年齡、舌脈、主訴及癥狀等,診斷為氣滯血瘀證。患者既往高血壓,舌紅,脈弦數,為肝氣不疏,腦絡瘀阻,發為本病。治療以理氣通瘀為大法。取穴首選病損大腦功能分區體表投影區:病灶側運動、感覺區上1/5、病灶對側運動區上1/5、言語一區,調節大腦受損局部神經功能,疏通局部氣血。風池、完骨疏通肝氣,調暢氣機,理氣通瘀,增強腦部血液循環。金津/玉液、廉泉功能上可治了不語,乃臨床常用穴。地倉、迎香乃陽明經穴位,經絡五行屬土,此患肝氣瘀滯,木太過,補土以制木,防木太過。且位于口周,穴位局部主治口歪不用,從而可幫助改善語言功能。通里屬心經,心在五行屬火,火為木子,《難經》云:“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故在此,通里有瀉其子之意,子瀉則母不實,肝氣不郁,則氣不滯。俠溪素有平肝熄風之效,且為膽經滎穴,可祛肝火,平肝氣,防肝氣瘀滯化火生風。部分中風失語患者不能恢復或預后極差,即便在準確辨病辨證選穴的基礎上仍然無法達到滿意的療效,體現了本病的難治性。
中風失語癥臨床治療難度較大,治療周期、預后、療效等受個體差異及發病情況影響較大。審析案例1和2:年齡、性別、發病情況、治療周期不同,但持續堅持針刺、中藥治療,更可能獲得滿意療效;案例1和3:患者個體差異,疾病過程差異,最終治療結果也有差異,也體現了中風失語癥的不確定性、難治性;對比病例2和3:患者年齡相近、臨床舌脈表現相近,性別相同,但由于病性不同,中醫手段介入的時間不同,因而結果迥異,盡早進行針灸、中藥治療更可能獲得滿意療效。選取孫師治療中風失語癥的3個較為典型病例,意在說明中風失語癥雖是臨床工作的重點難點,但治療上仍有規律和依據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