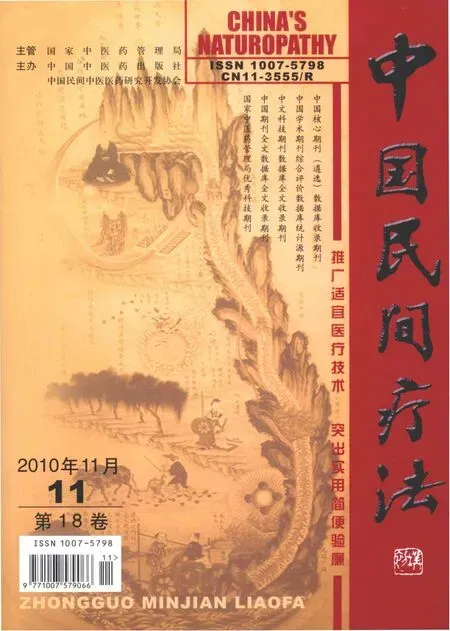中藥針劑合中成藥治療帶狀皰疹60例
李紅英
(云南省水富縣人民醫院,657800)
筆者2004~2007年對在我科就診的60例帶狀皰疹患者采用中藥針劑合中成藥治療,并與同期60例采用西藥治療的帶狀皰疹患者進行對照觀察,報道如下。
一般資料
參與對比的兩組均為門診帶狀皰疹患者(孕婦、糖尿病、對清開靈及雙黃連過敏者除外),均符合觀察的入選標準。將其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60例,男23例,女37例;平均年齡68.7歲。對照組60例,男 24例,女36例;平均年齡67.9歲。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治療方法
治療組采用氯化鈉注射液250ml加入清開靈注射液30ml,5%葡萄糖注射液500ml加入雙黃連粉針劑3.0g,滴速60滴/min,靜滴,1日1次。同時口服血府逐瘀膠囊,每次6粒,1日2次。外用六神丸以食醋調成糊狀外敷。
對照組:給予阿昔洛韋片0.2口服,1日5次,維生素B1片20mg,口服,1日3次;消炎痛片25mg,口服,1日3次。外用阿昔洛韋軟膏外擦。
治療7~10天為1個療程(60歲以上者治療10天,其余年齡患者治療7天),觀察療效。
治療結果
療效標準:治愈:皮疹消退,臨床癥狀體征消失,無疼痛后遺癥。有效:皮疹消退30%以上,疼痛明顯減輕。未愈,皮疹消退不足30%,仍有疼痛。
治療結果:治療組60例,治愈40例,有效 18例,未愈2例,總有效率 96.67%;對照組 60例,治愈30例,有效18例,未愈12例,總有效率80.00%。
討論
西醫學認為,帶狀皰疹系由水痘-帶狀皰疹病毒引起。初次感染時多為免疫力較低的兒童,表現為水痘或呈隱性感染,此后則成為帶病毒者。這種病毒具有親神經性,長期潛伏在腦神經節或脊髓后根神經節的神經元內。當機體免疫功能較低時,在感冒、外傷、月經期、過度勞累或惡性腫瘤、放療、器官移植等誘因影響下,使神經節內病毒活化,病毒的生長繁殖會使原來受侵犯的神經產生炎癥或壞死,出現疼痛。同時病毒也可沿周圍神經纖維移動到皮膚,而引起神經支配區內皮膚節段性水皰疹。治療以抗病毒、消炎、止痛為主。
帶狀皰疹屬中醫“蛇串瘡”、“纏腰火丹”、“蛇丹”、“蜘蛛瘡”等范疇。本病是感受毒邪、濕熱、風、火郁于心、肝、肺、脾,經絡阻隔,氣血凝滯而成。情志內傷,心肝氣郁化熱,熱郁久而化火,火熱溢于肌表,流竄經絡,再感風、火邪毒,使氣血郁閉,則見紅斑、丘皰疹、癢痛等癥;脾失健運而生濕,脾濕蘊結而化熱,濕熱外發肌膚,再感濕熱邪毒,使肺的宣發、肅降、治節功能紊亂,致水液循經絡閉聚于肌表,則見水皰累累如珠;濕熱風火邪毒,損傷經絡,經氣不宣,氣滯血瘀,不通則痛,常致疼痛不休或刺痛不斷。治療原則以解毒、清火、利濕、祛風、通瘀為主。清開靈注射液和雙黃連粉針劑均具有清熱解毒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血府逐瘀膠囊具有活血祛瘀、行氣止痛的功效,同時能緩解因疼痛而引起的煩躁、眠差等伴隨癥狀。六神丸中雄黃解毒殺蟲;牛黃、冰片涼血消腫;蟾酥、麝香通絡止痛;珍珠除濕收斂,調以食醋活血化瘀消腫,增強藥物的滲透作用[1]。治療組所用中藥針劑合中成藥對帶狀皰疹的病因病機有較強的針對性,與對照組相比,具有縮短病程、減輕癥狀、減少藥物副作用、加速治愈等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對初次使用清開靈注射液、雙黃連粉針劑的患者要注意觀察;其二,60歲以上的患者大多由于機體功能衰退,免疫功能低下,易患后遺神經痛,治療時應連續用藥10天,以預防后遺神經痛的發生。
[1]周世杰,呂松芬.六神丸外用治療帶狀皰疹76例.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1993,13(6):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