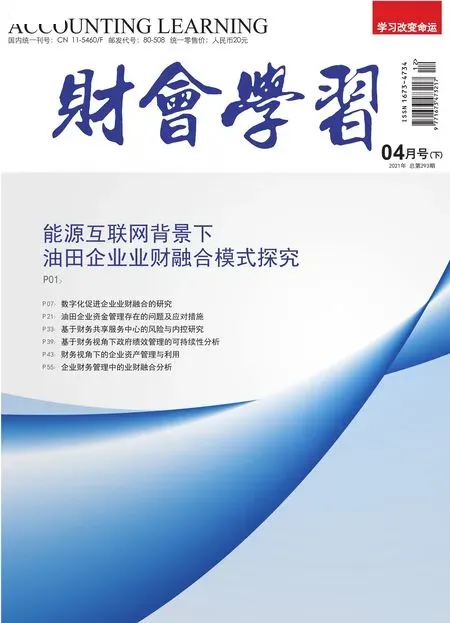戰略差異度、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風險承擔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
引言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更多公司在戰略規劃方面會更傾向于多元化,以更好地適應多變的市場環境,并提升企業集團整體的競爭力和品牌價值。彈性組織理論指出,企業只有順應多變的市場環境,不斷調整自身整合資源的能力,才能在市場中有更加穩固的地位。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企業受制于外部環境,但是企業所依賴的資源往往不能由其自己生產,而需要與其他企業進行良性互動。生存對于企業而言是第一要義,企業需要更加理性的管理組織架構,并對緊缺的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才能夠在復雜的市場環境中可持續性發展與生存(Pfeffer and Salancik,1978)。那么,公司對于多元化戰略的發展是否能夠提升自身競爭力呢?風險是發生損失的可能性,但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機遇。風險承擔反映了企業進行投融資決策時的風險偏好(Faccio et al.,2011),尤其對于投資項目而言,公司應當對所有凈現值為正的項目進行投資,以追求股東財富的最大化。然而,在兩權分離情境下,管理層為了規避風險,極有可能降低公司的風險承擔能力,而過于保守的進行投資決策,這對于公司價值是有很大損失的。已有研究結果表明,公司具備較高的企業風險承擔能力有利于追求更高的項目投資回報,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力(李文貴和余明桂,2012)。那么,執行柔性戰略的企業是否有效提高了自身的風險承擔水平呢?

目前,學術界公認股東結構會對公司的治理存在顯著而長遠的影響。機構投資者被認為是更具有專業化能力的外部監督和治理機制(蘇錦依,2019),他們憑借其廣泛的信息和資源渠道,往往會對被投資企業行為決策施加影響。但是學術界對于機構投資者所發揮的作用存在對立的觀點,部分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能夠幫助公司進行資源規劃與調整,促進公司獲取長遠的利益,但也有研究認為機構投資者更傾向于“自利主義”,追求短期利益攫取,并不會注重公司可持續發展。那么,機構投資者持股在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二者關系方面發揮何種作用呢?
本文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以2010—2018年間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以期探討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之間的關系,并且檢驗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于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戰略被認為涵蓋了組織的目標和為實現相關目標需要的資源(Chandler,1962)。戰略整合觀認為,公司之間戰略差異的實質在于管理層對于公司內部資源配置的差異。由此,學者大都采用與行業常規戰略維度水平相比之后的偏差來衡量公司層面的戰略差異度(葉康濤等,2014)。已有研究表明,某些偏離行業慣例的戰略會給企業帶來更大的邊際利益,獨特的戰略會提高競爭者的模仿壁壘,提升市場占有率。較高的戰略差異會讓企業面臨更多的創新壓力,在業績壓力驅動下,會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游達明等,2017)。風險承擔的能力和意愿決定了公司整合資源并進行有效配置的程度,較高的風險承擔水平意味著公司能夠盡可能多的開展NPV大于0的項目的投資,較低的風險承擔水平意味著公司對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的偏離。一方面,當公司戰略差異度較高時意味著公司更加傾向于多元化的投資和發展,這將提升公司對于外部環境波動的抵抗能力,預期能承擔更多的風險。另一方面,較高的戰略差異度使公司在戰略投入過程中會獲取更多的信息,減少信息偏差程度,進而提高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公司的決策實質上是受制于有限資源和信息偏差的,在有限資源情況下,如何進行股東財富最大化的投資,并且避免認知偏差和決策失誤是公司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機構投資者被認為在市場動蕩時能夠發揮“市場穩定器”的作用,并通過其自身優質的信息以及資源獲取能力給市場中上市公司注入更多的生命活力。但是,中國當前的市場發展并沒有十分成熟,部分機構投資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可能會選擇“用腳投票”,僅僅是想要短期投資增值,并不會對被投資企業進行長期的價值投資(姚頤等,2007)。已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中的機構投資者整體來看屬于“短期機會主義者”,他們在參與公司決策的過程中,會給部分風險較大但具有一定投資前景的項目投否決票,因而會抑制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抑制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二、實證設計
(一)樣本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18年度滬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全樣本范圍,并在此基礎上剔除了ST公司、當年IPO的公司、退市公司,以及剔除了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數據來源于CSMAR、RESSET和CCER數據庫,利用Stata進行變量的數據處理工作,并對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分位數的縮尾。
(二)變量含義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isk),借鑒余明桂等(2013)的衡量方法,采用公司ROA的波動程度來看衡量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具體而言,先對ROA進行標準化處理,將公司每一年的ROA減去行業平均值得到Adj_ROA,然后,計算公司當年和未來兩年Adj_ROA的標準差,即得到公司當年的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isk)。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戰略差異度(DS),借鑒葉康濤等(2014)的研究方法。首先,獲得公司在廣告和宣傳、研發和管理費用三方面的投入,以及資本密集程度、固定資產更新程度以及財務杠桿水平三方面的資本情況,共計六個維度來衡量企業的戰略差異度。其次,將六個戰略維度指標分別按行業情況進行標準化處理,并取絕對值。最后,將標準化處理以后的六個指標取平均值即得到企業的戰略差異度(DS)。
本文的調節變量采用的是RESSET數據庫中所有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shr)的加總。
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托賓Q指數(Tbq)、杠桿水平(Lev)、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管理層持股比例(Manshr)、獨董比例(Indr)、是否為兩職合一(Dual)、實際控制人性質(SOE)和被分析師關注度(Analyst)。
(三)實證模型

為驗證假設H1和H2,分別構建如上實證模型(1)和(2),預期模型(1)中系數β1顯著為正,預期模型(2)中系數β2顯著為負。
三、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表1為本文主要指標的描述性統計量結果,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isk)樣本范圍內最大值為0.1914,最小值為0.0012,平均值為0.0274,標準差為0.0323,說明個別公司之間風險承擔程度差距比較大;戰略差異度變量(DS)的最大值為1.8451,最小值為0.2023,平均值為0.6045,標準差為0.3046,說明樣本范圍內的公司存在戰略的差異性;機構投資者持股最小值為0.0002,最大值為0.8597,平均值為0.2641,標準差為0.2379,說明公司的持股結構有比較大的差異,部分公司由機構投資者控股,也有部分公司表現為機構投資者參股水平很低。

表1 主要描述性統計量
(二)主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依照實證模型對樣本進行了OLS回歸,并在公司層面進行了聚類。回歸結果列示于表2的第(1)列和第(2)列。第(1)列的數據顯示,DS的回歸系數為0.0124,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驗證了假設H1,說明了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公司的柔性戰略有利于進一步提高自身在多變環境下運作資源的能力。第(2)列的數據顯示,交乘項InstshrDS的系數為-0.0116,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發揮了抑制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之間正相關關系的調節作用。假設H2得到了驗證,說明機構投資者整體更傾向于機會主義行為,利益至上的原則會使其抑制公司多元戰略的發展,避免承擔過多風險。

表2 主回歸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結果分析
本文替換風險承擔的衡量方法,采用3年Adj_ROA的極差來衡量,再次對假設H1和H2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列示于表2的第(3)列和第(4)列。回歸結果顯示,假設H1和假設H2得到了驗證,說明本文的回歸結果穩健地支持了理論分析和假設。
結語
從外部資源有限和認知偏差的客觀事實出發,本文討論了公司戰略差異度對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影響。同時,引入了外部股東——機構投資者持股這一調節變量,檢驗了其對前述二者關系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的滬深A股數據,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公司的戰略差異度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呈正相關關系,機構投資者整體更傾向于歸類為“短期機會主義者”,其行為會阻止公司承擔較高的風險,從而發揮了抑制公司戰略差異度與風險承擔水平的調節作用。
伴隨著國際國內形式的日趨復雜,公司需要提高自身競爭力以適應市場的波動。本文的研究結果說明,企業的柔性戰略有利于提升自身的風險承擔能力,應適當鼓勵公司進行合理的多元化發展。并且,市場監管應更加注重引導機構投資者的良性發展,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對被投資企業的監督和治理機制,因此推動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