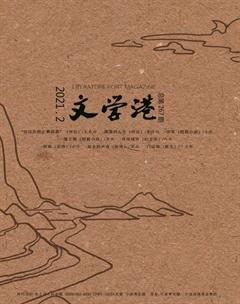“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王春林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這是現代杰出詩人卞之琳先生那一首膾炙人口的《斷章》。但正所謂“詩無達詁”,尤其是如同《斷章》這樣一首內在思想含蘊異常豐富的詩歌來說,到底要傳達給讀者什么樣的一種情感或者意思,長期以來一直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不管怎么說,在其中隱含著某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相對主義或者說互為主體的意味,乃是無可否認的一種文本事實。當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的時候,你是確證無疑的主體,然而,場景一旦轉換為“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的時候,你就在一種根本就不可能自覺的情況下,由主體轉換為客體。而那位置身于樓上的人,也就隨之成為了新的主體。依照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對后面的兩句,我們也完全可以做如是解。
筆者之所以在這里不僅要專門提及卞之琳的這首《斷章》,而且還要對它做如此一番剖析,主要是因為不期然間讀到了方曉短篇小說《雨夜》。說實在話,對于方曉其人,到底是男是女,究竟年長年幼,甚至,連同這個名字是本名抑或筆名,我自己的確一無所知。既如此,我們關于方曉其人的一切理解和判斷,所依憑的,就只能是《雨夜》這樣一個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說文本。正是在對《雨夜》先后兩次認真閱讀的過程中,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情感甚或精神方面那樣一種簡直就是撲朔迷離的迷亂狀況,促使我情不自禁地聯想到了卞之琳的這一首《斷章》。也因此,雖然對于方曉其人的情況一無所知,但根據我的閱讀感覺來推斷,首先,從性別的角度來說,因其情感描寫的細膩入微程度,我覺得這位作家十有八九應該是一位女性。其次,從年齡的角度來看,方曉不管怎么說都應該是一位年輕作家。如果我的判斷無誤,如果說方曉的確是一位年輕女作家的話,那么,我首先要大加肯定的一點,就是作家那種非同尋常的藝術控制力。情感上明明已經處于劍拔弩張的狀態,但敘述者卻依然可以那么不動聲色,那樣沉靜內斂,無論如何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盡管作品并沒有采用敘述者直接現身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但一開始就被提及的李桃卻毫無疑問可以被看作是一位身兼觀察功能的視角性人物。而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小說中的一切人和事,都是通過李桃的眼睛,在經過了她的一番其實是不自覺的過濾后,才被傳達給廣大讀者的。很多時候,甚至連同作家自己都未必都能明確意識到的一些思想,也都是通過這位視角性人物才能夠被凝固定型。也因此,對于如同李桃這樣一位視角性人物的藝術設定,作家無論如何都不能掉以輕心。具體來說,小說之所以被命名為“雨夜”,乃因為其中的核心事件,是一樁發生在雨夜里的車禍:“那天夜里,她趕到現場時,馬納趴在路邊,身體蜷曲在風衣下,仿佛正在支離破碎。密集的雨點像閃著寒光的刀尖落在他身上,每一滴雨,都戳出噴濺的血來。然后警察和救護車陸續到了。一個穿著紅色雨衣的小個子男人,一直等待在原地,現在驚魂未定地向警察講述,他看見有輛黃色面包車加速沖上坡,在轉角處精準地撞上了馬納,一個戴口罩的黑衣男人下車來翻弄著馬納,似乎要確認是否已經死亡,又駕車迅速離去。警察斷定是蓄意的,但除此之外也沒有給出更多的結論。”事實上,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說,也根本就不需要警察給出相應的更多結論。說到底,這一場車禍,也不過是小說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作家不過是要借助于這樣一場早有預謀的車禍,來講述呈現兩對青年或者說中年(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是,置身于當下時代,什么樣的年齡段算是青年,什么樣的年齡段算是中年,的確莫衷一是很難判斷)夫妻之間特別撲朔迷離的情感與精神危局。
其中的一對夫妻,就是視角性人物李桃和那位因車禍而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馬納。九年前結識并最終結合在一起的這一對夫妻,盡管婚后的數年間,曾經兩情相悅,但到最后,最起碼在李桃這里,卻根本就沒有料想到,他們之間的感情竟然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大約在兩年前,生性敏感的李桃,就已經根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蛛絲馬跡,判斷出丈夫馬納很可能在情感上出軌了。但很可能是李桃出于一種本能的逃避與延宕心理作祟的緣故,這一真相卻一直到車禍發生后才徹底曝光。這一確證和曝光,對李桃形成了極強烈的精神刺激:“另一個女人,代表的是另一種生活,她們像一根根箭簇將我和我的生活擊穿,哪怕她們消失,也留下了一個彌補不了的洞口。哪怕我的生活沒有被摧毀,也至少被背叛過。”一種實際的情形是,在已經敏感到他們的情感面臨危機之后,李桃竟然沒有采取任何應對的方式,而是“愿意繼續維持下去,是因為她連破壞的欲望都沒有。”如此一種情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李桃所持有的那種甚至連她自己都未必能自覺到的潛隱世界觀緊密相關:“她改變的努力都只停留在內心的想法里,無法形成語言也只是因為她害怕了,所有的努力,他的和她的,都不過想回到他們的最初,然后呢,又重復一次愛情終將減弱、模糊、隕落的過程嗎。”難道說所有的愛情都要經歷由最初的萌生,到后來減弱、模糊,乃至隕落的過程嗎?假若真的如此,那李桃干脆就不去努力的想法,其實也還是有一點道理的。令人不可思議的一點是,那位倍覺自己遭受傷害的周森,竟然會提出以和李桃一起出軌的方式來報復馬納和唐婉的荒唐建議。關鍵的問題是,在馬納出軌的同時,李桃自己也并沒有閑著。與此相關的兩個細節,一是李桃坐等情敵唐婉,當一位清瘦男子出現時的一種自由聯想:“她在想,他身材清瘦但結實,與他發生關系會怎樣,一開始也能相互體會到新鮮刺激吧,但又如何才能說服自己這種新鮮刺激不是廉價的呢。”一位女性,能夠在丈夫生死未卜,坐等情敵攤牌時產生這樣的一種自由聯想,所充分說明的,正是李桃個人潛意識的復雜與曖昧不明。另一個,則是那位只是偶爾被提及,一直處于“神龍見首不見尾”狀態的左原。盡管作家始終沒有做出明確的交代,但依據字里行間的一些蛛絲馬跡來判斷。這個左原,毫無疑問是李桃的地下情人。
同樣處于情感和精神危局中的另一對夫妻,是車禍的制造者周森和他那位出軌的妻子唐婉。按照周森的敘述,他們之間的情感危機似乎是一下子就出現的:“很奇怪,突然有一天,我們之間進行不下去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我和她沒法進行之后,我妻子和你丈夫,卻像干柴烈火,一天三次,有一回連續九天。”吊詭處在于,正是在發現了妻子唐婉和馬納的奸情后,周森才又重新對妻子產生了強烈的欲望。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妻子的奸情做出這樣的理解與評判:“一般他們都說愛的。為了找個延續的借口,欺騙對方,也好欺騙自己。他們找不到其他的借口了,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動物沖動罷了。”實際的情形是,正是出于被羞辱后某種不可遏制的報復沖動,周森方才一手制造了那場車禍。但對自己和馬納的出軌行為,當事人唐婉的理解,卻與周森的看法大相徑庭。唯其如此,她才會在面對李桃時特別強調,那是“一份難以抗拒的愛。是因為我,我能這么說嗎。我也是,我遇見他,也一樣。”既然彼此間有愛情,為什么不走到一起呢?對于李桃的這個問題,唐婉的回答是:“我回答過你了。他說他不想放棄婚姻。他還說,一旦出軌,就是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同樣帶有一定吊詭意味的是,在那個雨夜,馬納和唐婉在一起,原本是要討論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夠理性地分手,沒想到,就是在那個雨夜,那場為周森蓄謀已久的車禍不期而至,“他被撞了”。
請一定注意,方曉對小說中兩對夫妻之間情感迷局的設定,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當我試圖在這里概括復述這個情感迷局的時候,都會感到有言不及義的表達困難。很大程度上,無法被條分縷析地復述清楚本身,就強有力地證明著作家那樣一種層層剝繭式的情感迷局敘事的成功。那么,這兩對自以為曾經擁有過愛情的夫妻,到底為什么會喪失愛的能力呢?馬納和唐婉之間的感情,到底可不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愛情?盡管確切的答案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文本中的一個象征性細節卻不容忽視:“她起身去書架旁,抽出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如她猜測,里面是空的,只是一個徒有其表的空殼。她無聲地笑起來,心中充滿酸澀的快慰。”雖然說所謂的象征一般都是多義的,但在我的理解中,這一細節恐怕更多還是暗示著真正愛情的缺位。唯其缺位,所以才會有一種撲朔迷離情感亂象的生成。但從根本上說,因此于此種撲朔迷離情感亂象背后的,其實又是當下時代某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精神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方曉的《雨夜》就既是一篇情感敘事,同時也更是一篇精神敘事的小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