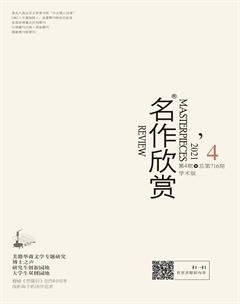淺析弗吉尼亞·伍爾夫作品中的“家中天使”意象
摘 要:弗吉尼亞·伍爾夫生活在工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婦女不被允許參加社會工作,而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庭主婦。因此,她對“家中天使”的艱難生活有著深刻的理解,伍爾夫作品中的天使形象是伍爾夫女性主義傾向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試圖以伍爾夫的《到燈塔去》和《達洛衛夫人》為例,分析伍爾夫作品中的“家中天使”的文學意象。這一意象和伍爾夫的生活經歷共同揭示了伍爾夫作品中“家中天使”的深層含義和女性主義思想。
關鍵詞:家中天使 拉姆齊夫人 《達洛衛夫人》 女性主義
一、 簡介
《到燈塔去》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部長篇小說。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變遷和動蕩給人們帶來的焦慮、恐懼和傷痛。這部小說描繪了伍爾夫自傳體的家族歷史,小說以“燈塔”為主要線索,敘述了一戰前后拉姆齊一家和幾位客人的生活經歷,拉姆齊先生的小兒子詹姆斯想去燈塔看看,但由于天氣不好沒去成,到燈塔去始終是詹姆斯的一個愿望,后來戰爭爆發,拉姆齊一家人被迫過上了悲慘的生活。戰爭結束后,拉姆齊先生親自帶著兒女駛向燈塔,最后小兒子終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燈塔。小說中心人物拉姆齊夫人代表了作者的母親,伍爾夫對拉姆齊夫人的細節描寫無處不在,展現了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見她的女權主義思想。《達洛衛夫人》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以倫敦為背景創作的,小說主要描寫了達洛維夫人和幾個女人的生活,她們早晨準備派對,晚上派對結束,客人離開。通過對這一天生活的描述,我們看到上層社會的生活雖然表面奢華舒適,但太太們的內心無比空虛。在“家中天使”的靈魂里充滿了孤獨和沉重的精神負擔。這部小說關注女性的自我認同,同樣反映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
二、“家中天使”的意象
伍爾夫生活在父權制社會,當時,婦女沒有受過教育,不能工作。她們只能待在家里,照顧家里的一切。因此,她們被稱為“家中天使”。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都是溫柔純潔的淑女形象。為了維護女性的權利,伍爾夫想通過寫作改變人們對“家中天使”的偏見。《到燈塔去》中的拉姆齊夫人完美地詮釋了“家中天使”的形象。當時男性的思想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女人只能服從男人,成為他們喜歡的純潔的“天使”。工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多數女性不參與社會工作,而是以家庭為生活中心,時刻追求成為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和敬業的家庭主婦。伍爾夫之所以會對“家中天使”的生活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是因為她本人就生活在一個被父權制籠罩的傳統家庭中。她沒有像哥哥那樣被允許上大學,而是被迫待在家里接受關于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的教育。從孩提時代起,母親就教育她,女人的自我價值是由做妻子、母親來實現的。如果說過去的“家中天使”只是扮演著家庭主婦的角色,那么維多利亞時代的“家中天使”不僅要為家庭瑣事操勞,在日常生活中還要為男人充當陪襯,用自己亮麗的外表和體面的言行來展示男人的成就,滿足男人的虛榮心。伍爾夫作品中“家中天使”最鮮明的特點是建立在有限的自我意識之上的獨立傾向。伍爾夫作品中的“天使”愿意有自己的工作,而不僅僅是一個家庭主婦;她們會對男人的言行進行評論;她們對藝術和科學感興趣,更愿意花時間學習鋼琴和數學,而不是在家侍弄花草;她們還會大膽地追求愛情。伍爾夫作品中的“家中天使”向讀者展示了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家庭女性的真實面貌。盡管伍爾夫作品中的“家中天使”只能在男人的控制下表達自己的思想,但她們也在逐漸找到自我。
三、“家中天使”的特點
(一) 順從的“家中天使”
在《到燈塔去》的開篇,為了安慰兒子和丈夫,拉姆齊太太說:“明天不會放晴。”“但也許明天會放晴,我想天氣會轉晴的。”盡管拉姆齊夫人想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她言語中的“也許”和停頓表明她缺乏自信,她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社會根本不允許她在任何人的眼中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她是“拉姆齊先生的妻子”,沒有自己的獨立身份,只能被男人認作“拉姆齊夫人”。這展現了那個時代女性身份的缺失。“作為本書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拉姆齊夫人代表了伍爾夫試圖揭露的被父權制度壓抑的女性身份,同時也是一個喪失話語權、缺乏身份認同的被壓迫的形象。”
在《達洛衛夫人》中,伍爾夫揭示了父權制社會的傳統思想對女性的束縛,女性不得不服從于男人,生活在男性的可控范圍之內。女主人公克拉麗莎·達洛衛從小就渴望自由的生活,然而,她的初戀情人彼得·沃爾什要求她必須和他分享所有事情,這讓她感到沒有自己獨立的空間,于是選擇離開他。達洛衛夫人放棄相戀的彼得, 選擇嫁給下議院議員達洛衛先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從不過問她的任何事情, 這樣, 就可以一方面把身體全部交給丈夫, 做一個稱職的“家中天使”;另一方面可以安頓自己的心, 盡量保持婚姻中的平衡感。她認為“在婚姻中, 在同一所房子里朝夕相處, 夫妻之間必須有一點自由, 有一點自主權”,但她還是像同時代眾多女性一樣,沒能逃過淪為丈夫的附屬品的命運。她婚后處處以丈夫為中心,成為家庭中的賢妻良母和社會領域的優雅淑女,逐漸失去自我。克拉麗莎五十歲時,一場大病使她感到更加空虛,她覺得自己毫無價值,她不會思考,不會寫作,甚至不會彈鋼琴。時隔多年,初戀情人彼得回來看望她,看到她現在的樣子,彼得深感遺憾,在他看來,克拉麗莎的婚姻簡直就是一場悲劇,因為她在婚姻中失去了自我,一切都要以她丈夫的意愿行事。法國女權主義思想家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指出,“她”是附屬的人,是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
(二)無私的“家中天使”
拉姆齊太太的優雅、熱情和體貼使每一位客人都感到滿意。“她挎著提包,拿著鉛筆和筆記本去親自訪問這個寡婦或那個為生活掙扎的妻子,記下工資和支出、就業和失業。”她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照顧好身邊的每一個人。當她進城時,她會問鄰居:“你需要什么嗎?郵票,信紙還是煙草?”拉姆齊先生是一位頗有威望的哲學家,然而迫于社會的壓力,他總是擔心自己會失敗,所以他總是熱衷于向太太尋求安慰,拉姆齊太太面對丈夫時總是那么溫柔,她安慰的話語會讓丈夫重拾自信;她的理解會讓丈夫的虛榮心一次又一次得到滿足。拉姆齊夫人是一位擁有自我追求與夢想的婦女,但由于她身處當時的社會背景中,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們能夠從她的家庭地位著手進行探討,拉姆齊夫人屬于整部小說中的關鍵性人物之一,是主線故事的引領角色,雖然她個人能力極強,然而在接受婚姻關系之后,她必須要將自己的能力都收起來,扮演一個合格的家庭主婦。
達洛衛太太是一位中產階級婦女,她年輕時有夢想和追求。然而,維多利亞時代對女性的要求使她放棄了深愛的彼得,嫁給了有著較高社會地位的理查德·達洛維。薩利·塞頓是克拉麗莎最好的朋友,她是個叛逆的女孩,敢于沖破塵世,有獨立的思想。她和克拉麗莎一起研究柏拉圖的著作和雪萊的詩。薩利認為女人應該有自己的價值和思想,但當她嫁給紡織廠老板成為羅塞特太太后,她也漸漸失去了自我,也成了“家中天使”的一員。小說的結尾,薩利變成了一位上流社會的太太,有五個孩子,她把所有的愛和熱情都奉獻給了園藝事業。因此,那些比達洛衛夫人思想更獨立的婦女也沒有逃過成為男人的附屬品的命運。由此可見,在男權社會中, 原本具有叛逆的個性與美好追求的克拉麗莎與薩利, 通過婚姻擠進上流社會后,并沒有實現自我,而是整天忙于養育孩子,以及一些家庭瑣事中,在這種生活狀態下她們逐漸麻木以致失去自我。 她們由于在社會中沒有地位,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發揮作用,她們的智慧與才能受到壓制無法在社會中表現自己, 發揮作用。 伍爾夫把自己在男權社會中受到的壓制與不公平待遇投射到她所塑造的克拉麗莎身上,通過克拉麗莎的遭遇來表達自己在男權社會中的失落之感,以及探索女性人生價值缺失的社會根源。
四、結語
“家中天使”這一形象是伍爾夫作品里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形象,在當時,女性生命的全部就是服務于男性,服務于家庭,學著如何成為一個好妻子,一個好母親,一個好女兒,似乎女人生來就不應該有自己的思想。伍爾夫用一句話概括了“家中天使”的特點:“她們從來沒有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她們總是更愿意同意別人的意見和愿望。” 這些特點在《到燈塔去》和《達洛衛夫人》中都有明顯的體現。通過對這兩部作品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女性要想從傳統的形象轉變成有自己思想的新女性還需要很長時間。女權主義作家伍爾夫通過塑造“家中天使”這一類型的女性形象揭示出女性思想和其社會地位的改變還需要不斷探索。
參考文獻:
[1] 柯珂.從女性主義角度重讀《到燈塔去》[J].英語廣場,2017(8):12-13.
[2] 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衛夫人[M].孫梁, 蘇美, 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3] 趙冬梅.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達洛維夫人》中的女性形象[J].外語學刊,2014(2) .
[4] 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M].王家湘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182.
[5] 山立.從女性主義角度賞析伍爾夫《到燈塔去》[J].喜劇世界(下半月),2020(6):35-36.
[6] 張嫣然.論伍爾夫的精神遭遇對其創作的影響——以小說《達洛衛夫人》為例[J].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15(4):108-112.
作 者: 陳洋,吉林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編 輯: 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