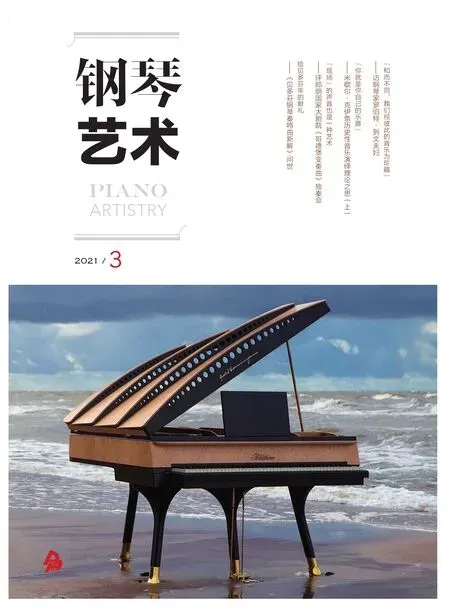暫 別
——紀念恩師卡麗娜·波波娃
文/ 劉云天

北京的夜空,悠悠地飄起了雪花。一片孤獨的雪花落在擋風玻璃上,我還沒來得及細看,它便已化成了水痕,被昏黃的路燈刷得無影無蹤。熟悉的情境從腦海深處浮現:十三年前敖德薩的夜晚,我清楚地記得是五月的第一天,在去長途汽車站的路上,天空居然下雪了。夜色中的蘇式拉達小轎車里,烏克蘭大叔一手夾著煙一手握著方向盤,帶著我穿行在冷清的街道上。匆忙的比賽安排,讓我在這座深沉而有韻味的城市只停留了短短一天,這也是我在烏克蘭的最后一天。這一天所有的經歷都是神奇而美好的,熱情的人們、黑海邊的燒烤、老式有軌電車、氣派的“波將金”石階、低調的音樂學院,這一切還不足以形容這座城市的浪漫。普希金、鐵木辛哥、奧伊斯特拉赫、吉列爾斯、里赫特這些偉大的名字與這座城市的歷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我堅持在最后的烏克蘭行程中,從基輔來回坐兩次通宵長途汽車,懷著崇敬的感情來到這里,原因很簡單,這里是我敬愛的老師卡麗娜·波波娃的故鄉,是她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地方。
波波娃老師曾于1994年跟隨丈夫亞歷山大·布加耶夫斯基(Alexander Bugaevsky)來到廣州,任教于星海音樂學院,直至1997年回國。2001年,布加耶夫斯基先生積勞成疾,倒在了比賽的評委席上。收拾了悲痛的心緒,波波娃老師在2003年決定重返她心愛的中國,繼續在廣州的教學事業。那時的我,還只是一名星海音樂學院附中高二的學生。當我聽說波波娃老師要再次來星海任教的時候,心中充滿了期待。初次與老師見面是在選拔學生的考試現場,可能因為過于緊張,我對當時的場景已有些淡忘,依稀只記得她嘴角帶著微笑,用一種嚴厲而神秘的眼神看著我。師徒之緣就在這樣一種神奇的狀態下開始了。
不得不說,波波娃老師對我們這一批新學生是極其嚴厲的。通過簡單的俄語、英語甚至中文的溝通,我們都能感受到她的熱切期待與嚴格要求。在課上,我們很少被要求去想象一些虛無抽象的概念,而是最直接地通過示范聽到并感受到她對于聲音與音樂的想法。通過自己頭腦中這些想法的積累,讓我們衍生出自己的特性。我大概是讓她最不省心的學生,在學校貪玩出了名的我,落下技術不穩定、讀譜不嚴謹的壞毛病。最初的一個學期,被吼上兩個小時對我已是家常便飯。工字樓323琴房旁邊的樓道不再是學生們偷偷抽煙、談戀愛的“好”地方,因為總有一串串憤怒的俄語單詞從天而降,破壞氣氛。有幾次晚上加課,波波娃老師發現我的情緒開始沮喪,便有些不好意思地要我關上琴蓋,招呼我到她家,塞給我一顆巧克力。也是從那之后,一直標榜“靠感覺走天下”的我,開始好好讀譜、練技術了。
也許是以前技術上的缺失太大,而我又著急將它填平,不顧疲勞的高強度練習讓我的手終于堅持不住了。2004年“金鐘獎”比賽前的一天,我右手的四指忽然失去了控制,波波娃老師也很著急,但是大賽在即,也沒有更好的方法,只能祈禱。后來別的老師告訴我,波波娃老師在賽場觀眾席中聽我演奏,緊張得嘴唇緊閉,雙手緊緊捏住提包,結束后才放松下來,滿頭是汗。只有我知道,她是擔心我的手多于比賽的成績。第二輪結束后,我回到學校,還來不及換下西褲和皮鞋就跑去打籃球,被波波娃老師在球場上狠狠訓斥了一通。這一回她是真的生氣了,以至于我第二天專門去道歉,并保證以后一定不穿西褲皮鞋打籃球了。



附中的生活是短暫而平靜的。沒有太多猶豫,我留在了星海音樂學院繼續我的本科學習。手的傷勢愈發嚴重,我的母親帶我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診所、醫院,甚至拜訪了赤腳醫生尋求奇方秘藥,仍得不到好轉。我的心態開始變得焦躁,雖然每周依然回到附中跟波波娃老師上課,但我已經明顯處在自暴自棄的邊緣。我開始抵觸波波娃老師的話,甚至會跟她爭論,有時還會編造一些理由蹺課。有幾次,我在課上完成了災難性的演奏后,我們一言不發,許久,她會帶著發紅的眼圈輕聲安慰我說:“你彈得很好,那是心理作用。”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確實把心中的壓抑全發泄在了老師身上,她無能為力,卻默默地承受了這些委屈。大學三年級時,我賭氣般挑選了拉威爾《夜之幽靈》這樣壓力極大的作品。波波娃老師見我根本聽不進她的意見,便帶我來到家中,拿出一張師兄黃業崴演奏的《夜之幽靈》比賽實況錄像說:“你要彈,起碼不能比這個差太多。”看完錄像的我沉默了,深知自己的差距,一種懊惱的情緒涌上心頭。見我眉頭緊鎖,波波娃老師塞給我兩大盒巧克力,在烏克蘭人心中,沒有什么事是一顆巧克力解決不了的,她還讓我拿走了視線內的所有水果。自此之后,我慢慢調整了心態,在波波娃老師的開導下改變了演奏的狀態,傷病的影響逐漸減少。



本科學習結束前,我必須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波波娃老師的耐心開導下,我在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與美國帕克大學中選擇了后者,跟隨著名鋼琴家斯坦尼斯拉夫·尤丹尼奇(Stanislav Ioudenitch)先生繼續學習鋼琴表演。說起來也挺有緣分,波波娃老師的老師伊戈爾·蘇克瑪尼諾夫(I g o r Sukhomlinov)是涅高茲的高徒,而尤丹尼奇先生的老師德米特里·巴什基洛夫(Dmitri Bashkirov)則出自著名的戈登威澤爾的教研室。兩位老師都是根正苗紅的俄羅斯學派繼承者,雖然當時他們互不相識。波波娃老師給我列舉了繼續彈琴的好處,比如“不用學數學”“不用通宵上班”等,還幽默地說“你與新老師長得挺像的”。分別的時刻總會來到。臨行前,我到波波娃老師家坐了一個下午,用奇怪的語言與手勢的組合,聊著我們自己才能明白的事。離后面學生的上課時間越來越近,我陪著她慢慢走到琴房。在琴房門口,我們四目凝視了幾分鐘,想著誰能說點兒什么,然而淚水搶先涌了出來。我就這么抱著老師哭了好幾分鐘,直到樓下傳來學生的腳步聲。她也趕緊抹了一下眼淚,勉強笑著嘟囔了幾個我沒聽懂的單詞,我們就這樣告別了。
結束了美國的學習生活,我回到了星海音樂學院任教。以前與現在的學生們定期為老師舉辦生日聚會,也在節假日組織一些聚餐活動。平時幾乎不沾酒的老師,這個時候也會開心地舉杯暢飲,感受難得的輕松愜意。生活中的波波娃老師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節奏,教室與住所兩點一線,除了偶爾出現在音樂會觀眾席,她很少參加其他社會活動。年齡的印記越來越明顯,除了日漸花白的頭發,波波娃老師患上風濕的雙腿讓她步履艱難。有時候在樓下碰到她緩慢地爬著樓梯,我想幫她拎一下提包,她總是擺擺手示意不用。更多的時候她會發信息招呼我下來吃東西聊聊天,她不太習慣飯堂的口味,課多的時候面包抹點果醬就對付了一餐。大家都擔心她的飲食習慣對健康的影響,比如愛吃甜食,不吃青菜。每當這個時候她就笑著一擺手,轉頭又給自己的茶里放一大勺糖。
2019年底,波波娃老師如往常一樣回烏克蘭了。臨走前她跟我們開玩笑,說回去可能不會回來了,我們笑著沒當回事。每一年她回國都會跟我們說一遍同樣的話,我們也理解,雖說中國已然是她第二故鄉,但落葉歸根的想法隨著她年齡的增長也愈發強烈。她舍不得在中國生活的女兒卡佳,更舍不得早已被她當作兒女的學生們。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讓所有人的生活受到了極大影響。波波娃老師不得不取消了年后回中國的計劃,開始了漫長的等待,期間她最關心的還是留在廣州的學生們。在疫情得到緩解后,她就立刻要我們這些師兄師姐為附中的學生們授課。當時,國外的疫情開始不斷惡化,直到我們忽然得知老師感染“新冠”的消息,緊接著就是老師突然離世的噩耗。半夜醒來的我得知這條消息,便再也無法入睡。強忍著悲痛上完一天的課,再次躺在床上的我,看著一張灑滿陽光的323教室照片,才忽然意識到,這間教室里不再會有老師的背影、熟悉的琴聲與嚴厲的吼聲了。我控制不住溢滿眼眶的淚水,不愿接受這個現實。努力在腦海中回憶老師的形象,試圖把逐漸虛化的身影搶回來,但這一切都已無濟于事了。
我體會過生死相隔的感覺,我將之理解為暫時的離去,只不過每個人乘坐的列車班次不同而已。我寧愿相信從人世間逝去的親人朋友們只是在另一個地方繼續著她們日常的生活,她們經常回到我的夢中,讓我分不清哪一邊才是真實的世界。生活恢復了平靜,老師可能有點兒急事先走開了一陣,等疫情好轉了,說不定老師就回來了,還要趕上明年的生日聚餐呢,一定是這樣的,對吧?
(2020年12月12日夜,書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