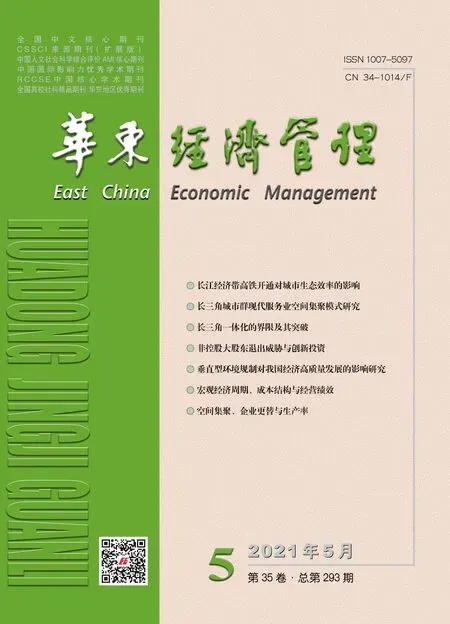垂直型環境規制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2021-05-11 05:03:40原偉鵬
華東經濟管理
2021年5期
原偉鵬,孫 慧,閆 敏,2
(1.新疆大學a.新疆創新管理研究中心;b.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830046;2.伊犁師范大學 生物與地理科學學院,新疆 伊犁836000)
一、引 言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推動“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如期實現我國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長期目標,實現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國夢”,中央政府必須制定行之有效的差異化環境規制政策。目前大多學者將全要素生產率或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質量的代理變量[1],圍繞不同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異質性展開討論[2],但鮮有基于我國中央政府直接發起并監控執行的垂直型環境規制為切入點,展開垂直型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作用機制的探討。
回顧以往研究,國內外關于環境規制的研究由來已久,但關于指標測定評價的研究方興未艾。國內學者陳剛和魯籬(1993)提出環境污染法律規制的對比研究,標志著環境規制工具研究的開始,環境規制具體測度方法有指數合成法和單一指數法[3]。單一環境規制指標主要以法律法規、環境政策條例、管理體系標準、環境稅收、環境治理投資、單位產出排污比、三廢排放量、政府補貼、公眾環境信訪數等作為替代變量[4];綜合型指標主要運用投入產出法、DEA 模型以區域減排績效、三廢治理等綜合指數作為復合衡量指標[5]。從環境規制工具分類上,按照設計范圍分為廣義與狹義環境規制[6];……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當代陜西(2022年5期)2022-04-19 12:10:12
中老年保健(2021年12期)2021-08-24 03:30:40
中國傳媒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年1期)2021-06-09 08:43:00
當代陜西(2021年1期)2021-02-01 07:18:02
當代陜西(2020年20期)2020-11-27 01:43:10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6期)2020-02-01 06:28:50
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年3期)2019-05-28 23:47:21
中國生殖健康(2019年11期)2019-01-07 01:28:02
中國科技博覽(2016年2期)2016-04-25 20:32:39
小學生導刊(2016年34期)2016-04-11 00:4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