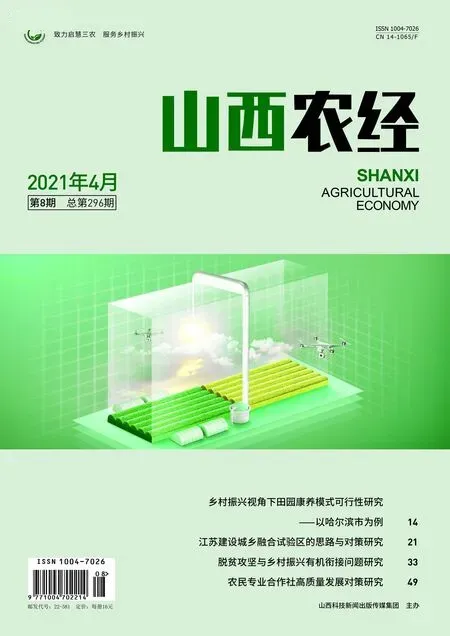土地流轉政策執行中的農戶間耕地流轉問題研究
——以山西省Y縣為例
□李 帥
(晉中信息學院 山西 晉中 030800)
隨著農村勞動力就業形式和渠道的多元化發展,以及耕地對于農村勞動力吸引力降低,部分農村出現勞動力過度轉移的情況,出現“人去地留”和無人耕種的問題[1-3]。耕地保護及利用事關國家糧食安全。為了提高耕地有效利用率,國家出臺土地流轉政策,促進勞動力和耕地重新匹配。土地流轉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不利于政策目標的實現。其中,地處非糧食主產區且耕地資源較差的山區“農戶—農戶”型土地流轉問題較為明顯。山西省Y 縣地處山區,其農戶間耕地流轉問題會對當地執行土地流轉政策產生不利影響。
1 Y 縣耕地流轉供需模式概況
山西省Y 縣位于山西省中部、太行山西麓,縣域面積1 699 km2,屬于黃土丘陵山區,其耕地總面積2.25 萬hm2。《山西統計年鑒2020》顯示,Y 縣2019 年主要糧食作物播種面積1.36 萬hm2,占縣域總面積比重約8%,占全縣耕地總面積比重為60.44%。受地形等自然條件的影響,Y 縣可耕地資源較少,導致作物播種面積和產量都較小。
由于耕地資源自身狀況的限制以及農戶自身耕種能力有限,農戶間耕地流轉呈現出零散、非規模性的特點。從農戶用地意愿和能力兩個維度,對Y 縣農戶間耕地流轉模式進行分析,可以得到耕地流轉類型,如表1 所示。
Ⅰ型農戶會主動尋求耕地來耕種,且耕地成為其經濟和食物的來源,因而土地生產和照料投入較多,耕地利用率較高。Ⅱ型農戶擁有其他經濟來源,且其他經濟來源高于靠耕地取得的收入,因而對耕地的依存減少,成為流轉耕地的來源。Ⅲ型農戶一般是年老體弱或者失能的農民,因為受勞動能力的限制而不得不放棄耕種土地,成為流轉耕地的來源。Ⅳ型為整村搬遷之后復墾的耕地,由于搬遷之后居住地距離舊村較遠,且原有生產生活設施已經無法繼續使用,個人耕種成本較高,因而成為規模性流轉耕地的來源。

表1 農戶用地意愿和能力影響下的耕地流轉類型
2 Y 縣農戶間耕地流轉存在的問題
耕地保護的最終目的在于維護糧食安全,而耕地數量不減、用地類型不變的要求只是剛性約束條件。在保護耕地時,必須注重耕地高效利用問題。如果耕地無效或低效使用,也會造成實質性的糧食生產減少,造成耕地實際生產力降低。為此,國家適時出臺土地流轉政策,旨在通過對勞動力和耕地重新匹配,讓耕地得到高效利用。就Y 縣來說,農戶間耕地流轉主要還是用于糧食作物種植,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
2.1 信息不對稱導致耕地流轉低效
耕地流轉的供需雙方缺少信息資源和交流平臺。涉及規模性土地流轉時,政府部門會發布相關信息。農戶間耕地流轉較為零散,規模小,相關政府部門不會針對此類情況進行信息搜集和發布。考慮到耕種成本問題,農戶流轉耕地一般遵循就近原則,優先考慮本村耕地。
對于耕地資源有限的村,需要到其他村尋找可耕種土地。由于對其他村可流轉耕地信息掌握較少,村民一般需要通過親戚、朋友等熟人關系尋找可流轉耕地的信息。對于有耕地需要流轉但缺乏信息交流渠道的農戶來說,這可能導致在耕種季節到來時仍未找到可以流轉的對象。同時,一些土地承包者認為種植收入低,造成土地撂荒等問題。耕地流轉雙方信息不對稱,將降低耕地利用率,不利于糧食生產。
2.2 管理粗放導致政策引導力降低
基層管理方式粗放將會導致國家政策導向作用減弱。Y 縣在對農戶間耕地流轉管理方面存在以下兩個問題。一方面,對耕地增量的把握不準確。國家耕地普查和管理主要針對已有土地進行,側重于對存量耕地的管理。一些村民在集體土地上開墾種植,這些增量耕地并未納入精細化管理范圍。一些農戶將這些耕地進行“農戶—農戶”流轉,不利于后續依法依規管理。另一方面,影響國家對糧食作物類型的調控。為了調控糧食作物類型、提高種糧農民的積極性,國家對糧食進行分類補貼,但補貼依據是農戶自己上報的作物類型,而不是根據實際收獲的作物。當耕種者變化時,土地承包者對流轉出去的土地種植什么類型的作物并無硬性要求,通常由新的耕種者決定,導致政策引導種植的作物與實際種植的作物不一致,減弱了國家政策的引導作用。
2.3 剛性約束不足導致利益難協調
農戶間耕地流轉大多建立在口頭協議的基礎上,對流轉雙方相關權益和利益劃分并不十分清晰。由于耕地流轉通常在鄰里或熟人之間進行,采用書面約定的極少,而口頭約定簡略而缺乏細節,在問題和矛盾出現后缺乏依據,不利于耕地流轉的持續、健康發展。流轉雙方因耕地租金產生矛盾,影響雙方對土地流轉的滿意度,甚至會影響鄰里關系。此外,對耕地受災的補償也是容易引起矛盾的因素。對耕地的災情評估和補償在原承包者名義下進行,但實際耕種者認為自己投入受損,易引起矛盾。
3 解決農戶間耕地流轉問題的對策
3.1 搭建信息交流平臺
一方面,當地政府應構建耕地流轉信息共享平臺。盡管農戶間耕地流轉較為零散且不具有規模性,但隨著農戶數量增加,需要流轉的耕地數量也會有所上升。當地政府應當借助已有的信息發布和交流平臺,對相關供需信息加以公布,加強對耕地流轉雙方信息的審核,進而促進耕地流轉。
另一方面,借助社會力量進行信息交流。農村地區鄉土性仍然較強,應利用網絡通信技術和志愿者的力量,搭建“鄉土性+志愿性+網絡化”的信息發布、驗證、交流平臺,發揮信息傳播中社會力量的作用,促進耕地流轉供需信息的高效匹配。在耕地流轉信息真實性驗證方面,需要加強社會力量監督,確保相關信息真實、有效。
3.2 構建精準管理模式
加強對農戶自己開墾土地的管理。農民在集體土地上開墾的耕地不屬于農戶承包地,但只要其不違背現有法規政策、不影響農村集體和其他村民的生產生活,對其開墾耕地的使用一般采取默許的方法,因而農戶可獲得該土地的使用權。此類耕地作為增量耕地部分,應該加強對地塊的登記和管理。否則,遇到征用、集體占用等其他使用情況時,此類耕地相關損失難以得到補償。當地村委會應該明示土地性質,避免此類耕地被農戶輸出流轉。
加強結果控制,強化政策的導向作用。轉變根據農戶自己填報作物類型給予種糧補貼的做法,改為種前公示國家種糧補貼價格,由農戶自己決定作物種植類型,最終根據實際收獲作物進行實際補貼。在耕地流轉后,承包者與實際租種者要加強溝通,明確作物種植的種類,從而強化政策調控的作用。
3.3 加強利益分配協調
發揮駐村工作隊的引導作用,對耕地流轉雙方行為加以規范。為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情況的出現,原駐村工作隊仍將繼續在農村開展工作。駐村工作隊作為代表公共部門的力量,嵌入實行村民自治的農村社會中,對農村社會管理及農村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在群眾中的威信較高。發揮駐村工作隊的引導作用,可以幫助愿意開展耕地流轉的農戶雙方理順利益分配關系,并且能為其他農戶耕地流轉行為起到示范作用。
發揮公序良俗的作用,倡導社會新風氣,化解矛盾。應注重鄰里情感,珍惜守望相助的情分。對于一些小的利益矛盾,可以在鄉土性較強的熟人社會中化解。流轉雙方應該進行利益互償,增強耕地流轉的可持續性。
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大。山區農業基礎設施較落后,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差。如果完全按照市場化方式開展交易,可能導致利益糾紛增多,不但難以持續維持耕地流轉,還會誘發農村地區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因此,應探索構建新型交易補償模式。
4 結束語
鄉村經濟發展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性動力。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和執行土地流轉政策的過程中,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規范農戶間零散耕地流轉行為,提升其獲得感,實現耕地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