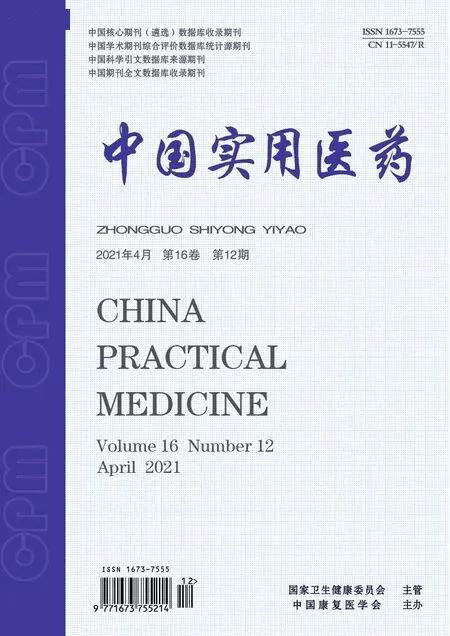內軸型膝關節(jié)假體在全膝關節(jié)置換術近中期的效果分析
周輝 常海峰 李新衡 赫明堂
目前TKA 廣泛用于治療中重度膝骨性關節(jié)炎,已成為過去幾十年最成功的骨科手術之一[1]。但術后患者多存在疼痛、關節(jié)異響、關節(jié)不穩(wěn)等并發(fā)癥,在多種影響TKA 術后患者滿意率的因素中,假體設計與手術技術最為重要,其中膝關節(jié)置換術假體不符合自然膝關節(jié)的生理運動是TKA 術后滿意率相對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2]。根據假體設計中提供機械限制程度可分為非限制性假體、部分限制性假體、限制性假體和全限制性假體(鉸鏈式假體),其中目前常用的假體為非限制性保留后交叉韌帶假體(CR 假體)、后穩(wěn)定型(posterior stabilized,PS)膝關節(jié)假體,不論CR 假體或PS 假體都不能完全重建正常膝關節(jié)的力學關系,從而影響TKA 后臨床效果和患者滿意度。內軸型(medial pivot,MP)膝關節(jié)假體則能夠重建正常膝關節(jié)的力學特點,使膝關節(jié)運動更符合自然解剖形態(tài)軌跡,其具有高穩(wěn)定性、高活動度的特點,解決了穩(wěn)定性和活動度的矛盾[3]。盡管MP 膝關節(jié)假體的設計有力學上的改進,但以往對MP 膝關節(jié)假體在TKA 術后臨床效果研究較少,隨著手術技術不斷提高,選擇符合正常膝關節(jié)生物力學假體的爭論一直存在[4]。為此,本研究回顧分析了MP膝關節(jié)假體和PS 膝關節(jié)假體兩種假體置換術后患者的臨床資料,以期對臨床膝關節(jié)假體的選擇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6 年1 月~2019 年1 月于本院關節(jié)外科接受TKA 患者176 例的一般資料,隨機分為MP 組(87 例)、PS 組(89 例)。MP 組中位年齡69 歲;男26 例,女61 例;平均體質量指數(BMI)(24.5±2.7)kg/m2。PS 組中位年齡67 歲;男24 例,女65 例;平均BMI(24.7±2.4)kg/m2。兩組患者年齡、性別、BMI 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①2016 年1 月~2019 年1 月因膝骨性關節(jié)炎于本院關節(jié)外科接受TKA 患者,且為同一組醫(yī)師完成;②BMI≤35 kg/m2;③Kellgren-Lawrence分級,OA 嚴重程度達Ⅲ級或Ⅳ級者;④初次接受人工膝關節(jié)置換手術者;⑤內翻畸形<20°、外翻畸形<10°;⑥無髕骨低位;⑦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方法
1.3.1 手術方法 MP 組使用MP 膝關節(jié)假體,PS 組使用PS 膝關節(jié)假體。主刀為同一位高年資醫(yī)師,兩組采用同樣的手術方法和術后康復計劃。均采用膝前正中切口,內側髕旁入路,切開關節(jié)囊后清除部分骨贅和滑膜組織,清理關節(jié)腔游離體,切除內外側半月板和前交叉韌帶。股骨髓內定位、脛骨髓外定位,行股骨力線軸外翻5°截骨,脛骨平臺后傾角為3~7°,截骨厚度約8~10 mm。平行于股骨遠端內外上髁,行遠端髁外旋截骨,外旋3°,選擇合適的股骨假體型號。切除后交叉韌帶,清除后髁的骨贅和游離體,修整髕骨并予以去極化處理,測試屈伸間隙平衡,根據軟組織情況適當予以松解,用脈沖槍徹底沖洗關節(jié)腔及截骨面,骨水泥固定假體各組件,兩組安裝不同的脛骨墊片。膝關節(jié)腔周圍關節(jié)囊注射“雞尾酒”,膝關節(jié)外側放置引流管1 根,逐層縫合傷口,氨甲環(huán)酸 1 g 關節(jié)腔灌注。
1.3.2 圍手術期管理 術前30 min 至術后 72 h 內給予靜脈滴注抗生素預防感染;術后 8 h 后開始口服利伐沙班預防靜脈血栓形成,劑量5 mg/次,1 次/d 直至術后3 周。患者麻醉藥效結束后立即進行相應功能鍛煉,主要包括踝泵和股四頭肌肌力練習;術后第2 天給予拔除引流管,開始借助步行器行部分負重行走、練習膝關節(jié)主動屈伸,并進一步加強踝泵及股四頭肌肌力鍛煉;術后第3 天加強練習膝關節(jié)主動屈伸,并逐漸延長行走距離;術后 7~14 d 出院,并繼續(xù)在康復師指導下鍛煉。
1.4 觀察指標及判定指標 對兩組患者進行為期24 個月的隨訪,記錄并分析以下指標:①KSS 評分,評分越低患者膝關節(jié)功能越差;②FJS,FJS 較高意味著關節(jié)置換術后患者在日常活動中高程度的“忘記”人工關節(jié);③膝關節(jié)活動度,采用關節(jié)角度測量儀測定最大屈曲度及關節(jié)活動度;④并發(fā)癥發(fā)生情況,包括傷口感染、深靜脈血栓形成、肺部感染、膝關節(jié)周圍感染等;⑤影像學觀察,攝膝關節(jié)正側位及髕股關節(jié)軸位X 線片,評估關節(jié)力線、髕骨高度,了解假體與骨邊緣是否有透亮區(qū)。
1.5 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21.0 統(tǒng)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手術前后KSS 評分比較 兩組術后3、6、12、24 個月KSS 評分均高于本組治療前,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兩組間術前及術后3、6、12、24 個月KS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手術前后KSS 評分比較(,分)

表1 兩組手術前后KSS 評分比較(,分)
注:與本組術前比較,aP<0.05
2.2 兩組FJS 及膝關節(jié)活動度比較 MP 組FJS 及膝關節(jié)活動度分別為(88.7±4.3)、(107.5±4.17)°,與PS組的(87.9±5.6)、(109.0±5.88)°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t=1.061、1.948,P>0.05)。
2.3 兩組并發(fā)癥發(fā)生情況 MP 組共5 例患者發(fā)生并發(fā)癥,其中2 例術后10 d 出現(xiàn)傷口淺部感染,清創(chuàng)、抗感染治療6 周后痊愈;2 例早期出現(xiàn)腓靜脈血栓形成,溶栓后痊愈;1 例術后5 d 肺部感染,治療2 周后痊愈。PS 組共6 例患者發(fā)生并發(fā)癥,其中3 例早期出現(xiàn)深靜脈血栓形成(2 例腓靜脈、1 例脛后靜脈),溶栓后痊愈;2 例術后12 d 出現(xiàn)傷口淺部感染,清創(chuàng)、抗感染治療6 周后痊愈;1 例術后3 周膝關節(jié)周圍輕度感染,經靜脈抗生素治療2 周,口服頭孢呋辛酯、利福平及氧氟沙星治療3 周后癥狀消失。
2.4 兩組影像學觀察 兩組均未出現(xiàn)進展性的透亮帶或≥2 mm 的明顯透亮帶。
3 討論
MP 膝關節(jié)假體作為一種新興假體,有多個國外相關學者做了術后的中遠期隨訪研究,但對于亞洲人群研究尚未有報道[5-7]。MP 膝關節(jié)假體設計利用仿照人體伸直時膝關節(jié)自然有輕微的外旋,以保證站立位時穩(wěn)定性的鎖扣機制 (screw-home mechanism);假體設計通過球窩關節(jié)面實現(xiàn)穩(wěn)定,鎖扣機制所需要的旋轉度為 7~8°,設計中采用 15°滑軌,是為了滿足假體對骨的覆蓋,而且能獲得鎖扣機制所需要的 7~8°內外旋。屈曲時內旋,形成后滾,防止股骨髁和脛骨的撞擊,所以內軸膝在獲得了自然關節(jié)的穩(wěn)定性的條件下又不犧牲活動度。即仿照股骨正常矢狀面曲率設計假體,屈伸過程保持單一曲率半徑,即單屈曲半徑設計,從而重建符合力學的一個解剖學幾何結構[8]。MP 膝關節(jié)假體系統(tǒng)由于避免了凸輪和立柱的撞擊,從而延長了假體壽命[9]。另外,MP 膝關節(jié)假體系統(tǒng)取消了股骨髁的凸輪,減少股骨髁間截骨,保留了更多的骨量,為可能存在的翻修留有余地。大量的膝關節(jié)翻修資料證實,脛骨假體的位置改變如松動移位等仍是導致膝關節(jié)假體翻修的主要原因[10]。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術后3、6、12、24 個月KSS 評分均高于本組治療前,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兩組間術前及術后3、6、12、24 個月K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MP 組FJS 及膝關節(jié)活動度與PS 組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MP 組共5 例患者發(fā)生并發(fā)癥,PS 組共6 例患者發(fā)生并發(fā)癥,兩組經針對治療后并發(fā)癥均痊愈。兩組均未出現(xiàn)進展性的透亮帶或≥2 mm 的明顯透亮帶。
綜上所述,MP 膝關節(jié)假體與PS 膝關節(jié)假體近中期總體療效相當,但MP 膝關節(jié)假體可更好地提供膝關節(jié)自然的屈伸及內外旋運動,防止股骨髁和脛骨的撞擊,滿足自然關節(jié)的穩(wěn)定性。遠期效果有待進一步臨床觀察和隨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