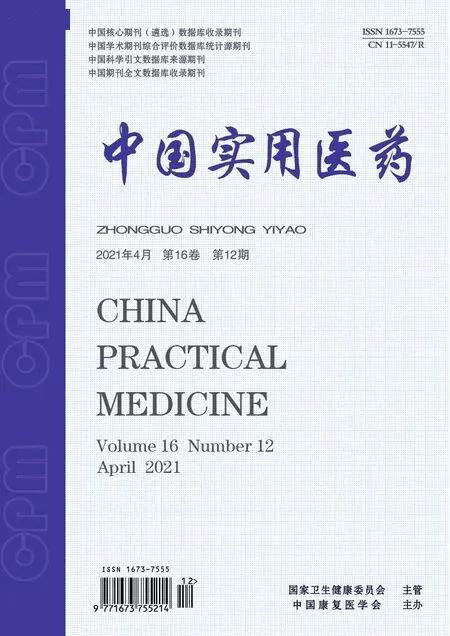多措并舉降低剖宮產(chǎn)率的有效性分析
叢建萍 楊靜
高剖宮產(chǎn)率屬于全球性問(wèn)題,因剖宮產(chǎn)可產(chǎn)生近遠(yuǎn)期母兒并發(fā)癥,如產(chǎn)后出血、臨近臟器損傷、切口延期愈合、新生兒濕肺、兇險(xiǎn)型前置胎盤、子宮破裂等風(fēng)險(xiǎn),且近些年我國(gu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剖宮產(chǎn)帶來(lái)的瘢痕子宮妊娠明顯增加[1],均嚴(yán)重危及母兒健康,甚至產(chǎn)生母兒死亡等不良結(jié)局,故應(yīng)嚴(yán)格把控剖宮產(chǎn)指征、減少不必要的剖宮產(chǎn),將剖宮產(chǎn)率控制在合理范圍。世界衛(wèi)生組織認(rèn)為合理剖宮產(chǎn)率應(yīng)<15%[2],現(xiàn)全國(guó)剖宮產(chǎn)率仍較高,本院剖宮產(chǎn)率亦接近50%,目前國(guó)內(nèi)外很多產(chǎn)科醫(yī)師已經(jīng)意識(shí)到降低剖宮產(chǎn)率迫在眉睫,為此也努力了很多年,但大多從單一措施去控制剖宮產(chǎn)率,結(jié)果卻收效甚微,其原因是綜合因素所致,故如何合理、有效的降低居高不下的剖宮產(chǎn)率已經(jīng)成為全世界產(chǎn)科醫(yī)師及孕產(chǎn)婦共同關(guān)注的問(wèn)題,也是非常棘手的問(wèn)題。本研究有充分的前期工作為基礎(chǔ),通過(guò)回顧2018~2019 年剖宮產(chǎn)率、主要剖宮產(chǎn)指征,并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證實(shí)多措并舉降低剖宮產(chǎn)率的有效性,為產(chǎn)科醫(yī)師臨床工作提供參考,減少母兒近遠(yuǎn)期并發(fā)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8~2019 年本院所有分娩產(chǎn)婦的臨床資料,2018 年總分娩14124 例,2019 年總分娩15617 例,孕周均≥28 周。
1.2 方法 2019 年本院通過(guò)多種措施包括行政干預(yù)、孕期全程管理、減少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提高陰道分娩助產(chǎn)技術(shù)、推廣瘢痕子宮陰道試產(chǎn)、降低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率、開展分娩鎮(zhèn)痛等方式共同干預(yù)降低剖宮產(chǎn)率。回顧性分析2018~2019 年所有分娩產(chǎn)婦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孕周、胎位、胎兒數(shù)量等,按術(shù)前第一手術(shù)指征統(tǒng)計(jì)剖宮產(chǎn)率、統(tǒng)計(jì)手術(shù)指征及構(gòu)成比。
1.3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采用SPSS19.0 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計(jì)數(shù)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yàn)。P<0.05 表示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產(chǎn)婦基本情況比較 2018 年分娩產(chǎn)婦年齡為(30.36±4.04)歲,分娩總數(shù)14124 例,剖宮產(chǎn)7105 例,剖宮產(chǎn)率為50.30%;2019 年分娩產(chǎn)婦年齡為(30.30±3.98)歲,分娩總數(shù)15617 例,剖宮產(chǎn)6358 例,剖宮產(chǎn)率為40.71%。2019 年的剖宮產(chǎn)率低于2018 年,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χ2=275.437,P<0.05)。
2.2 主要剖宮產(chǎn)指征比較 2018 年主要剖宮產(chǎn)指征以瘢痕子宮(23.50%)為首,其次為社會(huì)因素(18.21%)、相對(duì)過(guò)大胎兒(10.18%)、胎位異常(8.64%)、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8.56%);2019 年主要剖宮產(chǎn)指征以瘢痕子宮(25.17%)為首、其次為社會(huì)因素(15.26%)、相對(duì)過(guò)大胎兒(12.35%)、胎位異常(10.11%)、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9.09%)。2019 年瘢痕子宮、相對(duì)過(guò)大胎兒、胎位異常占比高于2018 年,社會(huì)因素占比低于2018 年,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2018 年與2019 年的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占比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表1。

表1 2018 年、2019 年主要剖宮產(chǎn)指征比較[n(%)]
3 討論
近年,高剖宮產(chǎn)率是全球性問(wèn)題,美國(guó)剖宮產(chǎn)率從1996 年剖宮產(chǎn)率20.7%,以后開始逐年上升,2014 年剖宮產(chǎn)率為34.9%[3],國(guó)內(nèi)外對(duì)于降低剖宮產(chǎn)率均極其重視,目前尚缺乏適合我國(guó)國(guó)情現(xiàn)況的合理、有效的降低剖宮產(chǎn)率有效的綜合措施,有學(xué)者認(rèn)識(shí)到提高無(wú)痛分娩可有效降低剖宮產(chǎn)率,減少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4],亦有專家認(rèn)為通過(guò)社區(qū)健康教育干預(yù)模式可有效降低剖宮產(chǎn)率,微信健康公眾號(hào)推送,結(jié)合孕婦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進(jìn)行學(xué)習(xí),達(dá)到孕期全程教育[5],或孕期營(yíng)養(yǎng)干預(yù)與自由體位分娩可降低剖宮產(chǎn)率[6],可見,國(guó)內(nèi)外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意識(shí)到降低剖宮產(chǎn)率的必要性,但往往相對(duì)片面、或者樣本量較少結(jié)果均不夠理想,故本研究總結(jié)前期工作的經(jīng)驗(yàn),利用本院大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總結(jié)出適合我國(guó)現(xiàn)況有效的、可持續(xù)的降低剖宮產(chǎn)率的措施,減少不良母兒結(jié)局。
作者團(tuán)隊(duì)前期總結(jié)了本院2015 年、2016 年剖宮產(chǎn)指征構(gòu)成比及剖宮產(chǎn)率,剖宮產(chǎn)指征前5 位分別為社會(huì)因素、瘢痕子宮、相對(duì)過(guò)大胎兒、胎位異常、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這五大原因是占比較高、也是相對(duì)的剖宮產(chǎn)指征,亦是相對(duì)可控的指征,針對(duì)其有的放矢的總結(jié)分析降低剖宮產(chǎn)率的干預(yù)措施,主要包括孕期全程監(jiān)控、減少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推廣瘢痕子宮陰道試產(chǎn)、降低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率提高陰道助產(chǎn)技術(shù)、開展分娩鎮(zhèn)痛。2019 年本院多措并舉共同干預(yù)剖宮產(chǎn)率,通過(guò)回顧性總結(jié)2018 年、2019 年本院的剖宮產(chǎn)率,結(jié)果顯示: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率由18.21%降至15.26%,總剖宮產(chǎn)率由50.30%降至40.71%。分析以上結(jié)果,通過(guò)本院多種措施的干預(yù),在保障母嬰安全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剖宮產(chǎn)率,其中貢獻(xiàn)最大的是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下降最明顯,而且剖宮產(chǎn)率降低的同時(shí)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率無(wú)明顯變化,胎兒窘迫率4.47%降至2.98%,新生兒窒息率無(wú)明顯增加,足以證明干預(yù)措施安全有效,大大保障了母兒安全,且可持續(xù)性較高。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原因各異,孕婦對(duì)陰道分娩缺乏信心、懼怕分娩疼痛、擔(dān)心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為孩子出生選擇良辰吉日、擔(dān)憂盆底肌松弛等,故應(yīng)對(duì)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個(gè)體化分析原因,具體分析孕婦及家屬心理,找出問(wèn)題所在,耐心講解,正確引導(dǎo)孕婦及家屬心理,充分告知陰道分娩為正常生理過(guò)程,對(duì)產(chǎn)婦及新生兒近遠(yuǎn)期的好處,分析剖宮產(chǎn)對(duì)母兒的近遠(yuǎn)期并發(fā)癥,倡導(dǎo)各級(jí)醫(yī)院加大力度,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會(huì)明顯減少。
本院2019 年全程分娩鎮(zhèn)痛的開展對(duì)降低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有很好的促進(jìn)作用,通過(guò)大力開展分娩鎮(zhèn)痛,對(duì)孕婦及家屬講解實(shí)施麻醉對(duì)母兒影響的因素,宣教分娩鎮(zhèn)痛的好處,且醫(yī)院給予全程分娩鎮(zhèn)痛大力支持,以往還是宮口開大3 cm 入分娩室后行分娩鎮(zhèn)痛,現(xiàn)大力開展全程分娩鎮(zhèn)痛技術(shù),規(guī)律宮縮、宮口開大1 cm 進(jìn)入產(chǎn)程后即可入分娩室享受全程分娩鎮(zhèn)痛,由專門麻醉醫(yī)師分配于分娩室,24 h 可行分娩鎮(zhèn)痛,且麻醉師全程床頭跟蹤鎮(zhèn)痛效果,實(shí)時(shí)調(diào)整,分娩鎮(zhèn)痛效果可達(dá)產(chǎn)后,真正使產(chǎn)婦享受“無(wú)痛的正常分娩”這一生理過(guò)程,這一舉措的實(shí)施使產(chǎn)婦及家屬的滿意度極高,但開展全程分娩鎮(zhèn)痛是否會(huì)延長(zhǎng)產(chǎn)程、是否會(huì)增加產(chǎn)前發(fā)熱發(fā)生率等問(wèn)題還需要大數(shù)據(jù)調(diào)查分析。
通過(guò)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可以看出,瘢痕子宮作為剖宮產(chǎn)指征有明顯上升,分析原因可能與我國(guó)二胎政策的全面放開有關(guān),2019 年較2018 年瘢痕子宮陰道試產(chǎn)率1.62%上升為3.75%,相信通過(guò)繼續(xù)大力推廣剖宮產(chǎn)后經(jīng)陰道分娩、提升瘢痕子宮妊娠助產(chǎn)技術(shù)、盡量消除患者對(duì)瘢痕子宮陰道試產(chǎn)的誤解,瘢痕子宮剖宮產(chǎn)率會(huì)大大控制,Souza 等[7]研究表明剖宮產(chǎn)后的陰道試產(chǎn)成功率較高,子宮破裂風(fēng)險(xiǎn)<1%,但需嚴(yán)格掌握其適應(yīng)證及禁忌證,瘢痕子宮不僅包括剖宮產(chǎn)后再次妊娠,亦包括既往有子宮肌瘤切除史、宮角切除術(shù)及子宮成形術(shù)后等,Kim 等[8]研究表明子宮肌瘤切除術(shù)術(shù)后再次妊娠者,妊娠晚期子宮破裂發(fā)生率較剖宮產(chǎn)后再次妊娠者高,故需更加給予重視,分娩方式的選擇需詳盡了解病史,充分評(píng)估病史、既往手術(shù)時(shí)間、既往手術(shù)方式、既往手術(shù)肌瘤位置及肌瘤大小等,產(chǎn)程中加強(qiáng)監(jiān)護(hù)孕婦生命體征及腹痛等病情變化及胎兒宮內(nèi)情況,尤其是行分娩鎮(zhèn)痛的孕婦,要認(rèn)真仔細(xì)鑒別孕婦情況,下腹部壓痛情況,及時(shí)行床頭彩超檢查,注意動(dòng)態(tài)監(jiān)測(cè)子宮下段瘢痕處宮壁厚度及連續(xù)性,加強(qiáng)胎心率監(jiān)測(cè),注意胎心基線變化,培訓(xùn)醫(yī)師及助產(chǎn)人員早期識(shí)別子宮破裂征象,必要時(shí)需行緊急剖宮產(chǎn),甚至床旁緊急剖宮產(chǎn),最大程度的保證醫(yī)療安全,減少母兒不良結(jié)局。再者,二胎政策放開以來(lái),有些孕婦認(rèn)為順產(chǎn)更易于生育二孩,此類孕婦及家屬越來(lái)越多,可以通過(guò)孕期門診及社區(qū)的健康教育,針對(duì)心理,指導(dǎo)全程合理監(jiān)控,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亦會(huì)相應(yīng)減少,從而減少瘢痕子宮妊娠的數(shù)量[9]。結(jié)果還顯示,相對(duì)過(guò)大胎兒及胎位異常亦有上升趨勢(shì),可繼續(xù)通過(guò)門診與病房聯(lián)動(dòng)控制胎兒體重、加強(qiáng)外倒轉(zhuǎn)術(shù)等技術(shù)來(lái)干預(yù),近來(lái)本院通過(guò)外倒轉(zhuǎn)術(shù)成功復(fù)位2 例經(jīng)產(chǎn)臀位孕婦,母兒安全成功陰道分娩,對(duì)于外倒轉(zhuǎn)術(shù)技術(shù)還需進(jìn)一步培訓(xùn)及實(shí)施,對(duì)于高危孕婦孕前做好咨詢,孕期實(shí)時(shí)監(jiān)控,全程跟蹤孕期檢查情況,電話及微信實(shí)時(shí)聯(lián)系,解除孕婦思想負(fù)擔(dān),未定期來(lái)院孕檢者電話隨訪,引起孕婦及家屬對(duì)產(chǎn)前檢查的重視,減少孕期并發(fā)癥及合并癥,監(jiān)控并發(fā)癥發(fā)展情況,此干預(yù)手段未來(lái)需繼續(xù)努力。
值得強(qiáng)調(diào)的是,2019 年本院增加了醫(yī)院行政干預(yù),通過(guò)行政手段分析各科的剖宮產(chǎn)率,獎(jiǎng)勵(lì)剖宮產(chǎn)率低的科室,相應(yīng)懲罰剖宮產(chǎn)率高的科室,將合理剖宮產(chǎn)率與經(jīng)濟(jì)效益結(jié)合,醫(yī)保政策相應(yīng)扶持,將合理控制剖宮產(chǎn)率納入產(chǎn)科質(zhì)量控制系統(tǒng),制定完善的產(chǎn)科質(zhì)量控制體系,對(duì)于降低總體剖宮產(chǎn)率亦有很大的促進(jìn)作用。
綜上所述,通過(guò)本院大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充分證實(shí)通過(guò)行政干預(yù)制定降低剖宮產(chǎn)率的制度、加強(qiáng)產(chǎn)科門診點(diǎn)對(duì)點(diǎn)進(jìn)行孕期全程跟蹤監(jiān)控管理且與產(chǎn)科病房聯(lián)動(dòng)、降低社會(huì)因素剖宮產(chǎn)率、繼續(xù)推廣瘢痕子宮陰道試產(chǎn)、降低中轉(zhuǎn)剖宮產(chǎn)率、開展全程分娩鎮(zhèn)痛及導(dǎo)樂(lè)服務(wù)、加強(qiáng)晚期妊娠引產(chǎn)技術(shù)的提高、加強(qiáng)分娩室人員配比及技術(shù)力量的提升,通過(guò)以上多項(xiàng)干預(yù)措施,多措并舉,能夠有效的降低剖宮產(chǎn)率。降低剖宮產(chǎn)率不僅為減少近期母兒并發(fā)癥,對(duì)于遠(yuǎn)期孩子的過(guò)敏、感統(tǒng)失調(diào)癥、肥胖等也大有益處,故合理的降低剖宮產(chǎn)率是產(chǎn)科臨床醫(yī)生及患者家屬共同奮斗、共同受益的目標(biāo)所在。
- 中國(guó)實(shí)用醫(yī)藥的其它文章
- 實(shí)時(shí)熒光PCR 檢測(cè)腹瀉患者腸致瀉性大腸桿菌的分布情況研究
- 乳管鏡灌洗液液基細(xì)胞學(xué)檢查與脫落細(xì)胞學(xué)檢查的病理對(duì)比分析
- 認(rèn)知行為治療對(duì)新型毒品濫用患者神經(jīng)精神癥狀及生活質(zhì)量的影響觀察
- 早期肢體康復(fù)訓(xùn)練對(duì)高血壓性基底節(jié)區(qū)腦出血后偏癱患者運(yùn)動(dòng)功能的影響研究
- 個(gè)體化營(yíng)養(yǎng)干預(yù)對(duì)低體重新生兒生長(zhǎng)發(fā)育及免疫功能的影響
- 不同類型貯血試管對(duì)生化檢驗(yàn)結(jié)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