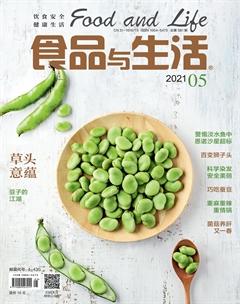五月楊柳依依茶情濃

吉洺萩:自由作家、茶文化跨文化交流推廣傳播講師、企業文化品牌顧問。茶領域研修者二十余年,荷蘭solidaridad可持續發展公益機構茶項目專家,上海陶瓷藝術家協會副秘書長。
五月,正是楊柳依依的季節。這期的專欄,我想寫一位名叫“楊柳”的女子。

和楊柳認識是在20 年前,我當時在杭州負責一本茶文化方面的雜志,她當時在溫州開著兩個已經有5 年歷史的茶莊。介紹我們相識的朋友說,感覺我倆氣質挺像的,都是“70 后”,個頭也都差不多,關鍵是做事情都特認真。那時茶文化剛剛興起,沒有微信,開茶館的也不多,我們雜志社組織了全國百家茶館聯盟,我也因此認識了不少全國各地的茶館館主,某些活躍而有實力的茶館館主會商議著匯聚到某個地方,進行面對面有溫度的行業交流和文化互動。那時候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日本、韓國乃至各個寺院組織的一些茶文化活動也會邀請主要的館主參與互動。回想那些年,我們青春靚麗、意氣風發,大家努力做推動中國茶文化進程發展的先驅者,也應驗了“天下茶人是一家”這句口號。

只是這20 多年,天翻地覆的變化發生了,不管是外部環境、交流傳播手段還是個人生活。茶文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越來越熱,但內核卻越來越散,一個行業老人退場、新人上場是必然趨勢,所以,走著走著自然就散了。慶幸的是,我和楊柳還在一起,沒有走失。

我說,可能是因為我倆名字的意思是兩種植物,我是水邊一棵有生命的小草(萩),而她是水邊的楊柳。同類物種之間總是會有惺惺相惜的感覺。
這些年里,我和楊柳都經歷過人生的一些大變化,在最難最苦的日子里,我們會通個電話,聊個天,三句話后又離不開我和她都愛的茶。很慶幸,茶是我們心里的一畝田,我們有所寄托,也借它安慰著自己,修養著自己。
我們倆有時會互相寄茶樣品鑒,茶樣里總會夾著一封手寫的信。楊柳的字寫得娟秀,像她內心一樣安靜而溫暖。

楊柳是東北姑娘,大學畢業到了溫州,因著茶、因著單純的愛開啟了她第一次的創業之路。12 年前,風生水起的茶莊生意遭遇了生活的一次意外變故,她收拾心情再次啟程,和父母一起撐起了這家在溫州已經是一張名片的“忘憂茶莊”。踏踏實實的一家人,因著對茶的初心從未變過,楊柳在溫州終于安居下來,而這家深深扎根在土壤里的茶莊,不管外部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始終如她的主人般低調而安靜,健康而穩定的存在并豐滿著。
我心里的楊柳是極其努力而精進的,這些年里,她在茶中不斷修研學習,孜孜不倦,對遇到的每一款茶都懷著謙卑和敬意。泡好一杯茶,是每個茶人修煉自己的目標和要求,如同楊柳在她的微信里所寫:“茶人,經年累月,在固定的形式上演練。先做出形,再入其心,久而久之,即使身處鬧市,依舊可以將心安定下來。”
4 月的幾天,我待在溫州楊柳的“忘憂茶莊”,看著她給客人講茶、泡茶,不慌不忙,從從容容。這里的氣場穩定而溫暖,和溫州的氣質形成反差,因著不同,所以更具魅力。
我看著掛在教室墻上的“全國技術能手榮譽證書 ”“武夷山杯首屆全國評茶員職業技能總決算特等獎”“溫州第五輪首席技師”“溫州市技能大師工作室”等榮譽,忍不住感嘆,正是她日日習茶的積累,才顯化出了這些收獲。她淡淡一笑:“你也知道,在實踐中去學習、去修為自己就是最好的。這些年,也是一步步被推著走到現在,去經歷這些行業里專業的比賽,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其實每一個機會都是學習。回到日常,和茶在一起的是才最踏實的生活。”

這個內心細膩的東北姑娘,用她善良美好的心和明亮的眼睛觀察捕捉著自然的美好,然后和茶之間產生著通感;用她敏銳的眼、耳、鼻、舌、身、意捕捉著心已經變味了。我在‘忘憂已經重新一點點做起來了。”我聽后內心非常喜悅和贊嘆,蔡老師書上所寫“無我茶會是一種茶道思想,一種茶會形式的名稱,‘無我應被解釋為‘懂得無的我”。“無” 中才可以生“有”,心中充滿了財富、名譽、地位、美麗和忙碌,幸福無從產生。“無我”的“無”也不是白癡、死亡的無,而是有如光線的無,乃有七彩融合而成,紛雜的生命色彩借“茶”將之純化為無。


早上,楊柳帶著我去家門口的小河邊散步,看著那些細微的小草、那些盛開的花、那些透亮的葉,我倆會像兩個兒時的小伙伴一樣歡笑而驚嘆,然后蹲下身子,玩著春泥,楊柳說:“這里我曾撒下過牛膝菊的種子,每天都會來看看它有沒有發芽,可剛看著它長出來了,卻被物業當野草給拔掉了,唉……”忽然,我們發現地上又冒出了繡球的兩片新葉,楊柳開心地笑起來,“哈哈,這是我曾經種下的繡球花噢,看來它還沒有死,春天來了,它又頑強重生了呢!”
“你看到路口那棵小樹了吧,到了冬天,北風忽忽的,每次路過,我還擔心它被吹倒,只是第二年春夏它長得可真健壯。”
我倆笑了:風再大,我們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