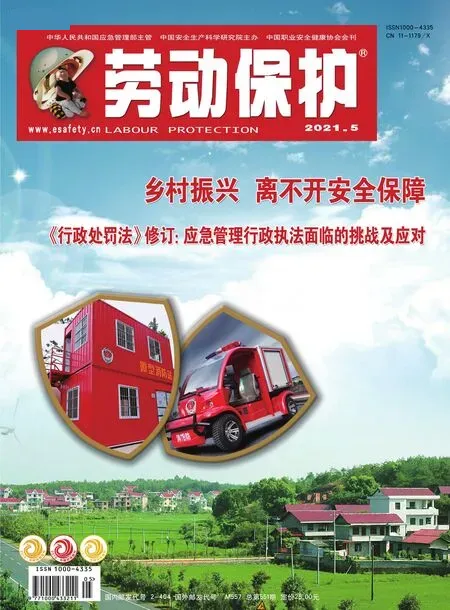國外安全生產責任制度探析
文/周永平
自2018年我國開啟新一輪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以來,有關安全生產工作該如何抓的思考不斷深入。本刊刊發系列文章,回憶并探討我國安全生產工作的發展的變革,以饗讀者。本文是第五篇。
我們常說,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此話可以說是責任制度的常識性法理表達。安全生產有多類主體涉及其中,其行為具有怎樣的性質,如何承擔責任,這便是安全生產的責任制度。從現實層面看,我國安全生產的責任制度與其他國家的相關制度差異巨大,為何如此?理據何在?似有必要對其進行學術性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先就國外安全生產責任制度進行分析。
責任是什么?法學上的標準定義是違反義務(作為或不作為)所應承擔的后果。后果又將怎樣?要視其義務的性質及其被違反(不履行)所帶來損害程度。即主體沒有履行相關義務(可以是約定的,也可以是法定的)具有可原諒性(譬如和解或情節極輕微)和不可原諒性,后者轉化為制裁,即是違反義務的主體所承擔的具體責任。在任何法律關系中,其相應主體均承擔相應的義務,當其違反,將會面臨相當的后果,最終可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構成特定的責任制度體系。

勞動者在安全生產月活動中簽字承諾
安全生產屬于勞動關系領域的事項,其中涉及多類主體——雇主、雇員、政府機構及執法人員、技術服務組織及工作人員、可能的第三人。這些主體在安全生產的法律關系中,均享有相應的權力、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各國根據其法律傳統及奉行理念,對這些主體的權利義務的具體規范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但由于其屬于勞動關系的性質,主要集中對雇傭雙方主體進行規范,其他主體的權利義務則由其他法律予以調整。譬如,行政執法人員的相關行為歸行政法規范,受到傷害的第三人由侵權法管轄,技術服務組織與雇主間的關系屬民事關系,屬合同法調整范圍。因而其相關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力)和承擔的具體責任根據相關法之規范確定。
勞動法被稱為“勞動者權利法”,是指在雇傭雙方的關系的強弱對比中,雇主處于相對強勢地位,雇員則處于弱勢,即勞動關系屬于雙方主體處于實質不平等狀態。據此,勞動法為勞動者創設了一系列權利,譬如:休息權(工時及加班限制)、報酬權(最低工資制度)、平等就業權(反就業和職業活動中的一切歧視)、社會保障權(享有各種社會保險待遇)、安全健康權、團結權等,并且在這些權利項下還包含著許多具體的權利內容,它們統一構成勞動者的法定權利體系。其作為“法定權利”是指不是與生俱來的所謂“自然權利”,也不是主體根據其意愿(民法上所謂意思自治)約定的權利,而是雙方約定改變不了的、由法律創立和明確規定的權利。保障勞動者的這些權利的實現就是雇主的法定義務,如果其不履行相關義務,便面臨相應制裁的不利法律后果。可見,勞動法這套權利義務制度體系完全顛覆了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權利義務對等均衡(所謂享有一個權利,承擔相當義務)的法理。雇主主要承擔的是義務,雇員主要享有的是權利。如果要套用權利義務對等均衡的一般法理的話,雇主享有招募雇員,助成其事業,實現其人生價值的權利,對應義務則是保障勞動者實現其勞動法上的權利。
安全生產法作為勞動法的特別法,其規范勞動者安全健康權利,即勞動者基本人權,秉承了勞動法的基本理念。同時,由于勞動者此項權利的特殊重要性,使其在制度設計上體現為勞動者權利的更為剛性和雇主義務及其履行方面的嚴格化特征。根據這一基本法律邏輯,主要工業化國家對雇主在保護勞動者安全健康權利方面的義務(責任)主要體現在3 個方面:無過錯責任原則下的民事責任、違反具體法定義務的行政責任和有嚴重過失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刑事責任。
每個人都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是一般的判定主體責任的原則,即過錯責任原則。法學基于對理智的正常人具有判斷事物是非能力的假設,設立公認的標準,來確定具體主體之具體行為的對錯,裁量其處于各種法律關系糾紛中應承擔的責任。刑法根據犯罪嫌疑人的過錯過失程度處以相當的刑罰;行政法依據行政執法人員行為中的違法狀況及其對相對人造成的損失給予處罰及向相對人支付國家賠償;民事法律關系中,一方主體對另一主體違約或侵權,均會以其過錯的大小承擔其應付的相應責任。
可見,過錯責任原則是理性的、普遍適用的法律責任原則。而無過錯責任原則是特別責任原則,甚至可以說是一項不講道理的原則。論辯者可以稱,沒有過錯憑什么讓我承擔責任?因此,在工傷領域發明并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不僅源于勞動法對勞動者傾斜保護理念,更是迫于對復雜的生產過程中傷害事件進行過錯認定受到客觀條件限制的無奈選擇。
鑒于生產活動對于人類生存發展的不可或缺,以及幾乎所有職業活動都存在危險性,職業風險理論應運而生,對此風險的解決不僅是雇主的義務,也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工傷保險制度便在此基礎上建立并完善起來:被保險人是勞動者,保費全部由雇主負擔,由此承擔其無過錯責任;費率不是體現雇傭雙方合意而約定的,而是由居于第三方的政府確定的,體現了其社會保險的強制性;如果勞動傷害發生,雇主便可通過向政府有關機構申請,經鑒定后按相關標準,從匯聚所有雇主繳納費用形成的基金中支付相應費用(醫療費、誤工費及傷害賠償),雇主不再支付其他費用,體現出工傷保險的社會分擔屬性。
經由工傷保險承擔無過錯責任,并未包括雇主在工傷事故中承擔民事責任的全部內容。在現代安全生產的治理體系中,一部綜合性的法律處于核心地位(見2021 年第3 期《安全生產的法律邏輯》一文),其中規范的雇主的具體義務,如若沒有得到切實履行,一旦發生工傷事故,雇主還將承擔違法過錯所帶來的民事賠償責任。我國現行《安全生產法》第53 條規定:“因生產安全事故受到損害的從業人員,除依法享有工傷保險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本單位提出賠償要求。”便是規范雇主的此種民事責任。即雇主在安全生產上的民事責任既包含通過繳納工傷保險費而履行法定的、常規性的無過錯責任和工傷事故發生后可能存在的違法過錯賠償責任。
雇主的行政責任并不是指其沒有履行行政法上賦有的義務,而是由于其違反了安全生產法上規定的義務,而由行政執法機構對其施以處罰,表現出的責任承擔。由于職業傷害事件中準確判定主體過錯及其程度的困難,迫使人們創立了無過錯責任制度;因為認識到職業風險的普遍性,無過錯責任又被泛化成社會共擔性質的工傷保險制度。雇主承擔的工傷保險費用在風險等同或類似的行業、領域是相同的,同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由雇主先期支付的這些費用事實上都可以轉嫁給社會,由全體社會成員共擔。由于人人都存在機會主義傾向,在這種制度框架下,雇主并無動力和壓力去履行一般性的保護勞動者安全健康權利的義務。因此,現代各國的相關法律均系統規定了雇主需要履行的具體義務,并配以相應的行政執法人員對其予以監督,確保相關措施落實到位。譬如,英國1802 年的《學徒工道德與健康法》為保護學徒工的身心健康,規定:學徒的工作時間每天不能超過12 小時;宿舍每年必須粉刷兩次,并配通風設備;男女學徒工分開居住,每床不能超過兩人等。為使雇主切實遵守這些規定,政府專門配備治安法官督促雇主實行之。否則,雇主將面臨行政處罰,承擔相應責任。
法律往往采用結果主義原則。即就具體事項或行為規定一般性義務,以結果來判斷相關主體對義務的履行情況。安全生產涉及勞動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如果完全采用結果主義,則面臨巨大風險;同時,由于現代生產系統的多樣性和復雜化特征,要使法律像英國《學徒工道德與健康法》那樣簡明具體地進行規范,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法律授權行政執法機構頒行專業技術標準,并賦予其具有強制法效力的制度就尤為必要。譬如,為確保勞動者健康,經過科學研究論證,對確知的職業健康危害因素實行濃度(各類有害粉塵和有毒化學品)、強度(噪聲、輻射等物理因素)限值控制,作為相應雇主的具體義務。雇主則必須履行到位,否則將承擔與安全生產法上規定義務一樣的違法責任。
雇主因不履行安全生產法及技術標準規定的義務,被行政執法機構以違反法定義務為由予以懲罰,便是其承擔的行政責任。行政責任的形式多種多樣,因其尚未造成危害的事實,一般以糾正違法行為(譬如我國的限期整改、停業整頓等),或處以罰款為主。具體裁處須按行政法程序規則和安全生產法實體規則作出。
刑罰涉及當事主體的人身自由,當慎之又慎。根據罪刑法定和罪刑相當的刑法原則,受刑罰的主體一定要有法定犯罪事實,并證據確鑿。由于安全生產關涉勞動者生命安全,因此安全生產法援用刑法規則,以強化對勞動者這一基本人權的保護力度。從安全生產活動中雇主的行為性質來講,其不可能有意致其雇員群死群傷(如有主觀故意便超越安全生產刑法范疇,歸普通刑法管轄),一般只能定性過失性犯罪。雇主要承擔安全生產法上的刑事責任必須由發生了重大事故的結果和確實存在重大過失(包括不履行法定義務)的原因兩個要件,而且二者構成因果關系。有鑒于此,一般對雇主的刑事處罰維持在輕微的水平上。
雇員作為安全生產法整體上的權利主體,在安全生產法的責任則相對有限。為確保雇員自身、其他雇員的安全,安全生產法一般地規范雇員必須履行遵守安全規程、服從管理和指揮,積極配合雇主方業務需求等義務。沒有主觀故意或重大失誤,一般不承擔責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