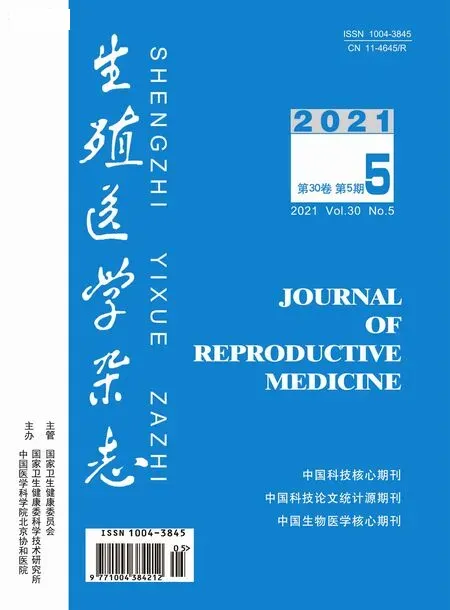子宮內膜增生患者IVF-ET的妊娠結局分析
范亞珍,張印峰,羅海寧*
(1.天津醫科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0070;2.天津市中心婦產科醫院,天津 300100)
子宮內膜增生是因子宮內膜長期受到雌激素刺激而缺少孕激素拮抗、呈持續增生的一種疾病。對于伴有子宮內膜增生的不孕女性,建議首選藥物治療,在內膜完全逆轉后盡快接受輔助生殖技術(ART)助孕治療[1-2]。而在藥物治療過程中反復刮宮和大量孕激素的使用是否會導致子宮內膜容受性下降、是否會降低妊娠率以及助孕過程中雌激素升高是否會導致子宮內膜病變復發或/和惡化尚無定論。針對以上問題,現對天津市中心婦產科醫院生殖中心不孕癥合并子宮內膜增生患者藥物治療后行IVF-ET治療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以期探討子宮內膜增生對助孕治療妊娠結局的影響。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4年6月至2019年6月于天津市中心婦產科醫院因不孕癥行IVF-ET助孕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診刮病理檢查結果判斷是否患有子宮內膜增生,不伴有子宮內膜增生(分泌期子宮內膜、增殖期子宮內膜或其他無異常改變的子宮內膜)的患者為對照組(A組),伴有子宮內膜增生的患者為子宮內膜增生組(B組)。
納入標準:(1)年齡≤40歲;(2)有強烈生育要求;(3)所有患者均經診刮病理檢查;(4)子宮內膜增生患者經藥物治療病理證實完全緩解后接受IVF治療。排除標準:(1)男方因素所致的不孕;(2)夫妻雙方染色體異常;(3)甲狀腺疾病;(4)合并存在子宮畸形、剖宮產史及其他內膜疾病(如子宮內膜息肉、內膜結核病史等)者。
本研究共納入833例患者,其中A組755例、B組78例,使用傾向評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的方法均衡組間變量,得到組間協變量均衡的樣本各52例,觀察患者行IVF-ET的結局。根據患者子宮內膜增生的病理類型不同將B組又分為子宮內膜增生不伴不典型增生組(B1組,55例)和子宮內膜增生伴有不典型增生組(B2組,23例),隨訪至2020年6月,分析不同類型子宮內膜增生患者的1~6年的復發率。
二、匹配基線資料
為了避免A組與B組基線資料的不同對妊娠結局造成偏倚,使用PSM對基線資料進行匹配,包括:患者年齡、不孕年限、體重指數(BMI)、基礎FSH(bFSH)、基礎LH(bLH)、基礎E2(bE2)、基礎睪酮(bT)、基礎孕酮(bP)、基礎催乳素(bPRL)、獲卵數、HCG日子宮內膜厚度等。
三、治療方案
1.子宮內膜逆轉治療方案:經病理證實的子宮內膜增生患者,口服甲地孕酮(青島國海生物制藥)160 mg/d或甲羥孕酮(浙江仙琚制藥)250 mg/d,用藥3個月后經宮腔鏡復診,根據子宮內膜病理結果評價療效,達到完全緩解后轉入生殖中心繼續治療。IVF-ET后未孕患者及妊娠患者產后均定期復查。
2.療效判斷標準:(1)完全緩解:治療后病理檢查結果為分泌期子宮內膜、增殖期子宮內膜或其他無異常增生性改變的子宮內膜;(2)部分緩解:指病變殘留伴有子宮內膜腺體的退行性改變或萎縮;(3)疾病穩定:治療后病理檢查結果與治療前相同;(4)疾病進展:治療后病理檢查結果提示病變重于治療前;(5)疾病復發:治療獲得完全緩解后在隨訪過程中病理再次提示子宮內膜增生。
3.輔助生殖助孕治療方案:促排卵、常規IVF或卵胞漿內單精子注射(ICSI)、胚胎培養及移植等均按本中心常規進行。(1)短效長方案:前一周期的黃體中期開始給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達必佳(醋酸曲普瑞林注射液,輝凌,德國,0.05 mg/d)或達菲林(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博福益普生,法國,0.1 mg/d),用藥14~21 d,于月經周期的第2~3天返回本中心檢測激素,達到降調標準(LH<5 U/L、E2≤183 pmol/L、子宮內膜厚度≤5 mm)后給予Gn促排卵,用藥5 d后陰道B超監測卵泡發育情況,綜合卵泡生長速度及血清激素水平調整Gn種類及劑量。當B超提示雙側卵巢內有3個以上卵泡直徑達到17 mm或2個以上卵泡直徑達到18 mm時予HCG(珠海麗珠制藥)4 000~10 000 U肌肉注射誘導卵泡成熟。(2)拮抗劑方案:月經周期第2~3天使用Gn促排卵,連續4~6 d后,當主導卵泡直徑≥12~14 mm加用GnRH拮抗劑(GnRH-ant,西曲瑞克或加尼瑞克,默克,美國),每日皮下注射1支至HCG日。期間,陰道B超監測卵泡發育情況,綜合卵泡生長速度及血清激素水平調整Gn種類及劑量。當B超提示雙側卵巢內有3個以上卵泡直徑達到17 mm或2個以上卵泡直徑達到18 mm時予HCG 4 000~10 000 U肌肉注射或GnRH-a 0.2 mg皮下注射誘導卵泡成熟。上述方案均于扳機后36 h經陰道超聲引導下取卵,取卵后3 d行新鮮胚胎移植第3天(D3)卵裂期胚胎至少1枚。
內膜準備采用自然周期和激素替代方案。(1)自然周期:根據患者月經周期長短安排首次B超觀察卵泡的時間,監測至優勢卵泡自然消失,2 d后行凍融胚胎移植(FET),移植至少1枚凍融D3卵裂期胚胎;(2)激素替代方案:從患者月經周期第3~5天開始每日應用戊酸雌二醇(補佳樂,拜耳,德國)2~8 mg約12 d,B超監測至內膜厚度≥8 mm時加用黃體酮注射液(浙江仙琚制藥),連續使用5 d,于肌肉注射黃體酮第6天行FET,移植至少1枚凍融D3卵裂期胚胎。移植后14 d檢測血HCG>25 U/L為HCG陽性,移植后28 d經陰道B超檢查見孕囊為臨床妊娠。
四、觀察指標
匹配后比較兩組患者的累積妊娠率、累積活產率、早期流產率、晚期流產率、妊娠期并發癥發生率、早產率及新生兒體重。其中,累積妊娠率=臨床妊娠的患者數/進入刺激周期的患者數×100%;累積活產率=獲得活產的患者數/進入刺激周期的患者數×100%。
五、統計學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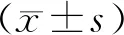
結 果
一、一般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833例患者,其中A組755例、B組78例,匹配后每組各52例。匹配前納入患者取卵年齡25~40歲,平均取卵年齡(30.99±3.26)歲;不孕年限1~17年,平均不孕年限(4.35±2.70)年;BMI 15.9~37.0 kg/m2,平均BMI(22.76±3.21)kg/m2。匹配后入組患者取卵年齡25~40歲,平均取卵年齡(32.20±3.53)歲;不孕年限1~17年,平均不孕年限(5.48±3.46)年;BMI 17.2~33.2 kg/m2,平均BMI(24.05±3.57)kg/m2。
匹配前兩組患者的取卵年齡、BMI、不孕年限、原發性不孕比例、合并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比例、bE2水平比較均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而bFSH、bLH、bT、bP、bPRL水平、獲卵數及HCG日內膜厚度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匹配后兩組患者的bE2水平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其余各項指標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s),%]
二、助孕結局
匹配前兩組患者的晚期流產率有統計學差異(P<0.05),而累積妊娠率、累積活產率、早期流產率、孕期并發癥發生率、早產率及新生兒體重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匹配后兩組患者的各項妊娠結局指標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表2)。

表2 兩組患者妊娠結局比較[(-±s),%]
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累積妊娠率與患者取卵年齡[P=0.005,OR=0.789,95%CI(0.670,0.930)]及獲卵數[P=0.024,OR=1.078,95%CI(1.010,1.150)]有關(表3)。

表3 累積妊娠率Logistic回歸分析
三、疾病復發
B1組患者1~6年復發率為5.5%,B2組患者1~6年復發率為21.7%,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6)。兩亞組取卵年齡、BMI、不孕年限、原發性不孕比例、合并PCOS比例、bFSH、bLH、bT、bP、bPRL、bE2、獲卵數及HCG日子宮內膜厚度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表4)。
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復發與病理類型有關[P=0.018,OR=0.101,95%CI(0.015,0.680)](表5),子宮內膜不典型增生組(B2組)的復發率顯著高于不伴不典型增生組(B1組)。在復發的8例患者中,3例來自B1組,5例來自B2組;B1組復發的3例患者,保守治療至復發的時間分別為18、20、21個月,復發后病理均為不伴不典型增生;B2組復發的5例患者,保守治療成功后至復發的時間分別為10、19、43、43、49個月,復發后病理2例為不典型增生,3例為不伴不典型增生。

表4 子宮內膜增生兩亞組患者一般情況及復發率比較 [(-±s),%]

表5 復發率Logistic回歸分析
討 論
一、患者臨床特點
子宮內膜增生與長期雌激素刺激而無定期孕激素的保護有關,相關的危險因素有:吸煙、不孕、持續性無排卵、肥胖、月經不調、PCOS和代謝綜合癥[3-4]。在本項研究中,匹配后子宮內膜增生組(B組)患者的bE2水平仍顯著高于對照組(A組),說明基礎雌激素水平過高是子宮內膜增生的危險因素;不孕年限、原發性不孕及是否伴有PCOS兩組間比較雖無統計學差異但有增高的趨勢,提示這些也可能是子宮內膜增生的高危因素。因此,對于不孕癥伴有以上高危因素的患者在助孕過程中應更加重視對其內膜的檢查,以便早發現、早治療。
二、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緩解后IVF-ET治療效果
在本項研究中,匹配后B組的早期流產率為6.5%,晚期流產率為8.0%,累積妊娠率為59.6%,累積活產率為44.2%,與匹配后A組相比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累積妊娠率與患者BMI、合并PCOS、原發性不孕病史、bE2水平、子宮內膜厚度無關,與患者取卵年齡及獲卵數有關(P<0.05),提示隨著患者年齡增加及卵巢儲備功能下降,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IVF-ET累積妊娠率會隨之下降。關于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影響妊娠的相關因素,Inoue等[5]認為影響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妊娠結局的相關因素有:疾病是否復發、排卵期子宮內膜厚度、妊娠年齡。Zhou等[6]認為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行ART的患者更有可能懷孕,與病理類型、BMI、是否伴有PCOS無關。納入本研究的患者,均為助孕過程中發現子宮內膜增生,經藥物治療內膜完全緩解后即行IVF-ET治療,故未研究這類患者ART妊娠與自然受孕相比對妊娠結局的影響。Koskas等[7]通過meta分析認為年齡、既往不孕病史、肥胖均與妊娠率無關;而Gonthier等[8]認為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BMI≥30 kg/m2的患者妊娠率明顯低于BMI<30 kg/的患者。但以上研究均為樣本量相對較小的回顧性研究,尚需高質量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進一步明確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妊娠結局的影響因素。
三、影響子宮內膜增生復發的相關因素
對于影響子宮內膜增生復發的相關因素目前尚無統一的意見。本研究中,伴有不典型增生組(B2組)復發率為21.7%,顯著高于不伴不典型增生組(B1組)(P<0.05),與Gallos等[9-10]的報道一致。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年齡、不孕年限、原發性不孕、合并PCOS與復發均無關,復發僅與病理類型有關(P<0.05)。Ohyagi-Hara等[11]亦認為復發與病理類型有關;但Chen等[12]認為復發與年齡、BMI、疾病完全緩解所需的時間有關,而與疾病類型無關,這種結果的差異可能是由于納入研究的群體不同。何翊姣等[13]認為,影響子宮內膜藥物治療后復發的因素有孕激素治療的持續時間、孕激素治療后的維持、超重、年齡、雌激素受體(ER)和孕激素受體(PR)的表達及高胰島素水平。
BMI是否會影響復發尚有爭議,目前國內以BMI≥25 kg/m2定義為超重,BMI介于30.0~34.9 kg/m2為肥胖。有研究認為,BMI是影響孕激素治療完全緩解及復發的因素;Park等[14]和Renehan等[15]報道稱BMI≥25 kg/m2使孕激素保守治療效果差且易復發;Yang等[16]認為BMI≥30 kg/m2是疾病復發的唯一危險因素,因為在肥胖患者中內源性雌激素過多將會拮抗孕激素治療的活性;但Gonthier等[8]研究表明BMI≥30 kg/m2與BMI<30 kg/m2的患者有相似的復發率。在本項研究中8例復發的患者中有6例患者的BMI>25 kg/m2,提示BMI可能是疾病復發的危險因素。
此外,子宮內膜增生是由于長期暴露于雌激素而無孕激素保護所致,因此,助孕過程中促排卵藥物的使用導致雌激素升高是否會增加患者的復發風險?Park等[17]和Ichinose等[18]的研究表明,助孕過程中雌激素的升高是一過性的,不會增加疾病復發。本研究復發的患者中,使用拮抗劑方案和短效長方案的比例相等,表明不同促排方案的使用可能不是影響復發的因素。
四、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的新生兒結局及孕期并發癥的發生情況
目前,以“子宮內膜增生(endometrial hyperplasia)”、“藥物治療(drug conservative therapy)”、“妊娠期并發癥(pregnancy complication)”等為關鍵詞在萬方醫學網、中國知網、PubMed均未檢索到相關文獻。本研究結果表明,與A組相比,B組孕期并發癥的發生率和新生兒體重均無統計學差異,提示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不會增加不良妊娠的風險。但本研究可能會受到小樣本回顧性研究局限性的影響,因此,關于子宮內膜增生藥物治療后孕期并發癥的發生率和新生兒結局有待于進一步積累樣本量進行前瞻性研究。
綜上,本研究通過對病歷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現,子宮內膜增生患者經過積極的藥物治療不會明顯降低其累積妊娠率和累積活產率,且不會增加不良妊娠的風險,但隨著年齡增加及卵巢儲備功能下降,累積妊娠率明顯下降。藥物治療只是為助孕治療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時間窗口,為保證該類患者助孕治療的成功率及延緩疾病復發或進展的時間,藥物治療后應積極行助孕治療。對于伴有肥胖、多囊卵巢、稀發排卵等高危因素的患者,助孕過程中應更加關注其內膜情況,以便及早發現盡早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