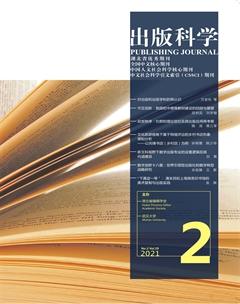新文科視野下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邏輯及其內涵建設
[摘 要] 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邏輯應當是:首先,數字出版專業應該將計算機應用技術作為重要支撐;第二,數字出版專業必須基于多種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第三,數字出版專業的主干知識結構應該圍繞傳播學來建構。據此,數字出版專業有著新的專業內涵:“新文科”理念是數字出版專業精神的核心;多學科知識融合、數字應用技術和文化產品生產技能兼通是數字出版專業學生及其師資知識結構的基本要求;寬厚的理論基礎、深度的社會實踐和與業界同步的實操訓練并重,是數字出版專業課程設計的基本原則。由此,數字出版專業的內涵建設基本方略應為:(1)要對師德師風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建立一支多學科融合的師資隊伍,每一位教師具有多學科知識的學習能力,同時,還要建構一支“學界”“業界”相融合的“雙師型”隊伍。(2)要更新教育管理理念、創新教學管理制度,打破“專業主干課程”與非“專業主干課程”之間的界限,打破課堂教學和課外學習的界限,把教學任務設計和教學安排權力下放到院系。(3)重視教學平臺建設,引入最先進的智能數字設備,建構多功能的融媒體平臺,讓學校實驗室平臺與業界實務平臺良好接入,使其能與業界實務平臺同步升級。
[關鍵詞] 新文科 數字出版 專業設置 專業內涵建設
[中圖分類號] G23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1) 02-0089-10
Research on Digital Publishing Logic Setting and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New Liberal Arts Perspective
Bai Y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Abstract] The logic setting digital publishing should be as follows: firstly, digital publishing should be based on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secondly, digital publishing must b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rdly, the main knowledge structure of digital publishing should be constructed arou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As a result, digital publishing has a new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which includes: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ion is the core of digital publishing professionalism;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digital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 production skills 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publish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knowledge structure; broad theoretical basis, deep social practice and synchronous practical training with the industry are equally important,which i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design of digital publishing. The basic strategy of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should be as follows: higher requirements should be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morality and style, and a multi-disciplinary teaching team should be established. Every teacher has the ability to learn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a“double qualification”tea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circles”and“industry”should be constructed. It i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innovat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break the boundary between“professional main courses”and non“professional main courses”, and also brea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Therefore, the power of teaching task design and teaching arrangement should be devolved to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Meanwhile,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platform, introduce the most advanced intelligent digital equipment, and construct a multi-functional media platform, so that the laboratory platform of the college can be well connected with the practical platform of the industry, so that it can be upgraded synchronously with the industry practice platform.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Digital publishing Specialty setting Specialty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任何一個本科專業的設置,都必須依據特定的邏輯。就傳統的本科專業設置而言,其設置的邏輯主要源于兩個原點:一是依據該專業所培養的人才在未來從事的行業歸屬而設置,如會計、車輛工程專業等;二是依據該專業所屬學科的特定研究對象和領域而設置,如社會學、材料學等。這種設置邏輯的合理性在于,在幾十年前,一種行業形成后會有一段相當長的成熟穩定期,一種學科在成熟后也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著比較穩固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因此,以行業屬性和研究對象來劃分專業也會是相對穩定的。
但是,在當下,由于新興的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上述狀況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現有的行業格局開始瓦解,許多行業的界定被粉碎、重組,以致行業與行業之間的邊界模糊不清。比如,由IT行業、軟件行業、通訊行業、運輸業、零售業甚至制造業統合而成的新物流業態,能把它歸屬到一個具體的行業中嗎?另一方面各個學科的研究對象出現了巨大的轉移、擴張和重置。比如出版學,將面對著許許多多在過去并未囊括進入其研究視野的研究對象和問題,如音視頻技術、數據挖掘、用戶分析、3D打印等,這些原本不屬于“出版學”研究的對象和問題,現在直接扼制著出版業的生死咽喉。
正是為了應對這一“變局”,教育界提出了所謂“新工科”“新文科”的主張。筆者曾在《基于融媒體發展的新文科專業內涵及其人才培養規格》一文中,提出“新文科”的人才培養,應以如下要求為目標:具有應對復雜社會變遷、文化變遷和生活變遷的能力,包容多種知識領域,具備全球視野、人類情懷而又不失“中國心、中國情、中國味”的多元素質[1]。按照這一培養目標,“新文科”專業的設置,其依據的邏輯起點就不再是特定的行業歸屬或學科研究對象,而是“應變”的策略與方向。而數字出版專業,就是為了“應變”而誕生的一個“新文科”專業,因此,這一專業的建構邏輯及其內涵,也應在其“應變”方略中尋求解釋。
1 大變局中的數字出版與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邏輯
數字出版是數字技術帶來的媒介革命的產物,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數字出版看成出版業的延伸或者轉型,更不能把數字出版專業(本科)看成傳統出版專業的替代或者升級。因為,就其內涵而言,傳統的出版與數字出版,傳統的出版專業與數字出版專業,有著本質的不同。
傳統的出版,可以理解為一個邊界清晰而完整的行業門類,也可以理解為一套操作對象和操作工藝明確的生產流程,更重要的是,它向社會提供的產品與其他行業所提供的產品幾乎不相重疊—比如,傳統的出版業與展覽業提供的產品自然是涇渭分明。由此,基于傳統出版行業所需要的理論、技術和工藝而設置的出版專業,其基本內涵,就是建構出版生產需要的理論體系,解決出版專業面臨的技術問題,培養能夠從事出版生產的各類人才。
但是,數字出版,首先就不能理解為一個邊界清晰而完整的行業門類:你能說“騰訊”“神州專車”“微信”不是數字出版嗎?其次,我們也很難區分“數字出版業”與“非數字出版業”提供的產品有什么不同:“數字展覽館”的提供商與“電子書包”的提供商完全可以是同一家企業。這樣,如果把“數字出版”看作一種業態,那么,其生產流程所涉及的操作流程和操作工藝恐怕就不是這個業態所專有的了:數據挖掘、智能軟件編寫、文學創作、藝術設計、廣告策劃乃至用戶定位,哪一個能為“數字出版”所專有?由此,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就不是基于哪一個行業所需要的理論、技術和工藝了,其基本內涵,也不是為哪一個行業提供理論支持或技術解決方案,它所培養的人,也自然不能以特定的行業作為輸送目標。數字出版的誕生,是社會各界為應對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巨大變革做出各種努力而形成的綜合結果。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談這一問題。
1.1 文化生產方式的變革重新定義了“出版”概念
其實,“數字出版”這一概念最早是傳統出版界提出的。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傳統出版業深切感受到數字技術的突飛猛進而帶來的嚴峻挑戰:首先是出版物形態的巨大變化—紙質出版物被電子出版物嚴重擠壓;其次是讀者消費方式的轉變—新生代讀者不但從紙質讀物轉向在線閱讀,而且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向非傳統出版業的文化產品,如電子游戲、社交媒體等。為此,出版業界出現了所謂向“數字出版”轉型的主張。但是,“轉型”一詞很容易引起一種極為狹隘的理解:數字出版似乎就是把計算機技術引入傳統出版流程的新業態。但是,只要認真觀察一下近十年來各類數字內容產品的市場狀況,就會發現,“出版物”產品最成功的提供者不是那些引入了計算機技術的出版企業,而是那些傳統上根本不屬于出版業的企業:如騰訊、喜馬拉雅等。也就是說,數字出版生產,可以完全不依賴既有的傳統出版經驗、技術甚至理論,甚至也不依賴既有的任何一個行業的經驗,它是一種完全嶄新的、統合了多種領域經驗和技術的新的生產形態,它可以屬于許許多多不同的行業。你把“抖音”算成互聯網企業還是出版業?你說“喜馬拉雅”算不算出版企業?在“騰訊”平臺上提供各類文化服務的企業或個人又屬于哪個行業?
更進一步的考察還會使我們發現一個更為深刻的變化,那就是,數字技術帶來了我們對“出版物”的重新理解。最為傳統和狹隘的理解就是:所謂“出版物”,就是被稱為“出版社”的那些單位發行的產品。許許多多提供人們文化生活服務的東西不被看作“出版物”,如展覽服務、旅游服務等。如果把展覽、旅游等服務通過特定的計算機軟件作品來實現,這些軟件作品不就是“出版物”嗎?于是,在數字技術廣泛運用的情況下,“出版物”的內涵和外延大大擴張了。
其實,所謂“出版物”,在數字技術被廣泛運用之前,在法律意義上,就被界定為提供有知識專屬權的文化產品,如書籍、唱片、廣播、表演、影視等。只不過在當時,被人們所廣泛使用的、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都較低廉的產品主要還是那些能夠將知識內容附著在廉價固體物品上的產品,如書籍、雜志、唱片、DVD等,由于這些產品的制作、發行有著大體相近的運營管理流程,我們把生產這些產品的單位歸屬為“出版業”,這些產品就被稱為“出版物”。但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更為便捷和廉價的知識產品可以用虛擬形態方式提供:網絡讀物、電子游戲、虛擬旅游、數字博物館等。于是,文化產品的提供就不僅僅來自所謂的“出版”單位,而且更多地來自任何一個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文化生產和服務的部門,“出版物”就不再是僅僅由“出版部門”提供的產品,而可以是任何企業提供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由是,可以看到,在數字技術之下,文化產品的生產不再歸屬某個特定行業,而可以成為任何一個行業或部門都可以開展的經營活動。由此,“出版”的概念將被重新定義。關于此,李曉丹、賀子岳曾提出:出版在本質結構上,就是關于知識、信息等精神產品進行專業化和傳播的社會化活動[2]。這個定義的內涵何等寬厚,它把出版的對象囊括為幾乎所有的精神產品,這是符合當下文化生產實際狀況的。同樣,考慮到數字技術對出版活動的全面介入,張新新在總結了近二十年關于“數字出版”的概念定義后,認為“數字出版,是指以數字技術將作品編輯加工后,經過復制進行傳播的新型出版”[3]。這個定義實際上承認,任何“作品”,只要運用數字技術對其加工和傳播,就是“數字出版”。綜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所謂數字出版,就是所有具有知識產權專屬的文化產品的數字發布。
1.2 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變革規定了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邏輯
筆者上述關于數字出版的定義,實際上是根據當下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所面對的巨大變革而提出來的,它說明了如下兩種變革狀態:一是數字內容產品的生產和發布不再歸屬某一特定的行業—任何行業運用計算機技術,都可以進行符合其行業特征和需要的數字出版,一如淘寶網上的那些小插件;二是知識產品的生產方式、經營模式和傳播樣式是多元化的,但都極為依賴數字技術平臺,包括動漫產品、“李子柒”的宣講、知網上的文獻以及微信提供的社交服務等。完全不同的產品形態和產品流通方式,是對傳統文化生產和運營的全面革新,但其核心工藝,是基于數字技術平臺的。
可以看到,為應對上述兩大變革,數字出版就必須采取如下應對方略。
一是要深刻理解計算機技術帶來的文化生產新手段和文化產品傳播新形態,要把數字技術邏輯融入到文化生產邏輯中。這不僅僅是“互聯網+”的問題,而是要認識到數字技術的介入導致的文化產品內容的內在結構變化—比如,傳統的文化產品的內容因主要依賴文字表達,往往形成線性的、理性的思想結構,而因數字技術的介入引起的音視頻和文字符號相融合的表達形態可以將知識產品結構呈現為非線性的、感性與理性相互交融的結構。內容結構的變化勢必給文化產品的受眾帶來全新的接受體驗,形成復雜的社會效應,從而引發許多始料未及的社會問題。
二是要深刻理解文化產品的多元化和產品形態的急劇變換、更替,以及傳播手段的不斷創新。書籍作為主流的文化產品形態持續了幾千年,電影作為主流的文化產品形態持續了幾百年,電視作為主流的文化產品形態維持了幾十年,而DVD作為主流的知識產品形態只維持了十幾年……短視頻似乎方興未艾,殊不知5G一旦普及,或許就變成“長視頻”的天下。為此,作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經營和傳播者,就必須培育出對人們文化需求、市場乃至社會的敏銳的分析預判能力,也必須具備對新技術運用的自我更新能力。
三是要深刻理解數字空間已然成為文化產品傳播和接受的主要場域。這不僅僅是因為媒介的轉換,更重要的是人的活動空間的無限拓展和活動時間限制的突破。比如,在過去,書籍是極為重要的傳播媒介,但是,人們使用書籍的活動空間是受許多限制的:要在合適的地方攜帶合適的書籍,或者必須身處所需書籍的收藏之地;對書籍閱讀的時間也不是隨心所欲的,特別是在碎片化時間里,很難進行正式的閱讀活動。但是,數字媒介讓我們的精神活動拓展到了虛擬空間中,移動終端的便攜性使我們在任何時空節點上進行文化產品的傳播和接受成為可能。于是,對出版物的制作,除了傾心于內容的設計之外,還要更多地關注產品形式對不同數字媒介的適應性。也就是說,數字出版產品形態的微小變化,可能會帶來產品運營的巨大影響。我們不能說數字出版對產品形式的關注高于對產品內容的關注,但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對同一產品內容的不同的形態加工,可以成為數字出版的重要產業鏈。因此,就數字出版運營的人力需求而言,對產品形式加工(主要運用互聯網應用技術)的人員需求可能多于對產品內容加工的人員需求。
基于上述應對方略,可以初步縷析出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邏輯。
第一,數字出版專業應該將計算機應用技術作為重要支撐。因為,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等,已經成為數字出版的基本技術手段。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把數字出版歸結為“文科”專業,如果沒有深厚的計算機技術和智能科學等“工科”知識背景,我們很難在數字出版的實際工作中執行具體的任務,更無法構思出版產品的設計和制作流程。
第二,數字出版專業必須基于多種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因為,數字出版對產品內容的加工,主要不是對內容表達正誤的把關(觀點的是非判斷、表達邏輯的合理性、文字句法的正確性等),更重要的是對產品內容接受效果的研判能力—這種能力基于兩個方面:一是對特定知識領域內,其產品社會影響的深度和廣度的研判,比如,音頻節目中的心理輔導或“心靈雞湯”類的節目究竟會使聽眾產生怎樣的心理反應?引發怎樣的輿情?這就需要節目編輯或策劃者具備一定的社會心理學基礎。二是對數字媒介時代傳播效應復雜性的敏感,比如,“李子柒”在自媒體場域中引發的各種始料未及的討論—中西文化沖突問題、帶貨問題、國家形象問題等。
第三,數字出版專業的主干知識結構應該圍繞傳播學來建構。這是因為:(1)數字出版主要是對數字媒介的應用,同時,也主要是在數字媒介中來完成的;(2)作為數字出版產品,其基本功能是向受眾或用戶提供文化產品與精神體驗,因此,對數字產品的研究,核心問題就是其傳播效果問題;(3)最重要的是,數字出版作為社會活動的實現,主要是在傳播活動中完成的。由此,無論數字出版涉及多少學科的融合,但它以傳播學為基礎理論是毋庸置疑的。
2 數字出版專業的新內涵
確定了數字出版專業的設置邏輯,數字出版專業的內涵即可依此邏輯而定。也就是說,無論是專業建設的理念,還是專業的人才培養、師資隊伍結構建設、學科建設乃至課程體系建設,都是在上述專業設置邏輯規范下的。
2.1 “新文科”理念是數字出版專業精神的核心
正如上文所指出,數字出版是在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邏輯起點上誕生的一個專業,這也是新文科理念提出的基本背景。具體而言,這個基本背景的畫像就是:數字技術日益實質性介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介入人們的文化生活;互聯網運營規律和發展態勢不斷形塑人們的新觀念、新思維;互聯網技術、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全球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沖突、融合日益頻繁,也使得全球的經濟生活密切聯結成一個整體,人類逐漸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由此,人類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的不同維度在數字空間中相互交織融合,人文社會科學從分析時代重新走向綜合時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大融合指日可待。這個畫像決定了新文科建設理念的三個基本要素,筆者把它總結為“一個視野,兩個融合”,即:全球化的視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懷,數字技術思維與人文思維的融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同視角、不同對象、不同方法之間的融合[4]。
作為新文科專業之一的數字出版專業,也必然依據上述理念構建自身的專業精神。在專業學習和研究中,要把數字技術對人類精神生產和文化產品的影響作為思考的主線;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要注重技術思維與傳統文科思維相融合;在人才培養目標上,要讓學生樹立關懷人類、熱愛社會的高尚情操,培育學生廣闊的視野;在教學改革中,要始終緊跟技術進步的路線和社會變革的步伐,不斷融合多學科的內容,更新專業知識結構。在此理念基礎上,我們可以提出數字出版專業人才培養的基本規格:在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面,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熱愛祖國、熱愛生活,關懷人類命運,關心人類文化發展和變革;在專業能力方面,要文理綜合發展,掌握主要的人文社會科學門類的基礎知識,精通數字技術應用,能夠深刻理解人們的文化需求特征和文化心理,對不同文化產品的數字形態的使用需求敏感;在社會適應性方面,能夠成為在數字技術和文化形態劇烈變革中具有極強應變能力的普適性人才。
2.2 多學科知識融合、數字應用技術和文化產品生產技能兼通是數字出版專業學生及其師資隊伍知識結構的基本要求
就課程體系設計而言,已經不能把計算機應用和數據分析等類課程作為“通識類”課程的點綴,而應該把與數字技術相關的基礎性課程納入數字出版的專業基礎課體系。就筆者調研的幾所高校的數字出版專業培養方案來看,有關數字技術及其應用的課程,大都列為通識課程,只有少數幾門列入專業課程;而且,這類課程的總學分大都不超過8個學分,最多的也沒超過12學分。這自然還是一種“數字+出版”的培養模式。依照本文所述的數字出版專業設置邏輯,數字出版專業的課程體系應當分作四大板塊:數字技術類、傳播學類、人文社會科學綜合類、實踐類。按照這一邏輯,數字技術類的課程在數字出版專業課程體系中,應當占有除公共課之外的至少四分之一學分。
當然,這樣的課程體系設計勢必對數字出版專業的師資隊伍建設提出特別的要求。一般的解決方案是,用多學科的師資隊伍建設來解決這一問題,如中南地區的某高校數字出版專業就有意引進了計算機科學、經濟學、文學、哲學、新聞傳播學、出版學、圖書情報學乃至醫學等多個學科的師資。但是,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因為即便是多學科組合的師資隊伍,如果其中的每一位教師自身拘謹于特定的學科領域,而對其他學科缺乏較為深刻的理解,那么,面對具有多學科交叉融合知識背景的學生,師生之間的思維模式之間勢必產生齟齬,從而影響學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對數字出版專業而言,不僅僅是師資隊伍的結構要多元化,其中每一位教師的知識結構也要多元化。我們必須重視這一問題,要加強對數字出版專業師資的培訓和再培訓,特別是對文科背景教師進行數字技術方面的培訓—這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2.3 寬厚的理論基礎、深度的社會實踐和與業界同步的實操訓練并重,是數字出版專業課程設計的基本原則
正如上文所述,數字出版針對的不是特定領域的生產流程,而是承擔涉及社會文化全面變革的精神生產,因此,數字出版專業所培養的人才,首先就要有能力在哲學高度上把握社會文化變革的實質,這就需要極高的理論思維訓練。同時,作為精神生產者,又特別需要對社會公眾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生活變遷極度敏感,因此,要在多元視角下理解復雜的社會現象和多變的社會心理,就需要極為深厚寬廣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基礎。由此可見,數字出版專業的學生,相對于傳統的出版學專業乃至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就需要獲得更多門類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充分涵養。
其次,由于大變革時代文化生產者必然承擔著解決諸多社會文化問題的重大責任,數字出版專業的學生亟需培育問題導向意識—在面對具體社會問題中,運用所學知識提供解決方案。如此,數字出版專業的學生就不能總是坐在書齋里或實驗室里紙上談兵,而必須在深入的社會實踐中獲得實際體驗,習得同理心、同情心,由此才能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可以說,寬厚的理論知識,必須在豐富而深入的社會實際體驗中才能悟得其中的真諦;而歷經社會實踐而獲得社會敏感,又能為理論水平的提升和理論創新提供鮮活的動力源泉。
最后,由于數字出版是基于計算機應用技術和互聯網應用技術而開展的文化生產活動,而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智能技術呈現著日新月異的態勢,人們一定是在緊密的跟蹤實踐中才能熟練把握不斷更新的技術應用,因此,數字出版專業的學生乃至教師就需要浸淫在數字技術的具體操作實踐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人們文化消費方式的變化和文化產品形態的創新。同時,數字出版專業還是一門實操性非常強的專業,該專業的學生乃至教師,需要深入互聯網公司、文化創意企業中,及時了解新技術的應用狀況,把握文化創意在新技術影響下的新特點,掌握新技術應用的核心。為此,數字出版專業的專業認知實習就不是淺嘗輒止的參觀體驗,而應是貫徹四年的、進階式的實習過程。
上述三個方面,可謂是數字出版專業的新內涵。這些內涵的確是在劇烈變革中必然產生的,也勢必對專業建設提出變革性的要求。下面,我們就著重談談數字出版專業的內涵建設問題。
3 數字出版專業內涵建設的基本方略
一個專業內涵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的任務自不可能作全面的探討,筆者僅就本文提出的一個基本命題—由應對大變局而產生數字出版專業的新內涵—來衍生數字出版專業內涵建設的幾個主要問題。這些問題的主要焦點在于:應變的主體—教師和教育教學管理者—所應賦予的建設責任,以及應變的物質手段—教學平臺和環境—所應具備的條件和要素。
3.1 數字出版專業的師資隊伍建設
首先,“新文科”的專業精神對師德師風建設提出更高要求。“新文科”既然是在大變局中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交流和認同為己任,那么,“新文科”專業必然是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專業。要培養具有理想主義的人才,要培養具有忘我精神為社會服務的人才,要培養聰明睿智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才,無疑需要一支具有信仰堅定、情操高尚、胸懷寬廣的教師隊伍。“新文科”專業的教師,應成為崇高理想的信仰者,社會思想的引領者,社會變革的指導者,這實際上也是數字出版專業教師的師德要求。
其次,數字出版專業的多元融合性,不僅需要建立一支多學科融合的師資隊伍,還需要每一位教師具有多學科知識的學習能力。比如上述舉例提到的中南地區某高校,其跨學科的師資隊伍組合的思考邏輯就在于:作為數字技術革命的產物,數字出版專業自然離不開計算機科學;而作為提供文化知識商品的出版,經濟學和管理學是必要的背景知識;當然,作為內容生產者,文學和新聞傳播學是其主干支撐;特別地,作為新冠疫情時代而生發的諸多社會問題、傳播問題,醫學、公共衛生學也是重要的素養。當然,該高校的數字出版專業教師結構的形成,與其數字出版專業定位與學校本身具有強大理、工、醫學科背景有關。其實,不同高校的數字出版專業可以有自己的定位,教師隊伍中的學科組合自然沒有一定之規,但是,文理交融、多元組合恐怕是數字出版專業的必然要求。
第三,數字技術的日新月異和數字出版專業極強的實操性,要求建構一支“學界”“業界”相融合的“雙師型”隊伍。傳統的新聞傳播學專業也重視對業界教師的吸納,通常做法是把有豐富業界經驗且有一定理論素養的教師直接調入學校作為專任教師;后來,發現這一做法還不能很好滿足加強學生實踐經驗訓練的需要,就有了所謂的“掛職”制度。但是,面對當下數字技術的極速發展以及媒介形態的極速演化,上述方案明顯“遠水不解近渴”。為此,筆者認為,相對較優的辦法是在數字出版專業中實行“雙導師”制度:即在互聯網企業、新媒體企業乃至新聞出版業中聘請技術人才和經營人才,作為校外導師,與校內專任教師共同定點指導學生。特別是在實踐課程中,業界導師應發揮主導作用。
3.2 更新教育管理理念、創新教學管理制度
數字出版專業的多學科融合,強力挑戰著傳統專業設置邏輯下形成的教育管理理念和教學管理制度。我們應該認識到,“融合”并非“組合”,也就是說,并非在某一專業中開設一些其他專業的課程就達到了“融合”—事實上,有許多高校和許多專業都做過學科交叉融合的改革與嘗試,但總體來看,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究其根本在于,教育教學改革在理念上并未達成與學科融合時代相適應的共識。這里,筆者想從三個方面來討論。
一是要打破“專業主干課程”與非“專業主干課程”之間的界限。既然傳統的專業設置是以專屬行業或特定研究對象為依據的,為培養專屬行業經驗技能或基于特定學科研究對象而開設的系列課程就稱之為“主干課程”。但是,新文科的專業打破了行業邊界,泛化了研究對象,那么,新文科專業的課程體系就應該像一塊“集成電路”—不同課程的內容相互交織滲透,相互牽扯而不能獨立。就數字出版專業而言,數字技術應用類的課程、社會分析方法類的課程、內容生產和傳播類的課程應該是互相包含的—既要學會用數字技術分析社會問題,也要學會開發能夠分析社會問題的數字技術;不僅要知道怎樣的內容產品能夠引導社會的良性運行,也要知道內容產品應該通過怎樣有效的數字技術進行傳播;等等。因此,在課程設置的模塊中,不同課程之間的課時分配就不能按照主干課程和非主干課程的比例予以劃分,而是要考慮課程內容的關聯度予以重新計算。尤其不同課程的內容設計不再是獨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相互關聯的。因此,相應的教材編寫和備課工作,也應當要求不同課程的教師相互協同、密切溝通。
二是要打破課堂內外的界限。既然課程模塊中打破了主干課程與非主干課程的界限,打破了課程之間的相對獨立性,那么,每門課程的課堂教學學時就不可能再依照既有的課程學時比例予以分配。對于新文科專業而言,各門課程之間的學習相互關聯,需要掌握的知識門類急劇增加,因此,企圖靠課程教授完成一個專業所需要的基本知識訓練顯然力有不逮。我們必須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完成這種新的應對挑戰的任務:首先,要充分調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以自主學習為主,課堂教授為輔,由此才能讓學生從容地接納爆炸式的知識輸入;其次,要大量引進外專業、外校的智力參與教學工作,就目前而言,似乎沒有哪一所大學或哪一個專業能夠儲備足夠的多學科融合的教師,因此,許多課程的教學一定要廣泛從外引進多元知識背景的教師,共同參與完成授課任務;第三,要打破行政班級的界限,要讓學生擁有依據自己的興趣、需要自主選課的權利。所有這一切,在教學管理上,就需要打破課堂內外的邊界—不能再機械地執行統一課表制度,而應當由課程負責老師根據不同的教學需要靈活安排課堂的時間和地點,也要讓學生有更大的學習時間安排自主權。
三是要把教學任務設計和教學安排權力下放到院系。一旦打破上述兩個邊界,我們就會看到,再讓學校—特別是大型的綜合性大學—來統一安排教學過程是無法有效實施各類教學改革的。應該把教學安排的自主權下放到學院一級,最好是系一級—這里的系指的是以一個專業作為教學組織單位的機構。因為只有系,才最了解自己的專業特性和具體的教學要求;也只有系,才能最高效地與任課教師就教學安排進行溝通。在一個學院,或一個系里,能夠靈活地進行彈性的教學管理:具體一個教學單元需要多少課時?具體請哪些校外的教授在何時何地上課?一門課程需要多少實習時間?在哪兒實習?哪個單位在什么時間能夠接待實習?等等。這些都不可能在一張統一的課表上事先規定,而必須是因人因時因地靈活處置。因此,必須要在觀念上和管理上進行創新,改變傳統的由上而下的教學安排管轄權。我們總說要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殊不知,自主學習能力來自學生的自主學習管理;學生的自主學習管理依靠的是教師的教學自主安排,而教師的教學自主安排就需要院系的教學管理自主權予以保障。
3.3 重視教學平臺建設
“新文科”是需要“花錢”的。“新文科”與傳統文科在學習過程中的最大不同,就是技術應用的訓練成為“文科”學生的核心科目之一。技術應用的訓練帶來兩個方面的平臺建設:一是校內實驗設備和實驗室的建設,二是校外技術實訓和實習平臺的建設。
我們已經無法避免高新技術對文科教學的全面滲透,如智能設備對新聞寫作的深刻影響,融媒體系統對內容生產帶來的變革,大數據分析對社會研究的核心支持等,使“新文科”學生成為“眼觀社會,手拿書本,肩扛設備”的全副武裝的“特種兵”。對數字出版專業而言,智能采編系統、大數據的市場分析和輿情監控系統、情景體驗式的虛擬仿真系統等,都是培養核心能力的利器。因此,引入最先進的智能數字設備,建構多功能的融媒體平臺,是“新文科”的數字出版專業所必需的。
數字技術日新月異的變化,又帶來另外一個嚴峻的問題:花費大量資金建立的技術教學平臺可能面臨著很快過時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讓學校的實驗室平臺與業界的實務平臺良好接入,使其能與業界實務平臺同步升級。因此,學校應大力加強與行業中先進企業的產學研一體化建設,不僅為學生提供實踐基地,更重要的是與學校的實驗室平臺兼容。如此,學校的教學過程可以容納到企業的工作流程中—特別是對文化產品的生產,數字化的文化產品可以大量讓學生以實習的方式參與制造。同時,企業也能從中受益。這是因為:數字化產品制造的失敗不會造成物理上的損失,同時,學生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可以提升企業的文化創意品質。
數字出版專業極強的實踐性,也特別需要學校與先進企業建立穩固的實踐基地。學校應當采取有效的激勵措施,調動企業參與教學實習基地的建設。上述的“雙導師”制度可以是一項措施,此外,學校還需要在科研指導、人力資源培訓以及資金配套等方面給予參與實習基地建設單位有力的支持。
4 結 語
數字出版專業是“新文科”建設事業中誕生的一個嶄新的專業,我們不能簡單地通過課程體系的重新設置來完成這一專業的建構。數字出版專業的建設,關乎我國高校文理融合的教學改革,關乎數字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相互拓展研究領域和應用場域,關乎我們培育出來的一代“新文科”人才能夠有足夠能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引領中國文化的發展。因此,不僅要看到我們在建設一個新專業,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認識到,我們在開展一項革命性的教育教學新事業—芬蘭連傳統的中小學課程都敢于嘗試廢除,難道我們秉承新時代高等教育改革新理念的“新文科”建設,還需要束縛在傳統的專業教學模式中嗎?
注 釋
[1][4]白寅,帥才.基于融媒體發展的新文科專業內涵及其人才培養規格[J].中國編輯,2020(2-3):102-106
[2]李曉丹,賀子岳.論出版概念的“變”與“通”[J].出版科學,2020,28(4):54-61
[3]張新新.數字出版概念述評與新解:數字出版概念20年綜述與思考[J].科技與出版,2020(7):43-56
(收稿日期:20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