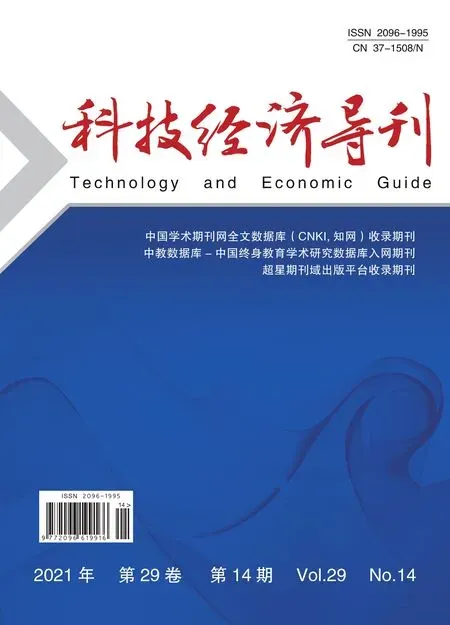談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時空效應
張 明
(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財政局,山東 濟南250300)
自步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步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但同時我國的內部發展差異也逐漸加大,城鄉居民收入比例嚴重失控。在1977年我國的城鄉收入比為2.47,但在2017年城鄉收入比已上漲至2.73。我國的城鄉收入差是整個亞洲最大的,我國西部地區的收入指數明顯高于中東部[1]。掌握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差異發展過程,是有助于合理縮進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
1. 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時空效應的研究設計
1.1 研究方法
判斷事物是否出現了空間集聚或溢出的重要依據即是空間自相關,此方法用于檢驗地區屬性值和鄰近地區是否存在較為顯著的相互作用,通過此分析來反映研究課題的空間分布情況和時間演化特征。

此公式用于研究區域內各單元間的關聯度和顯著性,進而研究變量的空間分布情況。I為雙變量空間相關系數,X和Y為區域屬性,n為樣本總量,s為樣本方差[2]。
1.2 數據總結和指標選取
根據2005~2017年中國各省數據進行分析比較,變量說明見下表1。

表1 變量說明

此公式中pi j代表城鄉總收入,Z為人口總數,IJ為標量,各地區按相應消費價格進行適當調整[3]。
2. 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時空效應的實證分析
2.1 時空格局分析
通過處理2005~2017年的數據,整理得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整體上來說東部地區的收入差距不高,但中部和西部有較高差距,具體表現為沿海向內陸梯度遞增的分布情況,區域間差距較少,沿海地區優勢明顯。而政府支出比例在西部地區偏高,東部地區相對較少。
2.2 空間關聯性分析

表2 2005~201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政府財政支出的莫蘭值
由表2可以看出,莫蘭指數全部通過了百分之一的水平檢驗,這說明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政府財政支出各自都存在空間集聚現象并呈現階段性波動的特征,上升期空間依賴性不強,下降期間則逐漸減弱,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財政支出空間依賴性存在波動,上升和下降時波動頻率較高,總體上來看,數據呈上升后下降的勢頭,在2009年莫蘭值攀升到巔峰,說明了這種依賴性正在逐漸減弱。
2.3 效應分析

表3 模型檢查結果
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的空間性表明了兩者間顯著的關聯性。模型的合理選擇是結果檢驗成功的有效前提,通過朗日系數和拉格朗日系數進行對空間形式判斷,選擇哪一種模型,通過瓦爾德檢驗和似然比檢驗判斷模型是否可以退化。從表3分析得出 ,拉格朗日系數和拉格朗日乘數都超過了0.05指數的監測水準。而瓦爾德檢驗和似然比檢驗都通過了0.01的標準提高,表現為拒絕假設退化[6]。
3. 總結討論
通過對于2005~2017年的省級數據統計分析,結合DSDM模型進行研究,本文深入剖析了財政支出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時空效應。可以進而得出以下結論。我國各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正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以東部地區最低,向西部地區逐漸增高,越靠近西部,收入差距越大。進一步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降低是保證我國高速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我國各個省的收入差距會間接導致鄰近地區的經濟差距擴大,差距較高的地區對周邊地負向影響問題嚴重,內部溢出效應相對較為明顯,呈現出空間集聚的特征。財政支出占比的提高會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極大的影響,根據不同的支出情況,收入差距也會相應變化,當發生教育支出加大、城市化率增高的情況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會進一步縮小,而當鄰近地區出現財政支出增高時,又會加劇本地的經濟動蕩形式。國家想要改善當前的這種惡性情況,需要加強各個地方間的相互學習與溝通,制定政策時,要根據自身情況,合理制定計劃,進而保持經濟的穩步提升[7]。
在制度安排上要改變財政支出模式,加強對農村鄉鎮的投入力度,扭轉當地政府對發達地區傾向性投入政策,將城市公共服務均勻分布在各個地區。大力開展對農業的支持建設,在確保農用財政基金每年穩步上升的情況下,提高用于農村發展的資金投入,開展鄉村旅游業,進而讓城市居民和鄉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降低。不僅如此,政府還要對農業的補貼,資助金額逐步加大。以生產的方式分次投入,盡可能地保證每一戶、每一人都能享受到政府的福利,確保能夠真真正正地提升農民收入。加大農村城市化建設,將公共運輸、公共服務、公共設施等深入優化,不僅為農村生活的方便快捷、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還進一步推動城鄉一體化,縮小兩者的經濟差。加強監督、完善政策,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8]。
4. 結語
由上述總結可發現,財政支出的提高會加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但隨著時代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正逐年下降,加強對財政支出的控制可以有效減緩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長趨勢,對財政資金的支出進行合理的規劃,依照不同類別的支出進行相應的政策制定。將每年的數據進行系統嚴謹的整合,進而不斷優化政策措施,一定可以將我國內部經濟差大幅度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