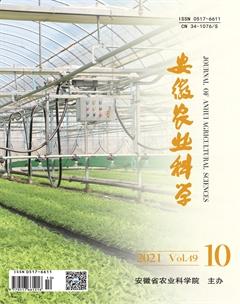研究性教學模式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的改革探析
王玉 徐倩倩
摘要 近年來,研究性教學模式作為提升教學質量的一種有效手段,已經被各大高校廣泛應用。針對遺傳學實驗教學中存在的綜合性實驗少、教學內容與專業特色結合不緊密、教學方式單一、考核方式不合理等諸多問題,闡述了研究性教學模式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改革的具體措施,并在日常的實驗教學中加以實踐和總結,為高等農林院校遺傳學實驗的教學改革提供參考。
關鍵詞 高等農林院校;遺傳學實驗;研究性教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 S-0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21)10-0268-02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0.069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Analysis on the Reform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in Genet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
WANG Yu,XU Qian-qi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3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universities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genetics experiment teaching,such as few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not clos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single teaching method and unreasonable assessment method.We put forward concrete measures to reform research-based teaching mode in genet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summarize and practice it in the daily experiment teaching.We expect our resear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genet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
Key words Highe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Genetic experiment;Research-based teaching;Educational reform
遺傳學是生命科學的基礎性分支學科,不僅理論性強、涵蓋面廣,而且與實際緊密聯系、發展迅速。遺傳學實驗是遺傳學教學中重要的課程內容,不僅能有效地幫助學生掌握基礎理論知識,還能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思維能力、創新能力等綜合素質[1]。隨著遺傳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遺傳學實驗課堂不能再以單純的驗證性實驗內容為主,而是要結合專業特色,不斷創新教學的方式方法。研究性教學模式作為提升實驗教學質量的一種有效途徑和方法,已被各大高校應用到實驗教學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3]。研究性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主體,在一定的教學情境中教師加以引導,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和科研興趣,通過自主學習、探究和小組交流合作的方式,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并獲取知識的能力[4-5]。目前,各高等農林院校的遺傳學實驗教學大多數仍然是以教師講解示范,學生照搬模仿的傳統教學方式為主。筆者針對遺傳學實驗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把研究性教學模式引入實驗教學中,結合研究性教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并在實際教學中加以實踐和總結,努力推動高等農林院校遺傳學實驗的教學改革。
1 遺傳學實驗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1 驗證性和單一性實驗較多,應用性和綜合性實驗較少 遺傳學實驗內容的選擇一般是圍繞遺傳學的理論課程進行開展,目的是加深學生對基礎理論知識的理解和記憶。由于每個實驗僅僅安排了3學時,學生只能進行簡單的驗證性實驗,選擇的實驗內容往往是實驗材料易獲取、操作簡單、實驗現象明顯的項目,每個實驗之間是獨立的,對于應用性和綜合性實驗的開展相對較少,不利于提高學生的實驗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性思維和科研素養。
1.2 教學內容偏基礎,與本專業特色結合不緊密 遺傳學實驗是圍繞分離定律、自由組合定律和連鎖互換定律這三大基本定律開展的,在日常的教學中實驗內容基本固定,包括實驗材料的選取、實驗方法的設計等也一成不變,教學內容偏基礎。授課對象有來自不同院系和不同專業的學生,但授課內容與本專業的結合度不夠緊密,忽略了專業特色的內容。
1.3 教學安排不合理,學生未完整參與到整個實驗過程中 遺傳學實驗教學中有些實驗項目因受課時的限制,實驗樣品的前期處理都是由教師代勞,如用于觀察植物細胞減數分裂的玉米材料的種植、取樣和細胞固定等,學生只是參與到制片和鏡檢觀察的階段,未完整參與到整個實驗過程中,雖然完成了實驗,獲得了教師預期的實驗結果,但卻忽略了實驗興趣的培養,同時不利于鍛煉學生的綜合實驗技能。
1.4 教學方式單一,實驗報告格式化,考核方式不合理
傳統的遺傳學實驗的教學模式是教師對實驗內容進行講解和演示后,學生按照實驗步驟被動地開展實驗,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很少進行積極思考和創新,同時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也比較少,教學方式單一,缺乏創新性。實驗結束后,學生按照教師講的PPT內容將實驗原理、實驗材料、實驗方法和步驟、實驗注意事項這幾個部分進行謄抄,再將自己的實驗結果及討論部分補齊,實驗報告格式化。最后實驗課程考核時,教師的評判標準主要根據學生的實驗報告和平時表現打分,考核方式不合理,沒有體現出對學生的綜合能力的考評,不能真實反映學生的實驗成績。
2 研究性教學模式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的改革措施
2.1 構建研究性教學模式
相比較傳統的教師講授實驗課的理論部分,學生按照既定的實驗過程去動手操作,最終撰寫完成實驗報告,研究性教學模式是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輔,通過合理設計實驗內容和過程來培養學生自主探究學習的能力,通過實驗的開展,學生不僅僅獲得基礎知識和實驗操作技能,還可以培養學習能力以及分析問題、發現問題和系統地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在實驗的過程中還可以加強團隊協作和他人溝通的能力。目前國內外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探索和開展研究性教學模式。研究性教學模式一般分為以下幾個環節[6-8]:①教師提出實驗課題,并把實驗的目的和內容等告知學生;②學生分組,教師指導學生搜集并整理相關實驗課題信息;③每組學生自主設計實驗方案;④教師對學生的實驗設計進行點評和指導完善;⑤教師提供一定的實驗設備和條件,學生開展實驗,并認真觀察記錄實驗的過程和結果;⑥學生對實驗結果進行分析,并撰寫實驗報告或者實驗論文;⑦教師組織各組學生對實驗過程和結果共同進行總結和研討,查漏補缺,進一步加強學生對理論知識的掌握以及學科思維的發散;⑧教師綜合各位同學在實驗環節的表現和實驗結果進行最終的實驗成績評定。
2.2 構建研究性教學內容
目前,安徽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遺傳學實驗針對不同的院系和專業所開設的實驗課有21和24學時的差異性,包括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驗證、遺傳平衡定律的驗證、植物花粉母細胞減數分裂觀察及其制片、果蠅唾腺染色體的制片與觀察等實驗項目,但大多數都是驗證性實驗,內容較為單一,對于學生綜合實驗技能和創新思維的培養不利。因此,可以在保留一定比例經典的驗證性實驗的基礎上,結合學生的專業特色多開設一些綜合性、學生自主設計的實驗課程。其中驗證性實驗是較基礎的實驗,主要是培養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和實驗技能,同時也是對理論內容的進一步驗證和加深認識。而綜合性實驗可以遵循研究性教學模式,讓學生從實驗的設計,到實驗的開展以及實驗的反思等環節全程參與,在這個過程中學生不僅可以小組分工合作,討論設計實驗方案,而且在遇到問題時,通過自主思考、動手查閱參考文獻,來強化自主學習,從而讓學生對實驗課充滿了無限的渴望,激發學生的自主探索和創新能力。例如學生自主設計理化因素誘發染色體結構變異這一實驗時,擺脫了傳統的通過半致死劑量Co60γ射線處理蠶豆種子的單一方式,而是通過聯系生活,采用污水、洗潔精、農藥、紫外線等更加豐富多樣的方式處理不同的材料。通過構建研究性教學內容,以自主學習、探究和小組交流合作的方式,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并獲取知識的能力,這些能力對于學生以后讀研或是工作都大有幫助。
2.3 構建研究性教學的評價體系
研究性教學模式的教學改革還必須有與之配套的評價體系才能確保教育目標的實現。評價體系的主體要多元化,不僅是教師,也需要學生的參與,同時評價內容和評價標準也要具有多樣化。首先,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收集學生在實驗教學過程中每個環節的評價和反饋,并做好相關記錄,根據相關信息,及時調整和改進教學方式和內容,這是一個不斷促進和完善研究性教學的重要環節。其次,學生作為實驗教學的主體,教師也要教會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去進行自身的評價和反思總結工作,一方面包括對整個教學過程、教學環節的評價和反饋,另一方面對自身的實驗環節的設計、問題的解決、實驗結果的分析等環節進行評價,這個過程可以提升學生對新知識的探索興趣,訓練學生的科研思維和技能,使學生獲得更好的學習體驗感和成就感。最后,評價的內容和標準要靈活多樣化,打破以往固定的單一標準來進行評價,比如學生設計理化因素誘發染色體結構變異的實驗時,要更加注重學生的實驗設計和創新性,而不是以最后的實驗結果作為評判的主要參考。通過建立有效的研究性教學的評價體系,教與學有機銜接,相互促進和融合。
2.4 構建研究性教學的師資隊伍
傳統的遺傳學實驗課教學模式中,教師教授實驗課的理論部分,學生按照既定的實驗步驟去進行操作,實驗結果往往是教師已知的,但是在研究性教學模式下,學生自主設計的實驗方案,最終的實驗結果一般是不確定和未知的,教師面對這樣的教學模式的改革,就需要做出改變,構建研究性教學的師資隊伍是遺傳學實驗教學模式改革的關鍵。
第一,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與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性教學是學生自主探究的教學模式。教師要立足于新課改的要求,重視學生在實驗教學中的主體地位,讓學生參與到教學活動的每一個環節,而教師要轉變為授業解惑者的角色,培養學生積極思考、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以及創新思維的能力。同時教師要將科研和本科生的遺傳學實驗教學有機結合起來,培養學生的實驗技能和科研思維能力。
第二,教師要不斷完善研究性教學模式的內容,加強自身專業技能的學習。“要給學生一杯水,教師要有一桶水”,構建良好的研究性教學師資隊伍,就要求教師在日常的教學課程中不斷地積累教學經驗,豐富自身的知識結構,多聽取教研室其他優秀教師的課程,不斷完善遺傳學實驗的教學方法。同時在學生開展實驗過程中要做好詳細記錄,并整理和總結問題,及時和學生溝通交流,根據不同專業的學生需求,靈活多樣的改變教學方法和內容,創建研究性教學模式下的新型師生關系。
2.5 構建完善的實驗室開放管理機制
研究性遺傳學實驗教學模式的開展,必須有完善的實驗室開放管理機制與之配套服務。傳統的實驗教學模式中學生只在規定的上課時間內開展實驗,而研究性教學模式就要求遺傳學實驗室配套相關的實驗儀器和實驗試劑耗材,還要求工作時間內實驗室相關平臺要全天開放提供給學生使用,同時還要建立完善的儀器預約和使用的管理制度等[9]。目前,安徽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對于大型儀器都安裝了儀器保護卡裝置,生物技術中心和儀器共享平臺也可以正常預約使用,另外遺傳學實驗室還采購了一批數碼顯微鏡互動的教學系統,教師不僅可以在教師電腦端控制演示,發放作業下達教學指令,還可以及時就學生的實驗結果進行講解,與傳統的顯微鏡相比,學生能更加直觀地在電腦上觀察顯微鏡下的圖像,如減數分裂的各時期細胞分裂相等,方便學生將圖片保存和繪圖。完善的實
驗室開放管理機制不僅有利于研究性教學模式的改革,還可以為學生的校、省、國家3級的大創類項目、“互聯網+”等大學生競賽課題提供一定的支持和保障,促進學生的自主探究學習和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
3 結語
高等農林院校中的遺傳學實驗在遺傳學教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新課改的推進,研究性教學模式能夠有效地解決實驗教學中存在的綜合性實驗少、教學內容與專業特色結合不緊密、教學方式單一、考核方式不合理等諸多問題,已經被各大高校廣泛應用。在推進教學改革的過程中,研究性實驗教學模式仍然存在一些挑戰[10],例如實驗室平臺的日常維護和管理需要花費教師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同時教師要不斷總結和更新自己的知識,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指導等,所以研究性實驗教學模式還需要教師不斷地去完善和革新。總之,研究性教學模式作為遺傳學實驗教學改革的有效措施,創建了新型的師生關系,培養了學生的實驗技能和科研思維,促進了創新人才的培養。
參考文獻
[1]
李華東,梅志遠,白雪飛.研究性教學模式在實驗課程中的應用研究[J].實驗教學與儀器,2017,34(2):19-20,27.
[2] 楊春玲,朱敏,張巖.數字電子技術基礎研究性教學方法的探索與實踐[J].中國大學教學,2014(2):58-60,74.
[3] 楊宏偉.強化實踐環節,促進研究性教學與素質教育相結合[J].實驗技術與管理,2007,24(1):14-16.
[4] 崔學榮,曹愛請,李娟,等.研究性教學模式在實驗教學方法改革中的應用[J].實驗技術與管理,2016,33(1):176-178.
[5] 劉曉雪,田中偉,馮金俠,等.研究性教學模式在實驗教學中的改革和應用:以遺傳學實驗為例[J].高校實驗室科學技術,2019(1):47-48.
[6] 付學琴,陳蘇,龍中兒,等.研究性學習教學模式在微生物實驗教學中的應用[J].高師理科學刊,2018,38(5):94-97,107.
[7] 鮑智娟,邢秀芹,蓋平.遺傳學研究性實驗教學模式探索與創新人才培養[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1,30(1):114-116.
[8] 曹洪恩,王爽,袁樹忠,等.環境分析化學課程研究性教學的實踐與思考[J].安徽農業科學,2019,47(2):274-277.
[9] 劉曉雪,張慧,胡艷,等.植物生產類本科生遺傳學實驗實踐教學模式改革探究[J].高校實驗室工作研究,2016(2):23-25.
[10] 程秀花.高校研究性教學改革瓶頸剖析[J].山東畜牧獸醫,2020,41(6):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