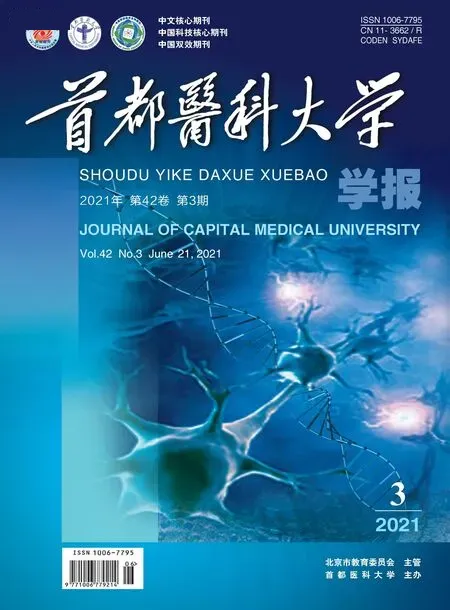神經系統損傷的ANCA相關性血管炎患者14例臨床特點分析
趙瑩瑩 孫金梅 張擁波 許春伶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神經內科, 北京 100050)
抗中性粒細胞胞質抗體(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相關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AAV)是一種少見的以小血管受累為主的系統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包括顯微鏡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tis, MPA),肉芽腫性多血管炎(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GPA)[原稱為韋格納肉芽腫(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G)]和嗜酸性肉芽腫性多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EGPA)(原稱為Churg-Strauss 綜合征)3種類型[1-2]。AAV可發生于任何年齡段,在歐洲其患病率為每年每百萬人20~25例。AAV可影響全身各個部位,最常見的是上呼吸道、肺臟、腎臟、眼以及周圍神經[3],中樞神經系統受累并不多見(<15%)[4]。由于中樞神經系統癥狀的復雜多變,影響了AAV患者的早期診斷,延誤治療,造成患者的不良預后、疾病復發甚至是死亡[4]。本研究總結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近年來AAV合并出現神經系統癥狀和以神經系統癥狀為首發表現的14例AAV患者,通過對其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和影像學檢查資料的分析,提高臨床醫生對AAV的認知,做到早診斷早治療。
1 臨床資料
14例出現神經系統臨床表現的確診AAV患者,診斷均符合1990年美國風濕病學會診斷標準[5]及2012年Chapel Hill血管炎共識會議分類標準[6]。
14例患者中男性7例(50%),女性7例(50%),男女比例1 ∶1。就診年齡53~74歲,平均年齡(64.9±7.31)歲。病程5個月到8年不等,大部分患者病程2~5年。4例患者既往體健; 4例既往患有高血壓病,其中1例同時患有2型糖尿病, 1例同時患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和心房纖顫,1例同時患有高尿酸血癥,1例同時患有高脂血癥和精神分裂癥; 1例既往患有慢性支氣管炎和十二指腸潰瘍;1例既往患有骨質疏松;1例既往患有慢性胰腺炎;1例既往患有肺纖維化;1例既往患有高脂血癥和糖耐量異常;1例既往患有肺結核和腰椎間盤突出。所有患者均無相關疾病家族史。2例患者同時合并繼發性干燥綜合征,其中1例同時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炎。
14例患者中出現中樞神經系統受累患者8例(57.1%)(病例1~8);出現周圍神經系統受累10例(71.4%)(病例5~14);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同時受累4例(28.6%)(病例5~8)。14例患者中MPA 12例(85.7%),GPA 2例(14.3%)。12例MPA患者中累及中樞神經系統6例(50.0%),累及周圍神經系統9例(75.0%),同時累及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3例(25.0%),除神經系統以外不同程度累及肺臟和/或腎臟。2例GPA患者均累及中樞神經系統,其中1例同時累及周圍神經系統。2例GPA患者均存在廣泛全身系統受累,包括肺臟、腎臟、五官(病例4累及耳,病例7累及眼)和關節肌肉。除1例GPA患者為胞質型-ANCA(cytoplasmic pattern-ANCA, c-ANCA)陽性(7.1%),其余13例患者均為核周型-ANCA(perinuclear pattern-ANCA, p-ANCA)陽性(92.9%)。髓過氧化物酶-IgG(myeloperoxidase, MPO-IgG)陽性12例(85.7%), 蛋白酶3-IgG(proteinase 3, PR3-IgG)陽性2例(14.3%),其中MPO-IgG、PR3-IgG均陰性1例,MPO-IgG、PR3-IgG均陽性1例。所有患者均完善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抗可溶性抗原抗體(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antibodies, ENA)、類風濕因子、抗鏈“O”及免疫球蛋白+補體,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和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檢查,其中2例患者抗干燥綜合征抗原(Sj?gren syndrome antigen,SSA)抗體陽性,1例抗核糖核蛋白(ribonucleoprotein, RNP)抗體陽性,1例抗鏈“O” 升高,7例患者類風濕因子升高,7例患者IgG升高,其中合并IgA升高3例,所有患者均出現CRP升高和ESR增快,詳見表1和2。

表1 出現神經系統表現的AAV患者臨床特點概況

表2 出現神經系統表現的AAV患者實驗室檢查結果

續表2
8例累及中樞神經系統的患者中,腦梗死7例(87.5%),腦出血2例(25.0%),蛛網膜下腔出血1例(12.5%),腦膜炎1例(12.5%)。其中3例(37.5%)患者反復發作中樞神經系統病變,病例1首先出現蛛網膜下腔出血,診斷AAV后拒絕治療,1個月內出現腦出血(圖1),病例4先后出現2次腦梗死和2次腦出血,病例8先后出現2次腦梗死(圖2)。病例3同時出現腦梗死和腦膜炎改變。臨床表現主要包括肢體無力、肢體麻木、癲癇發作、記憶力減退和精神障礙。頭顱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或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顯示2例患者的顱內病變分布在單側大腦半球;其余6例患者的顱內病變分布在雙側大腦半球不同區域及腦干,非單一血管供血范圍。2例患者未完善腦血管相關檢查,1例患者頭頸部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提示輕微腦動脈狹窄,其余5例患者均未發現與顱內病變部位相關的責任血管病變,詳見表3。

圖1 病例1,女性,60歲,頭顱影像學

表3 8例中樞神經系統受累的AAV患者的臨床特點

圖2 病例8,男性,66歲,頭顱影像學
周圍神經系統受累的患者多表現為肢體麻木、疼痛。10例累及周圍神經系統的患者中9例為肌電圖證實的周圍神經受損,1例僅表現為四肢麻木,未完善肌電圖檢查。肌電圖檢查提示患者存在多發性單神經病、單神經病、多發性神經病三種表現形式,其中大部分患者以多發性單神經病為主要表現,運動感覺均有受累,髓鞘和軸索均有損傷,以軸索為主,詳見表4。病例5肌電圖呈動態變化,最初僅為單神經損害,隨著疾病進展,逐漸發展為多發性單神經病,損傷程度亦不斷加重。病例13肌電圖表現為多發性神經病,呈長度依賴性,但同時合并糖尿病。病例9完善了腰椎穿刺腦脊液化驗、神經活檢和腎臟活檢。腰椎穿刺壓力160 mmH2O(1 mmH2O=9.8 Pa),白細胞(white blood cell,WBC) 2×106/L,蛋白47.16 mg/dl(正常15~45 mg/dl),免疫球蛋白G 82.6 mg/L(正常0~34 mg/L),寡克隆區帶陰性,腦脊液的IgG鞘內合成率9.06mg/24 h(正常<7.0 mg/24 h),腦脊液髓鞘堿性蛋白 9.09 μg/L(正常<3.5 μg/L),血髓鞘堿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 MBP)9.39 μg/L(正常<2.5 μg/L)。血和腦脊液副腫瘤相關抗體、神經節苷脂譜抗體均陰性。神經病理提示:周圍神經的主要病理改變是出現有髓神經纖維中重度丟失,較多軸索變性,個別再生簇結構,伴隨神經內衣水腫改變,符合急性軸索性周圍神經病的病理改變特點,不同束間病變分布不均;腎臟病理提示:腎穿刺組織可見30個腎小球,6個小球缺血性硬化,1個小球細胞纖維性新月體形成,其余小球系膜細胞和基質輕度節段增生,腎小管上皮細胞顆粒變性,約25%腎小管萎縮,約25%腎間質纖維化,小動脈壁增厚伴玻璃樣變性。符合腎小球輕微病變(圖3)。

表4 10例周圍神經受累的AAV患者的臨床特點

圖3 病例9,男性,53歲,神經活檢和腎臟活檢
14例患者中有3例(病例1、9和10)是以神經系統表現為首發癥狀就診于神經內科,經檢查發現已合并出現肺臟和/或腎臟受累。其中病例1為中樞神經系統受累,病例9和10為周圍神經系統受累。
除1例發現胸腺瘤患者僅給予對癥營養神經治療外,其余13例患者均給予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劑治療,10例患者給予激素加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1例患者給予激素加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P),2例患者僅給予激素治療。經治療后9例(64.3%)患者臨床癥狀有所好轉,2例(14.3%)患者臨床癥狀無明顯改善,2例(14.3%)患者遺留神經系統后遺癥,包括肌無力、肌萎縮、肢體麻木疼痛。1例(7.1%)GPA患者呈反復發作,多次住院治療。所有患者隨訪截至2020年12月31日,無患者死亡。
2 討論
AAV的發病無性別傾向,大部分研究[7]顯示男性發病較女性稍有增多,男女比率1.07~1.48。隨著年齡增長發病率有所增加,近年來發病年齡峰值呈逐漸上升趨勢,由55~64歲上升至84歲,可能與檢查技術手段和對疾病的認識水平提高相關[7]。本研究顯示在出現神經系統臨床癥狀的AAV患者當中男女比例相當,平均年齡(64.9±7.31)歲。神經系統受累在AAV患者當中并不少見,可發生在疾病的任何階段,GPA患者中的發生率為22%~54%,MPA患者中的發生率為34%~72%。中樞神經系統受累占所有AAV患者不到15%[4],周圍神經損傷更多見。本研究中14例出現神經系統表現的患者占同期醫院確診的146例AAV患者的9.6%(14/146),中樞神經系統受累5.5%(8/146),周圍神經受累6.8%(10/146),由此可見中樞神經系統與周圍神經損傷比例相當。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AAV患者由于呼吸系統、腎臟受累就診于呼吸科、感染科和腎內科而被確診,且既往研究[4]顯示,中樞神經損傷通常發生在疾病的晚期,本研究顯示個別患者可以中樞或周圍神經系統損傷作為首發癥狀起病,并且臨床癥狀無特異性,容易與其他神經系統疾病相混淆。且該研究者[4]認為“局限于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AAV”可能是AAV的一種特殊亞型。
AAV出現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可能機制為:(1)炎癥反應增加了顱內小血管的通透性或引起血管阻塞;(2)臨近結構肉芽腫病變的侵犯或壓迫;(3)中樞神經系統內產生的肉芽腫性病變[4]。臨床上可出現腦梗死、腦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肥厚性硬腦膜炎、肉芽腫樣占位性病變、脊髓病變等等[8-13]。本研究顯示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AAV患者中腦梗死最常見,其次為出血性腦血管病(包括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腦膜炎最少,與既往文獻[14]報道一致。腦梗死臨床表現無特異,多為肢體無力、麻木,部分患者出現記憶力下降、精神障礙,個別患者可出現癲癇發作。影像學檢查顯示病灶呈腔隙性梗死灶,多數患者梗死灶分布范圍較廣,同時累及雙側前循環,個別同時伴有后循環梗死,不符合單一血管分布區,且血管檢查未發現嚴重大動脈狹窄的證據,符合AAV廣泛小血管損傷的特點。另有報道[8]顯示,AAV患者也可表現為大面積梗死并出血轉化。尸檢顯示患者病理改變為壞死性小血管炎[15]。此外,還有研究者[4]發現有頭顱MRI T2加權像廣泛分布的非特異性白質高信號,包括側腦室旁、皮質下、基底節區、中腦和腦橋,通常與患者認知損害相關。AAV患者發生腦梗死后給予抗血栓治療需謹慎,因小血管炎性改變導致通透性增加,患者出血風險也相應增加。有報道[16]給予1例伴有低熱、肌痛、盜汗、皮疹的缺血性卒中患者進行tPA靜脈溶栓后出現出血轉化,患者病情進展加重,最終檢查確診為AAV。出血性腦血管病臨床表現及影像多無特異性,需完善全面檢查,排除其他疾病。文獻[11]報道,AAV可導致肥厚性硬腦膜炎,而本研究中1例患者頭顱MRI顯示軟腦膜強化,完善腰椎穿刺排除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推測與軟腦膜血管炎癥相關。由于中樞神經系統活檢病理較難獲得,因此患者顱內病變缺乏病理診斷的支持,但患者給予傳統腦血管病治療效果欠佳,給予激素和免疫抑制劑治療好轉可協助臨床醫生評判診斷的正確性。
AAV周圍神經損傷最初表現為急性起病的遠端肢體麻木疼痛,常多見于下肢。病初感覺異常分布區符合多發性單神經病,也有小部分患者表現為多發性神經病。隨著病情進展,多發性單神經病最終演變為對稱性或非對稱性多發性神經病。肌無力程度和對稱性各異,可能主要累及感覺受累肢體的遠端。病初無明顯肌萎縮,隨著病情進展可出現肌萎縮。腦脊液化驗顯示細胞數和蛋白正常。病理改變主要是因血管炎導致缺血而產生的軸索變性,有髓纖維的減少或喪失,神經纖維密度減低,脫髓鞘改變相對較輕,偶見再生簇。盡管血管壁炎癥損傷是鑒別血管炎性神經病的主要表現,但實際檢出率并不高[17-18]。本研究中周圍神經損傷患者臨床特點與既往文獻[18]報道相似。臨床上以肢體麻木疼痛,肌無力、肌萎縮為主要表現,肌電圖檢查提示患者主要表現為多發性單神經病,運動及感覺均有受累,髓鞘和軸索均有損傷,以軸索為主。動態監測肌電圖可發現患者從單神經病發展至多發性單神經病的過程,提示病程初期患者可能僅表現為單神經病。表現為多發性神經病的患者如合并糖尿病則較難鑒別。腦脊液細胞數正常,蛋白、免疫球蛋白、鞘內合成率稍有升高,血和腦脊液副腫瘤相關抗體、神經節苷脂譜抗體均陰性,提示存在非特異性神經損傷。神經病理提示炎性細胞浸潤不明顯,有髓神經纖維中重度丟失,較多軸索變性,個別再生簇結構,伴隨神經內衣水腫改變。
本研究14例患者中,12例(85.7%)患者診斷為MPA,無論在中樞神經系統受累還是在周圍神經系統受累患者中MPA均占大多數,與既往報道[14]相一致。MPA和GPA患者中既有中樞神經系統損傷也可以存在周圍神經損傷。GPA患者累及全身系統范圍相對更廣泛。有研究者[14,19]認為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并不影響AAV患者的生存率,合并周圍神經損傷的MPA患者的5年生存率為58%,并非不良預后的預測因素。本研究中大部分患者經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劑治療后有所好轉,少部分患者遺留后遺癥,個別患者臨床上反復發作。
總之,AAV可累及中樞神經系統亦可累及周圍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系統受累略多見,而中樞神經系統損害亦不少見。中樞神經系統可表現為腦梗死或出血性腦血管病等,腦梗死最多見,多為腔隙性梗死灶,分布范圍較廣,不符合單一血管分布區,且多無大動脈嚴重狹窄。由于影像難以顯示小血管病變,活檢病理可明確診斷,但較難獲得。周圍神經損傷主要表現為多發性單神經病,以軸索損傷為主,亦可出現多發性神經病,炎性細胞浸潤檢出率并不高。中樞神經受損和周圍神經受損均可作為AAV首發癥狀出現,而全身其他臟器損傷經詳細檢查后才被發現。因此,臨床醫生需提高對AAV的認識,以免延誤治療,AAV患者經積極治療后多數臨床癥狀可明顯改善,神經系統受累并不影響患者預期生存率,患者不良結局多由于肺、腎功能受損,繼發感染以及心血管事件引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