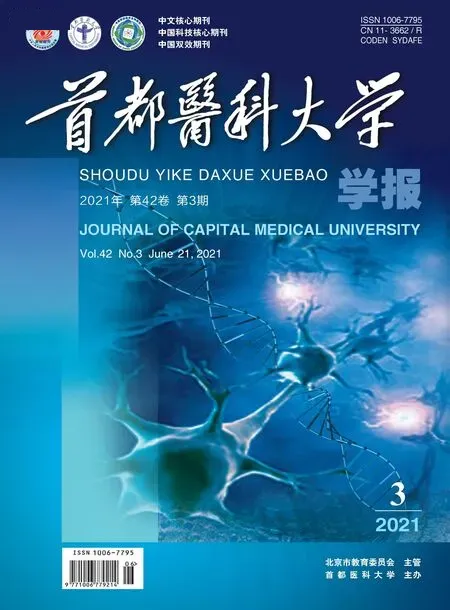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北京市青少年抑郁焦慮情況調查及影響因素
劉珊珊 陳 旭 李亞瓊 袁曉菲 于紅曄 房 萌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精神疾病診斷與治療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8)
新型冠狀病毒對人類來說是一種全新的病原體,其傳播速度快,感染范圍廣,能在短時間內爆發,逐漸波及全球,防控難度空前絕后。2020年1月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已被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研究[2]顯示,抑郁、焦慮、藥物濫用、驚恐發作、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精神問題通常伴隨著重大災害或經濟危機。如果此模式適用于COVID-19,那么這種突發的壓力性事件、長期的緊張恐慌讓人們不時處于緊繃狀態,極易出現各種各樣的精神問題。研究[3-5]顯示,暴露或接近COVID-19的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擾。特別是對于相對脆弱的、缺乏社會經驗的兒童、青少年,感染疫情的風險、社區隔離封鎖、生活方式的改變、疫情對未來學習生活造成的不確定性影響,這些都可能會對他們的心理產生一定的負面沖擊。
兒童、青少年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在這次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極易被忽視。青少年身心成長發育處于關鍵時期,他們對心理和社會轉變非常敏感,很容易受到不良應激源影響,此次疫情可能會讓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更加嚴峻,甚至不排除會帶來長遠損害。抑郁、焦慮是兒童青少年最常見的精神疾病,約有一半的首次抑郁發作出現在青少年時期[6]。研究[7-8]顯示,20%左右的青少年在18歲時會經歷重性抑郁障礙,15~18歲的青少年抑郁癥的終生患病率為11%~14%,如果沒有適當的干預,青少年的抑郁焦慮通常會持續到成年,并且對成年生活有持久影響。Essau等[9]研究發現,青少年時期焦慮癥的存在預示著成年期會出現一系列負面的心理社會問題(例如,工作適應不良、家庭關系、應對技能等)。故無論是家庭、學校,還是社會、政府,均應重視青少年群體的精神健康問題,尤其在COVID-19期間。本研究著重調查了COVID-19疫情期間北京市青少年的抑郁焦慮情況及影響因素,為北京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危機干預提供有價值的數據和科學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7日通過微信“問卷星”平臺,利用滾雪球抽樣方式對北京市初高中青少年進行橫斷面在線調查。調查對象為11~18歲在北京市就讀初中或高中的青少年,且在疫情流行期間居住在北京市。本次調查每個手機號只能參與一次,同時排除了有明顯邏輯錯誤和問卷完成時間低于120 s的數據以保證數據的可靠性,同時剔除年齡11~18歲之外的數據,本研究共有1 142名北京市初高中學生納入分析,其中,男性440例,女性702例,調查對象年齡11~18歲,平均年齡(15.8±1.6)歲。在參加研究前所有研究對象及其監護人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已通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倫理審查,倫理審批號2013科研第(6)號。
1.2 調查內容及方法
1.2.1 調查內容
(1)研究對象的人口統計學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居住地、年級、學校類型等信息。
(2)家庭或疫情相關調查:本項目收集了調查對象父母的職業,是否參與到疫情一線工作,平時是否嚴格執行戴口罩、勤洗手等防護行為。
(3)學習與生活行為習慣:調查研究對象近1周每天睡眠的時間、每天學習的時間、學習效率有無變化以及每天參加體育鍛煉的時間等。
(4)兒童流調用抑郁評定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CES-DC)[10]:是一個簡短、結構化的自我評估量表。CES-DC量表適用于測量6~17歲兒童青少年在近1周內的抑郁癥狀。該問卷包含4個維度(共20 個條目),即抑郁情緒、積極情緒(反向計分)、軀體癥狀和人際關系。分0~3級計分,0分代表“根本沒有”,1分代表“一點”,2分代表“有時”,3分代表“許多”。總分跨越0~60分,得分>15分表明存在抑郁癥狀,得分≥20分提示有明顯的抑郁癥狀。
(5)廣泛性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Scale,GAD-7)[11]:是一個簡明焦慮癥狀自評量表。GAD-7量表由7個條目組成,用來評估過去兩周焦慮癥狀的發生頻率。量表采用4級評分方法,即0分代表“完全沒有”,1分代表“有幾天”,2分代表“一半以上的時間”,3分代表“幾乎每天都有”。總分≥5分提示存在焦慮癥狀。較高的分數代表更嚴重的焦慮癥狀,比如5、10、15分分別被確定為存在輕度、中度和重度焦慮。
1.2.2 調查方法
在線收集研究對象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和臨床特征、與疫情相關的家庭情況調查、學習與生活習慣調查等。利用CES-DC評估研究對象的抑郁癥狀及程度、 GAD-7評估研究對象的焦慮癥狀及程度。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分類資料統計使用卡方檢驗。多因素關聯性分析使用Logistic回歸模型,以探討與抑郁癥狀或焦慮癥狀相關的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1 142名研究對象中,CES-DC得分>15分的有465例,GES-DC得分≥20分的有357例;GAD-7≥5分的有275例,不同分類條件下抑郁組、非抑郁組和焦慮組、非焦慮組之間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和相關變量見表1。15~18歲(抑郁:P=0.001,焦慮:P=0.027)、女性(抑郁:P=0.048,焦慮:P=0.007)、高中(抑郁:P<0.001,焦慮:P=0.030)、每天睡眠時間<6 h(抑郁:P<0.001,焦慮:P<0.001)、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抑郁:P<0.001,焦慮:P<0.001)、每天體育鍛煉的時間<30 min(抑郁:P<0.001;焦慮:P=0.009)的青少年其抑郁癥狀和焦慮癥狀檢出率明顯高于其他組。而學校類型、父母是否為疫情工作一線工作人員、是否執行戴口罩勤洗手等防護行為、近1周每天學習時間的亞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續表1
2.2 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
除外混雜因素影響,進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因變量的賦值依據CES-DC>15分劃分為抑郁組和非抑郁組、依據GAD-7≥5分劃分為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分別建立兩個Logistics回歸模型。自變量為年齡、性別、年級、學校類型、父母是否為一線、是否執行防護、睡眠時間、學習時間、學習效率的變化、體育鍛煉時間。女性(P=0.034)、睡眠時間<6 h(P<0.001)、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P<0.001)、體育鍛煉時間<30 min(P<0.001)是出現抑郁癥狀的獨立因素(表2)。高中(P=0.002)、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P<0.001)、體育鍛煉時間<30 min(P<0.001)是出現焦慮癥狀的獨立因素(表3)。

表2 與抑郁癥狀相關的Logistic 回歸分析

表3 與焦慮癥狀相關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抑郁癥和焦慮癥是青少年很常見的精神疾病,會引起患者軀體不適,認知功能受損、情緒波動、活動異常、社會關系受影響等[12],而COVID-19的爆發及其所帶來的大規模隔離封鎖、社會行為模式的轉變、恐慌、沮喪、焦慮等負面后果無疑加劇了這種風險[3]。此外,抑郁癥和焦慮癥的終生患病率很高,青春期焦慮障礙也會給成年后患焦慮或抑郁障礙帶來較高的風險[13-15]。一項對144 060名中國中學生進行的系統回顧和Meta分析[16]表明,抑郁癥的總患病率為24.3%。此外,據估計,全世界6~18歲的兒童青少年中有6.5%的人群患有11種焦慮亞型中的至少一種[17]。本研究調查的北京市青少年群體中有40.7%的個體存在抑郁癥狀,并且有明顯抑郁癥狀的人群占31.3%。24.1%的人有焦慮癥狀,0.5%的人既有抑郁又有焦慮。本研究結果提示北京市兒童青少年有抑郁癥狀或焦慮癥狀的比例更高,這意味著COVID-19是導致抑郁癥狀和焦慮癥狀出現的危險因素,提示應重視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早期發現和預防對保護青少年精神健康意義重大。
本研究還發現,年齡、性別、年級、睡眠時間、學習效率、體育鍛煉時間與抑郁癥狀和焦慮癥狀的發生顯著相關。其中,女性、睡眠時間短、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每天體育鍛煉時間<30 min是出現抑郁癥狀的獨立因素。高中、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每天體育鍛煉時間<30 min是出現焦慮癥狀的獨立因素。與本研究結果相一致,在流行病學報告[18-20]中,與男性相比,女性患抑郁癥的比率更高,尤其是在青春期。這可能與女性的人格特質或激素變化水平有關,在青春期,女性比男性早熟,思維方式比男性復雜,容易多慮,更容易有內心沖突或受到外界不良因素沖擊,故患病率更高。
另外,本研究觀察到睡眠時間短和較少的體育鍛煉與較高的抑郁風險顯著相關,這與現有文獻[21]結果一致。一項青少年抑郁癥和睡眠剝奪相互作用的研究[21]表明,睡眠量的減少會增加其患抑郁癥的風險,反之,抑郁癥也會增加睡眠減少的風險。另一項納入了8 998名青少年被試的橫斷面研究[22]結果顯示睡眠不足與各個年級學生的抑郁癥均有關聯,而且對高年級學生構成的風險更大。此外,有研究[23]提出適量的體育鍛煉是治療抑郁癥的有效方法,甚至可以作為一種輔助抗抑郁藥治療的可行方式。因此在疫情期間,即使被限制活動甚至隔離在家,也不應忽視體育鍛煉和充足睡眠的重要性。
此外,本研究中高中生與焦慮癥狀發生的風險顯著相關,不難理解,與初中相比,高中的學習難度更大,考試次數增加,還有高考壓力及來自父母的期望,高中生面臨的是巨大的學業壓力和社會壓力,均助長了焦慮的發生[24-25]。此外,本研究結果提示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顯著增加了抑郁癥和焦慮癥發病的風險。在COVID-19疫情期間,很多學校延長放假時間,關閉線下教育轉而改為網絡授課,學生被迫在家、注意力難以集中、缺乏課堂互動、缺乏學習策略很容易導致學習效率低下,進而誘發厭煩、焦慮抑郁情緒,甚至失去學習的興趣。青少年正處于逆反時期,這種相對閉塞的環境和枯燥的學習狀態,再加上父母的不理解,促使青少年產生焦慮情緒。相反,積極的情緒有助于提高學習效率[26],這提示在開展網絡教學時不僅要重視彈性教學、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提高學生們的學習效率,也要積極地開展心理教育及心理疏導工作。
本研究也有一定限制。首先,樣本的納入只有北京市,北京市是經濟相對發達的區域,其教育水平與文化觀念與其他地區有一定差異,因此不能代表全國,結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本研究是在線網絡調查,默認只納入了常使用手機微信的個體。同時也不能排除被試的軀體狀態、既往史、家族史、家庭支持等可能導致抑郁焦慮的混雜因素。進一步可完善以上因素、擴大樣本量,進行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
總之,本研究發現在COVID-19疫情期間,北京市兒童青少年群體存在抑郁癥狀或焦慮癥狀的比例顯著增高。女性、睡眠時間短、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每天體育鍛煉時間<30 min是出現抑郁癥狀的獨立因素。高中、學習效率比疫情發生前低、每天體育鍛煉時間<30 min是出現焦慮癥狀的獨立因素。這提示應重視以上因素,關注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盡早在青少年群體中開展心理危機干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