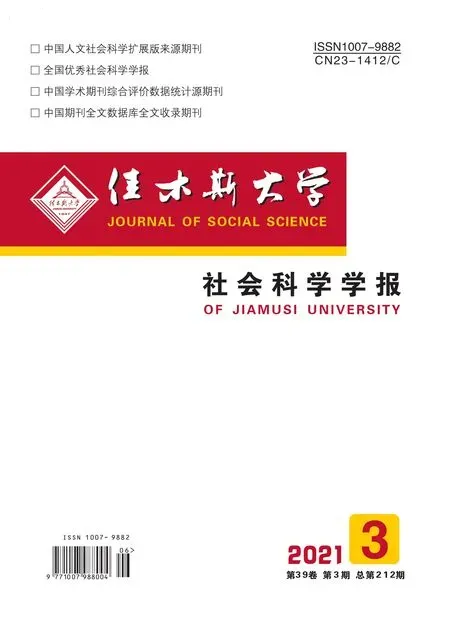環境行為學視角下的老城區廣場“社會向心空間”改造研究*
李 里,儲凱鋒
(安徽理工大學 土木建筑學院,安徽 淮南 232001)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59.58%[1],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逐漸趨于成熟。在此基礎上,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環境不斷得到優化,休閑娛樂方式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但是,快速的城鎮化發展導致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老城區公共空間與市民的精神活動需求之間矛盾重重。
“社會向心空間”(sociopetal space)被心理學家索姆爾(R.Sommer)描述為促進交流、創造一種輕松友好氣氛的心理空間;在物質空間層面是由場所的內向弧形圍合或座位半包圍結構構成,使得空間有利于親密關系的建立[2],以此形成內聚性的方向引導。城市廣場作為傳統城市區域的公共開放空間,可以調節區域土地密度,提高社會交往的有效性,是設計“社會向心空間”、激發城市活力的最佳選擇。本文探究了環境行為學理論下居民公共生活的行為需求與“社會向心空間”構成的邏輯關系,以此對老城區廣場的開放性、空間尺度以及形態進行規劃改造,促進鄰里關系,為老城區公共開放空間的改造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二、老城區廣場“社會向心空間”的研究現狀和問題
早在20世紀70年代,老城的復興就在英國作為一項城市規劃議題提出,英國《牛津詞典》對于“舊城復興”的解釋為旨在為一個地區帶來新的活力,發展新的組織[3]。我國早期的老城公共空間更新研究主要以文化、商業以及生態景觀[4-6]等主題為導向,與市民傳統生活格格不入,缺少人性化設計。2015年12月,我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通過實施城市修補,解決老城區環境品質下降,空間秩序混亂等問題,恢復老城區的功能和活力[7]。
作為城市公共開放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老城區廣場的更新研究開始逐漸向“人本”理念轉移,探討市民集體記憶與空間更新[8]、市民活動與空間特征的關系[9]以及空間適宜性分析[10]等內容,但大多基于現狀進行優化,缺少對“社會向心空間”的綜合性研究:一方面,老城區廣場的使用人群和時間段單一,青壯年毫無參與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對市民生活的深度調研,無法將傳統生活行為與城市規劃、文化宣傳相結合;不僅如此,商業活動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使得商業功能無法和其他人本功能相協調。由此可以看出,現階段老城區廣場的更新不再是單一功能的置換,而是要解決限制條件和不利因素的影響,探討如何減小城市居民之間的距離,塑造新的鄰里親密關系,規劃建設新型“社會向心空間”。
三、基于環境行為學的“社會向心空間”分析研究和基本特征
環境行為學是研究人與周邊不同尺度的空間環境間相互關系的科學[11],通過結合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探討人對不同空間環境產生的反應和情緒,以此研究人群、空間感知以及行為偏好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本文選取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博物館前的城市廣場作為研究對象。身為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城市廣場利用率卻極低,城市公共生活缺乏“煙火氣”。因此,必須通過了解市民群體的行為偏好和空間現狀的關系,總結適合古城傳統生活的“社會向心空間”基本特征。
(一)分析研究
1.場地現狀。近年來,旅游業的發展擴大了壽縣老城區商業和文化空間的面積,城市廣場的建設主要以展示城市形象為主,忽略了市民生活的重要性。現存的壽縣古城平面呈正方形,面積3.65平方公里[12],人口達到10萬以上,具有典型的建筑密度高、人口密度大等特點。城墻的四門相連形成十字,打造出城市商貿文化軸線,沿線分布古城主要的商業、景點和教育資源。研究場地位于西大街的壽縣博物館前,場地的正北方為孔廟和奎光閣。作為展現壽縣歷史文化和城市形象的公共空間,廣場視野開闊,功能單一,平面以博物館的中軸線為中心,左右的景觀和鋪裝呈現出大致對稱的形態。
2.使用人群。如表1所示,由于古城的老齡化嚴重,目前廣場主要的使用人群共分為四類:分別為退休的中老年人、學生、游客以及研究團隊等等。其中,老年人在廣場的停留時間和頻率最長,人數最多,主要以休閑娛樂等活動為主;學生主要來自于附近的中小學,一般于放學后在這里游戲玩樂;游客和學者通常以廣場作為有標志性的集散地,僅僅作短暫的停留和休息,目的較為單一。
3.行為特征。由于中老年人對交流和公共活動的需求較大,因此,由表1可知,根據不同的興趣愛好,老年群體在廣場上呈散點狀分布,主要集中在邊緣墻角和樹下,活動時間段以清晨和傍晚為主。附近的工作人員、散步的市民以及游客由于停留時間較短,因此更傾向于選擇相對安靜、人數較少的地方休息,如樹下、花壇邊以及博物館入口處。而放學后游玩的孩子,由于其活動路徑的規律性小,缺少限制要素,因此活動范圍較大,往往分散在廣場的各個角落。

表1 傳統文化古城鎮的主要游客團體與其行為目的、偏好的對應關系
(二)老城區廣場“社會向心空間”的基本特征
根據分析可知,目前古城廣場缺乏空間的限定和規劃,導致目前的市民活動雜亂而分散,且主要沿邊界分布,空間利用率低,不利于綠化維護。因此,古城廣場“社會向心空間”應具有以下特征:
1.引導性。根據人對交往行為的需求,誘導不同個體進入場地,提升在場地內面對面的幾率,增加聚集和交談的可能性。
2.聚合性。通過塑造圍合和內向型的幾何空間,提高人的安全感和歸屬感。
3.安全性。保障老年人、孩子等特殊群體的安全和健康,遠離道路、集市等容易發生事故的區域,創造積極的空間尺度,提升市民精神狀態。
4.舒適性。空間的設計要根據不同群體的身體和尺度進行人性化的設計,創造優于室內物理環境的室外空間,提高市民外出的幾率。
5.社交性。幫助市民在公共空間中尋找具有共同愛好的群體,激發交流的可能性,增強鄰里的親密度。
四、舊城區城市廣場“社會向心空間”的改造設計研究
通過對老城區廣場使用人群的行為和“社會向心空間”特征的分析總結,可以發現:目前廣場存在封閉性較強,功能簡單以及使用群體缺乏交互行為等不足,因此要分別從廣場和綠地的邊界、樹下以及鋪裝、景觀等不同的方面對空間的圍合性、社交性以及尺度感等進行更新。
(一)圍合性:打破封閉的沿街商業空間
目前,廣場的邊緣主要由用墻隔離出來的沿街商鋪、圍墻以及孔廟遺址的欞星門組成,在視覺上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效果,對人流的引導性較差,必須通過打破邊界吸引更多的人群:第一,重新構建一個內向型的商業空間,通過打斷沿街商業,規劃一個新的廣場入口。第二,將原始的旅館、店鋪改造成向內圍合的院落式休閑餐飲,不僅契合城市年輕人的生活模式,也可以增加休息空間的面積,為更多的年輕群體和游客提供一個舒適的等待和餐飲場所。
(二)社交性:促進交流的休息空間
為了保證廣場展示城市形象的功能,對邊緣綠地和花壇進行了空間拓展,并在邊緣設計了具有高低層次的休息座椅。作為新的交流空間,一方面保護綠化的完整性,增加優化環境的生態空間;另一方面,通過不同的高度,拓展行為的多樣性。老人和孩子可以通過大小、高度更換姿勢,選擇合適的地方打牌、讀書寫字和聊天。不僅如此,座椅由拼接的六邊形構成,通過鈍角空間,增加人群面對面的可能性,刺激社交行為。
(三)尺度感:觸發小群體的微空間
針對有共同愛好的小群體,諸如打牌、跳舞以及聊天等,可以對舒適度較高的樹下空間進行改造:一方面打破原有花壇和綠地的邊界,在樹的周圍設計通道、桌凳以及鋪裝等,讓小群體可以根據人數選擇用于聚集的微空間。另一方面,通過草地和植物的圍合,加強微空間的邊界感和安全性,減少空間內外的相互干擾。
(四)參與性:利用地面鋪裝打造游戲場地
由于原始的場地缺乏游憩功能的規劃,導致兒童的游樂行為往往具有隨機性和突發性。因此,可以通過不同色彩的鋪裝在地面打造兒童的游戲場地,將孩子的游樂空間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減少突發事件的發生。同時,在邊緣綠地與欞星門附近的區域增加與城市文化、歷史有關的游戲景觀小品,不僅強化城市廣場的文化形象和博物館的宣傳功能,增加游客的停留時間和游覽行為,也讓孩子通過游戲的形式認識和學習區域的歷史文化,對傳播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結論
人的社交行為和需求可以通過空間形態、功能和氛圍等特征進行刺激和引導,以此增加城市生活的豐富性和交流性,促進城市活力和經濟的發展。因此,要改造具有社交引導性的“社會向心空間”,應基于環境行為學的理論知識,分析城市廣場的市民群體和行為特征,將行為和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作為規劃依據,總結“社會向心空間”應具有的特征,并針對城市廣場的現狀,提出具有社交聚合性和引導性的空間規劃策略:第一,打破城市廣場邊緣的圍合性;第二,引導并創造內向型空間;第三,增強休閑娛樂空間的交流性;第四,根據不同尺度設計小群體微空間;第五,利用鋪裝和環藝裝置豐富娛樂性和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