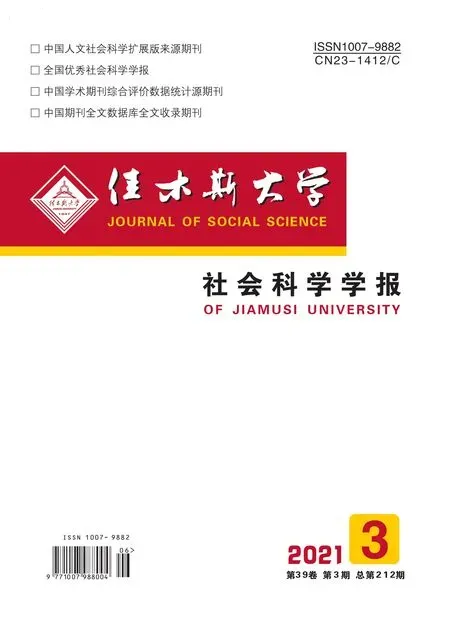遼朝除名法探析*
高云霄
(河北大學 a.宋史研究中心;b.燕趙文化高等研究院,河北 保定 071002)
“除名”即中國古代政府削奪犯重罪官員的官職和爵位,屬于“五刑”外的一種附加刑罰。除名法可溯源至先秦時期,“除名之稱始于漢世”[1]490,《漢書》云:“奪爵為士伍,免之”,顏師古注:“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2]141,但檢諸史籍,發(fā)現(xiàn)“除名”一詞最早見于《三國志·華佗傳》:“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3]800,其于晉季成為定法,《太平御覽》據(jù)引《晉律》載:“吏犯不孝、謀殺其國王、侯、子、男、官長,誣、偷、受財枉法,及掠人私賣、誘藏亡奴婢,雖遇赦,皆除名為民”[4]2909,除名法完善于李唐之世,作為后世刑律藍本的《唐律疏議》曰:“諸除名者,官爵悉除,課役從本色。六載之后聽敘,依出身法”[5]58。遼朝實行“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6]773的“因俗而治”的統(tǒng)治政策,其因襲唐律以治漢人,除名法自然被契丹統(tǒng)治者應用于罪官懲罰的制度中。
比年以來,關于中國古代除名法的研究較為零散,其中北朝、隋唐及金朝①是學界的重點研究方向。當前法史界對遼朝法律文化的研究較薄弱,這大致是緣于遼朝史料甚于簡略造成的。涉及遼朝除名法的研究,可謂鳳毛麟角,部分學者僅在探討職官管理制度時略有提及,如張志勇認為除名即開除公職,屬于最為嚴厲的一種行政處分[7]149。武玉環(huán)、尹宿湦指出在遼朝官員犯罪的懲罰措施中,罷官、貶官、削爵位是最為常見的[8]37-45,其中削爵為民正是“除名”的同義術語,二位學者未就此展開深論。孫振江指出“奪官”分為奪爵免官和奪爵不免官兩種形式[9],孫文單獨羅列“除名”的刑罰,未與“奪爵免官”相聯(lián)系,有失偏頗。而目前學界尚未對遼朝除名法進行專題研究。遼法是中華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擬勾稽相關史籍及碑刻資料,以遼朝除名法的同義表達、應用時間、適用范圍及其特點與作用為切入點,窺探遼朝法律文化的價值,不當之處,請方家不吝賜教。
一、遼朝“除名”的同義術語及其應用時間
(一)遼朝“除名”的同義術語
“除名”即對官職與爵位的雙重剝奪,除名法是“漢律”,不屬于契丹族習慣法的范疇。在遼朝,與“除名”具有相同含義的術語有8種:第一種“廢”,如保寧六年(974)宋王喜隱坐謀反廢[6]102,九年(977)喜隱被起用為西南面招討使[6]107,“廢”即指官爵皆奪。第二種“免官”,如重熙十五年(1046)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敵魯古坐贓免官[6]266,從數(shù)年后敵魯古復封漆水郡王來看,這里的“免官”相當于“免官爵”。第三種“削爵為民”,如大康七年(1081)武定軍節(jié)度使耶律仁杰以罪削爵為民[6]324。第四種“降為庶人”,如咸雍八年(1072)參知政事耶律觀矯制營私第,降為庶人[6]312。第五種“除屬籍”,如天祚帝誅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屬籍[6]399,“除屬籍”即取消皇族的身份,貶為庶民。第六種“削爵免官”,如韓滌魯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阻卜貢物,事覺,決大杖,削爵免官[6]1424。第七種“奪爵”,如保寧八年(976)寧王只沒妻造鴆毒,只沒奪爵,貶烏古部[6]1087,后復封寧王,這里“奪爵”相當于“奪官爵”。第八種“放歸田里”,如明王安端子察割弒逆被誅,穆宗赦通謀罪,放歸田里[6]1072。《遼史》粗疏簡陋,訛誤較多,部分情況下,“免官”僅指罷免官職,不涉爵位,“奪爵”僅削奪爵位,不涉官職。有關遼朝“除名”的同義術語,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二)遼朝“除名”的應用時間
遼朝除名法是逐步吸收和借鑒唐律的產(chǎn)物,其法須在完整的官爵框架內(nèi)應用與完善,并以成熟的職官獎懲制度作為輔助。神冊元年(916),耶律阿保機“變家為國”,此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曷魯)乃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6]1347,至神冊六年(921)“詔定法律,正班爵”[6]19,遼初庶事草創(chuàng),源于唐、五代的漢制官爵多為籠絡歸附漢官的工具。會同元年(938)后,一套依從漢制的官爵體系初步在遼朝確立,《劉承嗣墓志》記載:“嗣圣皇帝都城大禮,圣澤無私,崇德報功,行爵出祿”[10]48,耶律德光南下中原,滅亡后晉,曾詔“晉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漢禮”[11]39。伴隨太宗、世宗、穆宗三朝職官管理制度的發(fā)展,除名法至晚于景宗朝被契丹統(tǒng)治者應用,檢索《遼史》,發(fā)現(xiàn)“除名”一詞首見于《景宗紀上》,保寧八年(976),“秋七月丙寅朔,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高勛等除名”[6]103,需要注意的是,除名法對契丹皇族只沒與漢官高勛均適用,側(cè)面說明景宗時期已出現(xiàn)“番漢合流”的趨勢。
二、遼朝除名法的適用范圍
翻檢《遼史》《契丹國志》及相關宋代史籍,并輔以遼代的石刻文,發(fā)現(xiàn)遼朝除名法涉及官員多種類型的罪狀。為了方便研究,特將除名官員的具體信息列表如下。

表1 遼朝除名官員簡表
通過上表,可以總結(jié)出遼朝除名法涉及官員的罪狀主要有威脅皇權、破壞政權、連坐得罪、職務犯罪、軍事獲罪等五大類。
(一) 威脅皇權類
《遼史》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jié)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為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6]1668皇族耶律氏與后族蕭氏是遼朝的統(tǒng)治核心,二者內(nèi)部的矛盾與斗爭加速了遼王朝的滅亡。契丹貴族身犯威脅皇權類的重罪,情節(jié)嚴重者會處以極刑,部分與皇帝關系緊密者會列入“八議”的范疇,免死除名,貶為庶人。
1.謀逆造反
太祖弟明王安端與其子察割通謀弒逆,遼穆宗“赦通謀罪,放歸田里”[6]1072。耶律李胡子喜隱“應歷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6]1338,喜隱謀反后,先前獲封的“趙王”爵位被削奪,景宗即位改元,赦宥喜隱,并進封其為宋王。保寧六年(974),“宋王喜隱坐謀反廢”[6]102,“廢”字即貶為庶人,意味官爵的削奪,但喜隱憑借自己的尊貴身份,于保寧九年(977)被起用為西南面招討使[6]107。
2.謀廢立事
謀廢立是對皇權的嚴重威脅,貴族和高官密謀更替最高統(tǒng)治權的行為,已邁入遼朝皇帝的“禁區(qū)”,即使被誣陷,依然會予以除名。遼道宗朝著名的“昭懷太子案”,牽連眾多官員受到除名的重懲,大康三年(1077),權臣耶律乙辛糾結(jié)黨羽向太子集團發(fā)起猛攻,誣陷蕭速撒、耶律撒剌等人謀立皇太子耶律濬,道宗聽信讒言,“廢皇太子為庶人,囚之上京”[6]318。除事件的主角耶律濬被除名外,眾多與乙辛不協(xié)者,均逃不過死刑、除名、籍沒的懲處,如中京留守耶律奴“被誣奪爵,沒入興圣宮,流烏古部”[6]1621。直至乾統(tǒng)元年(1101),天祚皇帝為案件受害者昭雪,“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6]355,先前被誣除名者的官爵得以恢復,部分官員得到贈官的優(yōu)賞。
3.篡權自立
歷朝篡權自立者均被視為“逆臣”,即使身死,仍會將其生前的官爵剝奪,給予除名的附加刑。秦晉國王耶律淳在回離保、耶律大石等人的勸進下,于保大二年(1122)自立為帝,改元建福,但好景不長,耶律淳不久離世,政權土崩瓦解,東奔西逃的天祚帝“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11]142,官員死后被罰除名屬于特殊情況,其生前被卷入政治風波的可能性較大。
(二)破壞政權類
破壞政權類犯罪行為嚴重損害政府形象、破壞政權內(nèi)部團結(jié),遼朝官員多以造毒謀命、私議宮掖、語涉怨望等罪名被開除官籍。
1.造毒謀命
官員私自造毒,并以毒藥謀取他人性命,這嚴重破壞政權內(nèi)部的和諧、穩(wěn)定,此類案例多出現(xiàn)于封建王朝利益集團間的斗爭中,造毒謀命的部分官員會被特赦死刑,予以除名。如在遼景宗保寧八年(976)的一場政治風波中,寧王只沒與南院樞密使高勛密謀用毒藥謀害駙馬都尉蕭啜里,寧王只沒的妻子制造鴆毒,事情敗露后,“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高勛等除名”[6]103。
2.私議宮掖
私議宮掖事在遼朝是被嚴令禁止的行為,官員私自議論宮掖事或是謗訕朝廷,易使政權受到流言的中傷,抑或是發(fā)生泄露機密的情況。乾亨四年(982),圣宗初即位,政權內(nèi)部暗流涌動,當年十二月發(fā)生了撻剌干乃萬十醉言宮掖事的違法案件,按照律法規(guī)定,乃萬十應當被處以死刑,但承天后與圣宗法外開恩,僅對乃萬十施加杖刑的處罰[6]116。再如蕭迭里得族弟黃八的家奴告其主私議宮掖事,迭里得為包庇族弟而掩蓋住事情的真相,“事覺,決大杖,削爵為民。清寧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為南京統(tǒng)軍使”[6]1665。
3.語涉怨望
官員平日言論不當或是言辭涉及怨望,會招致除名的處罰。道宗朝的文臣王鼎剛正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昌初年(1095)王鼎升任觀書殿學士,在一次酒宴中,鼎“醉與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道宗得狀,十分惱怒,對鼎“杖黥奪官,流鎮(zhèn)州”[6]1602,其中流刑作為王鼎的主刑,而“奪官”指官爵皆奪,同“除名”之意,為王鼎的附加刑。語涉怨望對皇帝觸動很深,造成對政權的不良影響,以致于在大赦的條件下,道宗仍不愿寬宥王鼎。
(三)連坐得罪類
除名是連坐案件中常用的處罰方式之一。“連坐”即“因他人犯罪而使與犯罪者有一定關系的人連帶受刑的制度”[12]375,遼朝官員參與謀反、厭魅,往往會受到連坐除名的嚴懲。
1.參與謀反
謀反屬于“十惡”重罪,無論官員是主動謀劃,還是被迫參與,都會被政治漩渦卷入其中。在謀反類案件中,連坐除名很常見,道宗清寧九年(1063)的“重元之亂”牽涉范圍廣泛,連坐官員眾多,如衛(wèi)王貼不“訴為重元等所脅,詔削爵為民,流鎮(zhèn)州”[6]299;因直系親屬犯罪連坐的豐國王蕭孝友“坐子胡睹首與重元亂,伏誅”[6]1469,其生前的官爵均被削奪;因薦引官員犯罪連坐的北院樞密使蕭圖古辭“為樞密數(shù)月,所薦引多為重元黨與,由是免為庶人”[6]1645。
2.參與厭魅
厭魅屬于“不道”,《唐律疏議》云:“厭魅者,其事多端,不可具述,皆謂邪俗陰行不軌,欲令前人疾苦及死者”[5]10。在遼朝,厭魅也是不合禮法的行為,厭魅事件的參與人員均會嚴懲,涉事官員予以除名,如大安二年(1086),道宗惠妃母燕國夫人削古“以厭魅梁王事覺,伏誅,子蘭陵郡王蕭酬斡除名,置邊郡,仍隸興圣宮”[6]330。
(四)職務犯罪類
在遼朝,違法收受財物、挪用官物或是濫用職權的官員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嚴懲,其中除名法是施加給罪官的附加刑。
1.貪贓受賄
遼朝重視廉政建設,貪贓受賄的官員會受到死刑、除名、免官、杖刑等不同程度的處罰,重熙十五年(1046),西北路招討使、漆水郡王耶律敵魯古坐贓免官[6]266,十九年(1050),耶律敵魯古因軍功復封漆水郡王的爵位[6]275,說明敵魯古先前已被除名,這里的“免官”指的是“免官爵”。
2.私取官物
遼朝官員私自挪用官家財物,或是以官物進行牟利活動,可能會斷送其官場生涯。重熙十年(1041)遼興宗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6]258,興宗以詔令的形式增加了對私取官物類犯罪行為的懲處力度。恰在此際,西北路招討使韓滌魯利用職權便利,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阻卜貢物,事情敗露后,韓滌魯被“決大杖,削爵免官”[6]1424。道宗朝的張孝杰因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兩條罪狀,被罰除名[6]1637。
3.濫用職權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官員濫用職權,牟取個人利益,將國家和百姓拋諸腦后,必然會受到嚴厲處罰。清寧五年(1059)十二月,“參知政事吳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爵為民”[6]292,吳湛利用參知政事的職權,為弟換取官員的身份,被道宗剝奪官爵。咸雍八年(1072),知南院樞密使事王觀濫用權力,矯制營造私第,做出不合禮法之舉,道宗將其貶為庶人[6]1551。
(五)軍事獲罪類
遼朝軍官常因妨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擾民、搶掠、臨陣脫逃、失軍期、不親追擊、作戰(zhàn)不利等獲罪,皇帝視其嚴重程度,給予杖刑、免官和死刑等處罰[13],除名法也被納入遼朝的軍法體系。
作戰(zhàn)不利。大安十年(1094),敵烈部發(fā)動叛亂,烏古敵烈統(tǒng)軍使蕭朽哥率軍鎮(zhèn)壓,與戰(zhàn)不利,被罰除名[6]341。遼末,刑罰無章,蕭嗣先征討女真失利,“但免官而已”[6]367,軍法不嚴,士無斗志,遼王朝被推向滅亡的深淵。
三、遼朝除名法的特點與作用
(一)遼朝除名法的特點
1.除名法主要針對的是身處核心權力圈的高級官員
罪官同時擁有官職與爵位,是對其施行除名的先決條件,無官階的胥吏和無爵位的下級吏員犯重罪,會直接判處死、流、徒、杖、笞等不同程度的刑罰,除名法是其“享受”不到的附加刑。有遼一朝,除名案例中出現(xiàn)的官職大致有:北院樞密使、南院樞密使、知南院樞密使事、參知政事、諸行宮都部署、西北路招討使、西南面招討使、烏古敵烈統(tǒng)軍使、洛京留守(遙領)、中京留守、武定軍節(jié)度使、觀書殿學士、國舅詳穩(wěn)等,其中既有樞密院、中書省、館閣等朝官系統(tǒng)的高官,也有五京、招討司、統(tǒng)軍司等外官系統(tǒng)的大員。遼朝除名官員的爵位有:秦晉國王、豐國王、明王、趙王、宋王、寧王、秦王、衛(wèi)王、漆水群王、蘭陵郡王等,其爵位均不低于王爵,且集中在一字王爵和郡王爵。除擁有高品級的官爵外,除名官員的出身顯赫,多數(shù)為近支宗室和后族的重要成員,長期處于核心權力圈。明乎上述論證,可知遼朝除名官員的身份尊貴,且官爵基本在三品以上,進一步證明除名法針對的群體是身處核心權力圈的高級官員。
2.除名法的主體內(nèi)容與《唐律》基本匹配
首先,《唐律疏議·名例律》載:“諸犯十惡、故殺人、反逆緣坐,雖會赦,猶除名”[5]48,遼朝的高官顯貴身犯十惡重罪,可入“八議”,免死除名,如數(shù)次謀反的耶律喜隱;故意毒害政敵的高勛被處流刑,附加除名;耶律貼不、蕭孝友、蕭圖古辭等人在“重元之亂”中,連坐除名。其次,《唐律》規(guī)定,“監(jiān)臨主守,于所監(jiān)守內(nèi)犯奸、盜、略人,若受財而枉法者,亦除名(奸,謂犯良人。盜及枉法,謂贓一匹者)”[5]48,遼興宗朝的韓滌魯在西北路招討使任上,因私取外族使者的貢物,被處杖刑,附加除名,耶律敵魯古也在西北路招討使任上,坐贓除名,但唐、遼在贓物的類別和數(shù)量規(guī)定上應有不同。再次,唐朝犯“五流”有官爵者也要除名,“五流”指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子孫犯過失流、不孝流和會赦流,其中造毒謀命應判處流刑,“造畜蠱毒,雖會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有官者仍除名”[5]36寧王只沒妻造鴆毒被誅,參與造毒案的只沒和高勛等人被處流刑,附加除名。最后,唐朝法外施加除名的案例較多,且集中于軍事獲罪的官員,《遼史》疏漏頗多,僅發(fā)現(xiàn)烏古敵烈統(tǒng)軍使蕭朽哥因作戰(zhàn)不利被除名。綜上所述,遼朝除名法的主體內(nèi)容與《唐律》基本匹配,遼朝律令對《唐律》存在明顯的承繼關系,是中華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3.除名法的執(zhí)行效果不佳,民族性差異不顯
“社會現(xiàn)實與法律條文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14]2,遼朝除名法在司法實踐的過程中,暴露出隨意性較強的問題,其執(zhí)行效果與皇帝的個人喜好及與皇帝的親疏遠近有關。如太祖弟安端與子察割通謀弒逆,遼穆宗免其死罪,放歸田里;耶律李胡子喜隱數(shù)次謀反,景宗免其死罪,予以除名后,竟提升王爵等級,繼續(xù)委以重任;世宗子只沒造毒謀害駙馬都尉蕭啜里,被處流刑,附加除名,統(tǒng)和元年(983),皇太后稱制,詔復舊爵。安端、喜隱、只沒都是近支宗室,遼朝為了體現(xiàn)對貴族階層的保護,在效仿中原王朝制定法律時,貫徹了“貴賤有序”的思想,這體現(xiàn)在八議制度中的“議貴”上[15]。再如玉田韓氏家族的韓滌魯,私取外族使者的貢物,削爵免官,“俄起為北院宣徽使”[6]1424;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敵魯古坐贓除名,僅三年后,起用為北道行軍都統(tǒng),后復封漆水郡王[6]275;蘭陵郡王蕭酬斡因母厭魅梁王延禧(天祚帝),被道宗處以流刑,附加除名,至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妃,召酬斡為南女直詳穩(wěn),遷征東副統(tǒng)軍”[6]1574。據(jù)上述可知,除名官員的聽敘時間與律令有較大出入,且犯經(jīng)濟類罪名的官員可較快重返官場,但官員犯“十惡”、“不道”等嚴重威脅皇權、破壞政權的罪名,需要聽敘的時間較長,且取決于皇帝的個人喜好。此外,蒐羅遼朝的除名案例,發(fā)現(xiàn)契丹族官員的數(shù)量占壓倒性優(yōu)勢,漢官較少,這與遼朝的國家體制相適應,契丹人占主導的統(tǒng)治地位[16],且長期活動在政治核心圈,更易觸犯除名法。在除名法的執(zhí)行上,契丹族官員與漢官未見顯著差異。總體言之,遼朝除名法的執(zhí)行效果不佳,民族性差異不顯。
(二)遼朝除名法的作用
1.強化皇權
“遼之內(nèi)難,與國始終”[6]1339,皇族的內(nèi)部叛亂,影響著王朝命運。耶律氏對謀逆造反、謀廢立事、篡權自立等重罪予以除名的嚴懲,在客觀上,具有強化皇權的作用,但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契丹貴族“合理”運用八議制度,以減輕自身所受的刑罰,或是憑借與皇帝的親緣關系,獲得聽敘時間上的優(yōu)待。整體而言,除名法對契丹貴族犯罪懲處的效果甚微。
2.整肅官風
歐陽修謂:“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后亂從之,此勢之然也”[17]9413,吏治腐敗是法律體系崩潰的催化劑。遼朝對犯貪贓受賄、私取官物、濫用職權等罪名的官員予以除名,具有整肅官風的作用。官爵皆無深刻影響著個人和家族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及社會名譽,對官員具有較大的震懾力。
3.維護禮法
耶律奴妻蕭意辛言“厭魅不若禮法”,她認為遵守禮法,應“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6]1621。厭魅屬于“不道”的范疇,遼朝對參與厭魅的官員施加除名的處罰,具有維護禮法的作用。
四、結(jié)論
北宋名臣富弼上疏論:“(契丹)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18]3641,“除名”非契丹本族的習慣法,其源于“中國法令”,主體內(nèi)容基本與《唐律疏議》的相關記載匹配,是逐步吸收和借鑒唐律的產(chǎn)物。“除名”即對犯重罪官員的官職和爵位予以削奪,屬于主刑外的附加處罰。在遼朝,與“除名”具有相同含義的術語有“廢”“免官”“削爵為民”“降為庶人”“除屬籍”“削爵免官”“奪爵”“放歸田里”等8種。伴隨遼朝職官管理制度的發(fā)展,除名法至晚于景宗朝被耶律氏應用,其法適用范圍廣泛,因威脅皇權、破壞政權、連坐得罪、職務犯罪、軍事獲罪的官員,除判處死、流、徒、杖、笞等不同程度的主刑外,往往會附加除名。清人沈家本謂:“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1]2144遼朝除名法在實踐過程中,暴露出隨意性較強的問題,這一方面和契丹統(tǒng)治者貫徹“貴賤有序”的法律思想,實行八議制度有關,另一方面涉及到皇帝的個人喜好及與皇帝的親疏遠近。總起而言,雖然除名法在遼朝的執(zhí)行效果不佳,但其客觀上起到了強化皇權、整肅官風、維護禮法等重要作用。此外,遼朝除名法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內(nèi)涵。
[注 釋]
①夏志剛《北魏除名制度特點探析》(《青海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夏志剛《北朝除名制度管窺》(《貴州社會科學》,2007年第8期)、孔祥軍、李傳成《隋朝除名制度探析》(《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王偉歌、張劍光《唐代官員除名制度探析》(《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李傳成《隋唐除名制度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高云霄《金代官員除名制度探析》(《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張宸《金朝除名制度研究》(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