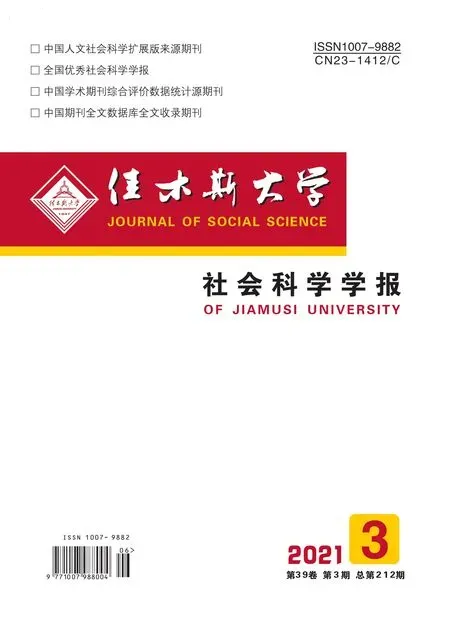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的形式及其美術史貢獻*
王 超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一、徽商藝術贊助的背景及時間界定
“觀史如觀水,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 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經形成人數眾多、勢力較大的一個商幫。明代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言:“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到了清代,徽商勢力達到高峰,《歙縣志》記載在康乾之際,“兩淮八總商,邑人恒占其四。”徽商作為徽州地區活躍的商幫,不僅在商業層面做出了貢獻,也在美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選取明末清初的時間段,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明末清初為徽商鼎盛階段,徽商家族獲得大量財富,不止滿足于物質生活享受,更進一步模仿文人雅士的生活習慣,參與藝術的積極性較高。徽州的休寧、歙縣許多新富之家爭相購置書畫古器,模仿文人士大夫于壁上懸掛畫幅,把原屬于士大夫階層的藝術品鑒與收藏文化從逐漸擴大到庶民階層。吳其貞在《書畫記》中有記載:“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徽商財力物質的豐裕,江南地區開始出現了奢靡的風氣,古器和書畫等藝術商品的購藏,成為當時一種商業投資的方式,也是商人階層互相攀比的方式。另一方面,徽商想依靠財富提高個人對于社會的影響力,對包括建設會館等地方發展的投資無非是想用經濟資本積累在官場以及地方上的社會資本,對于教育方面的扶持是要讓家族的子孫可以通過文化教育資本進入官場或士紳的領域,而對于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投資和贊助則可以結識更多的官員階層和文人階層,有助于徽商在商業上的表現。
二、徽商藝術贊助的形式
藝術贊助既是藝術史現象,也是一種經濟史現象,圍繞的是經濟與文化藝術的關系,是藝術商業化和藝術娛樂化在中國的早期體現。中國藝術贊助的形式與西方既有區別也有聯系。西方一直為宮廷贊助和私人贊助兩種形式并存,最明顯地例子是美第奇家族贊助下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并形成了佛羅倫薩畫派。而中國的藝術贊助則可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元朝前主要是宮廷贊助時期。贊助者多為歷朝歷代帝王,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有至唐代的藝術收藏者名單:漢朝漢武帝、漢明帝、梁朝梁武帝和梁文帝、隋朝的隋文帝、唐朝的唐玄宗和武后等。書畫的性質為依附禮教而行,其功能在達成“成教化,興人倫”。至宋代,由于皇室的支持和推崇,藝術的贊助和消費的群體為王公貴族所獨有。元朝,文人因政治抱負受阻,轉而投入書畫藝術等其他精神寄托,文人畫傳統得以蓬勃發展,文人間形成了相互支持和聯系,繪畫、書法作品透過文人社交活動得以展示、品評,在資助者的報酬下創作而成。第二階段為商人階層贊助時期。明代后期書畫活動繼承了宋元發展處的特色,然而,由于商業經濟與社會奢靡風氣的推波助瀾,書畫的性質由教化工具轉變為文人雅士的藝術品,以至可以買賣流通、具有市場價值的商品。其中有政治變革統治階層的原因,也與中國封建王朝后期小資產階級的興起有關。徽商正是商人階層藝術贊助的代表,目的是徽商冀望通過藝術贊助得到文人階層和統治階層的肯定,獲得話語權。擁有雄厚的財力是徽商能夠進行藝術贊助的基本條件,但關鍵條件是徽商“士商相融”的本質賦予了徽商對于文化藝術的熱愛和參與,引導其進行藝術贊助。同時徽商從小在富裕的家境中成長,受程朱理學文化的熏陶和培養,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藝術鑒賞力。明末清初,徽商藝術贊助達到頂峰,吳其貞《書畫記》中云:“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其風開于汪司馬兄弟,行于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榆村程氏、繼之余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所得皆為海內名器。”1640年4月25日吳其貞在《書畫記》中記載前往溪南吳氏做客,吳氏家長吳文長拿出了二百余幅畫作、五十扎手卷,書本畫冊供其鑒賞和把玩,從中可見當時徽商收藏之豐盛。徽商藝術贊助和經營的方式有:付錢請藝術家作畫、收購舊時名畫、投資當時名家作品,提供藝術家生活所需,成為其藝術贊助人等。
1.藝術品的收藏
藝術品的收藏包括購買藝術作品和藝術品的以物易物。經營文藝產業的徽商,會資助一些尚未成名的藝術家,鼓勵創作并收購其作品。這些作品,除了投入市場換取利潤外,或成為禮物,借以結交官員,乃至妝點身分,進入文藝圈。在徽商的贊助下,畫家紛紛放下架子,突破文人儒家重義輕利的道德規范,而照樣保持自我的尊嚴。藏于日本的《金冬心十七扎》是揚州八怪之首金農和徽商方輔書信往來的見證,金農在書信中多次提及書畫買賣和酬金的言語,如第四扎“輞川圖有古色,頗可蓄也,議值2金。”畫家鄭燮更明確標榜潤筆:“大幅6兩,中幅4兩,小幅2兩。書條、對聯1兩。”更言:“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在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記載了他在萬歷37年至42年間,一位夏姓商人多次持藝術品前來買賣的記錄,見表1,可以部分展示出當時江南藝術市場的活躍,以及士商交會的社會現象。

表1 一位夏姓商人的買賣記錄
藝術品的以物易物或互通有無是徽商藝術品收藏的另一種方式,他們在互相觀賞藏品之后,交換各自喜愛的藏品。如詹景風在《詹東圖玄覽編》中多處提及汪道昆、汪道會和汪道貫藝術品交換活動。“長一尺五寸,闊一尺許,今歸汪仲嘉。”一句描述了文征明的作品《歲寒圖》的交換過程。
2.藝術家資助
藝術家資助包括聘用藝術家修建園林和提供生活所需,資助其游歷寫生。徽商行走于天下,對于故鄉徽州山水的思戀,是其聘用藝術家修建私家園林的原因之一。另一個目的是源于心中的儒家文化讓他們在商業之外寄情于山水,代表為揚州園林。揚州在康乾之際,城中云集了一批造園名家,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云:“揚州以名園勝,名園以壘石勝。余氏萬石園出道濟手,至今稱勝跡。次之張南垣所壘‘白沙翠竹’、‘江村石壁’,皆傳頌一時。”此處的“道濟”為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濤,著有《苦瓜和尚畫語錄》,是一位承前啟后的著名畫家。徽商黃至筠聘請石濤修建其私家園林“個園”中的“夏山”,石濤以太湖石堆疊,以書畫技法壘石,把山水畫法運用到方寸磊石之間,太湖石的氣韻、池水的生動相呼應,體現出石濤講求獨創性的藝術理念。他的藝術智慧提升了揚州園林的品味,也正是徽商雄厚的財力資助,揚州園林才能達到“一山一水,咸登盛典之書。”同時,徽商對同代和前輩畫家作品的購藏,為畫家們作品的銷售提供了可靠的消費群體,從而使他們能夠安心創作,無需為衣食住行等生活瑣事分神。為了使畫家們能深入自然,實地感受山川造化之變幻多姿,徽商還為一些畫家的出行和寫生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例如,漸江游歷黃山期間長期居住在徽商家中,繪有《黃山真景冊》五十幅,奠定了新安畫派的基礎。
三、徽商藝術贊助的美術史貢獻
徽商的藝術贊助行為,無論目的如何,但在客觀上使得藝術家們的創作積極性有所提高,同時對于書畫藝術品市場的繁榮有著積極意義。徽商成為推動江南藝術發展的力量,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發展和藝術變革,并側面影響了地域藝術發展的面貌。梁啟超在《清代藝術概論》中感嘆:“然固不能謂其于茲學之發達無助力,與南歐巨室豪賈之于文藝復興若合符契也”。徽商在藝術上的貢獻,理應得到重視。具體反映在:
1.促成了江南藝術市場的形成
明末清初商品經濟發展下,古玩和書畫等藝術品出現了商品化趨勢。原屬于文人士大夫特有的書畫收藏與消費行為,開始為商人階層競相效仿,此類物品的擁有成為當時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征。徽商與文人畫家們的頻繁交往,有意無意間提高和鞏固了儒商形象,有利于他們社會地位的改變,進而有助于他們的商業競爭。另外,畫家們創作的藝術作品本身在進入流通領域后,也為商人們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徽商透過大量的經濟資本進入藝術市場,是藝術市場可以蓬勃發展的動力。徽商對于藝術作品的追捧,目的是為了獲得文人文化中的風雅,本意不在于鑒賞繪畫作品,而是鏈接文人階層與商人階層之間的社會網絡。徽商作為早期小商品經濟的獲利者,出于自身“賈而好儒”的身份標榜和結交上流社會文人士大夫的交際應酬的目的,對藝術家和藝術作品進行贊助和消費,初步形成了江南文藝市場藝術經濟的良性循環。至明朝末年,江南地區的書畫市場形成了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固定的書畫市集以及古董商店,清初更增加了徽商活躍的揚州。其次,形成了行走于商人間的藝術作品推銷商,這些商人多來自徽州或江南地區的古董世家,也有少部分是僧人或庶民。在畫家身份上,形成了來自不同地區,主要靠售畫為生的職業畫家群,畫家們依靠商業市場達到自我表現的目的,他們完全以“潤格”來作為自我估價的手段,認為為他人畫畫必須索取適當的金錢作為報酬。明末畫家唐寅在《言志》中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因為徽商的贊助和藝術家的作品價值觀的凸顯,一個穩定的早期藝術市場就此形成。
2.影響了江南藝術發展和藝術審美的面貌
其一,徽商藝術贊助的影響促成了對于江南繪畫審美風格的變遷。徽商收購和崇尚元代畫家,使得江南書畫風氣轉變,畫家作畫一改之前對于宋畫的追求,崇尚倪黃,追隨沈周、文征明和董其昌,間接促成元畫成為當時江南社會藝術審美風尚。這些都與徽商對這類風格的藝術作品的大肆購藏,以及他們對當代畫家根據這一審美旨趣而創作作品的收購關系密切。其二,作品風格雅俗共賞。畫家應對市場和雇主需求改革畫面,繪畫的主題和形式,不是歌功頌德和一味摹古,而是與市井結合,以寫意為主。在畫面上,受市場需求的影響,在花鳥、人物等題材上進行了多種嘗試和開拓,對寫意傳統作了大膽的突破,使用適宜揮灑應酬的寫意花卉。在題材上,山水畫和花島畫盛行,文人畫普遍使用的梅、蘭、竹、菊及雜畫等主題也相當發達。其三,藝術家在藝術贊助者的推崇下,畫面追求新意,充滿激情和個性的創作。在作品內涵上,文人山水畫另辟蹊徑,創作出了富有生活氣息的繪畫作品。在表現手法上,一改之前浙派的宮廷畫風,繼承和發展了元代崇尚筆墨意趣和講究“士氣”、“逸格”的繪畫傳統,使畫面創作充滿個性化。
3.促進了藝術傳播
經營文藝產業的徽商,會資助一些尚未成名的藝術家,鼓勵創作并收購其作品。這些作品,除了投入市場換取利潤外,或成為禮物,藉以結交朋友。更成為妝點身分,進入文藝圈的“門票”。更明白的說,此處的藝術品,對于徽商而言,既為商品,更為藝術,既是經濟資本,也為文化資本。而藝術品之于文人,也同具有藝術與商品意涵,并藉此與商人循環地打交道,從而共同創造、活絡江南藝術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帶動文藝活動的盛行,也帶動商人與文人之間的互動頻率,具有經濟利益上的意義,同時也呈現了人際社交、政治活動等社會關系。從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中可知,明代中后期,賞玩文化已經成為時尚,藝術作品不僅僅是商人間的購買,也在于文人藝術家可以透過資本的購買,使藝術作品成為商品,形成創作、鑒賞、買賣等藝術市場化的環節。藝術消費的是以書畫作品為媒介,由參與其中的人員一起建立的價值體系和社會認同的過程,促進了當時藝術家、藝術作品和藝術贊助者之間的藝術傳播過程,造就明清江南藝術品市場的繁景。
4.提升了徽州地區藝術發展水平
首先,徽商除收藏前代藝術家的作品,也構藏同時代優秀藝術家的作品,這激發了當時藝術家們的創作欲望,催生出一批新安藝術家的出現,如查士標、程邃等,并最終形成新安畫派。其次,明清時期的徽州號稱文物之海,所藏文物難以計數,徽商所藏的歷代繪畫名跡,為徽州新安畫家們賞玩研摹構建了最重要的平臺,這些書畫巨跡也成為新安藝術家研習古人的摹本。同時,在徽商參與下,得以成熟于明代中后期的徽州版畫,為徽州地區新安藝術家們學習傳統繪畫提供了便捷的摹本。《十竹齋畫譜》《程式墨苑》和《方氏墨苑》對明清時期江南與徽州繪畫的發育、成長以及繪畫圖式的最終形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催化作用。例如,明末清初徽州有影響力的刻書坊有40余家,徽州版畫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就是新安畫家創作活躍的時期。
四、總結
徽商藝術贊助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小資產階級萌芽階段商業和藝術相互融合發展的顯現,是一種文化互動,并推動了中國早期藝術市場在江南地區的發展。徽商藝術贊助的范圍包括有文學、戲曲、書畫和園林等,本文僅僅介紹了其在書畫和園林方面的贊助方式和貢獻。其贊助目的不是為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而是具有個人價值觀的商業藝術模式。時至今日,經濟快速發展,一種扭曲的、金錢至上和泛娛樂化的文化生態出現在當下的社會中。在今日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建設目標下,資本在文化消費中雖不能起決定作用,但往往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左右文化的潮流,如何引導資本建立經濟與藝術、藝術市場、藝術家三者的正確平衡關系,如何建立符合當下價值觀的文化消費理念,對于徽商藝術贊助的研究無疑具有鮮明的歷史參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