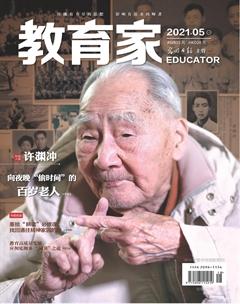“ 最美逆行者”的鄉村藝術行動
周麗


人來人往的街市,一爿簡陋的豬肉店內,一個身姿柔軟的小女孩沉浸在芭蕾舞的世界里,刻苦練習著基本功——這段出自紀錄片《小小少年》的視頻近期刷爆全網。視頻里的主人公叫鄔剛云,今年10歲,是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硯山縣的一名彝族女孩。在無數人為小云兒的“天賦”“勵志”點贊時,她身后的“伯樂”——舞蹈家關於、張萍夫婦及他們投身多年的藝術公益故事也為更多人所知曉、動容。
從“田埂上的芭蕾”到 “彩云計劃”
“彩云計劃”介紹手冊扉頁正中是一張合影——關於、張萍和十幾名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女孩,在村野的空地上一字排開,倚身毛竹做的練舞把桿,笑頰粲然。這張照片之下,橫列著一句翻譯自英文的教育名言:“教師力量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深信人是可以改變的。”多年來,關於和張萍用大愛無私的藝術公益行動詮釋著這句話。
關於是北京一所著名舞蹈高校的芭蕾舞教師,曾多次擔綱國家重大演出任務,在舞蹈界頗有名望。張萍則是一名舞蹈編導,集舞蹈、美術、音樂多項才能于一身。 在常人眼中,芭蕾舞應該出現在中央芭蕾舞團、國家大劇院等高大上的平臺。關於和張萍卻目光向下,反其道而行之,將“陽春白雪”送到田間、山谷,化身“最美逆行者”。
云兒所在的硯山縣是曾經的國貧縣,也是張萍的家鄉。2016年,假期回鄉的張萍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那奪村孩子的照片,“小孩眼睛又大又亮,很漂亮,但是那個村子很落后很貧窮”。那奪村是者臘鄉夸溪村委會的一個小組村,地處偏遠,土生土長的張萍此前從未聽聞。
在好奇心的驅使和冥冥中的使命感召之下,張萍和關於驅車35公里,探訪了這個剛通電不久、沒有手機信號的彝族村落。彼時,未脫貧的那奪村72戶人家有23戶為建檔立卡貧困戶。走訪中,張萍和幾個女孩深入交流,了解她們的身世。一個叫柯美的女孩一臉悲傷地說:“我最不開心的事情就是,每年過年的時候父母才可以回來一次,不能天天陪著我。”這里的孩子大多和柯美一樣,是留守兒童或者事實孤兒。
“如果你身臨其境看見這些小孩,就會覺得這是你的責任。”孩子們的貧困、弱小、無助讓張萍和關於揪心不已。“這些孩子,我一定幫!”一念既起,“彩云計劃”應運而生。
實際上,在將芭蕾舞帶到那奪村以前,早在2013年,關於、張萍就在河北端村針對農村孩子進行鄉村藝術教育,開創了“田埂上的芭蕾”,引發國內外關注。在3年多的時間里,他們積累了豐富的鄉村美育實踐經驗。
端村位于現在的雄安新區,條件相對較好,孩子們可以在教室里訓練,而在那奪村,一塊平整的空場都難以尋覓。關於到那奪村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帶領村民們平整出一塊空地,并尋求資助買來一個大帳篷,搭建了“帳篷藝術經典大講堂”。此后,每個寒暑假,張萍、關於都會跨越2800多公里,從北京前往那奪村教孩子們跳舞,平時則請當地的教師和志愿者,免費教授舞蹈專業基本功和劇目課。
“最開始是想嘗試通過教孩子們藝術,讓他們擁有一個夢想。” 關於表示,開展鄉村藝術教育源于理想主義而非現實主義。來到那奪村后,他更多希望借助藝術溫暖的力量,給山里孩子帶來“美”和“尊嚴方面的提升”。
為了讓孩子們看看外面的世界、開闊視野,2017年1月,關於、張萍自費帶著那奪村的12名孩子來到北京——在此之前,很多孩子連汽車都沒坐過。這趟文化交流之旅,孩子們參觀了清華大學、舞蹈院校,游覽了動物園、海洋館、博物館,得到了愛心人士贈送的iPad和“金龜子姐姐”的愛心禮物……問及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孩子們答:“我們來到了天安門,給毛主席跳了舞。”那日,天氣很冷,孩子們脫下棉襖,露出里面的民族服裝,在廣場上跳起剛學會的弦子舞。孩子們出乎意料的舉動和回答讓關於夫婦深受震動。
舞蹈讓彩云孩子看到了生活的其他可能,但他們幼小的心靈最渴求的是“有一個溫暖的家”。為了實現孩子們的這個愿望,2019年,張萍毅然辭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家鄉,拿出和關於多年的積蓄,在那奪村建造了“彩云計劃公益志愿中心”,給彩云孩子提供一方學習、生活的港灣,全身心陪伴他們成長。志愿中心被村民們認定為“那奪村第73戶”,關於、張萍也成了越來越多孩子的阿爸、阿美(彝語,媽媽)。
“藝術家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你來了,從此,美神降落鄉間,天地飄灑花瓣;踩著你的肩膀,鄉村女孩輕盈地踮起腳尖。諾言一出便成信仰……”這是“CCTV2017年度三農人物”組委會給關於的頒獎詞。在很多人看來,芭蕾舞是貴族藝術,具備貴族精神,但關於認為,貴族精神是扶助弱勢群體,“藝術家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在委內瑞拉,有一個“音樂改變命運”的項目——一群藝術家通過音樂教育改變了許許多多貧窮孩子和問題少年的命運。關於最初的鄉村藝術教育嘗試便是由此觸發。如今,他將“用藝術幫助孩子”修正為“藝術教育精準扶貧”。“孩子喜歡唱歌、喜歡跳舞,我們就得下去,就是這么簡單。”關於表示,“彩云計劃”要做的是把那些散落在鄉村、不被人發現的一顆顆小珍珠串起來,變成一串項鏈,并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
事實上,在關於和張萍眼里,每一個鄉村孩子都是值得珍視的珍珠。對于參與“彩云計劃”的孩子,特別是那些“別無出路”的孩子,他們基本破除了身體條件等門檻,“來者不拒”。對每個從零開始的彩云孩子,關於、張萍都不遺余力、傾囊相授,并帶著支教團隊認真觀察和分析每個孩子的特點,為他們規劃專業發展方向,例如云兒。云兒的天賦曾吸引舞蹈院校拋來橄欖枝,但張萍和關於清楚,嬌小的云兒可能難以達到專業芭蕾舞者嚴苛的身體條件,而更適合走“芭蕾舞民族化”的路子。同時他們也并未因此限定云兒的發展路徑。現下,云兒在張萍、關於的指導下,接受芭蕾舞、民族舞、街舞等多舞種的學習。
為形成長效扶貧造血機制,也為解決彩云孩子畢業后的就業問題,2020年,關於、張萍借助雙方父母分別貢獻的30萬元養老金和自家老房子,在硯山縣建起彩藝文化藝術培訓學校(以下簡稱“彩藝學校”),用“取富濟貧”的方式,扶助更多貧困鄉村子弟。每到周末、假期,張萍就包車到各個村子把孩子們接到縣城,提供免費藝術培訓,并解決他們的食宿。如今在彩藝學校學習的140多個孩子中,有60多個彩云孩子。有償培訓的收入勉強維持教師薪水和公益支出,很多時候還需要關於倒貼自己在舞蹈學校的工資。
4年多來,“彩云計劃”以那奪村為圓心,輻射周邊18個村,先后選送60多名來自彝族、壯族等少數民族村寨的孩子考取云南多所藝術院校專業學習舞蹈,目前還有110多名彩云孩子在進行預科學習,為踏入藝校作準備。考入藝校的孩子每年數十萬元的生活費用,全部由“彩云計劃”公益志愿團隊自籌解決。此外,關於、張萍還帶領一批批“大小彩云”登上國家、省、市各級各類舞臺,讓他們綻放生命與藝術的光彩。
在關於看來,“彩云計劃”不僅是讓孩子們通過藝術“閃光”,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在“閃光”、學成后能回來反哺家鄉。
有個女孩,曾給關於寫過這樣一封信:“阿爸,以前在學校老師和同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是個根本沒有人知道的人。我們在這兒,周而復始。我的一生是看得到底的。如果說我能讀到高中,家里砸鍋賣鐵也會供我。上不了,我會和村里很多人一樣,嫁人或者打工,生小孩,然后繼續留在大山里。但是你們來了,我有了希望。”這個女孩就是柯美。作為第一批走出大山的彩云孩子,如今,柯美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美麗自信,并和另外三個藝校畢業的“大彩云”回到彩藝學校,擔任舞蹈教師。
不僅是“大彩云”,此前通過“田埂上的芭蕾”走出鄉村的“白天鵝”——馬悅、張博聞等,也追隨“關爸”“張媽”的腳步,加入“彩云計劃”志愿團隊,幫助和曾經的他們一樣的孩子,“舞”出自己的別樣人生。
理想主義者的“鄉村文藝復興”夢
那奪在彝語中意為“躲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回憶初遇那奪的情景,關於仍難掩“如獲至寶”的欣喜。“曠野山谷,遠處是層層的梯田,在這大自然的環境里,我當時一下就明白了什么是天人合一。”
更讓關於驚訝的是,這個只有300多人的彝族仆支系村落里,蘊藏著一座巨大的文化寶藏——老人們全都穿著少數民族服裝;人類六大古文字起源之一的《畢摩經》在此傳誦;本村及周邊少數民族村寨散落著多種“輕松追溯至唐朝”的民族藝術和文化傳統。關於嘆其“活脫脫就是斗彩雞缸杯埋在土里”。
彝族流傳著“阿哥弦子響,阿妹腳板癢”的古老諺語,但在“彩云計劃”進駐以前,很多年輕人已不會跳本民族的舞蹈。痛心于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斷裂,關於和張萍在教授孩子們芭蕾舞、本民族舞蹈的同時,不斷搜集、挖掘、引進少數民族非遺文化,通過創編的方式讓孩子們展示出來并傳承下去。在彩云計劃公益志愿中心,孩子們可以跟著老藝人和藝術家們學習古法織布、刺繡、民歌、巴烏吹奏;彩藝學校則與硯山文化館密切合作,派指定傳習教師為彩云孩子排練壯族傳統民間舞蹈“草人舞”“棒棒燈”、彝族民間舞蹈“頂燈跳弦”等。
“芭蕾舞絕不能只存在于中國最頂尖的學府里,更應該存留在山水之間”是關於一直秉持的理念。他深切地覺知:“我們是農業國家、農耕文明,每一種美、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是從農村產生。我來到這兒是學習,是要把藝術帶回到它生成的地方。”
于是,在每部“彩云計劃”的紀錄視頻里都能看到這樣的場景:身著少數民族服飾的彩云孩子,頭頂藍天,腳踩大地,以明媚的陽光為燈,以遠處的綠水青山作景,在田埂上、山谷里翩然起舞,構成一幅天人合一的如詩畫卷。不僅如此,關於還提出了自己的“美麗鄉村”構想——在那奪村,他們栽下了400棵櫻花樹(愛心人士捐贈),并命名為“彩云谷”,為將來開展“大地藝術”提前布景。在關於為那奪設計的“彝族文化深度游”場景中,中外游客聞著桂花香,飲著松毛茶,著一身民族服飾,在古桑葚樹下看傳習千年的少數民族舞蹈和彝族版芭蕾舞劇《胡桃夾子》……
“我們最后要做的是中國鄉村文藝復興。”為此,關於積極整合資源,構建藝術家同盟,呼吁舞蹈家到田埂上去跳舞,文學家去寫田埂上的文章,音樂家來創造田埂上的樂派……在“彩云計劃”的宏偉藍圖里,關於還“幻想”著將來帶領自己培養出來的中國鄉村藝術家走進與那奪山水相連的越南村寨,“在無涉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構建藝術命運共同體”。
“‘彩云計劃不是一個項目,項目是有始有終的,而我們做的這件事,只有開始,沒有結束。”關於表示,鄉村美育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希望自己和張萍像一座燈塔,感召更多藝術家下沉鄉村,投身藝術公益行動和鄉村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