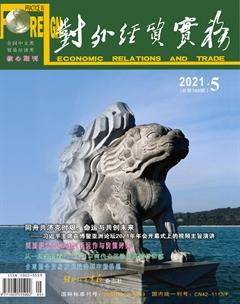中國FTA建設成效評估、制約因素及推進策略
梁剛
摘 要:FTA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以及與其他經濟體擴大經貿合作的平臺。在“十三五”期間,我國FTA建設取得了較大成就,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FTA建設穩步推進,RCEP簽署,與非洲國家締結第一個自貿協定,且大力推進已生效貿易協定的升級。然而,就整體成效看,我國FTA經濟領土覆蓋率較低,貨物貿易覆蓋率有所下降,利用外資覆蓋率和對外直接投資覆蓋率過度依賴于中國香港,FTA中的規則及標準與國際最新經貿規則差距較大。中美戰略博弈、地緣政治掣肘、逆全球化的影響及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挑戰是中國推進FTA建設的制約因素。由此,在未來,我國需要面向全球拓寬FTA締結空間,主動對接高標準經貿規則,激發潛在貿易伙伴與中國締結FTA的動力,同時要做好FTA建設地風險防控。
關鍵詞:FTA;自貿區;自貿協定;規則;標準
過去5年來,全球經濟持續下行,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思潮盛行。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脫歐的影響之下,全球化進程遭到了重大挫折。加上2020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基于此,自由貿易區(FTA)發展戰略是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和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的重要路徑。在“十三五”期間,我國FTA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較大的問題。為此,為了更好地擴大開放和推行多邊主義,我國需要調整FTA發展戰略,大力推進已經生效的FTA提質增效,面向全球貿易伙伴構建高標準的FTA網絡,不斷推動“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之間的銜接,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注入強大活力。
一、“十三五”期間中國FTA建設的成就
(一)“一帶一路”沿線FTA建設在不斷推進
在“十三五”期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的格魯吉亞、馬爾代夫、柬埔寨商簽了自貿協定。其中,格魯吉亞是絲路經濟帶的節點地區,中格FTA作為我國與沿線國家達成的第一個自貿協定,對歐亞地區甚至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均能夠起到較好的示范作用。馬爾代夫雖然經濟體量小,但處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地帶,中馬FTA的簽訂不僅可以豐富兩國的經貿合作形式,也能更好地推進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令人遺憾的是,因印度的干預該協定至今未能生效。中柬FTA的樣本作用更大,這是中國第一次與最不發達國家簽訂的自貿協定,也是將“一帶一路”作為專章納入的自貿協定,為中國與不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合作提供了新樣態。另外,在此期間,我國還與以色列、摩爾多瓦、巴勒斯坦、巴拿馬四國開展了FTA談判工作,進展也比較順利;與蒙古、孟加拉國、尼泊爾三國FTA商簽可行性研究也已啟動。
(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
迄今為止,RCEP是全球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最大的自貿協定,也是我國參與的第一個區域自貿協定。該協定作為5個“10+1”的組合,東盟始終處于中心地位。中國在談判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加強與各方協商,促進了協定的達成。從2012年11月啟動談判到協定達成,先后舉行了4次領導人會議、21次部長級會議和31輪正式談判,除了印度退出外,2020年11月15日15國達成正式協議。RCEP是一個涵蓋全球47.4%的人口、32.2%的GDP和29.1%的貿易量的巨型FTA,內容包括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技術合作等傳統議題,也包括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競爭政策、中小企業、政府采購等新議題,充分兼顧了域內發達成員方、發展中成員方和最不發達成員方的利益。
(三)與非洲國家締結FTA實現了零突破
在2016年之前,非洲國家并未納入到中國FTA建設網絡。在“十三五”期間,中毛FTA的簽署實現了與非洲國家締結FTA零的突破。2017年12月,兩國正式啟動自貿協定談判,經過4輪的磋商,2019年10月達成了正式協議。作為中國與非洲國家達成的第一個FTA,不僅標準較高,而且覆蓋的內容也比較廣泛,既有傳統的貿易投資等主題,也有技術合作等新議題。2021年1月1日生效后,中毛雙邊貨物貿易自由化率分別達到了96.3%和94.2%;服務業領域開放部門超過100個,投資保護規則在原來BIT基礎上也得到了升級。總體看,中毛FTA對于拓寬兩國經貿合作領域,為中國與非洲其他國家貿易往來提供支點作用。
(四)現有自貿協定的拓展升級
在過去5年內,我國更加注重FTA建設的質量,大力推進已經生效的FTA升級談判。其中,內地與港澳的CEPA規則與標準的全面升級,進一步深化了大陸與港澳的經貿合作關系。中國-東盟FTA升級版協定已經于2019年10月全面實施,更多的政策紅利惠及到各國企業和民眾,成為推進中國與東盟貿易升級的重要支撐點。中智FTA、中新(新加坡)FTA、中巴(巴基斯坦)FTA升級版協議也于2019年生效,中新(新西蘭)FTA升級版談判已經完成,中韓FTA、中秘FTA升級版談判正在積極推進中。
二、“十三五”期間中國FTA建設的成效評價
(一)FTA經濟領土覆蓋率不高
“經濟領土”指的是一國已經生效自貿協定的貿易伙伴GDP總和,其總量占全球GDP總量的比重稱為經濟領土覆蓋率。覆蓋率的大小是衡量一國FTA建設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在“十三五”期間,中國雖然新簽了五個自貿協定,但在期間內生效只有中格FTA,因格魯吉亞經濟體量小,對FTA經濟領土總量貢獻有限。至2020年12月底,中國已經生效的FTA15個,涉及到23個貿易伙伴。按照IMF的經濟展望數據庫,我國FTA經濟領土總量由2016年的8.1萬億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9.2萬億美元,但覆蓋率從2016年的10.5%下降到2020年10.3%。我國尚未與全球前10大經濟體簽署已生效的FTA,FTA經濟領土總量及覆蓋率遠低于日韓、越南等國家。因此,我國應在推進RCEP生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快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FTA談判,力爭在談判對象上取得突破。
(二)貨物貿易覆蓋率有所下降
FTA貨物貿易覆蓋率指的是一國與已經生效的自貿伙伴之間的貨物貿易總額占其年度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該指標包括進口覆蓋率和出口覆蓋率兩個方面,比率大小反映了FTA在一國對外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在“十三五”期間,商務部數據顯示,我國與已經生效的自貿協定自貿伙伴貿易額從2016年的14234億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7526億美元,但覆蓋率并未得到增長。2016-2020年,我國FTA貨物貿易平均覆蓋率約為38.1%,比2015年下降了0.4%。就出口覆蓋率而言,2016- 2020年這一數據平均為35.9%,與2015年相比下降了1.2%;就進口覆蓋率看,2016-2020年這一數據平均為40.8%,比2015年上升了0.6%,最高值是2016年(41.6%),2020年回落到40.5%。未來,我國應該積極推進與大型經濟體締結FTA,進一步拓展自由貿易空間。
(三)利用外資覆蓋率和對外投資覆蓋率過于依賴中國香港
利用外資覆蓋率指的是一國利用自貿伙伴的實際投資額占其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這一指標主要反映自貿伙伴在一國引資體系中的地位。在“十三五”期間,我國利用自貿伙伴的外資呈增長態勢,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利用自貿伙伴的外資約963.8億美元,2020年這一數據上升到1141.2億美元。相應地,利用外資覆蓋率也由2016年的75.4%上升到2020年的81.3%,與2015年末相比提升了2.7%。但是,自貿伙伴的外資大多來自于中國香港地區,在整個“十三五”期間,來自于香港的外資額占實際利用自貿伙伴外資總額的平均比重保持在68.1%,2019年更是達69.8%。對自貿伙伴的投資覆蓋率指的是一國對自貿伙伴直接投資流量占其對外投資總流量的比重,可以反映一國自貿伙伴一國對外投資體系中的地位。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對自貿伙伴的直接投資流量呈下降態勢,由2016年的1325.7億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1082億美元,年均降幅達6.3%,然而對自貿伙伴的投資覆蓋率卻呈上升趨勢,由2016年的67.4%上升到2020年的78.4%。這其中,中國香港是主要接受中國投資目的地,2016年接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142.1億美元,到2020年有所下降,但也達到了905.4億美元,中國對其他自貿伙伴投資較少。
(四)FTA締結標準不高
雖然在過去5年內,我國更加注重自貿區商簽的質量,主動向高標準經貿規則靠攏。在貨物貿易自由化方面,已經生效的FTA總體水平較高,如CEPA貨物貿易自由化率達100%,與澳、新加坡、智利等國家的貨物貿易自由化率也超過95%,最新生效的中格FTA貨物貿易自由化率接近94%。在服務貿易及投資方面,市場準入限制也出現了較大的放寬。如CEPA采用了“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RCEP也采取負面清單模式,中韓FTA升級版也采取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協定內容方面,中國締結的FTA在不斷拓寬覆蓋領域,增加了新的議題。如中新(新西蘭)FTA增加了環境保護、競爭政策等內容,符合國際經貿規則的變化趨勢。但總體看,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歐日EPA等高標準協定相比較,我國簽訂的FTA無論是開放水平還是規則標準均與其差距較大。
三、中國FTA建設的制約因素
(一)地緣戰略的掣肘
一直以來,推進與周邊國家商簽FTA是中國FTA建設的戰略重點,但因為周邊國家局勢復雜,互信基礎不強,在商簽FTA中容易受到地緣競爭的掣肘。最典型莫過于印度,印度作為中國周邊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因歷史原因,兩國政治互信度不強。出于國家安全的考量,印度一直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并不斷加強對中國的防范。在RCEP談判中體現極為明顯,印度就要求貨物貿易建立一套單獨的關稅保護機制,當某國對印貨物出口達到一定量時就觸發該機制,進而征收保護性關稅。就在RCEP達成后,印度還聲稱絕不加入中國主導的貿易協定,也不與中國簽署任何關稅優惠的貿易協定。不僅如此,中馬(馬爾代夫)FTA遲遲不能生效、中斯(斯里蘭卡)FTA談判停滯背后均有印度干預的身影。印度一直將印度洋、南亞次大陸視為自身的勢力范圍,對中國進入該區域持排斥態度,由此會嚴重影響中國未來與這一地區國家締結FTA談判。
(二)逆全球化思潮的影響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為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政策提供了溫床和土壤,加劇了逆全球化思潮。英國脫歐就是這一思潮的重要標志,歐美發達國家對外經濟政策日趨保守。中國作為全球化的獲益者,成為發達國家保守經濟政策的批評對象,導致部分國家不愿意與中國締結自貿協定。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華采取遏制戰略,在貿易、科技等領域頻起摩擦,使得部分國家出于貿易風險考量,對與中國開展FTA談判持謹慎態度。加上中國制造能力強大,對大部分經濟體的貨物貿易均呈順差態勢,很多經濟體擔心與中國締結自貿協定后開放市場會沖擊本國相關行業。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沖擊了全球經濟,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思潮,部分國家直接推行國家保護主義,對未來中國建設FTA網絡會帶來極大的挑戰。
(三)高標準經貿規則本身帶來的挑戰
近些年來,在發達國家的推動下,FTA的內容不斷擴展,標準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邊境后議題被納入其中。發達國家奉行這一規則導向,一方面是為了穩固自身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優勢,另一方面旨在削弱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競爭力,謀求重新主導國際貿易秩序。如CPTPP、USMCA中均有單獨的“國有企業”章節,不僅擴大了國有企業的范疇,還嚴格限制了國有企業的商業行為,要求建立透明、公平的非商業援助規則,取消政府補貼及市場優惠。USMCA更是將原產地規則與工資標準相掛鉤,引入勞工價值成分標準。同時,在新一代經貿規則中,發達國家擴大了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并提高保護標準,加強執法以維護本國利益。由此,當前中日韓FTA以及正在研究的中歐貿易協定均面臨著高標準規則的挑戰,對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