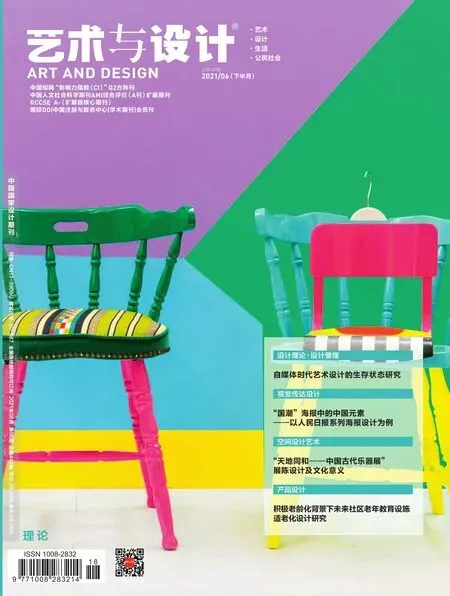“天地同和
——中國古代樂器展”展陳設計及文化意義
鄧璐
(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 100006)
音樂來源于生活,脫胎于時代的社會經濟基礎,映射著時代的精神價值取向,在推動文明發展、促進交流互鑒、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獨特的作用。樂器作為表現音樂、實踐音樂活動的物質媒介,其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物化的音樂史①。“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展”的舉辦是反映中國古代音樂發展演變歷程的代表性物證,彰顯中華優秀傳統音樂、樂器藝術的獨特魅力的展覽。在展陳設計上將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設計視覺元素和代表性色彩,以展現音樂中華文化發展中生生不息和中外文明互鑒的獨特魅力。
一、展陳內容和展陳設計思路
(一)“天地同和”——展陳內容主旨
作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樂的產生、建立和發展由來已久。早期中華文明遺址中,就有以笛、哨為代表的吹樂器和以鐘、鼓為代表的擊樂器。先秦時期隨著禮樂制度的建立,樂器的式樣和形制也更加復雜化,出現了編鐘、編磬等大型組合樂器;與此同時,以琴、瑟為代表的彈弦樂器產生,成為文人雅士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夏朝,樂器的演奏作為統治者享樂的工具。商朝,甲骨文中出現樂器的記錄。周朝,音樂的階級性和等級化明顯,禮和樂緊密聯系,并建立了專業的音樂機構,更好地完善了音樂制度,成為統治者的權勢的標志之一。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聯通歐亞大陸后,開辟了一條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黃金大道,使沿途各國的經濟、文化都受到了深遠的影響。我國古代的音樂、樂器也與沿途國家進行了吸收、融合和借鑒,使古代音樂文化更加繁榮,樂器的類型也日漸多元,達300余種之多。漢魏以來,南北方音樂交流互鑒,加之中原與外域音樂的融合和吸收,演奏水準越來越高,樂器的類型日漸豐富。中國古代樂器充分展現出中華音樂文明的輝煌迭起及持續的發展,展現出中華音樂文化廣博寬厚的胸懷,以及多元一體持續發展前進的宏偉格局。
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講述中國音樂文化博大精深的歷史,堅定文化自信,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個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學校。要把凝結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物保護好、管理好,同時加強研究和利用,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的指示,更好地發揮一個博物館的公眾教育職責,更加自覺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了“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展”,共甄選館藏文物約130件(套),并商借國內近20家文博單位相關藏品共計200件(套),從樂器物質文化自身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出發,以時間為敘述主干,結合音樂史文獻重現富有生命力的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生態。展覽按樂器和器樂共同交織的發展脈絡分為四個部分:鶴鳴九皋、聲聞于天;鐘鼓喤喤、大音至樂;絲竹相合、妙音飛花;云間鑼鼓、日月同輝。
(二)和合之美——展陳設計主導思想
“天地同和”出自成書于漢代的我國第一部音樂《樂記》,這是先秦儒學美學思想集大成者的著作,其豐富的美學思想對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古典音樂的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樂記》中強調的樂為“天地之和”,是一種至高、至大、至遠、至廣的富含有極大包蘊性的大樂觀,體現了宇宙自然萬物運動的生生不息、和諧平衡,與《禮記》“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②的觀念不謀而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華民族和諧的世界觀。以“天地同和”為展覽主題正是以“傳播最完美的音樂與天地自然和諧”為引,體現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而引發“和諧”深廣的社會認知意義和教育意義。
根據展陳大綱內容,展陳設計以深刻挖掘和闡發“天地同和”的文化意義,抒寫中華音樂文化廣博寬厚的胸懷,多元一體持續發展前進的宏偉格局為主旨,用多元化的展陳設計手段展示中華優秀文化的和合之美,求大同的時代意義。
文脈傳承是文化體系的延續,設計中注重中華文脈的傳承和視覺效果的延深,構建符合時代特征的空間場景,充分利用傳統元素、傳統色彩,燈光、多媒體技術等多種手段塑造時代精神,展現文物的時代特性,體現展覽的思想精髓,使觀者如身臨其境。用中華之境、中華之色、中華之美傳承中華之音,傳承和合之美。
二、文脈傳承——展陳空間設計
梁思成先生的著作《中國古代建筑史》有一段對中國傳統建筑的表述:中國建筑乃一獨立結構系統,歷史悠遠……但建筑之基本機構及部署之原則……直至最近半世紀,未受其他建筑之影響③。由此可見,中國傳統建筑發展至今無論從建筑結構、空間思想、裝飾手法上均獨樹一幟。傳統建筑的空間美學、藝術手法等方面與展陳空間設計有諸多異曲同工之處,展陳空間設計從中國傳統建筑文化中汲取養分,既可豐富展陳設計語言,推陳出新,使現代展陳設計語言與現代展陳手法技術和諧共生,又是對傳統文脈的繼承與發揚。此次“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展”展陳設計嘗試用中國傳統建筑的結構、色彩、意境,譜寫中國古代樂器的輝煌的發展史。
(一)中華之境——空間布局設計
展陳空間設計是建立在一定的建筑空間之上,并圍繞展陳大綱的章節結構構建起特定的空間,從內容和形式上賦予空間以時代精神和文化特色。“和合”是中華民族永恒而鮮活的文化精神,凝聚著中華民族對宇宙、自然及世界觀的理性思考,體現了人與自然互敬互畏、繁榮共生的愿望與追求。中國傳統建筑空間也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文化特質,注重“天人合一”的營造思想,此外受禮制等級觀念的制約,中國傳統建筑空間形成了布局呈軸線對稱,空間特性呈內向性、序列性和多變性的特點。王振復曾談到“關于中國建筑中軸線的存在,其實就是‘中國’觀在古代建筑美學思想上的反映”④。中軸線的布局在宮殿、廟宇、佛塔、園林及民居等建筑中廣泛應用。
1.禮制與軸線的傳承
展陳設計中將中國傳統建筑中禮制與軸線的理念貫穿始終。依據展覽大綱,樂器展展廳空間共分為前廳、序廳、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6個主要空間,展陳空間設計依據每部分空間的時代特征,以禮制與軸線的傳統建筑空間布局劃分展廳空間,設置5條主軸線,3條輔軸線。(圖1)

>圖1 展陳空間軸線分析圖
前廳是整個展覽的開篇,是觀眾進入展覽的第一序列空間。展覽入口位于展廳的北側,原建筑結構上有兩個寬3米高3米的入口。若以原建筑展廳門做展覽入口則尺度小,不能凸顯展覽主題,故將此次展覽前廳空間外推至館內公共空間,使前廳空間平面軸線與公共空間軸線重合形成規整劃一的空間序列,此種設計手法既使得展廳空間與建筑空間軸線有機結合、整體劃一,又使展覽的整體氣氛推至公共空間形成了恢弘大氣的空間氣勢,起到吸引觀眾的視覺效果。
將前廳軸線延伸至展廳內序廳空間,共同形成展陳空間的第一條軸線。沿第一條軸線進入展覽空間的第二空間序列,第一部分: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此空間平面成矩形,以矩形的中軸線設置展陳空間軸線,展臺和展品沿空間軸線兩側對稱布局,此為整個展覽的第二條空間軸線。與此空間相接的是第三空間序列,展覽的第二部分:鐘鼓喤喤、大音至樂。受建筑空間的限制設計將此部分空間劃分成兩個并列的矩形,沿矩形的中軸線設置展廳空間中軸線形成展覽的第三條和第四條軸線,集中展示夏、商、西周、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的樂器。此部分從秦、漢兩個時代的建筑遺跡及畫像磚上汲取建筑空間布局、高臺、木架建筑及室內陳設的典型性元素并轉化為展陳設計語言,傳承傳統建筑中的禮制觀念和文化符號以塑造展廳空間的時代文化特征。沿空間流線進入展覽的第三部分:絲竹相合、妙音飛花,此部分集中展示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的精美樂器。唐代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聲譽遠播,萬國來朝達到鼎盛。唐朝接納各國前來交流學習,經濟、社會、文化、藝術呈現出多元化、開放性等特點⑤⑥。空間布局設計為自由式和軸線對稱式兩種類型,在表現中國古代建筑室內空間禮制傳承的同時也體現出唐代文化的多元交融的特征。古琴為此部分展陳的重點,設計以唐代古建筑為視覺元素的集中展示區,古建筑的軸線形成展廳的第五條主要軸線。(圖2)
三條輔助軸線分別位于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是為把控空間秩序以形成有序的參觀流線而對主要軸線的補充(圖2)。主軸線和輔軸線既是劃分展廳空間的主要依據,也是觀眾參觀的主要和次要動線,起到引導參觀方向的作用。

>圖2 展廳軸線視角實景圖
2.自由與多變的傳承
有序和有機是中國傳統建筑空間構成的特點之一。建筑平面以“間”為單位展開空間序列,由一間或若干間構成單體建筑,再由單體建筑組合成建筑群落。這樣的布局方式每個單體規模無需很大,可根據使用功能組合變通。這種建筑群體的組合方式,在中國古典園林的使用中最為突出。中國古典園林是中國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源于先秦秦漢時期,形成于唐宋時期,到明清時期到達頂峰。中國的古典園林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自由的布局表現大自然的天然山水景色;所造假山池沼渾然一體,宛如天成,充分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和民族文化特色,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宇宙觀。這與“天地同和”所表現的宇宙自然萬物運動生生不息、和諧平衡的觀念有異曲同工之處。
展廳空間設計傳承傳統建筑、園林自由多變的空間意境,在第三部分唐代和第四部分明清的局部展陳空間內設計了自由的空間布局,體現出曲徑通幽、移步換景的空間趣味,以達到豐富展廳空間層次和合理規劃展廳流線的作用,使觀眾能夠跟隨展廳空間流線欣賞展出的精美樂器,品味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樂器文化。
小結:在展陳空間的設計上注重中國傳統建筑、室內、園林空間意境的傳承。用大空間、大意境抒寫中國傳統空間禮制與軸線、自由和多變的空間序列,用中華之境表達“天人合一”的營造思想,展現“天地同和”的展覽主題。
(二)中華之色——色彩設計
中國傳統色彩體系主要以象征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的陰陽五行的宇宙觀為架構,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古代典型哲學思想的五色體系,深刻影響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生活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對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認同、審美取向和性格塑造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失的“文化基因”。中國古代色彩體系中有“五色”(五正色)青、赤、黃、白、黑和“五間色”紅、綠、紫、碧、騮黃。
“五色”青、赤、黃、白、黑,誕生于遠古華夏先民對色彩的樸素認知,雖萌生于原始荒蠻時期,但卻為中國五色學說的思想建構提供了精神文化的雛形,物質文明的傳承也為此思想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五色始終說”在中國古代對色彩的運用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區分和色彩禁忌。《春秋繁露·五行之義》云:“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引申到五正色即青為始,赤為榮,黃為主,白為本,黑為終⑦。中國歷史朝代幾經迭易,但在用色上總體遵循著“五行五色”的哲學思想。“五色”名稱雖在幾千年記載中固定不變,但自然界五花八門的色彩僅憑此解釋顯然是不足以描繪的。隨著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五間色”理論,彌補了這種缺陷,豐富了中華五色系體。《禮記正義》:“正義曰: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間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色東方間……”⑧。與此同時產生了“正為貴、間為賤”的用色理念,強化了“正色”的正統性、階級性和合法性,從而為帝王統治與社會等級的劃分提供了理論依據。
展陳色彩是展陳設計中重要的設計語言,起到了烘托展廳氣氛、塑造空間意境、突出展覽主題和文化背景的作用,因此如何選擇符合展覽主題的色彩用于展陳空間是展陳設計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國古代樂器展將從中國古代五色和五間色體系中深入挖掘能象征各個時期政治、文化、思想的色彩,用中華之色描繪中華音色。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的用色既能反映當時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又主宰著臣民的審美情趣,構建著國家色彩文化的心理認同。展陳設計色彩將提取每個朝代的代表色、流行色進行調和,調和出能夠貫穿整個展覽脈絡,體現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承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氣的顏色。
五色中的是“赤”自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都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地位。“赤”字在甲骨文中是“一個人在地上點了一堆火”,在先人的生產生活中,“赤火”的廣泛應用形成了華夏先民的共同審美追求,也體現了先祖對太陽的崇拜。“赤”成為一種精神文化符號,象征著英勇、旺盛、收獲、喜悅。考古發現的遠古時期的紅色巖畫,也證實了先民對赤的推崇。紅色從古以來也是統治者政治的依托,預示著國家的繁榮昌盛。五色之中也只有紅色被冠以“中國”,稱之為“中國紅”。展陳色彩從眾多紅色中選取牡丹紅(C0 M99 Y72 K28)為基礎色。
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黃色中原土壤上孕育出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出土了精美而富有藝術張力的彩陶,土黃色、橙紅色的胎體上呈現出赭紅色、黑色等色彩的美麗圖案,是我國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彩陶的色彩具有自然和諧的配色特點,代表著先民對色的理解,表現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然觀。從遠古彩陶中提取代表色,沙棕色(C26 M53 Y79 K26)、玄色(C50 M90 Y90 K10)和黑(C0 M0 Y0 K100)為空間輔色,用色彩的文化符號充分體現遠古華夏先民的色彩審美,突出時代精神。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黑、白、赤三統(或三正)三色周而復始循環。秦尚黑,漢尚赤,到了秦漢時期,色彩更加鮮艷:金、朱、黃最高貴。選取正黑(C30 M0 Y0 K100)、番茄紅(C0 M100 Y82 K22)為主色,金色、赤金(C5 M25 Y95 K0)為時代代表色。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全盛時期,思想開放,兼容并蓄,既吸收中原及西域各個民族的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與歐亞大陸各國進行文化交流,使唐代在建筑、服裝、陶瓷等各個方面用色大膽,華麗明艷,尤其是受胡風影響的濃郁厚重的紅色,以及蓬勃朝氣的綠色成為當時的流行色。在《全唐詩》提及女性衣裙的625首詩歌中,紅色裙衫占36%,綠色裙衫占15.5%。紅配綠也成為最流行的搭配,在《虢國夫人游春圖》中,貴妃的兩位姐姐淺綠配粉紅的穿衣著色,明艷動人。在唐代,還有一種顏色比紅綠更讓人渴求,那就是不易獲得的紫色。展陳空間中選取紅梅(C0 M73 Y24 K0)、青竹(C92 M28 Y67 K0)、菖蒲(C71 M87 Y14 K0)、魚肚白(C12 M11 Y15 K0)為代表色彩。
宋代一度流行白色,講求淡雅和諧的配色觀。元至明初,褐色是當時的流行代表色,元代《碎金》和明初《輟耕錄》中出現了大量的褐色衣著。明中期,明人偏愛濃艷的色彩。這些色彩的流行趨勢在當時的繪畫作品中都得以體現。在這些濃艷的色彩上加以金色的裝飾是這個時期的用色特點。晚明后色彩流行變得柔和,玄色、皂色、白色等素色開始流行,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清代康熙前期,清后期流行色彩更豐富,紅、黃、藍、紫、白為主調,成為女性服裝色彩主調,表現出清雅平和的氣息。在這些色彩中唯有明黃色,自唐以來成為皇家的專用色。從此時代選取月白(C6 M4 Y10 K0)、藤黃(C0 M25 Y86 K0)為代表色。
從中國古代色彩體系“五色”和“五間色”中研究各個時代的色彩審美趨勢,并考慮展陳色彩的整體性和統一性,將各色進行調和,將選取的13個代表色透疊,調和出具有包容性的復合色彩,此色彩中既有紅色的基調,黃色的滲透,又有黑與白的調和,產生出具有神秘、悠遠氣質的色彩,定名為“大樂之韻”(C33 M66 Y66 K0)(圖3)。蘊含著醇厚和深遠的文化精神含義的復合性色彩,體現著中華民族質樸純真的原始審美追求,以及中國古代樂器發展的包容并蓄、博大精深和當代中國繁榮而又充滿活力的發展趨勢。

>圖3 展陳空間色彩推導圖
小結:回顧中國歷史上創造出的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大都能辨析出歷朝歷代鮮明的色彩特征,展現其獨特的時代風格。中華之色“五色”和“五間色”在展陳設計中的應用也為文物和歷史文獻的展示提供了一個歷史文化的視覺背景,具有傳承歷史和繼承文化基因的現實意義。
(三)中華之美——場景設計
展覽中的場景設計是展陳空間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符合文物的時代特點的空間場景的搭建,還原文物使用環境,塑造具有歷史特點的空間場景,通過立體三維的設計語言,聲環境和光環境設計使文物背后的文化歷史信息得到更恰如其分的傳達,帶給參觀者全方位的參觀體驗。
第二部分展陳設計從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的建筑和室內陳設中深入挖掘代表性元素,創造與展品的時代性基本吻合的空間場景。秦漢建筑繼承了商周初步形成的重要藝術特點,夯土臺基木構架、斗的應用,院落式組合和對稱布局等在這個時期均已出現。秦漢的統一促進了中原與楚吳建筑文化的交流互鑒,建筑形制日臻完善,形成了規模宏大組合多樣的建筑群。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為了與天神相通建起了高臺建筑,呈團塊狀,軸線對稱組合。西漢末年,長安南郊的名堂辟雍和宗廟遺址仍沿用春秋戰國的高臺建筑方法,用小空間木架建筑環包夯土臺,形成大體量⑨,但是由于年代久遠,目前尚未發現秦漢木構建筑。但可從有關史料和漢代墓葬出土的大量畫像磚和冥器中了解當時的建筑結構形式、建筑組群布局和室內布置的具體形象。如四川成都羊之山出土的畫像磚上的夯土臺基,抬梁式木構架,院落布局;廣西合浦漢墓群望牛嶺出土的穿斗式架構銅屋(圖4)。在此部分展陳空間設計軸對稱的以“間”為基本單元的“臺基式”獨立展示空間,底部空間抬起,頂部使用穿斗式木架支撐結構,在空間中排列組合形成“臺基式”展臺的群布局。屏風是中國傳統室內陳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秦漢時期屏風在室內空間得以大量運用,其集實用性和裝飾性于一體,既能分割空間營造室內空間氣氛,又能界定尊位,彰顯威儀,是階級地位和禮儀制度的體現。如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云龍紋漆一字型屏風,山東安丘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的“L”型屏風(圖5),我們從出土的大量文物中不難發現屏風是重要的室內陳設家具。在“臺基式”大型展臺文物展示空間的背后增加屏風的元素,通過時代性建筑及室內陳設元素的應用豐富展廳陳列的空間層次,凸顯中國古代樂器的禮儀性和階級性(圖6)。

>圖4 廣西合浦漢墓群望牛嶺出土的穿斗式架構銅屋

>圖5 山東安丘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的“L”型屏風

>圖6 “臺基式”獨立展示空間及屏的應用
古琴中的精品,唐代古琴“九霄環佩”是展覽第三部分的重點展出文物。古琴有著三千多年的歷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元素,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此部分空間的主體形象也以突出“九霄環佩”為展陳設計重點,空間造型選取唐代建筑氣勢雄偉、形體俊美、莊重大方的木構建筑的形式,轉化設計為展陳空間場景“古琴廊”,并植入古琴音源(圖7)。唐代古建筑舒展而不張揚、華美而不纖巧,古樸而富有活力的氣質,契合了古琴之音色深沉、安靜悠遠、音域寬廣和余音悠遠的特點,展現古琴深邃的文化內涵。

>圖7 古琴廊展廳效果
第四部分展覽中展示故宮的中和韶樂文物一組,為展現此組文物在演出時各個樂器的演出位置,特設計以清代宮廷戲臺為元素的大型“戲臺展臺”,使文物與展陳空間的空間意境和文物的文化意境匹配,傳達更豐富的文物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知識點。尾廳空間主要展出中國古代樂器的現代化改良和演變,以及與西洋樂器的相互影響、共生發展,展示中國古代樂器的無限包容,展現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永恒魅力,更突出了“天地同和”的新時代意義。榮格原型心理學理論分析,圓形是人類共通的、普遍的、世代相承的原型之一,有“無限”“永恒”“輪回”“向心”“和合”等觀念涵義。因此在展覽尾部設計圓形圍合空間,突出“和合”的空間意向,緊扣“天地同和”的展陳主旨思想。
小結:通過各個時期建筑及室內陳設代表元素的提取,設計符合時代性的空間場景,從而拉近觀眾與文物之間的時空距離。充分挖掘中華文化的獨有元素,用中華之美展現時代之境是此次展陳空間設計的一次重要嘗試。
三、結語
展陳設計是一門綜合的藝術表現形式,通過空間、色彩、燈光等綜合設計語言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產生活的差異,塑造獨具時代特色的空間效果。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展陳設計趨同化愈加明顯,如何運用中國的、本土的元素設計出獨具特色的展陳空間形象是展陳設計工作者值得不斷研究和挖掘的工作。
中國傳統建筑及室內陳設元素的多元化應用是創作具有中國特色歷史文化和獨有形象無可替代的主旋律,同時也帶動著展陳空間設計中包含著本土的和歷史的、地域性和時代性的文化因素的開發。中國展陳設計從中國傳統建筑和室內陳設中汲取營養,既是對學科藝術門類的豐富,也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符合時代精神的展陳空間設計以展出文物為基礎,以當下社會環境為背景,對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和精神達到一個再認知和再利用的目的。此次展陳設計中,中國傳統建筑的木架結構,以及室內陳設中的屏元素被廣泛應用到空間設計和展柜設計中,并將中國傳統五色、各時代流行色彩、古代空間和色彩的哲學思想應用到展陳空間設計中,以突出這些凝結著中國古代旋律和音容的中國古代樂器的時代性和文化性。通過傳統文化符號的應用使此次展覽既是傳統文化的現實展示,是公眾獲取知識的良好途徑,又是中華民族進入偉大復興新時代,展陳設計繼承中華優秀文化基因樹立公眾文化自信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當下我們步入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文化自信因時而生。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的環境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展陳設計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其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輔相成,進而促進以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為背景,汲取其精華而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展陳設計,這將是展陳設計工作者值得長期探索的命題和面臨的挑戰。
注釋:
①王春法.“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展”前言.
②《禮記·郊特性》第十一。
③梁思成.中國古代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④王振復.大地上的宇宙——中國建筑文化理念[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⑤《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丙申,詔以回紇部為瀚海府,仆骨為金微府,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渾為皋蘭州,斛薛為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蹛林州,白霫為置顏州。
⑥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七章〈唐五代的文化概況〉》
⑦董仲舒.春秋繁露[M].周桂佃,譯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413.
⑧戴圣.禮記[M].陳澔,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9.
⑨潘谷西.中國建筑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