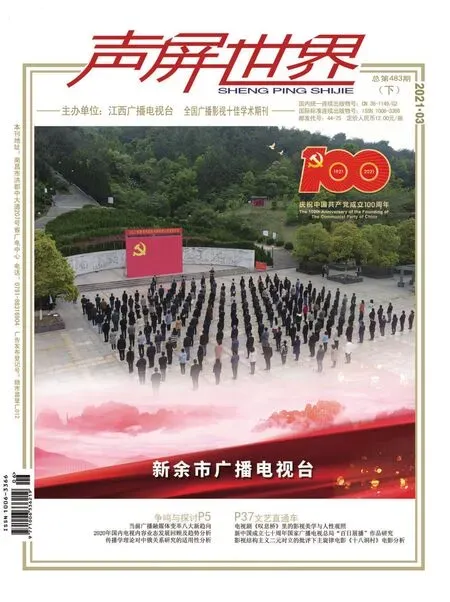敘事的高度類同和巨大悖反
——《偷自行車的人》和《小鞋子》敘事比較
□ 曾琦琪 陳紅光
按照接受美學(xué)理論,文本的敘事圖景勾畫出了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輪廓,并通過文本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召喚接受者參與其中。敘事高度類同的電影在審美接受上理應(yīng)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觀感體驗(yàn)。只是,《偷自行車的人》和《小鞋子》卻并非如此,前者令人絕望,后者溫暖感人。
兩部電影在觀感上嚴(yán)重悖反的成因是什么?這種敘事的異同比較,對(duì)中國(guó)主旋律電影的價(jià)值輸出,有什么借鑒意義?
電影敘事高度類同
敘事結(jié)構(gòu)高度類同。電影敘事結(jié)構(gòu)的五種常見類型分別是:因果式線性結(jié)構(gòu)、回環(huán)式套層結(jié)構(gòu)、綴合式團(tuán)塊結(jié)構(gòu)、交織式對(duì)比結(jié)構(gòu)、夢(mèng)幻式復(fù)調(diào)結(jié)構(gòu)。所謂“因果式線性結(jié)構(gòu)”,“其一是指該結(jié)構(gòu)模式主要以時(shí)間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為敘述動(dòng)力來推動(dòng)敘事進(jìn)程;其二是指其敘事線索以單一的線性時(shí)間展開”。
《偷自行車的人》與《小鞋子》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上,同屬于因果式線性結(jié)構(gòu)。以物品(自行車或鞋子)丟失為敘事元點(diǎn),以時(shí)間先后及因果邏輯為敘事規(guī)則,環(huán)環(huán)相扣,不斷形成新的敘事變奏。
敘事脈絡(luò)高度類同。《偷自行車的人》和《小鞋子》,都以生活中日常物件的丟失帶來生計(jì)威脅作為敘事動(dòng)因,以物件的尋找過程建構(gòu)電影文本。
在情節(jié)脈絡(luò)上,兩部電影幾乎可以劃上等號(hào):物品丟失——物品尋找——接近丟失物品——尋物首次失敗——提出新的辦法——尋物最終失敗——落寞歸家。
在情感走向上,兩部電影也近乎類同:兩部電影都經(jīng)歷了情感的沖突(父親的一巴掌妹妹拒絕原諒哥哥的粗心)、情感彌合(高檔餐廳的一頓飯妹妹接受哥哥的禮物)、情感互助(父子共同找車哥哥運(yùn)動(dòng)會(huì)上贏獎(jiǎng)品)三個(gè)階段。
底層敘事高度類同。“底層”,由意大利共產(chǎn)主義者葛蘭西率先提出,代表“下層階級(jí)”,主要指無產(chǎn)階級(jí)。《偷自行車的人》和《小鞋子》都將鏡頭對(duì)準(zhǔn)底層民眾,表現(xiàn)小人物的悲喜人生。
兩部電影都采用以小見大的敘述方式。一輛普通的自行車、一雙破爛不堪的鞋子,在苦難的底層社會(huì)卻意味著命運(yùn)的轉(zhuǎn)變或生活的暫時(shí)安穩(wěn)。在《偷自行車的人》中,自行車是妻子當(dāng)?shù)舸矄螕Q來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萬人競(jìng)爭(zhēng)的崗位所必須的勞作工具,更是改變家庭命運(yùn)的唯一出路。然而,這根救命稻草在眼皮底下被人偷走了。在《小鞋子》中,鞋子是順利到達(dá)課堂的必須物件,更是兄妹腳下卑微的尊嚴(yán)。
日常物件的被竊丟失,最終讓一對(duì)父子一雙兄妹陷入生活的絕境和精神的焦灼。如何在第二天上班前在不給父母添新麻煩的情況下,找到車或鞋子,成了電影主人公不得不去努力突破的難題。
親情敘事高度類同。兩部電影都將親情作為敘事的重要內(nèi)容,并在核心關(guān)系上同樣安排了兒童的角色。《偷自行車的人》涉及丈夫、妻子和兒子三個(gè)角色,核心關(guān)系是父子。《小鞋子》涉及父親、母親、哥哥和妹妹,核心關(guān)系是兄妹。
從尋車的成功概率來看,《偷自行車的人》中妻子參與尋車定然比兒子尋車成功概率更高。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德·西卡卻“極為巧妙地幾乎回避了妻子這一角色”,卻讓一個(gè)懵懂的兒子不斷見證父親的焦躁、沮喪乃至不擇手段。
此外,為了凸顯兒子的作用,德·西卡甚至在“選定這位小演員之前,并沒有讓他試演,而只是讓他走一段路。導(dǎo)演希望在大人的徐步旁看到孩子急行的碎步,因?yàn)榫瓦@種不和諧中的和諧本身來說,對(duì)于理解整個(gè)場(chǎng)面調(diào)度也是至關(guān)重要的”。兒子的加入,已經(jīng)不是尋物劇情需要,而是敘事的需要。細(xì)碎的步伐,難以跟上父親的步履匆匆,既強(qiáng)化了父子之間的敘事張力,更能突出一輛自行車丟失如何讓父親陷入到極端的焦灼。“兒子這一角色的獨(dú)特構(gòu)思確是神來之筆”,遠(yuǎn)勝于夫妻尋車的可看性。
在《小鞋子》中,導(dǎo)演同樣關(guān)注到孩童世界,卻幾乎屏蔽了成人世界的參與。導(dǎo)演通過一雙鞋子的丟失,兩個(gè)不敢聲張的靈魂,以成人觀眾的在場(chǎng)去到達(dá)銀幕上孩童世界的缺席。只是當(dāng)觀眾在銀幕上期待一場(chǎng)童真之旅時(shí),卻在孩子視點(diǎn)的引導(dǎo)下,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伊朗苦難現(xiàn)實(shí)的汪洋。這對(duì)兄妹為一雙破舊得早該拋棄的鞋子,用純真卻無力的行動(dòng)在自己的世界中互相扶持。這份艱辛令人淚目,這份純真讓人心疼,這份親情又令人感動(dòng)。
通過同點(diǎn)類比,可以看到兩部電影在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脈絡(luò)、底層敘事、親情設(shè)定四個(gè)方面的高度類同。只是,敘事高度類同的兩部影片,怎么在審美觀感上卻存在著嚴(yán)重悖反?這其中的敘事奧秘究竟是什么?
審美悖反及成因
本文將借用克羅德·布雷蒙的枝形結(jié)構(gòu)、麥茨的“八大組合段”,試圖分析兩位導(dǎo)演是以什么樣的敘事手法,使影片的情感表達(dá)從高度類同的內(nèi)容中逃離出來,忠誠(chéng)地皈依于兩位導(dǎo)演不同的美學(xué)旨趣。
枝形結(jié)構(gòu)與解決方案。1929年,克羅德·布雷蒙提出不斷二分的枝形結(jié)構(gòu)。其具體表述為圖1。

圖1 克羅德·布雷蒙的枝形結(jié)構(gòu)
在克羅德·布雷蒙看來,經(jīng)典電影的敘事結(jié)構(gòu)有兩種:A1-A3a模式,或A1-A4b模式。A1-A3a模式通過新的解決方案成功化解危機(jī),影片呈現(xiàn)團(tuán)圓結(jié)局,屬于正劇或者喜劇;A1-A4b模式無法通過各種方案解決難題,屬于悲劇。
顯然,《偷自行車的人》與《小鞋子》同屬于A1-A4b的悲劇模式。兩部電影雖然采用了類同的主線脈絡(luò),在細(xì)節(jié)的處理上卻存在著細(xì)微差別。也正是這些差別,影響著影片的審美觀感。
首先,解決方案的本質(zhì)區(qū)別:《偷自行車的人》與《小鞋子》都經(jīng)歷了尋找失敗的過程。只是在尋找失敗之后,里奇和阿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卻存在質(zhì)的區(qū)別。里奇尋車失敗之后,竟然突破道德和法律界限,想以偷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危機(jī)。而《小鞋子》主人公阿里的方案則是通過參加運(yùn)動(dòng)會(huì)贏得獎(jiǎng)品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目標(biāo)。盡管兩個(gè)方案最終都?xì)w為失敗,但里奇和阿里的做法,在觀眾接受層面會(huì)引起心理差異。前者令人唏噓感慨,后者讓人敬佩感動(dòng)。
其次,問題未解決的微調(diào)改造:《偷自行車的人》在里奇偷車失敗之后,便再也無能為力,沒有新的解決方案。《小鞋子》的主人公雖然沒有解決方案,但主人公的父親卻買了兩雙童鞋作為想象性解決。
《偷自行車的人》全片都在描寫努力的無能為力。在影片結(jié)尾,德·西卡既不曾安排里奇的妻子再做努力(比如再當(dāng)?shù)羰裁葱膼鄣奈锲罚膊辉鵀槔锲姘才判碌某雎罚ū热缃桢X買車),導(dǎo)演只是殘酷地看著里奇一家人走向失敗。“只提出問題,而沒有給出答案,這誠(chéng)然達(dá)到了真實(shí)的藝術(shù)效果,是那個(gè)特定年代和特定環(huán)境中人們普遍心態(tài)的真實(shí)反映,但也使影片自始至終籠罩著濃郁的悲觀絕望的情緒,觀眾看不到一絲的光明和希望,這將使受苦受難的普通的人們更加消沉、更加絕望。”
《小鞋子》則不然,馬基德·馬基迪對(duì)影片結(jié)局進(jìn)行了改造。開機(jī)前夕,《小鞋子》的劇本依然是以父親買鞋作為結(jié)尾。導(dǎo)演馬基德·馬基迪對(duì)此并不滿意,“還在思考怎樣可以有一個(gè)精彩的結(jié)局,他跟團(tuán)隊(duì)說,沒有好的結(jié)局不開機(jī)也罷……最后寫出了這樣的神來一筆:阿里跑步回來把腳磨破了,阿里把腳泡在池塘里,魚兒來親吻他的腳。”
“貧窮是可以打敗的,就像戰(zhàn)爭(zhēng)一樣。我們應(yīng)該告訴我們的孩子,生活是有希望的,我們要通過努力去戰(zhàn)勝它。每個(gè)人都是有責(zé)任感的,可以擺脫貧窮,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馬基德·馬基迪的影片,不回避苦難但不沉迷于苦難。他總是在苦難之外,專注于挖掘伊朗人民頑強(qiáng)的生活意愿,使影片呈現(xiàn)出濃郁的伊斯蘭文明的詩意特質(zhì)。
需要指出的是,馬基德對(duì)影片結(jié)局的改造,屬于敘事的強(qiáng)力行為。父親買鞋與阿里的努力在敘事脈絡(luò)上存在邏輯斷裂,買鞋從父親這條輔線來看也不存在前后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它憑空而出,硬性植入,不做解釋,是導(dǎo)演通過強(qiáng)力手段為敘事提供的想象性解決,也是導(dǎo)演對(duì)觀眾提供的想象性撫慰。
插曲式段落與情感溫度。麥茨認(rèn)為,一部電影存在如下八種獨(dú)立語段,分別是:鏡頭、平行組合段、括入性組合段、描述性組合段、交替敘事組合段、場(chǎng)景、插曲式段落和一般性段落。筆者發(fā)現(xiàn),在麥茨的八大段落中,插曲式段落的使用,對(duì)文本的情感走向有明顯的干預(yù)。
所謂插曲式段落,指發(fā)生的情節(jié)跟主要情節(jié)沒有直接、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段落。剔除插曲式段落,并不會(huì)影響故事意義的完整呈現(xiàn)。兩部電影的描述性組合段、線性敘事組合段、場(chǎng)景、一般段落所構(gòu)成的敘事脈絡(luò)有高度類同性,關(guān)于這點(diǎn)在前文枝形結(jié)構(gòu)部分已有論述,不再贅述。
面對(duì)苦難的現(xiàn)實(shí),《偷自行車的人》插曲式段落呈現(xiàn)出負(fù)向能量,整部電影滲透著濃郁的絕望與悲涼感。而《小鞋子》則呈現(xiàn)出正向能量,影片中的人物雖然浸泡在苦難的汪洋中,但插曲式段落中折射出來的人生態(tài)度,插曲式段落反應(yīng)出的人際關(guān)系,都洋溢著詩意溫情。
如果將《偷自行車的人》與《小鞋子》從解決方案、人物安排到插曲式段落做一個(gè)反向改造,在類似的苦難下,兩部電影呈現(xiàn)出來的定然是與影片相反的敘事溫度。
此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影片觀感的悖反,并非只是敘事單方面起作用。音樂的調(diào)性、演員的選擇、場(chǎng)景的使用、色彩與光線的安排,都在文本中發(fā)生綜合作用。如果一定要將眾多元素分個(gè)主次,筆者認(rèn)為,敘事依然是邏輯主導(dǎo)。
現(xiàn)實(shí)意義
底層敘事一直是電影表現(xiàn)的重要場(chǎng)域。在中國(guó)主旋律電影中,不少電影關(guān)注底層社會(huì),宣揚(yáng)“真善美”的價(jià)值觀,并期待以此縫合變革進(jìn)程中的社會(huì)裂痕。客觀地說中國(guó)主旋律電影中的底層敘事,創(chuàng)作數(shù)量很多,贏得成功的很少。電影敘事的假大空,為觀眾所普遍疏離。
中國(guó)主旋律電影固然無法參照《偷自行車的人》進(jìn)行創(chuàng)作,卻可以借鑒《小鞋子》如何借助團(tuán)圓結(jié)局與插曲式段落,在苦難與溫情中穿梭自如。
注釋:①德·西卡和馬基德·馬基迪都對(duì)兒童題材的電影有所偏愛。德·西卡導(dǎo)演過《孩子們?cè)谧⒁曋覀儭贰恫列?馬基德·馬基迪導(dǎo)演過 《手足情深》《父親》《天堂的顏色》《巴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