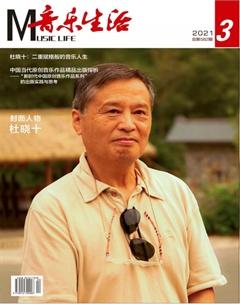從詩到樂
周靜 陳韻
受交感美學觀影響,德彪西的作品感官交互性強,常伴以超越聽覺的畫面感。德彪西的音樂中所呈現出情景性以及其生成過程是本文重點討論的問題。文章旨在通過其鋼琴作品《泛舟》作為個例分析,試圖探尋德彪西如何在魏爾倫的美學觀念影響下,借由音樂語言作為媒介完成音樂中的情景建構,從而達到“超感官”的審美效果。
一、《泛舟》之創作緣起
《泛舟》創作于1889年,基于象征主義詩人魏爾倫1869年出版的詩歌集《佳節集》中的同名詩歌所作,是德彪西極富視覺效果的代表作品之一。德彪西通過馬拉美所舉辦的“周二聚會”與魏爾倫結緣,而后德彪西的音樂創作便與法國象征主義詩人魏爾倫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聯系,近乎三分之一的藝術歌曲皆來自魏爾倫的詩歌啟發,可見,魏爾倫詩歌中所呈現出的交感美學觀也對德彪西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交感美學觀,即體現視覺的色彩感、聽覺的樂感和嗅覺交叉連通,使詩歌極富音樂性和畫面感。通過印象的捕捉及場景的構建實現對內心情感的抒發,拋棄詞語意義使詩歌中的象征場面形成朦朧的美感。在《泛舟》這一情景空間中,德彪西通過生動的音樂語言構筑了一個聲色交融的藝術空間,以音響為畫布、詩歌為依托完成了詩情詩景的建構和復現。

德彪西
二、構筑情景空間的音樂語言
(一)模擬主體物質形態
畫面中的主體是視覺感知的核心元素,而德彪西正是通過音樂語言模擬主體形態使其視覺化。鄭克魯在探討魏爾倫的創作特點時提出,“魏爾倫則僅僅以一種場景去象征或繪寫心靈狀態。而魏爾倫的象征總是運用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如月光、雨、狂歡場面、綠色的自然景物等”。同樣,德彪西也是以景物為創作的主要對象。就《泛舟》來說,水、舟都是“泛舟”情景畫面中的結構主體。
從德彪西的不少作品中都可以發現“水”的元素,而《泛舟》正是德彪西對水這一物質描繪的初步探索。通過對水在不同狀態下,如波紋、漩渦以及急流等形態的觀察,德彪西將琶音與附點四分音符的長音進行組合以模擬視覺上波紋的蔓延,從而達到視聽聯覺的效果。

譜例1 第70-71小節
除此之外,象征急流的音型(譜例1)是水在該曲中另一形態的表現。這一音型不僅成為再現部聲部Ⅰ的低音旋律,同時也作為銜接B部與再現部的自然過渡,使前者的意境得以延續和保留。在整個作品中,急流音型主要分布于B及A部分,共出現20次,并于再現部(A)在高聲部與低聲部交替出現。這種聲部上的交替,使空間上產生由近及遠的感覺,與華多(18世紀法國畫家)的《發舟》中從近景到遠景的構圖一致。德彪西運用擬態的手段使樂中之景更富畫面感的同時,也為《泛舟》中的空間流動提供了移動視點。
(二)空間流動性
在《泛舟》中,內部空間是連續的,不是割裂的。而這種空間的流動性主要由聲部Ⅱ的琶音織體支撐,連綿不斷的琶音推動著舟(聲部Ⅰ)向前行進。象征著水流的聲部Ⅱ在全曲中有較為明顯的形態轉變,例如“波紋”到譜例1“急流”音型的轉變,不僅體現出情緒上的遞進,也是情景畫面由近景向遠景的過渡。
除了貫穿始終的水流(聲部Ⅱ)形態變化所引起的畫面變化,其他結構主體的動態變化也引導聽者感知場景的轉變。德彪西在《泛舟》中使用模進手法,使畫面中的主體發生位移,從而使情景空間變得更為“立體”。如再現段中聲部Ⅰ的旋律以下行八度的模進,視覺上產生“舟”逐漸遠去的畫面感。模進所起到主體位移的功能同樣體現在全曲的各個部分,包括三度、四度、五度以及八度模進。另外,德彪西對于織體的變化處理,為畫面增添了景深的效果。主旋律的伴奏織體在A部分中原為琶音和弦,內聲部為柱式和聲。德彪西在再現部中采用了“急流音型”作為內聲部,與B部分結束處銜接,不僅延續了B部分的意境,且與樂曲開始部分的近景產生對比。
(三)色彩及層次變化
《泛舟》的色彩變化體現在變和弦、色彩音、半音線條及全音階的使用上。德彪西通過色彩音對畫面進行調色,突破調性的束縛。如譜例2所示,在此處德彪西通過加入和弦外音#d以及?f作為色彩音構成橫向的半音線條,將縱向和聲變為橫向旋律的線性流動。半音線條的使用在全曲中有三處。

譜例2 第40-43小節
從縱向來看,此處還體現了德彪西對于變和弦的運用。變和弦的運用是音樂色彩變化的重要體現,也是德彪西重要的作曲技法,在不改變和弦功能及不超出調性范圍的條件下,通過將調式中的全音進行改為半音進行,使其傾向尖銳化。在該曲B部分第41—50小節中較為集中地出現變和弦,共計出現3次。
此外,德彪西在該曲中進行了全音階的初步嘗試。將第70小節中的音列排列,“c-d-e-#f-#g”(譜例1)具有全音階的特征。第71—78小節重復以c音為始的全音階素材共6次,功能在于高潮之后的回落,由于在此之前不穩定的屬七結構的連續進行,全音階的出現帶來了色彩上的轉變。再現部第83—84小節同樣出現了全音階素材,但其音列不同于前者。德彪西在此處將全音階的素材作為延長的內聲部,和琶音式和弦的縱向排列。為了不讓音響產生渾濁的效果,因此在節奏的排布上是交錯進行的。
三、《泛舟》情景畫面的層次布局
(一)意以景為先
受文學、繪畫等姊妹藝術的影響,身處藝術交融語境下的德彪西,作品展露出超越聽覺的視覺性以及強烈的情景感。其中,交感美學觀給予德彪西最直接的影響體現于作品的描述對象,即大自然之景。漫天飛雪、浪潮迭起、海上明月、云雨變幻等都是德彪西的筆下之景。甚至連德彪西本人也自詡自然才是他的宗教及信仰。作品中的各種意象便是以各種自然之景為靈感,以《泛舟》為例,便是其中的湖水、月光。而標題則是聽眾從德彪西建構的情景畫面中所獲得的最初體驗。“泛舟”這一標題具有強烈的情景指向性,即便是沒有欣賞過華多的畫作或是拜讀過魏爾倫的詩歌,也能從標題中得到關于音樂內容的信息。這種提示使“泛舟”這一情景得以迅速生成,并為欣賞者提供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暗示。從接受角度上,當欣賞者看到《泛舟》的標題時,已經與作曲家德彪西建立一種對話關系,并遵循著作曲家的提示,對泛舟的畫面與音響的符合程度產生期待,這種期待便成為德彪西音樂畫面中的情景鋪墊。
(二)情因景而顯
古人論詩有云:“一切景語皆情語。”魏爾倫的詩歌寓情于景,借由景物抒發情感。作為德彪西的靈感來源,魏爾倫的詩歌是其情感體驗的基礎。隨著作品生成,在創作終止的同時,德彪西也會將魏爾倫原作中的這種情感繼承下來,成為德彪西建構音畫《泛舟》的情感依托并體現在其作品之中。音樂《泛舟》的結束部分是畫面中的遠景部分,德彪西以升高八度及延長休止呼應了原作中魏爾倫夢幻式的結尾:“與此同時,月亮升起來了。在他短暫的旅程中,在夢想的水面上嬉戲……”似乎有夢醒時的遺憾,也包含對象征著永恒之愛的西苔島的眷戀和向往。這種對渴求不得的愛情的幻想內化為樂中之景,通過德彪西的音樂語言呈現出來。
(三)音景合一
《泛舟》這一情景空間的建立是德彪西借由音樂語言作為媒介,通過象征音型對物質形態進行模擬、空間流動性、描繪色彩及層次關系等方面的塑造呈現的。從中可見德彪西對于傳統的突破及嘗試,其中不乏全音階、變和弦、雙調性等德彪西成熟時期典型的創作技法。從作品中所體現的情景性而言,得以看出《泛舟》是德彪西在創作早期階段將交感美學理念融于作品中的初步探索。正是由此,德彪西將觀念與精妙的作曲才能融會貫通,從而達到“音景合一”的境界。因而,無論是對德彪西美學觀念的探索,抑或是德彪西個人音樂風格的形成,《泛舟》都有其獨特的藝術價值。
參考文獻:
[1]鄭克魯:《心靈詠嘆與音樂性的結合——魏爾倫的詩歌創作》,《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2]戶思社:《試論魏爾倫詩歌美學思想的形成與演變》,《外語教學》,2012年第5期。
[3]Wright, Alfred J:“Verlaine and Debussy: Fêtes Galantes.” The French Review, Vol. 40, No. 5, 1967。
[4][美]湯普森:《德彪西——一個人與一位藝術家》,朱曉蓉、張洪模譯,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6年版。
周 靜 華南理工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陳 韻 華南理工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