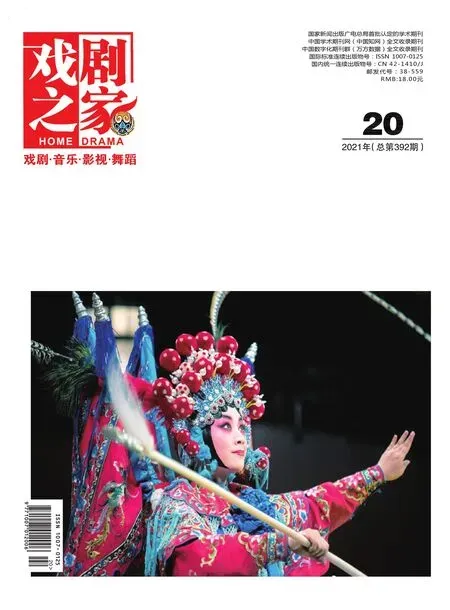哥特動畫電影《鬼媽媽》的造型設計研究
孫韻嵐
(大連東軟信息學院 數字藝術與設計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3)
動畫電影的造型設計往往凝結了創作者的藝術觀念,具有傳情達意的功能。一般來說,同一類型的動畫電影會表現出相似的造型旨趣,而造型中的細微差異又會產生不同的心理暗示作用,進而以一種無聲的隱喻話語向觀眾述說著劇情的發展,描摹出影片中角色內心的情感變化。導演亨利·塞利克創作的哥特動畫電影《鬼媽媽》(2009 年上映)改編自英國作家尼爾·蓋曼的中篇小說《卡羅琳》。導演不僅保留了原著中通過劇作技巧呈現出的奇幻構思,并且還延續了個人的創作風格——以一種幼兒自語式的呢喃述說或帶有荒誕色彩的言說方式來關注角色心理的成長變化,通過這種看似與大眾認知相悖的途徑揭示出現實世界中存在的不和諧現象,也向觀眾拋出了較之以往有所不同的理解方法。例如,其執導的定格動畫電影《圣誕夜驚魂》(1993 年上映),講述了身為萬圣節總指揮的骷髏王子杰克十分厭惡原本的邪惡生活,渴望能夠像圣誕老人一樣為人們提供歡樂,于是綁架了圣誕老人并帶領著各類鬼怪開始生產圣誕禮物的故事。杰克內心的變化并沒有被他手下的其他怪物所理解,它們還以為這些圣誕禮物是杰克精心密謀的一項整蠱計劃。在怪物們的努力“配合”下,本應喜樂祥和的圣誕節又變成了彌漫恐怖氛圍的萬圣節。又比如其后創作的《飛天巨桃歷險記》《影子之王》《鬼媽媽》等皆是基于兒童的視角展開的奇妙幻想。本文基于哥特類型電影的風格范式,結合《鬼媽媽》影片的創作特點,旨在從場景、色彩以及元素等方面解讀作品中視覺造型的設計思路及蘊含的隱喻功能。
一、哥特藝術的興起
(一)從民族范疇到藝術范疇的概念嬗變
基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學術界關于“哥特”(Goth)的詞源認識達成了較為一致的共識。韓笑教授指出,“這個詞匯起源于3-5 世紀侵略意大利并瓦解羅馬帝國的日耳曼部族。因此對推動文藝復興的意大利人來說,哥特意味著野蠻。”肖明翰教授對此做出了更加詳細的說明,他提到“條頓民族的哥特部落”是如何在文化同一性的作用下逐漸消亡的過程,其指出“在公元7 世紀以后,哥特人作為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消失了”。但是由該民族帶來的曠日持久的殘酷戰爭在意大利人的內心深處已經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使其對“哥特”一詞產生了非常復雜的心理感受。隨后,意大利藝術評論家法薩里將那些“文藝復興思想家們所不喜歡的中世紀建筑風格”統稱為“哥特”。此后,原本作為民族概念的“哥特”就成為了象征野蠻、怪異等帶有貶義色彩的藝術稱謂。法薩里所稱的“哥特建筑”是相對于古典建筑而言的,這些建筑具有相似的外形特征,即通過高聳的尖形棚頂或拱門、修長的束柱,輔以飛扶壁,營造出與構成建筑的石質材質有明顯視覺反差的輕盈感,往往給人以向上升騰的內心感受。沃爾夫林對比分析了哥特風格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風格差異,從時代精神的角度對此加以解釋,“哥特式的舉止肌肉僵直、動作刻板;什么都是尖利的,沒有一點松弛。也沒有一點柔軟。在這種最明確的形式之中,處處都表現出一種意志……與此相反,文藝復興時期則表現得寬松大方了,形式的每一部分都充滿了生氣,無論形式是在運動中還是處于靜止狀態”。也就是說,相對于哥特風格而言,文藝復興時期所提倡的作品風格與形式大多是以柔和的線條,較為具體、生動的形象,指向觀者對有機生命力的心理需求,更容易使人產生愉悅的心理感受,因此有利于移情的產生。相反,哥特風格呈現出了一種有悖于自然狀態的反作用力,因形式而導致觀者在情感上產生距離感,這使哥特風格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與幻想力量,當其再次復興時便逐步與黑暗、恐怖、頹廢、超自然等詞匯產生關聯,呈現出了與主流藝術相悖的風格傾向。
(二)哥特電影的美學基礎
如果只是將哥特電影的藝術特點等同于迷戀“死亡”,就會顯得有些草率。肖明翰教授就曾將哥特小說的美學基礎歸納為審美上的“壯美”,同時又判斷這類文學作品的心理基礎是人們內心的恐懼感。“在情節上,它濃墨重彩地渲染暴力與恐怖;在主題上,它不像一般浪漫主義那樣從正面表達其理想的社會、政治和道德觀念,而主要是通過揭示社會、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惡,揭示人性中的陰暗來進行深入的探索,特別是道德上的探索。”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特征,故將哥特小說稱為“黑色浪漫主義”。哥特小說在情節或主題上以一種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組織方式強化觀念的差異性表達,甚至有意強調與常人相悖的觀點與看法,以此來刺激觀眾產生進一步的思考,從而跳出生活的虛幻假象,直抵現實中隱匿的黑暗與未被關注的矛盾。因而創作者需要找尋的是一種向死而生的勇氣,以一種特殊的“平靜”——帶有頹廢狀態的生活方式,來獲得游離于現實之外的思考體驗。“游離”成就了逃離痛苦現實的冥想世界,被作者賦予最絢爛的色彩,而現實時空常常被表現為毫無生氣的、冰冷的深淵。
二、動畫電影《鬼媽媽》的造型設計及其功能分析
(一)依憑場景設計推進敘事進程
《鬼媽媽》主要通過平行時空中場景造型的反差完成影片的敘事。角色的表演空間也是導演精心設計的,女主角卡羅蘭的母親在影片中第一次亮相時就被安排在象征著女人的天堂的廚房場景中,但這個廚房場景的空間設計無論在陳設裝飾還是色彩搭配上都看不出一絲一毫家的味道。原本應該是家人圍坐在一起的聚餐場所被母親臨時征用為工作間,甚至當小卡羅蘭為了吸引母親的注意力談到了自己差點掉到水井被淹死的事情時,媽媽還是敷衍地回應著。不僅如此,父女對話環節也同樣刻畫出了冷漠的親情,作者巧妙地借助電腦屏幕上映射出的人影完成了卡羅蘭與爸爸的“隔空交流”。父親的工作室里堆滿了還未開封的行李箱,整個房間中唯一被妥當安置的物品就是辦公桌旁的公文包,以便于父親隨手拎起就能去工作,這表明不同空間的轉換是以忙碌的工作為鏈接的,唯獨把卡羅蘭“排擠”在了情感觀照之外。現實的空間都保持著低飽和度的灰冷色調,讓觀眾們直觀地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壓抑與沉悶。而現實時空對應的“另一個世界”則表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景象。在跳跳鼠的引誘下,卡羅蘭穿過隧道來到了與現實時空平行的奇異世界,眼睛鑲嵌著紐扣的“鬼媽媽”正在廚房準備晚餐,廚房里各類用品井然有序地陳列著,并且在暖色調的燈光烘托下顯得格外溫馨。吃飯環節被設計成了一場盛大的游戲,餐桌上擺放著各式珍饈美味,還有專門用來配送調料的“醬汁火車”,而裝有不同口味的奶昔機器如同被施加了魔法一般,作好了隨時待命的準備,只要卡羅蘭發出指令它就開始工作。當一切真相揭露之時,原本熱鬧溫馨的“另一個世界”瞬間瓦解,變為既沒有空間維度也沒有色彩傾向的純白之境,這種視覺上的反差與敘事有相同的作用,均給人留下了轉瞬即逝的虛幻遐想。
(二)借助色彩強化角色的性格特征
影片注重借助色彩來區分角色的性格特征。例如,主角卡羅蘭·瓊斯是一位具有獨到見解的女孩,有別于以往動畫片中女主角常見的金發碧眼的形象,藍色的齊耳短發表現出其倔強與果敢的性格。全片只有她喜歡穿著如同太陽般明媚的黃色雨衣雨鞋,穿梭在頗有歷史滄桑感的古老建筑之間。而卡羅蘭的“母親”又表現出三種不同的形象。首先,現實中的母親身著灰白色的毛衣與簡單的黑褲子,不僅與場景色彩相統一,而且當媽媽在電腦前工作時,這種無彩色在屏幕的映襯下呈現出偏冷的色調,與母親對待卡羅蘭的態度一樣冰冷。其次,平行世界的另一個“媽媽”總是面帶關愛的笑容,角色的主色調以飽和度較高的紅色和哥特風格常用的黑色為主。最后,恢復骷髏模樣的“鬼媽媽”則使用了象征著毒藥和女巫身份的綠色。
三、哥特動畫電影元素所蘊含的隱喻話語
影片伴隨著輕盈怪誕的音樂開場,從遠處飄來帶著紐扣眼睛的娃娃,暗示了被禁錮的靈魂與封閉的精神世界。一雙如蜘蛛爪一般細長而尖利、泛著金屬光澤的機械骷髏手,奠定了全片的影調氛圍——殘酷、堅硬與愛的缺失。紐扣無疑是《鬼媽媽》中的重要元素,它標識出現實空間與平行世界的差別,同時也象征著危險的來臨。另一個空間的“媽媽”以紐扣來換取孩子的自由,這種情節構思和《千與千尋》中用姓名做抵押具有相似性,但相較于后者而言,前者依托紐扣這種可見的物象,能夠更好地區分兩個不同時空之間的區別。另一個重要的電影元素是“門”。經歷了喬遷新居、遠離老友之后,小卡羅蘭來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生活,而父母因工作忙碌很少能陪伴其左右,這使得卡羅蘭急切地要為自己禁錮的內心找一個可以釋放的窗口。卡羅蘭在“迷你的我”的引導下找到了一扇通往夢幻與憧憬的小門,在另一個世界里有她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一切夢想:珍饈美味、溫馨可愛的房間、各類玩具、最重要的是還有父母的陪伴……穿過一條藍紫色的狹長隧道,墻上的小門連接了現實與平行的世界。藍色與紫色的搭配會讓人聯想到“神秘”“魔力”“享樂”等一系列詞匯,吸引著主人公的好奇心,引導著其走向“美好的烏托邦”。“貓”常常寓意著敏銳的直覺,在影片中如影隨形的黑貓象征了卡羅蘭的潛意識,而“老鼠”代表了紊亂的精神、貪婪與破壞力。在黑貓的提醒下卡羅蘭找回了自我,也體會到了現實生活中的父母在自己的心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同時也讓她看清了紐扣眼睛背后是一張邪惡的臉——另一個“媽媽”設置了一張大網,伺機等待著卡羅蘭墜入網內。
整部影片在環環相扣的緊張氛圍中落下了帷幕,前后呼應且主次分明。導演不僅遵循著哥特電影的常規創作方法,還注重影片細節的塑造,以隱喻的方式表達出愛是需要相互尊重與經營的觀點。在影片結束時,象征著迷失的濃霧也終于散去,卡羅蘭及她的父母都找尋到了內心的安寧與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