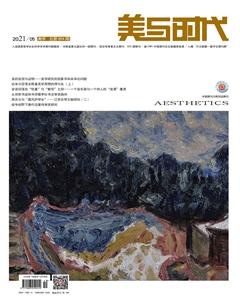論現代性視域下《塵埃落定》的時空書寫
摘? 要:阿來的《塵埃落定》譜寫了20世紀初中葉,漢藏交界地區社會轉型的歷史:前現代社會,舊的土司制度的統治盛極而衰至崩潰,新的現代社會在廢墟中新生。《塵埃落定》的故事建立在特定時間、區域內,這就確立了從時間、空間兩個維度闡述該小說現代性的可行性。
關鍵詞:塵埃落定;現代性;時間;空間
從歷史視域的縱線來說,現代性意味著現在和過去的分裂;從地理空間的橫面來講,現代性具有相對的地域性特征。從民族心理與文化層面來談,不同民族的現代性具有不同的特質。阿來在談到《塵埃落定》現代性主題書寫的時候,闡明自己的寫作更關注“人物的命運”,為了人物能夠具體形象地呈現出來,不得不認真關注“人物背后的歷史”[1]29,繼而肯定了自己在書寫藏區東北部歷史進程中對于現代性闡述的努力。罌粟(鴉片)、現代化軍事武器、邊境市場的建立、漢人軍隊的進入等加速了土司統治之地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了前現代社會制度崩潰和現代社會建立的步伐。
《塵埃落定》講述了20世紀初,“邊緣地域——漢族世俗政治中心與西藏高原神權中心皆鞭長莫及的川藏交界”[2]某地區,在現代性的沖擊下發生的震蕩、變遷和轉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土司和藏民經歷了已綿延幾百年的土司制度突然地極盛而衰以至崩滅,由此產生了心理精神上的惶惑、不安與不解。但這現代性的沖擊似乎不可避免,因為它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歷史是“不可停留”的,在土司制度極速發展到頂點以后,發展道路已經越出了常規的軌道,朝著另一個方向——現代社會邁去。小說通過傻子二少爺睿智的穿越時空的視線,看到了土司們的結局:“土司們一下就不見了”;看到土司制度的未來:分崩離析。在這片宗教與政權、漢文化與藏文化共同作用的混雜的、雜糅的交界地帶,伴隨著前現代社會的“將要完結”而起的是多義、多維度的現代性。文章擬從時間、空間兩個維度來探討《塵埃落定》的現代性。
一、時間:歷史滾輪,指向現代
現代性是什么?有人認為,現代性顧名思義是現時代一些基本特性的概括,比如16世紀的現代性主題是文藝復興,17世紀則是理性,18世紀則是啟蒙[3]。從這個意義來考察,現代性具有斷裂的特征,即“現代”是現在和過去的斷裂[4]。現代性理所當然地具有時間性質,又表現出連續性特征,一步一步推進社會文明,形成滾滾歷史長河,淘瀝掉不能適應歷史前進方向的東西——《塵埃落定》里的是土司統治的前現代統治制度。
《塵埃落定》的時間書寫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釋:一是時間作為故事情節展開的線索,展示了前現代社會崩潰與現代社會將要建立的過程;二是傻子“我”看事物的宿命視角,對土司制度必然崩滅的預言,宿命歸于時間,預示著歷史前進的必然;三是傳統土司集權利、金錢、領地擴張于一身的欲望,與末代土司繼承者的個人性現代思維和眼光形成對照,歷史車輪的前進與發展促成了新舊土司之間的差異。
從前現代社會崩潰的過程來看,《塵埃落定》的時間線索可以梳理為發展——高潮——塵埃落定,這是一條明線。發展的導火因素是土司之間領地擴張和占有百姓的統治欲望引發的沖突、戰爭,麥其土司轉向國民政府尋求幫助。辛亥革命是現代革命,至20世紀建立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現代意義的政權,國民黨代表黃特派員帶著現代軍事裝備、練軍方式進入藏區,意味著現代性步入藏區。依靠強勢的現代化槍炮的突入,麥其土司成了土司大地上日漸強大的統治者。對白銀欲望的增強,促使麥其土司引進了罌粟——作為土司大地上現代性的一針強效藥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罌粟(鴉片)是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封閉大門的一顆強大的炮彈,也是中國現代性開啟的先印腳步。藏區的現代性發生大致也這樣,雖然鴉片并不是好東西,甚至加劇了清政權的衰敗和國勢的衰頹。阿來質疑了對于現代性的一貫的看法:“輸入現代性就是只輸入好的東西,壞的東西可以關在門外”[1]29,但歷史不會這么一清二白、是非分明,應該是更復雜、更糾葛的。因此,阿來肯定了罌粟對于藏區現代性發生的積極意義,“西藏的現代性進程中,更準確地說,在我所書寫的那一塊地方——藏區的東北部,罌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當地的經濟政治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29。麥其土司種植的罌粟銷往漢地,從漢人手中購買新式武器,在增加了白銀財富的同時,提升了自己部隊的裝備和戰斗力。過于豐厚的利益獲得引起了別的土司的眼紅和效法,經過罌粟花戰爭,整個土司大地盛開了罌粟花,成了欲望彌漫的土地。在別的土司都種植罌粟的時候,麥其土司選擇種糧食。好運似乎總是在麥其土司一邊,風調雨順的年代,其他土司領地發生了饑荒,而麥其土司的領地卻獲得了糧食大豐收。麥其土司要其他土司用十倍的價格來買麥其家的糧食,獲得了強勢的話語權。這樣“罌粟使麥其強大,又使別的土司陷入了窘迫的境地”。傻子二少爺在豐厚儲備的糧食基礎上,順勢建立了邊境市場,“把麥子換來的東西運到漢地,從那里換成糧食回來,再換成別的東西。一來一去,真可以得到十倍的報償”。這時麥其土司的領地和百姓又擴增了,土司政權的發展也達到了頂峰。權利和經濟都發展到頂點的土司再無處可去、無路可走,傻子二少爺為無事可做又“沒有了未來”的土司們組織了一次“土司們最后的節日”。這是前現代社會在歷史長河中的最后一次狂歡。狂歡伴隨著糜爛,土司們在邊境小鎮染了梅毒,身體開始潰爛,土司們對邊境小鎮進行了詛咒,但詛咒是沒有用的,因為土司們肉體的腐爛與小鎮沒有關系,“跟這個鎮子不般配的人才會腐爛”。這是一種象征性的書寫策略,市場作為現代性的一種,處在歷史長河的順流向,土司們的意識和決策與市場不般配,自然與現代社會也不般配,他們的終結是歷史的必然。所以紅色漢人的軍隊進入藏區后,“互相爭雄的土司們一下就不見了。土司官寨分崩離析,冒起了蘑菇狀的煙塵。騰空而起的塵埃散盡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沒有了”。至此,時間線上——歷史滾輪下的前現代社會統治制度便如塵埃一般騰起而滅了。
《塵埃落定》時間線索的梳理,從現代社會建立的過程來分析,可以得到一條情節發展的暗線:萌芽——建立。傻子二少爺平等對待下人,以仁心和寬容對待奴隸,面對其他土司領地受饑荒之災的影響而流于乞討的百姓慷慨地施以援手,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而紅色漢人建立政權的基礎正是群眾力量,這似乎與現代社會的政權基礎形成了一種暗合。傻子二少爺的“傻”其實是在前現代社會中表現出來的超時代的睿智眼光和思維。傻子二少爺成功建立了邊境市場,用和平的方式得到了別的土司用武力也難以爭奪的領地和百姓,被認為是神的眷顧者,“他走到哪里,神就讓奇跡出現在哪里!”當潮涌一般的百姓將二少爺托舉起來,形成了如洪水一般的難以控制的力量時,傻子二少爺沒有及時地指引洪水的流向——土司位置,而是真正地陷入“傻”境,錯過了唯一一次可以成為土司的機會。他的母親恨鐵不成鋼地責怪他:“你是傻子,十足的傻子。”但傻子二少爺真的是因為傻才不知道給洪水力量指引方向嗎?或許可以有別的闡釋。傻子二少爺總能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抉擇,比如在種糧食還是種罌粟的決策中,作為標準的土司繼承者的哥哥選擇的是種罌粟,但傻子堅持要種糧食,事實證明傻子的堅持和主張是對的。當麥其家獲得糧食大豐收之后,哥哥認為應該趁此機會大大地打壓其他土司,把他們吃了完事,這個主張被麥其土司否定了,而傻子認為應該給麥其家的百姓免稅賦一年,這一舉動則使麥其土司獲得了更多百姓的感恩和擁護。同是往邊境地區去守護糧食,但哥哥一味地沉迷戰爭,致使麥其家在南方邊境的官寨失守,失去了大量糧食和精良的武器;傻子二少爺則是開放市場,和土司們進行交易,卻獲得了十倍的報償,使麥其土司領地、百姓和金錢大增。因為傻子的蒙昧具有一種超時代、超驗的神秘力量,“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傻”,而是擁有了不合于時代——指前現代社會的進步意識,所以和時代的正統顯得格格不入。從此來看,“跟得上時代”的傻子二少爺錯過成為土司的機會,沒有及時指引群眾方向,并不是因為他“傻”,是因為他早已看到土司是沒有未來的,文本的潛臺詞是土司制度崩潰的必然性,因為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是群眾,而不是個人統治天下。可以說,現代社會萌芽的基礎——群眾力量已經形成了,只不過指引他們方向的不會是某一個土司或其繼承者,而是他們自己,是他們自己覺醒的意識。隨著土司制度的發展漸漸走入絕境,也有越來越多的藏地百姓加入共產黨軍隊,成為紅色藏人,成為覺醒意識的一支,表明現代國家和軍隊進入的不可逆。當紅色漢人軍隊開進藏地,土司們要么投降、要么被打倒,一切都化為塵土,而“我”建立的邊境小鎮則作為超時代的象征得以保留。
宿命是阿來帶有宗教感的人生觀的一種。在談到作品中宿命的書寫問題時,阿來闡明自己對宿命的一種審美的看法:“一個常態的人,在常態的社會能夠得到比較好的發展;然而當社會進入非常態狀態的時候,就如一輛列車突然加速,不適應的人就會被拋下來。”[5]20《塵埃落定》譜寫社會變遷,也就是處于非常態狀態的社會,以傻子為敘述者,更予其“天賦異稟、先知先覺”,做出一些暗合社會歷史長河流向的決策,充溢著魔幻的視角跨越時空,看到好多“雖然不是發生在眼前”的事情,看到“整個制度的崩潰”,看到自己的運命。為什么“我”能看到這種未來發生的事?因為“我”“已經不是生活在土司時代”,“我”是作者塑造的一個超時代的幽靈似的講述者,“我”能看到別人的命和自己的命,能在被無法避免的宿命仇殺后依然開口講述“我”和土司大地上的盛衰。當漢人戰爭接近尾聲,國家的權利即將恢復,“我”開始惶惑不安,因為“國家再次強大時,就要消滅土司了”,我確實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土司們的結局,“感到將來的世上不僅沒有了麥其土司,而是所有的土司都沒有了”。這種超驗性感悟不僅是土司制度在強勢的現代性面前無力抗爭的歷史發展規律的表征,更是一種“天意,而非人力”[5]20,這種“天意”的操控者就是時間[6]。
麥其土司和其他土司對罌粟、現代性軍事器械的瘋狂癡迷,都是源于鞏固并擴張現有統治領地、百姓以及占有更多白銀財富的欲望,他們的行動和決策是出于集權和擴張的目的,卻在客觀的歷史進程中加速了現代性的發生。關于罌粟的種植,阿來的寫作是基于寫實的筆端,在《塵埃落定》中,歷史的真實性和文學的虛構性同構一體,共同熔鑄了文本的豐富內涵。他認為“罌粟這種東西”在“西藏的現代性歷史進程中,意義非常大”[1]30。因此,土司們出于集權和擴張的目的去引進罌粟,卻宿命般地打出了毀滅土司制度的第一槍。傻子二少爺的所做所為沒有明確的目的,卻又是合于歷史發展的,“我”寬容對待下人,分糧食給飽受饑餓折磨的災民,建立自由交換的市場,作者為“我”能做出這些暗合時代歷史走向的超驗的決策給出的解釋是,“我”不是一個“生活在土司時代”的人,也因此“我”每天醒來都要問“我是誰”“我在哪里”。這種充滿了現代性意義和個人性思辨的哲學叩問和超越前現代社會的決策,使“我”在這個土司時代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被認為是“傻子”,在將要殞命于宿命仇殺者的刀下時“我”才知道,“我”不是傻子,“我”只是上天特意安排在“土司制度將要完結的時候到這片奇異的土地上”走一遭,“我”因而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
二、空間:文化雜糅,傳統讓位
生活在一定空間區域內的人或民族,總是具有區別于其他族群的特質,空間之中的民族文化形態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對民族的作用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相互交叉作用的。
(一)漢藏交融區的政權與經濟
小說中土司管轄區域是漢藏交界地帶,活躍于這片土地上的土司,在臣服于東邊的中央政權時,精神上又與西邊的拉薩地方宗教政權有聯系。這個地方有諺語“漢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陽下面,達賴喇嘛在下午的太陽下面”。而土司地域“在中午的太陽下面還在靠東一點的地方”,這意味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藏民“與東邊的漢族皇帝發生更多的聯系”,也就是說,地域性決定了土司地區偏向更顯明的政治意識,而非宗教神權。
土司大地上現代性的發生與地域性有很大的關聯,因為土司地區的權利來源于東邊漢族皇帝。麥其土司對自己政治權利的來源有正確的判斷,他承認東邊的漢族政權對自己領導的合法性,因此在多次受到汪波土司的挑釁之后,轉而向四川軍政府求助,并帶回了象征國民黨政權的黃特派員和軍隊、武器,以及罌粟。麥其家憑借武器,打敗了汪波土司,獲得了武力話語權。又因為種植罌粟,積累了大量白銀,并開辟了邊境市場,因而獲得了經濟話語權。前面提到,阿來肯定了罌粟在藏地現代性歷史進程的重大意義,究其原因是在土司大地上,天高皇帝遠,種植罌粟所受的阻力幾乎為零,廣泛種植,運往內地銷售,并從內地購進物資,這樣一來一往的“生產與流通的過程中,內地的勢力自然而然的介入進來”。《塵埃落定》的歷史定位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這時候的中國已經刮起過數次現代風潮,早在鴉片戰爭開始,之后又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中國大地已經歷過多次奔騰起伏的現代性洗禮。自然地,在與內地的交易往來過程中,現代性的輸入無法避免,也不能忽視,比如對抗日戰爭進程的關注、對紅色漢人和白色漢人的戰爭情況以及治政理念的了解等。同時,需要強調的是,現代性不僅具有地域性,更因為地域性而生發出相對性,因為國民黨政權的時代特性對于西藏來說或許是現代的,但與同時代的西方社會相比,可能就不夠現代了。
從空間層面解析現代性的另一方面是經濟。麥其家因為罌粟的種植獲得了大量現代化精良的武器裝備和白銀,因為糧食大豐收得以建立邊境市場,依靠有利的地緣優勢促進現代性經濟模式的發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獲得了“十倍的報償”。邊境市場為了便于和內地交易往來,建立了銀號,擴大了交易范圍,簡化了交易程序,方便了交易過程,“我”也因為賺了錢,而將錢捐助給國家用于戰爭,走在同時代的土司們前頭,參與國家建設。阿來認為現代性的輸入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但不能因為是壞的東西就否定了現代性的意義。罌粟的種植打破了原有的土司格局,震蕩了這片寂靜的土地,加速了傳統的社會制度的崩潰;邊境市場的開辟,帶來了梅毒,沖擊了藏民的思想觀念,但同時也帶來了經濟權利的擴張。
(二)傳統文化的崩滅與新生
土司大地,政治上受東邊的漢族皇帝約束,精神上受西邊的拉薩影響,但這種約束和影響相對來說又是有限度的。土司們并不完全臣服于東邊的皇帝政權,比如汪波土司譴責麥其土司把漢人的勢力引進土司們的土地上。同時,土司們也不完全頂禮膜拜藏傳佛教,比如土司大地上的活佛總是受制于土司的恩寵與否,他們得不到如西邊的宗教領地上的活佛所得的那份尊榮,只能看土司們的臉色行事,因為一旦得罪了土司,活佛、喇嘛等都會陷入生存的困境。所以,在土司管轄區,翁波意西作為一位獲得格西學位的僧人,竟會因為直言對土司有所冒犯而被兩次割舌。可以看到,土司們掌權的土地上的民族性既有東邊政權的影子,也有西邊宗教的根底,呈現出政權和宗教混合、雜糅的特征。在東邊政權陷入戰爭困境的時候,土司政權得以暫時穩定、發展壯大。罌粟帶來的貿易流通,促進了現代性的發生。生產和交換的雙方以漢人和藏人為主體,自然地,藏地社會的現代性深受漢地影響,但并不完全相同,與同時期的西方現代性也有區別,可以說這樣的現代性是帶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現代性。
語言,特別是指代現代物體的名詞是現代性重要的一面。某些物體,在藏語言中沒有相對應的名詞,通常只能通過音譯來指代,人們在確切見到實物之前,只能囫圇吞棗似地記住名詞(指代詞),而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再慢慢成為民族語言。種植罌粟之前,人人都不知道罌粟是什么,只知道那一袋灰色細小的顆粒是罌粟種子,而后看到紅艷艷的花朵謝了,化成一顆顆包含白漿的果子。報紙、相機(照相術)、飛機(鐵鳥)、抗日戰爭、白色漢人、紅色漢人、共產主義等名詞,在時間的推移中進入藏地,為藏民所理解。概言之,現代性視域下的文化、經濟與政權意識附身于藏語言文字,促進現代性在藏區生根,也助力了藏語言文字擺脫僵化狀態,發生涅。
現代性對于民族傳統的超越表現在復仇的藏族傳統文化在現代政權(法律)面前失語了。復仇兄弟中的弟弟因為參加了紅軍成了紅色藏人,按照紀律,他不能隨便殺人,復仇的任務自然落到了哥哥頭上。但只有走近現代性的人物能超越民族傳統,拒絕現代性而選擇傳統宿命的人只能跟著土司制度一起滅亡,留下一曲蒼涼悲壯的民族哀歌。索朗澤郎為盡忠而死,行刑人小爾依因為行刑人沒有用處了,也選擇了去死。麥其土司拼死到最后,保住自己“最后一個麥其土司”的光榮,土司太太則吞鴉片自盡,在炮火中堅持自己上等人的尊嚴。
伴隨著土司制度一起崩潰的,還有土司大地上傳統的人的等級劃分模式。在這片土地上,骨頭即“轄日”是一個很重要的詞,“骨頭把人分出高下。土司。土司下面是頭人。頭人管百姓。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家奴。這之外還有一類地位可以隨時變化的人”。在漢人軍隊摧毀了土司官寨、土司制度后,所有人不再受等級劃分的約束,前現代社會中的農民和窮人都成了自由的人民。
《塵埃落定》用詩意的筆調,書寫漢藏交界地帶社會轉型時期,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土司、藏民們短暫的生命欲望高漲,而后平淡沉寂、惶惑不安的心理,他們面對現代性的侵入有畏懼、有反抗、有順從,但歷史大勢如龍卷風一般,摧枯拉朽地將土司制度連根拔起,將前一秒還受土司、頭人管轄的百姓一下子置于歷史前面,直面歷史變遷。
民族概念、民族性讓位于國家觀念亦是《塵埃落定》現代性書寫的一面。國家觀念和救亡主題在文本之中多次得到呈現。文本里首先將民族觀念置于現代國家觀念之下的藏族人是傻子的叔叔,也是他啟發了傻子潛在的超時代的國家意識。因為叔叔的引導,傻子才會捐錢給國民軍隊買飛機,可以說叔叔的存在價值無不體現于引發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關系的思辨之中,而叔叔的為國捐軀,則正面肯定了國家觀念在民族和個人面前的強力和合法性。
三、結語
本文認為現代性不會孤立地在某區域某方面發生影響,因此從時間與空間兩個層面進行解析才能最大限度地觸摸到歷史真實,才可發現現代性影響的實質。本文對于《塵埃落定》現代性的梳理,基于歷史時間范疇,基于地理空間的特殊性,基于民族文化的特質,深層次分析漢藏交界區域現代性的發生,力求廣泛且深刻地求知充滿奇幻色彩的藏地如何與漢地發生具有現代性意義的聯系,如何通過與漢地的政權來往與貿易交流而促進現代性發生,在面對現代性政權的威力和前現代社會難以為繼的現實時如何悲壯地認命。
參考文獻:
[1]何言宏,阿來.現代性視野中的藏地世界[J].當代作家評論,2009(1):28-39.
[2]程光煒.《塵埃落定》與尋根文學思潮[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7):67-81.
[3]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M].顧愛彬,李瑞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4]何延華.論現代性視域下《塵埃落定》的美學意蘊[J].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169-175.
[5]易文翔,阿來.寫作:忠實于內心的表達——阿來訪談錄[J].小說評論,2004(5):17-22.
[6]徐新建.權力、族別、時間:小說虛構中的歷史與文化——阿來和他的《塵埃落定》[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4):17-26.
作者簡介:楊蘭,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