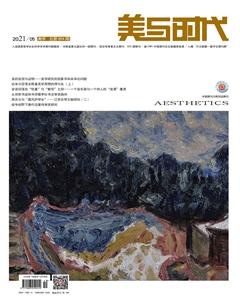從《奪冠》看女排精神對當下時代的意義
摘? 要:女排精神是在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精神。在1981年世界杯比賽首次奪冠后,愛國、團結、拼搏便成為了女排精神存在的核心。伴隨著中國女排的成長歷程,女排精神的內涵得以不斷豐富和發展,直到如今,女排精神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純粹的體育范疇而是擴散到全社會,成為各行各業發展的榜樣精神,構建出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奪冠》這部電影由“北上”導演陳可辛執導,呈現出濃郁的人文關懷和漂泊離散、懷舊的藝術風格。
關鍵詞:奪冠;國家;女排精神;主旋律電影
每年的國慶檔影片都備受關注,尤其近幾年一波又一波優秀影片都選擇在國慶首映更是加強了觀眾的期待。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里,需要一些主旋律電影來喚醒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讓觀眾有親切感與認同感。尤其是已經來到后疫情時代,前半年的壓抑與掙扎需要一個契機釋放,觀眾們疫情期間的所看所思需要一個發聲口。作為國慶檔第一部上映的電影,《奪冠》無疑具備這種特質,這部電影由“北上”導演陳可辛執導,濃郁的人文關懷和漂泊離散、懷舊的藝術風格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故而《奪冠》一經上映就引起了觀眾熱潮。
影片的時間線拉得非常長,從1978年改革開放時的女排開始,那個年代,經濟落后、物資匱乏,而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中國女排連續5次奪取“三大賽”冠軍,分別是:1981年第3屆女排世界杯、1982年第9屆女排世錦賽、1984年第23屆夏季奧運會、1985年第4屆女排世界杯、1986年第10屆女排世錦賽,向世界宣布了中華民族崛起的信心。其塑造的女排形象烙印于國人心中,賦予了人們奮發向上的昂揚斗志,激勵著各行各業的人們以飽滿的熱情投身改革開放事業,翻開了“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時代篇章。一直到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中國女排震驚世界,女排姑娘們在不拋棄、不放棄、不畏強敵、頑強拼搏中淬煉出了英雄精神,扎根于祖國大地,并得以繼承與發展。回顧一路走來的歲月,不是簡單地講述訓練不易,而是更多地立足于當下,探討這種“女排精神”對于人民對于祖國的時代意義。
作為一部取材真實的體育競技類題材電影,影片最大的難題在于:如何將人們已經耳熟能詳的故事講出新意、講出水平。尤其以時間線為軸的電影如何取舍每件事情所占比重,角色作用如此突出的電影如何對歷史素材進行取舍和整合,以及每個人物的選角、如何從真實原型上摘取形象用以塑造人物,繁雜冗亂的訓練與比賽以何種方式一一展現,如何搭建敘事結構,等等,這些問題也都是不小的困難。從電影中觀眾可以發現,導演選擇由人物串起事件,既避免了看起來過于紀實,又可以讓觀眾真正共情于人物,能夠以真實面貌描繪個人與集體的成長軌跡,這種巧妙的處理顯示出了導演以及演員的高超藝術水準。和一般的劇情片相比,以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受到歷史事實的制約,限制更多,但若改編巧妙,亦能激發出相當的力量。雖然依然在剪輯節奏、劇情取舍、人物形象烘托等方面有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瑜,不能否認的是影片開創了一個新的題材類型,是一次“開荒”式創作,是一次可貴的嘗試。
影片選角與人物類型展示無疑讓觀眾眼前一亮,選用郎平的女兒白浪演繹郎平的青年時代,兩人的外貌與性格都非常相似,直接讓觀眾夢回1978。選用彭昱暢與黃渤分別飾演主教練的青年時期與成熟時期,不得不說,兩人在許多小動作與口音等細節的處理上十分到位,不會讓觀眾因突然換角而出戲,兩人的形象也與當時年紀的人物形象較符。選用老戲骨吳剛飾演老教練袁偉民,訓練時的嚴厲、賽場上的鼓勵、賽后的驕傲,都向觀眾展示了一位外表嚴肅、內心細膩的嚴師形象。特別是鞏俐飾演的后期郎平,從外形到內心,無一不是“鐵榔頭”本人,一出場的眼神就非常入戲,凌厲且堅定。電影上映前從各種新聞中的路透就能夠看出鞏俐從站姿、說話方式等細節中對于郎平這個“人物角色”的理解,非常令人驚喜。
“體育承載著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夢想”,國家體育總局一樓大廳里懸掛著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金句,激勵著每一位體育人為體育強國而奮勇擔當、挺身而出、甘于奉獻、為國爭光。影片緊扣時代語境,三代女排人的拼搏精神深深打動在場的觀眾,激發起觀眾們的民族自豪感與國家榮譽感。影片開頭運用了一系列的蒙太奇鏡頭,碎片化剪輯展示當時的整體社會環境。1978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人民你追我趕追上時代浪潮,一系列真實情境再現非常具有代入感,也與影片重述歷史的內涵不謀而合。影片開場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半決賽,接著回溯至80年代的女排記憶,再一路順著時間線行進至2016年的巴西奧運會。最后的比賽高潮中,20世紀80年代與2016的時空被混合在一起。這樣的時空處理方式顯然是成功的。其將不同時空以相同的情緒觸點進行連接,將一個完整的故事進行拆分,使用倒敘、插敘的手法讓電影的首尾相接的敘事手法,使電影的煽情筆法具備強大的說服力。從老一代肩負沉重歷史使命的女排,到歷經失敗后由郎平重新帶隊“出征”,影片始終賦予每一次體育競技變革時代特征,觀眾跟隨鏡頭串聯起的每一個經典回顧,更能深切感受到女排的發展歷程,感受到每一位體育人的堅守與信仰。
離開文本層面的探討,電影也并不是在單純地講述故事,導演也想在視聽語言的細枝末節中體現自己對于體育或者說是對于“體育精神”的理解。在青年陳忠和來到中國女排作陪練、第一次進入女排訓練館的段落之中,推開訓練館的大門之后,電影開始了一次高速剪輯。高速剪輯充斥著影片接下來的幾乎所有部分,可以說,剪輯是《奪冠》成功的最大推手。每一次人物的“旋轉”“跳躍”,排球在空中的“起承轉合”,不會像3D電影一樣突然嚇到觀眾,所有的一切都順其自然,運動員與排球好像水里游動的魚兒一樣,非常具有舒適感。背景音樂是一段節奏感極強的弦樂協奏,它的節奏感和流暢性是構成視聽“流動”的基本框架。在背景音樂之上,是不斷響起的排球擊打聲,它們就像鼓點一樣不斷敲擊,應和著前面的弦樂,此時的體育不單單是一向運動,導演是將其當作一項藝術活動來體現的。接著是女排球員的人聲介紹,人聲作為旁白,配合教練反應鏡頭、緩慢前行的推軌視點鏡頭、全景女排隊員各種訓練動作的特寫鏡頭、排球飛躍的特寫鏡頭等各類鏡頭的高速剪輯,組成的節奏與背景音樂完美嵌合。這就是最好的視聽語言之一,它借助強力的剪輯,進行反復的感官刺激,制造“流動”和“跳躍”的生命力美學。這時的排球,不再是單純的“排球”了,排球對于女排來說,就像“如魚得水”一般,只要拿到球,她們在鏡頭中就熠熠生光,這是生命的律動,是藝術的旋律。
體育運動的魅力不僅在于比賽本身,也在于比賽的“觀看”。對于這一點,影片亦有挖掘:攝影機并不僅僅關注賽場本身,也同時關注著電視機前的“觀眾”,賽場的賽況常常隨著觀眾的反應鏡頭進行起伏。與賽況解說一樣,模擬電視轉播的畫面也不斷出現,這樣的區別于電影影像的“異質影像”的插入增加了影片視聽元素的豐富性。就好像是戲中戲一樣,層次非常豐富。如,在第一場比賽中的一個鏡頭中,女排隊員跳起對著鏡頭方向扣殺;接下來,電影瞬間轉場至觀看電視機轉播的觀眾,音樂戛然而止,鏡頭從電視機處一邊俯拍觀眾全局一邊快速后退。在實際觀看體驗中,這兩個鏡頭的銜接,仿佛那一記扣殺被扣出了電視機殺向觀眾一般,扣得觀眾啞口無言。在這一例子中,電影借助相似的“運動”銜接來打通界限,這是非常高明的剪輯構思。最后一場比賽中過去與現在的平行蒙太奇同樣是一個亮點。平行蒙太奇這種剪輯技法,本來就具有天然的情緒感染力,因為此法不僅在連接兩種影像,更是在連接兩種動作、兩個時空、兩種情緒。女排精神仿佛具有穿透力,像筆又像刀,刻在紙上,印在人民的心中。
不得不說,影片對于次要人物的形象處理稍顯欠缺,女排成員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幾個,相對于主要人物來說有些臉譜化、扁平化,對于觀眾來說,沒有出現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可能會有些許失落。作為一部新主旋律電影,《奪冠》如何處理集體和個體的關系,考驗著創作者的立場與技巧,也非常容易引起大眾對于創作者觀點的沖突。在最后一段,顯然《奪冠》明確了球員為誰而打球的問題——不是為了爸媽打球,不是為了獎牌打球,而是為了改變和提升自我而打球。這段對話不僅僅是在激勵女排,對于觀眾來說更是直擊靈魂的拷問,女排精神在這一刻與觀眾產生共鳴。雖然沒有簡單直白地進行喊口號式愛國,但接下來“輕裝上陣”的女排帶來的勝利與喜悅,本身就能夠含蓄地激起愛國情懷。
《奪冠》作為一部體育題材主旋律影片,主創團隊賦予了它新的表達方式與時代特征已經難能不易。可能觀眾并不止想看到真實歷史的重現,更想通過重新回味的方式了解女排、產生共情,從女排的身上獲取重新開始的力量,這或許就是《奪冠》最大的成功之處。
參考文獻:
[1]貝炫毅.中國女排精神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9.
[2]王世超.文化結構框架下中國女排大賽奪冠成因研究[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20(9):12-19.
[3]孫柏.《奪冠》:中國女排精神的時代變遷[J].電影藝術,2020(2):75-77.
[4]蘇楓.郎平:奪冠之外的人生[J].小康,2020(30):24-25.
作者簡介:李靜惠,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電影學方向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