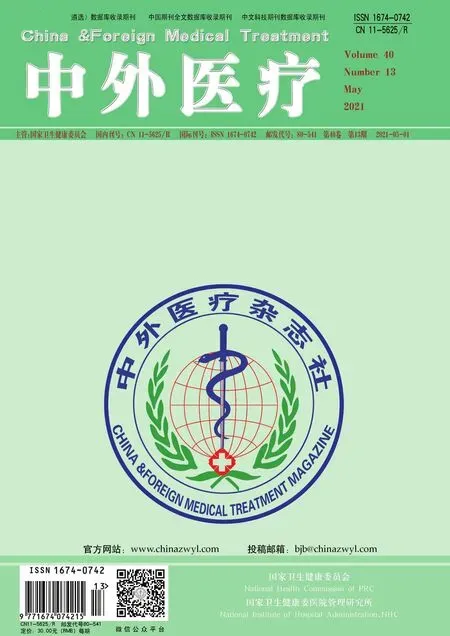胸腔鏡治療嬰幼兒先天性肺氣道畸形16例分析
章國(guó)棟
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兒科醫(yī)院廈門分院(廈門市兒童醫(yī)院)小兒外科,福建廈門 361006
先天性肺氣道畸形 (congenital pulmonary airway malformation,CPAM)是一種先天性畸形,表現(xiàn)為支氣管樹(shù)水平開(kāi)始病變,特征是肺部組織多囊樣包塊,可伴有支氣管異常增殖,其發(fā)生率在1/35‰~1/10‰,無(wú)性別差異[1-2];近年來(lái)由于產(chǎn)前超聲篩查的普及,其發(fā)病率呈增加的趨勢(shì)[3]。外科手術(shù)治療手段是切除病變的肺葉(肺段)[3-4]。既往采用開(kāi)胸的手術(shù)方式切除病肺,近年來(lái)隨著電視胸腔鏡技術(shù)發(fā)展,國(guó)際上經(jīng)胸腔鏡行肺葉(段)切除的方式治療先天性肺氣道畸形已逐漸開(kāi)展,國(guó)內(nèi)相關(guān)的報(bào)道不多。現(xiàn)將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兒科醫(yī)院廈門分院小兒外科在2018年3月—2020年7月期間經(jīng)胸腔鏡完成的16例先天性肺氣道畸形治療的患兒臨床資料進(jìn)行回顧性分析,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取先天性肺氣道畸形患兒16例,男性6例,女性10例;年齡3個(gè)月~7歲。納入標(biāo)準(zhǔn):臨床診斷肺或支氣管囊腫、增強(qiáng)CT顯示畸形及其血供來(lái)自肺動(dòng)脈、囊腫大小超過(guò)3 cm、年齡3個(gè)月以上、體質(zhì)量6 kg以上、有感染患兒已控制感染2個(gè)月以上,患兒家屬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shū)。排除標(biāo)準(zhǔn):隔離肺病例、合并心臟疾患、凝血障礙、感染未控制者。該研究通過(guò)醫(yī)院倫理委員會(huì)評(píng)審(廈兒倫審科研【2020】032號(hào))。
1.2 方法
采取全身麻醉,氣管插管,部分患兒行單側(cè)肺通氣。采取健側(cè)臥位,胸部稍墊高使軀干略呈弓狀以擴(kuò)大肋間隙。根據(jù)病變部位,在腋前線至腋后線、第4~7肋間,穿刺置入5 mm Troca 3枚;其中2例患兒采取2孔法,即5 mm Troca聯(lián)合單部位多通道穿刺器;配合低壓低流量CO2(4~6 mmHg)人工氣胸,條件允許時(shí)建立單肺通氣使肺葉自然塌陷。探查找到病變部位,采用電鉤分離粘連,游離肺葉間裂,暴露出目標(biāo)組織供應(yīng)的動(dòng)脈、靜脈,Hem-o-lok夾閉后使用超聲刀或Ligasure離斷,再游離支氣管,Hem-o-lok夾閉并離斷,完整切除病變組織。標(biāo)本剪開(kāi)后經(jīng)Troca孔取出,生理鹽水沖洗胸腔,麻醉師膨肺檢查無(wú)出血、漏氣,放置引流后關(guān)閉切口。
1.3 統(tǒng)計(jì)方法
數(shù)據(jù)處理采用SPSS 18.0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符合正態(tài)分布的計(jì)量資料以()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非正態(tài)分布的計(jì)量資料,以中位數(shù)(第25~75百分位數(shù))[M(P25~P75)]表示。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病變部位及手術(shù)信息
所有手術(shù)順利完成,其中肺楔形切除2例,肺段切除3例,肺葉切除11例(其中2例含胸膜粘連松解、1例膈肌粘連松解);1例術(shù)后第1天出現(xiàn)出血并發(fā)癥,急診胸腔鏡探查止血(膈肌粘連分離的創(chuàng)面滲血);平均住院時(shí)長(zhǎng)10.68(7~21)d,病理類型Ⅰ型11例,Ⅱ型5例,術(shù)后隨訪1個(gè)月結(jié)果均滿意。患兒病變部位、手術(shù)時(shí)間及術(shù)中出血見(jiàn)表1。

表1 病變部位及手術(shù)信息介紹
2.2 不同年齡組手術(shù)對(duì)比
患兒6例<2歲,剩余10例>2歲。在手術(shù)差別上,2歲以下組手術(shù)時(shí)長(zhǎng)較短,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手術(shù)出血量也較2歲以上組少,但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jiàn)表2。
表2 不同年齡組手術(shù)對(duì)比()

表2 不同年齡組手術(shù)對(duì)比()
組別手術(shù)時(shí)間(min) 術(shù)中出血(mL)<2歲(n=6)>2歲(n=10)t值P值144.67±29.47 195.50±51.45 2.195 0.046 12.33±10.46 38.40±59.82 1.044 0.314
2.3 術(shù)前有感染史與無(wú)感染史手術(shù)對(duì)比
患兒5例在術(shù)前有感染史,剩余11例無(wú)感染史。術(shù)前有感染史的患兒手術(shù)時(shí)間延長(zhǎng),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手術(shù)出血量也增加,但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jiàn)表3。有感染史組里1例發(fā)生出血并發(fā)癥。
表3 術(shù)前有感染史與無(wú)感染史手術(shù)對(duì)比()

表3 術(shù)前有感染史與無(wú)感染史手術(shù)對(duì)比()
組別手術(shù)時(shí)間(min) 術(shù)中出血(mL)有感染史(n=5)無(wú)感染史(n=11)t值P值224.40±58.09 154.64±27.62 4.291 0.013 57.20±82.25 12.20±11.17 1.127 0.333
3 討論
對(duì)于偶然發(fā)現(xiàn)的無(wú)癥狀肺氣道畸形是否施行手術(shù)治療一直存在爭(zhēng)議[5-6]。鑒于先天性肺氣道畸形可繼發(fā)感染和壓迫健康肺組織引起呼吸功能障礙,以及存在遠(yuǎn)期潛在惡變的可能性存在,學(xué)者認(rèn)為需要行手術(shù)治療[7]。手術(shù)基本原理是病肺組織切除,根據(jù)病變的分布情況行楔形切除、肺段切除或肺葉切除[8]。
嬰幼兒體格小,胸腔限制于肋骨輪廓,固有空間小;加之肺組織隨通氣起伏,給術(shù)者操作造成困難,既要保證患兒的通氣氧合,又不過(guò)多干擾手術(shù)操作,對(duì)麻醉技術(shù)提出更高要求。在該次研究病例中,3歲以上患兒采取纖支鏡引導(dǎo)下單肺通氣呼吸。單肺通氣的運(yùn)用可使患側(cè)肺塌陷,增大了手術(shù)操作空間[9];相對(duì)固定的肺組織使病變邊界及血管易于辨認(rèn),減少電刀等大能量器械誤傷健康組織,利于提高術(shù)者操作速度,從而縮短了手術(shù)操作時(shí)間。JH Lee等人[10]研究報(bào)道,單肺通氣具有一定的保護(hù)作用,在手術(shù)刺激下釋放的生物因子減少,在兒童肺切除手術(shù)后能減少肺部并發(fā)癥。
在病肺組織切除血管與支氣管處理上,該研究采取A-V-B的順序。首先進(jìn)行動(dòng)脈處理,打開(kāi)動(dòng)脈鞘后緊貼動(dòng)脈壁輕柔分離,逐個(gè)處理分支,若顯示不清血管走向時(shí)進(jìn)一步向遠(yuǎn)端游離,充分辨別后進(jìn)行hem-o-lok夾閉離斷;此時(shí)可能滲血較多但可避免誤扎血管。先夾閉動(dòng)脈阻斷高壓血流,利于減少創(chuàng)面滲血,保證術(shù)野清晰;再游離靜脈,由于靜脈壁薄,避免動(dòng)作粗暴撕裂,夾閉離斷靜脈,最后處理支氣管,需注意避免漏氣,該順序與此前學(xué)者報(bào)道一致[11]。
臨床中往往有些患兒確診時(shí)已發(fā)生感染或因感染發(fā)現(xiàn)該疾病。該研究病例中,有5例患兒在術(shù)中發(fā)現(xiàn)胸腔內(nèi)粘連嚴(yán)重,均合并有近期感染史。該研究中感染組與非感染組比較手術(shù)時(shí)間上較長(zhǎng);但出血量的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不具說(shuō)服力。急性感染期組織水腫粘連嚴(yán)重,解剖不清晰,創(chuàng)面易滲血,不宜手術(shù)。即使感染已控制,但胸內(nèi)組織水腫,粘連緊密,分離困難[11]手術(shù)時(shí)間長(zhǎng);創(chuàng)面出血多,為中轉(zhuǎn)開(kāi)胸的常見(jiàn)原因之一。該研究1例患兒術(shù)后發(fā)生出血并發(fā)癥,經(jīng)急診胸腔鏡探查證實(shí)為感染后粘連分離的創(chuàng)面滲血。因而認(rèn)為CPAM患兒應(yīng)在感染發(fā)生之前進(jìn)行干預(yù)。
手術(shù)年齡的選擇存在爭(zhēng)議,畸形發(fā)育的肺組織有隨時(shí)繼發(fā)感染潛在風(fēng)險(xiǎn),但新生兒對(duì)手術(shù)打擊耐受差,手術(shù)預(yù)后較差。該組病例中,年齡在2歲以下患兒手術(shù)時(shí)間相比更短;但術(shù)中出血量的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該研究病例量小,樣本代表性較差。張娜等人[12]的連續(xù)性胸腔鏡肺葉切除治療CPAM的報(bào)道中,<2歲組、2~4歲組及4~8歲組的患者(n1=55,n2=13,n3=22)手術(shù)時(shí)間分別為(76.56±30)min vs(77.85±53)min vs(77.23±33)min,出血量(7.73±3)mL vs(8.28±8)mL vs(8.32±7)mL,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可見(jiàn)低年齡患兒手術(shù)時(shí)間和出血量并無(wú)增加。兒童1歲內(nèi)肺泡細(xì)胞增長(zhǎng)迅速,肺組織擴(kuò)張快;早期手術(shù)利于促進(jìn)殘肺組織代償,避免了遠(yuǎn)期并發(fā)癥的發(fā)生。故研究認(rèn)為對(duì)手術(shù)年齡上并無(wú)嚴(yán)格限制,只要全身發(fā)育條件允許,嬰兒期也可手術(shù)治療。該研究組數(shù)據(jù)與上述學(xué)者數(shù)據(jù)相比,無(wú)論是手術(shù)時(shí)間還是出血量均較大,考慮原因之一是樣本量較小,還有更重要原因就是術(shù)者的經(jīng)驗(yàn)技巧差別。
總結(jié)分析,先天性肺氣道畸形的手術(shù)時(shí)機(jī)宜在早期、感染發(fā)生前進(jìn)行;術(shù)中血管的精準(zhǔn)處理和單肺通氣技術(shù)的支持助于手術(shù)者操作。目前外科開(kāi)展手術(shù)量仍較少,樣本代表性差,胸腔鏡行肺葉(段)切除術(shù)的安全性還有待更多病例來(lái)驗(yàn)證。
綜上所述,經(jīng)胸腔鏡治療嬰幼兒肺氣道畸形手術(shù)宜在早期、感染發(fā)生前進(jìn)行,年幼不是手術(shù)限制;正確的血管處理方法和單肺通氣技術(shù)的支持有于手術(shù)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