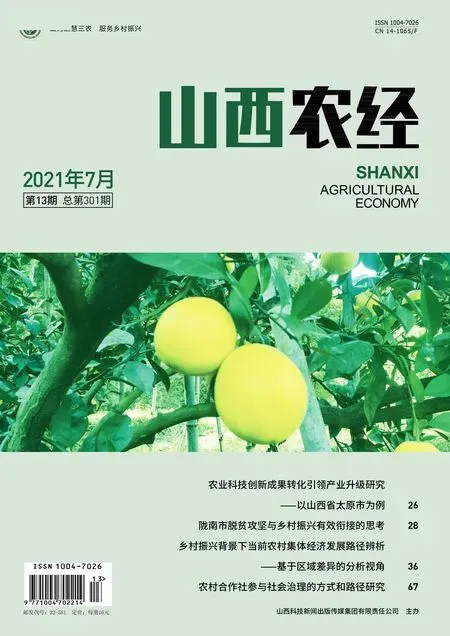農村貧困家庭資產建設研究
——以云南省石屏縣為例
□張俊彥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廣東 廣州 510006)
2020 年,我國決戰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指出,下一階段扶貧工作的目標主要是鞏固擴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目前的扶貧工作已經幫助貧困人口擺脫了最低生活無法保障的絕對貧困狀態,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但以“輸血”為主的扶貧措施具有缺陷,即政府不得不承擔較高的扶貧開支,長此以往可能會對國家財政造成較大的壓力;扶貧的標準較低,范圍較窄,只能滿足貧困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滿足其長遠發展的需要,容易造成政策依賴等。
與收入支持相比,資產支持是一種新的脫貧思路。資產的含義很廣泛,包括各種金融資產、實物資產、自然資產、人力財源資產和其他社會上的聯系。在資產的作用下,貧困者可以實施長遠的發展規劃,不必局限于滿足最低生活保障需求。
為了完成下一階段的脫貧任務,應該在接下來的扶貧工作中突出資產的重要性。為了讓窮人的資產能夠累積并正確發揮作用,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體系,引導貧困者進行資產積累和代際傳遞,發揮資產的積極效應。
1 文獻綜述
資產建設理論最早由邁克爾·謝若登提出。邁克爾·謝若登(2005)[1]在1991 年提出了資產效益理論,認為資產建設最顯著的效益是經濟效益。資產福利政策使得資產具有除創造消費之外的多元積極的福利效應,如促進家庭穩定、創造未來取向、增強個人效能等。在資產效益理論的基礎上,他創新提出了一種資產建設的工具——個人發展賬戶,同時在專著中詳細地介紹了個人發展賬戶的運行思路和程序,指出資產建設在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
桑德拉·貝福利等(2015)[2]進一步完善了資產建設理論。在個人發展賬戶項目的試驗過程中,他們發現收入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自主開設兒童發展賬戶并且儲蓄與收入正相關,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則不會自主開立賬戶。另外,擁有更多財務知識的家長更愿意開設個人發展賬戶,但需要政府提供合適的平臺和工具。
國內很多學者對資產建設如何與我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趙祁和曾國平(2008)[3]認為,我國福利政策制定者應該借鑒美國夢工程的成功經驗,建立以收入補貼為主,資產建設為輔的福利政策,同時不應該全盤否定收入補貼。童星(2011)[4]認為,以資產為基礎的福利政策應該發揮主要作用。以收入為基礎的福利政策只是受助窮人的“吊床”,以資產積累為基礎的福利政策則能成為受助窮人的“蹦床”。在社會保障中實施資產社會政策,或者提供資產建設型社會保障,是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善舉”。唐鈞(2005)[5]持比較折中的觀點,他認為應該建立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制度,即資產建設應該與現行以收入為基礎的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同時肯定作為政策工具的個人發展賬戶的積極作用。
有學者關注了資產建設的效益方面。除資產帶來的經濟效益,很多研究者認為資產積累還具有積極的社會效益。例如鄭秉文(2004)[6]認為,資產建設有利于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鄭麗珍(2005)[7]認為,參與資產項目能夠拓寬賬戶所有者的社交圈,有利于建立朋友關系,緩解孤獨狀態。
資產建設的變式是近年來較受關注的方面。在我國,有一種扶貧措施與資產建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金融扶貧。李創和吳國清(2018)[8]認為,金融扶貧是國內金融機構為貧困農戶和扶貧項目提供大量資金支持,激發廣大貧困農戶的內生發展動力,實現穩定脫貧和可持續發展。二者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使貧困者獲得長期發展的可能。
綜上所述,資產建設理論引進國內已有數年,但是仍然沒有出現以“資產建設”命名的政策措施。國內關于資產建設的理論研究已經很充分,但是實踐內容不多,基本上是在城市經濟欠發達地區開展,尚沒有針對農村貧困地區的實踐項目。隨著貧富差距逐漸拉大,收入差距經常受到人們的關注與討論,但是資產差距幾乎無人問津,資產不平等所帶來的問題會在未來逐漸顯露。
2 石屏縣扶貧項目中的資產建設嘗試
2.1 石屏縣貧困狀況
石屏縣位于云南省東南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是一個有“九分山有余,一分壩不足”之稱的山區農業縣。2017 年石屏縣總人口為316 785 人。2013 年貧困人口為10 188 戶34 593 人,貧困發生率為12.15%;2016 年末,當地貧困人口下降為5 022 戶10 853 人,貧困發生率降低為5.57%。2017 年上半年,石屏縣財政收入累計37 565 萬元,為年初預算數73 086 萬元的51.4%,同比增長了26.62%,共增收7 897 萬元。2018 年10 月,石屏縣已實現脫貧摘帽。
2.2 石屏縣的扶貧措施
通過歸納云南省石屏縣的調查數據和扶貧實踐發現,當地有很多扶貧措施與資產社會政策存在類似的地方,雖然尚未成為一項正式制度,但具有資產建設潛力。
石屏縣實施的扶貧政策中類似資產建設的措施見表1。表中的項目均著眼于貧困者的長期發展利益,希望改變以往政府“一頭熱”的模式,調動貧困者脫貧的積極性,使扶貧工作具有可持續性。因此,這些措施都與資產社會政策的具體做法具有相似性。

表1 石屏縣扶貧措施
3 農村貧困家庭資產建設可行性分析
開展工作技能培訓是資產建設工作中的一項具體措施,其目的在于提高貧困者的工作能力和社會技能,以獲取長期穩定的收入。從勞動者的角度看,掌握農業生產知識后,生產者的生產質量將會得到提高,有利于提高生產者的積極性。只有當居民收入不斷增加并能夠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時,居民才有可能進行儲蓄。從時代發展的角度看,開展工作技能培訓有利于促進貧困者與時代接軌。在當今時代,知識經濟日益發展,簡單機械勞動將會被逐漸淘汰。缺乏經濟實力的貧困者缺少獲取知識和信息的能力及渠道,長此以往會逐漸被時代淘汰,貧困情況也就得不到長期改善。因此,開展工作技能培訓是為了讓貧困者能夠自己創造更多收入,所以具有轉化為資產建設項目的作用。
安排職業崗位比工作技能培訓更有利于直接提高貧困者的收入,二者目的相同。但安排職業崗位難以進行大范圍推廣,因為安排的崗位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不高,獲得的收入也較低。如果低勞動水平的工作趨于飽和或者機器代替人力,那么工作者極有可能面臨失業風險,因此這項措施缺乏可持續性。同時,可供安排的崗位數量有限。以石屏縣為例,截至調查結束,當地只能為500 人提供崗位,脫貧效果不顯著。綜上所述,直接安排崗位的做法只能在短期內滿足少數貧困戶資產建設的需要。
設立教育專項扶貧基金,為貧困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資金支持,有利于年輕人掌握更高級的勞動技能,在未來獲得更高的收入。但這項措施缺乏對受教育者資產意識的培養,沒有規定助學金的適用范圍和目的,資金使用的可持續性沒有顯現出來。同時,對受資助者的鼓勵不到位,通常采取強制措施使其返鄉發展,不能體現資產建設的自愿性,但這項措施仍然具有轉變為資產建設的潛質。
危房改造款和拆遷款可以成為貧困者的一筆資產,但這不是這項措施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保證貧困者的住房安全。如果有配套措施對危房改造款和拆遷補償款的使用進行約束,比如只能用于修繕住房,修繕完畢后剩余的款項只能用于醫療、教育或從事小型買賣活動,這項措施就屬于資產建設的范疇。
健康扶貧工程把重點放在對人力資產的維護方面。人力資產屬于資產的一部分,身體健康是個人發展的基礎,是最重要的資產。因病返貧的情況廣泛存在于我國貧困地區,家庭主要勞動力因為過度勞累等原因患有重疾,原本擺脫貧困的家庭由于高昂的醫療費用被迫返貧。資產建設理論只關注人力資產中的教育水平,沒有把身體素質的重要性體現出來,忽視了因病致貧等身體原因導致貧困的情況。健康扶貧工程對資產建設理論進行了補充,在未來的扶貧實踐中可以發揮作用。
“五幫活動”是典型的“造血”措施,上述幾項措施或多或少包含在其中。Fred M.Ssewamala(2004)[9]指出,在沒有足夠社會資源的情況下,資產建設最好采取其他形式,如家畜飼養,同時還要考慮金融資產建設。目前,我國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源大范圍建立個人發展賬戶,需要通過其他方式積累資產。“五幫活動”有明顯的資產建設特征,但缺乏向金融資產建設轉變的發展跡象。
4 農村貧困家庭資產建設面臨的困難
4.1 脫貧意愿不強烈,“等、靠、要”思想嚴重,缺乏自我脫貧的主觀能動性
從國內外相關實踐案例中發現,參與者的積極性有待提高,很多參與者無法堅持存款,即使有存款,也不能達到存款標準。在后續采訪過程中,中途放棄的參與者提供了多種原因,比如認為麻煩、家庭住址搬遷、對孩子的期望值較低等。石屏縣在金融產業扶貧發展過程中也曾經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很多貧困農戶的脫貧意識仍然不強,又因為缺乏自我發展經濟能力,甚至還有不少農村貧困者把開展金融產業扶貧工作看成只是接受國家無償給予的補助。資產建設既需要政府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帶頭,也需要建設對象積極參與。存在不良生活習慣而又屢教不改的貧困者進行資產建設的意愿不強,而這部分扶貧對象正是每個脫貧項目的“硬骨頭”,需要做更多的思想工作。
4.2 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
農村偏遠地區的貧困者儲蓄時,不得不長途跋涉前往很遠的銀行網點辦理業務,這不利于資產社會政策在農村地區的廣泛應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網上銀行或許可以承擔一些業務,但在網絡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地區,信息技術無法發揮作用。石屏縣已經實現了寬帶網絡全覆蓋,具有開展網上銀行業務的基礎,但缺乏相應的配套設施和專業技術人員,在金融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需要加強。
4.3 金融教育缺乏,資產意識宣傳不足
農村貧困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不能自主進行資產積累,存在不能理解較為復雜的政策措施的情況。如果基礎教育跟不上,那么金融教育便無從談起。資產意識需要培養,資產意識不夠將直接導致資產建設無法進行。以往的收入—消費意識根深蒂固,缺乏目標導向的生活態度容易使貧困者過著“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生活。樹立生活目標,培養進取心是觀念糾正方面的重要舉措。
5 探索新型資產建設途徑
5.1 政府發揮職能,開展資產建設實踐
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政府有發揮職能的必要性,即項目或者政策的開展必須由政府發起。受中央集權思想的影響,政府在人們心中的威信相對較高,一般由政府牽頭的措施不會面臨很大的信任危機。政府機關的宣傳工作能夠更加便利地展開,宣傳面更廣,有利于實現政策的包容性。
關于資產建設實踐,在農村貧困地區可以先不設立賬戶,推動“造血”政策的實施,把社會資源積累到一定水平,再利用個人發展賬戶作為穩定的政策工具。在現實情況中,開發式扶貧政策會出現“造血”功能不足的現象,因此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應該加強項目監管與跟蹤,不能培養起一個產業后置之不理。如果出現經營不當或其他意外事故,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就會降低,收入受到影響,因此政府應該不定時檢查產業發展情況。
在專業技能培訓方面,必須提高培訓者質量,監督培訓過程,評估培訓效果,不能讓培訓課成為“走過場”。有些少數民族具有歷史悠久的文化資產,政府應該及時保留與傳承。利用網絡技術,將文化與當地特色產品結合起來,發展經濟作物和旅游業。
5.2 加快偏遠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資產建設要求具備相應的金融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沒有硬件作支撐,制度框架再完善也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政府應該發揮資源配置職能,完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僅完成道路、醫院、學校、水利工程、電力工程等項目已經無法滿足扶貧的要求,需要鼓勵銀行、慈善基金會、非營利機構共同參與。只有充分調動更多社會資源,資產建設才能從簡單的“造血”措施轉變為以金融為支柱的資產積累,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
5.3 注重培養資產意識,開展金融教育
從石屏縣的調查結果來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入學率幾乎達到100%,但僅根據入學率這一個指標還不能確定石屏縣的教育質量,還應該考量教師質量、課堂出勤情況、考試情況等內容。在貧困地區的教學活動中,應該在較高年級專門開設金融教育課程,培養學生的資產意識。為了更好地進行資產建設,相關人員應具備一定的金融知識,借鑒其他成功的實踐案例。例如“臺北市家庭發展賬戶”項目要求參與者至少要學滿135 h 的金融課程,在項目后期調查中發現,課堂參與者的受教育水平并不低,甚至有的受采訪對象表示“很久沒有在課堂上課了,很懷念這種感覺”。整體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貧困地區或偏遠地區應該重視提高基礎教育水平,便于貧困者更輕松地接受金融教育。在信息化和大數據時代,具備一定的金融知識和資產意識對個人發展來說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