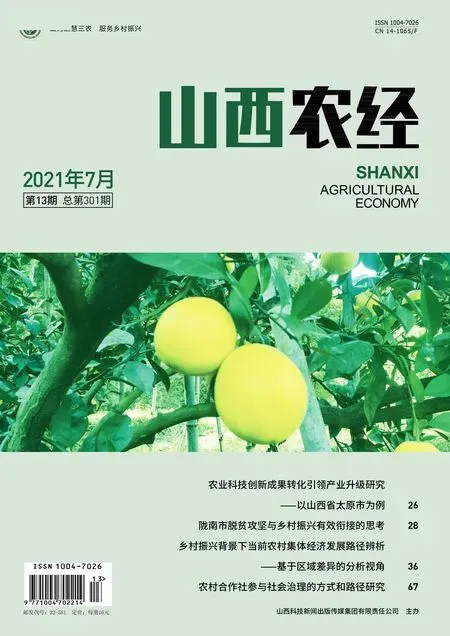后扶貧時代農村欠發達地區社會資本的結構性缺陷與重構路徑
□牛 蓉
(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持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對易返貧致貧人口及時發現、及時幫扶,守住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提到:“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
后扶貧時代,貧困治理的重心由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由生存型貧困轉向發展型貧困,由單維貧困轉向多維貧困。基于此,后扶貧時代貧困治理長效機制的建立迫在眉睫。社會資本扶貧能夠有效提升欠發達地區農戶的可行能力,對我國后扶貧時代長效脫貧機制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1 社會資本反貧困的相關研究
反貧困的社會資本模式認為,社會資源匱乏是窮人喪失發展能力的原因。從“三維資本”協同反貧困機制來看,物質資本扶貧具有不可持續性,人力資本扶貧的投資回報具有較長的周期性。相比之下,社會資本扶貧能夠彌補前兩者的不足,有效提升幫扶對象的內生發展能力,具有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不可替代的作用。從DFID 可持續生計框架來看,通過培育社會資本能夠構建解決“發展型貧困”的組織架構和關系網絡,形成反貧困的長效機制。
目前,國內學者對于社會資本反貧困的相關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喬文俊(2020)[1]側重于經濟學領域的社會資本概念,將社會資本與農業經濟發展、貧困減緩、貧困發生率等聯系起來,從社會資本支持農業經濟發展的動因與機理,到社會資本支持系統的結構模式和動態機制進行研究。李創和龔宇(2020)[2]從轉變政府扶貧方式、聯結農村關系網絡、彌補教育與醫療體系短板、完善土地流轉方式4 個方面探討社會資本培育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充分激發社會資本參與精準扶貧的活力。王陶濤和周梅(2018)直接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得出農業社會資本投入與農村貧困發生率呈負相關關系。另一方面,方志和黃荔(2020)[3]側重于社會學領域的社會資本概念,凸顯了社會資本的雙重作用,分析了貧困農戶社會資本的結構性缺陷“信任缺失、互助互惠網絡弱化、社會組織孱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貧困農戶社會資本的培育策略。孫軍(2020)[4]從激活社會資本的角度提出了推進民族地區貧困治理的實現路徑,解決民族地區信任資本流失、規范資本失效、關系網絡資本疏離等問題。成卓(2020)[5]認為,社會資本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深度貧困形成的原因分為表層與深層。
總體來看,采用社會學領域的社會資本概念,利用社會資本反貧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信任、規范、網絡、組織”等方面。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欠發達地區社會資本在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及社會組織3 個方面存在結構性缺陷。
2 農村欠發達地區社會資本的結構性缺陷
羅伯特·D·帕特南(2016)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借鑒帕特南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可知,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組織與社會資本密切相關,是社會資本的主要構成要素,且三者之間存在良性循環。參考靳永翥和丁照攀(2016)[6]的研究,形成社會資本的要素構成模型圖,見圖1。其中,社會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核心,只有社會處于較高的信任狀態,人們之間才有較高的合作意愿,以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的紐帶,基于信任與合作產生的社會網絡有利于社會資本的積累,使單個社會資本“節點”通過社會網絡的“紐帶”銜接而發揮作用,產生社會資本存量;社會組織是社會資本的載體,社會成員以社會組織為載體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抽象的“社會資本”概念依托具象的“社會組織”得以體現,為社會資本作用的發揮提供現實舞臺與有效途徑。同時,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組織三者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形成了一個閉合的良性循環系統,社會信任是社會網絡的基礎,“原子化”的個人基于社會信任形成“分子化”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維系社會組織的發展與運行,無論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社會網絡,都會對社會組織的類型、規模等產生影響;社會組織反過來能夠進一步強化社會信任,在社會組織中,人際信任與組織信任并存,當社會組織的宗旨、目標與成員的個人利益一致,組織信任得到強化,組織成員的人際信任也在組織運行過程中得到強化,并由此開啟下一階段的循環。
基于社會資本的要素構成模型,農村欠發達地區社會資本的結構性缺陷主要是社會資本存量不足、發展不充分、類型欠缺及失衡等原因導致,具體表現為社會信任方面的人際信任與組織信任失衡,社會網絡方面的同質性與異質性沖突,社會組織方面的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融合欠缺。
2.1 社會信任:人際信任與組織信任失衡
人際信任指村民之間基于人際關系的信任,組織信任指村民對正式組織規則以及宗旨等的信任。費孝通(2012)認為,我國傳統鄉村是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農村社會資本以“熟人社會”為主,社會信任程度更強,村民相信“熟人”和自己的利益訴求一致,因而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時,村民往往更注重對方與自己的親疏關系,這種情感因素干擾了理性判斷,血緣親情代替了規則意識,因而傳統農村社會出現人際信任過度與組織信任不足的情況。
一般而言,人際信任更多表現為對強關系的依賴,組織信任表現為對弱關系的信任。馬克·格蘭諾維特指出,強關系網絡易滋長封閉、排外、不寬容的狹隘意識,而弱關系網絡易產生相互合作、妥協、彼此平等的社會資本。我國傳統農村社會中,貧困戶人際信任沖淡了組織信任。在過往扶貧實踐中,存在貧困戶群體與村民委員會之間不信任,貧困戶群體與基層政府之間不信任,農村扶貧企業與貧困戶群體之間不信任等多種組織信任不足的情況,不利于進一步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2.2 社會網絡: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沖突
同質性社會網絡是一種橫向的社會網絡,由背景相同或相似的成員組成,農村地區貧困戶往往對與自己能力、家庭資產及社會地位等一致或相似的群體組成的同質性社會網絡的依賴更強,但貧困戶群體從同質性社會網絡中獲得的資源十分有限。異質性社會網絡是一種縱向的社會網絡,由不同身份和背景的成員組成。異質性社會網絡中不同群體的資源稟賦不同,但異質性社會網絡中通常存在“社會排斥”與“精英俘獲”現象。其中,阿馬蒂亞·森提出社會排斥理論,該理論認為貧困并不是收入問題,而是一個無法獲得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問題,社會排斥與貧困及能力剝奪之間有著密切聯系。“精英俘獲”現象存在于社會排斥的基礎之上,受限于貧困戶群體所處的經濟地位與收入狀況,資本“脫農”現象嚴重。與貧困人口相比,農村經濟實力較強的人更有可能獲得資金支持,可能最終導致“逆向選擇”,使真正需要幫扶的人被排除在外。貧困戶群體所依賴的同質性社會網絡具有較強的內斂性與封閉性,而擁有豐富扶貧資源異質性的社會網絡無法介入其中,或者由于“社會排斥”與“精英俘獲”使異質性社會網絡扭曲而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貧困戶群體的社會網絡存在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沖突,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失衡。
2.3 社會組織: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融合不足
安尼魯德·克里希納將社會資本分為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兩類。制度型社會資本由政府外部導入,與促進互利集體行動開展的結構要素有關;關系型資本以關系作為集體行動的基礎,在與他人的合作中影響個人的價值觀、態度和信念等。以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傳統農業生產合作組織為例,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融合的欠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種是政府主導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該組織依賴政府扶貧政策建立,政府扶貧政策或扶貧資金補貼直接催生了大量“吃政策”的不規范合作社。這類合作社缺乏對當地關系型社會資本的認識,忽視了農村社會的信任特征,農民缺乏對合作社的認同感,難以開展有效合作。另一種是村民自發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該組織基于血緣、地緣關系建立,情感紐帶凌駕于規范之上,缺乏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約束,動力不足,缺乏競爭力。關系型社會資本在合作社的初創階段發揮了推動作用,但是隨著合作社的進一步發展,關系型社會資本對合作社發展的消極影響隨之顯現。現實中,合作社的社會資本構成往往隨著合作社自身的發展而暴露出“先天”或“后天”缺陷,使其持續健康發展的能力下降,制度型社會資本應與關系型社會資本達到新的平衡。通過進一步融合,優化社會資本結構,從而提升社會資本在合作社發展中的效能。
3 農村欠發達地區社會資本的重構路徑
針對上述農村欠發達地區社會資本存在的三大結構性缺陷,提出以“著重培育組織信任”“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機制”“發展新型農村合作組織”為核心的三大重構路徑,如圖2。
3.1 擴大貧困戶群體的信任半徑,著重培育貧困戶的組織信任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信任半徑”的概念,即個體信任他者的寬度和廣度,并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在社會或其特定的群體之中成員之間的信任普及程度。調節欠發達地區人際信任與組織信任的失衡,需要在發揮特殊信任優勢的基礎上,多方位擴大貧困戶群體的社會信任半徑,將貧困戶群體對人際關系的特殊信任轉換為以契約、制度為基礎的普遍信任。同時,要著重培育貧困戶群體的組織信任,彌補貧困戶群體與村民委員會之間的信任缺失,增強貧困戶群體參與自治的能力,提高貧困戶群體在選舉與被選舉、調解與監督等自治環節中的參與度;彌補貧困戶群體與基層政府之間的信任缺失,堅持信息公開原則,保證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以增強貧困戶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形成基層政府與貧困農戶之間的良性互動;彌補貧困戶群體與農村扶貧企業之間的信任缺失,引導貧困戶群體以業緣代替傳統的地緣和血緣信任關系,獲取更多的社會機會,使貧困戶群體享受利益,增強貧困戶群體對扶貧產業發展的信心。
3.2 延伸貧困戶群體的社會網絡,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機制
多元主體具有不同的資源優勢、利益訴求和目標策略等,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涉及不同層次、不同部門。政府通過國家公共資源引導不同的主體通力合作,促使農民、合作社和政府在利益的驅使下發揮優勢。培育多元協同治理結構,一方面要注重建立同質性的橫向鏈式結構,另一方面要注重建立自上而下的異質性縱向層次結構。首先,由于扶貧項目往往處于復雜多樣的環境中,因而要擴大貧困戶群體與外界的交往面,在異質性社會網絡中搭建合作平臺,促進同質性社會網絡向異質性社會網絡的融合,有效整合各方優勢資源,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風險。其次,建立嚴格的利益聯結機制、契約機制等,做到決策民主、工作透明、監督有力,在制度上制約和防范“社會排斥”與“精英俘獲”,保障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再次,建立多元協調治理機制要以貧困戶群體為主體,締結穩定的溝通關系,增強社會網絡凝聚力,實現貧困戶群體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提高貧困戶自組織網絡的運行效率,有效構建共贏互利的關系網絡。
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機制,應從縱橫兩個維度形成多方參與、互動協作的社會支持網絡,為農村經濟欠發達地區持續脫貧提供資源。
3.3 發展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促進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的融合
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的建立,要促進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的融合。對于農村地區兩種傳統的農業生產合作組織,要積極進行引導和培育,使其向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的先進模式發展。首先,對于政府主導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政府在扶持過程中要關注當地關系型社會資本,根植于當地的文化習俗等,發揮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正向凝聚作用,加強對公平公正、平等合作等觀念的宣傳,使現代價值觀念深入農戶心中。其次,對于村民自發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政府在扶持過程中要加強制度型社會資本的供給,這類合作組織在制度型社會資本尚不完善的發展初期使用關系型社會資本獲取資源,但長期依靠血緣與地緣維持,在缺乏制度與規范的情況下,關系型社會資本容易導致特殊的信任取向,因此要頒布合作社發展的相關規范與章程,在制度上為關系型社會資本發揮作用提供保障。
根植于農村地區本土的社會信任、網絡、規范、信念等關系型社會資本同組織、規則、程序等制度型社會資本的有效融合,能在農村新型生產合作組織的建立與發展中起到良好的效果。要通過制度型社會資本整合本土的關系型社會資本,從而促進外發的制度型社會資本的成長,進一步推動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的發展。
4 結束語
實現鄉村振興需要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預防返貧,而發揮社會資本的優勢能夠有效防止返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基于社會資本的要素構成模型,分析農村貧困地區社會資本的三大結構性缺陷,包括社會信任方面人際信任與組織信任的失衡、社會網絡方面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沖突、社會組織方面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融合的不足。針對性提出三大重構路徑,包括擴大貧困戶群體的信任半徑,著重培育貧困戶的組織信任;延伸貧困戶群體的社會網絡,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機制;培育新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促進制度型社會資本與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有效融合。
總體而言,以社會信任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網絡能夠整合扶貧資源,提升扶貧資源利用效率;以社會網絡維系的社會組織能夠激活多元主體的資源稟賦,促進多元協同治理機制的構建。基于我國國情,構建以社會信任為核心、以社會網絡為紐帶、以社會組織為載體的社會資本反貧困模式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有效途徑。挖掘社會資本在反貧困方面的優勢,能夠開拓后扶貧時代長效脫貧新道路,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