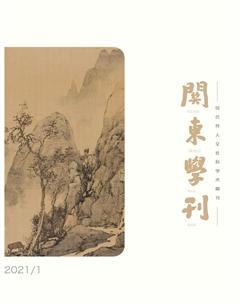丁玲土改敘事的流變與知識分子“矛盾”的改造
[摘 要]土改敘事作為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樣本對于丁玲有著更為特殊的含義。丁玲長篇土改小說的創作節點處于充滿巨大變動的過渡時代,它是丁玲跨越新中國以及新時期的思想樣本。兩者共享了同一段土改的經驗,卻因為時代語境與作家心理的變化而呈現出大相徑庭的表述。而與主流敘事模式的偏離更是使得丁玲在創作與修改的過程中備受爭議。因此,以丁玲土改敘事的流變來關注知識分子“矛盾”的改造歷程,將有助于我們在歷史的合力視野下窺探丁玲復雜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土改敘事;流變;知識分子;改造;矛盾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異文匯校、集成及文本演進史研究”(17ZDA279)。
[作者簡介]徐文泰(1990-),男,文學博士,蘇州大學文學院講師(蘇州 215123)。
伴隨著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講話與文件的發布,黨逐步確立了對待知識分子的系統化的方針。但是,理論的存在并不能夠代替知識分子的有效應對,在實踐與理論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脫節,因此如何在實踐過程中將理論消化吸收就成為知識分子改造不可避免的環節。解放戰爭期間,土地改革逐步由老解放區向新解放區蔓延,知識分子在黨的號召下深入土改一線,階級、立場、態度不再是文件中抽象的名詞而成為活生生的現實。當然,“所謂‘現實感不是對所有人都均質、一致的東西,認識的主體以各自的認識方式獲得各自的現實感”。
程凱:《革命的張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0頁。它既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更與個體經歷、氣質、性格有著直接的聯系。因此,研究知識分子艱難的轉軌就必須在這兩者的碰撞、摩擦與妥協中尋找更為復雜的線索。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在嚴寒的日子里》是丁玲土改敘事的姊妹篇,都是以她四十年代在冀中地區的土改經歷為創作背景。前者是對土改轟轟烈烈進行中的即時素描與反饋,后者則是經過時間沉淀之后對土改的回溯與反觀。不同于一般作家順乎潮流的正向靠攏,丁玲的土改敘事呈現出“吊詭”的逆向改寫,以至于在創作與修改的過程中始終受到文藝界的指責。為了回應這些指責,丁玲經常通過談話、書信、演講、日記等方式為自己的創作與修改辯護。然而這些不同形式的解說又存在著前后矛盾和似是而非的“嫌疑”,公開場合的冠冕堂皇與私下場合的率真吐露又呈現出表與里、明與暗的背反。這種一反常態恰恰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多樣性與復雜性的直觀體現。因此,以土改敘事的流變切入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要求我們不以“左和右”的政治態度簡化語境與心境的互動可能,而是以時代要求、知識結構、作家心理這種三位一體的合力視野來探究丁玲在跨越新中國與新時期的真實心態。
一、 文本周邊的言說與知識分子的精神癥候
文本周邊的言說包括作家的序言、開場白、創作談、日記、采訪等。這時文本的外圍卻指向文本,構成了理解文本的鑰匙。序言作為一種副文本,“即為一種情境和視界或情感基調,副文本正是提供了一扇進入正文本的門和窗,作用在于引導,由此進入,才能順藤摸瓜。”
金宏宇等:《文本周邊——中國現代文學副文本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4頁。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版的序言和1979年版重印本的序言發生了大幅度的修改,重寫的《在嚴寒的日子里》也增補了一段開場白。這種修改與增刪既是對作家現實處境的直接呈現,也是對作家隱秘心理的折射。丁玲公開發表的創作談與相對私密的日記也有很多涉及這兩部長篇土改小說的論述,不過對于同一個問題的表述卻經常大相徑庭。與此相關的是圍繞創作的訪談也會因為采訪對象的不同而得出甚至相反的結論。因此,有學者指出既有的丁玲研究“注意日常行為,而疏于心態分析;注意語言文字,而沒有顧及沉默,那未曾言說的部分;注意本體的部分,而不考慮支配她的外部環境”。
汪洪:《左右說丁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278頁。重新審視丁玲關于這兩部土改小說周邊的言說,就是要在復雜多變甚至相互矛盾的文字背后,考察知識分子的變與常,在纏繞的關系中透視丁玲的心路歷程。
1948年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序言給人撲面而來的感覺是一種“焦灼感”。“工作做得很不徹底,粗枝大葉,馬虎潦草,固然由于當時的戰爭環境的變化,但那些作風實在不足為法。”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頁。這種焦灼感來源于土地改革的正在進行時。中央關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包括:《五四指示》《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根據現實的發展在不斷調整中,這種不固定性使得丁玲始終無法對政策得出一個完整而穩固的認識。而對土改的即時記錄使得丁玲無法對現實經驗進行有效的沉淀,也沒有任何敘事的先例可以模仿。因此擺在作家面前的突出問題就是如何“呈現”土改。在1948年的序言中,丁玲說:“只想把這一階段土改工作的過程寫出來,同時還像一個村子,有那末一群活動的人,而人物不太概念化就行了。”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9卷,第47頁。這段話透露出兩個信息,她要反映土改的過程同時呈現出土改中的“人”。丁玲是“五四”的女兒,從《莎菲女士的日記》到延安時期創作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時》,性別的自覺支撐著丁玲對人的文學的理解,也在暗中以一種穩定的紐帶維系著丁玲的創作。這種帶有女性自我審視的創作不僅在延安時期時隱時現,就是在新的歷史時期也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影子。在1952年的總結創作中,她又說:“我是想,在這樣一個偉大的運動中,人們是怎樣的變化著,活動著。”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第363頁。而在徐光耀的回憶錄《昨夜西風凋碧樹》中,記載了丁玲和他的一次私下談話,“她說,這書是她的一種試驗,試驗怎樣用許多小事把人物刻畫出來”。
徐光耀:《昨夜西風凋碧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42頁。通過序言和公開、私下兩重創作表述的對讀,我們可以發現,丁玲將視角牢固地聚焦在了土改中人的思想與情感變化,這事實上隱含地延續了“五四”以來一以貫之的“人”的發現。當然,這個“人”更多地是指寫工農兵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曾經在1944年給丁玲和歐陽山發去一封賀信,祝賀她的《田保霖》標志著新的作風的轉變。丁玲在后來的天津文藝界座談會講話中認為:“就是從此以后,我特別堅定地深入到工農兵里邊去。”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頁。然而丁玲在這一時期的日記卻又為我們解讀作家的心境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在1947年5月29日的一則日記中,丁玲說:“我的不群眾化,我的不隨俗,是始終沒有改變,我喜歡的人與人的關系現在才覺得很不現實。為什么我總不能在別人發生趣味的東西上發生興趣,總覺得大家都在學淺薄的低級的趣味。”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1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336頁。這封信私密地呈現了丁玲在土改過程中的不適感和孤獨感。由于知識結構、生活經驗、個人趣味的差異,丁玲群眾化的努力在現實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敗。不隨俗的現實焦慮感使得丁玲在創作過程中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定性為“又長又臭”的文章,這是作家矛盾心態的直觀體現。通過公開的講話與私密日記的對讀,我們可以發現丁玲主觀上的確希望通過知識分子下鄉改造自我,拓展小說的人物譜系。然而知識結構和生活經驗又使得這種主觀努力呈現著某種不確定性和不和諧感。這種進退維谷的心態左右了她對土改的基本認知,也間接影響了她對小說人物和結構的判斷與選擇。因此,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確預設了一個“窮與富”的對立,但她小說中人物卻不等同于后來土改小說中僵化的階級的人。這源于丁玲更多地是用她的經歷和情感去把握、體會和塑造形象。“我以為我們是寫我們熟悉的人,寫腦子里面原有的人,寫我們自己喜歡的,或者不喜歡的人;也就是說寫自己發生過情感的人。”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3頁。丁玲將錯劃為經營地主的中農顧涌作為全書引發矛盾的焦點,并且在全書的修改中念念不忘為他的中農身份做辯護。而黑妮身上則投注了丁玲作為地主家庭反叛兒女的情感。她在創作談中不無矛盾地指出:“盡管作者不注意她,沒有發展她,但因為是作者曾經熟悉過的人物,喜歡過的感情,所以一下就被讀者注意了。”
袁良駿:《丁玲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第139頁。馮雪峰在評價丁玲的這篇小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作者還沒有在這本小說中帶來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但是,她已經現實主義地寫了真實的人。”
袁良駿:《丁玲研究資料》,第284頁。真實而非典型的人物恰恰說明丁玲在構思人物時并非簡單地依據政策的階級判斷,而是糅合了經驗、現實和理想。因此,相較于后來一些以政策為框框去塑造人物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更富有內在的張力和復雜性。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79年再版時,丁玲重新修改了序言。而1979年初刊在《清明》雜志的《在嚴寒的日子里》相較于1956年《人民文學》的前八章也增添了一則開場白。修訂的序言和開場白更加強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創作的引領作用,并且強化了黨性和無產階級斗爭的必要性。丁玲在重印前言中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不過是我在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在黨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據地生活的熏陶下,個人努力追求實踐的一點小成果。那時,我對于革命農民、對農村的階級斗爭,對農村的生活、對農民的心靈體會都是很不夠的。”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9卷,第97頁。這一篇序言在整體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顯得很不合時宜,以至于一位湖南老鄉質疑丁玲“為什么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里要那樣寫”
楊桂欣:《我所接觸的暮年丁玲》,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第21頁。。她在致蔣祖林和李靈源的信中強調,她對《在嚴寒的日子里》的人物“做了許多‘提純復壯的工作。這些人很自然的成長、成熟、變高、變大、變活”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11卷,第151頁。。這又使得這部小說的人物塑造陷入了高大全的藝術怪圈,以至于有學者認為丁玲已經被意識形態徹底地馴服。事實上,丁玲對自己創作的不合時宜也心知肚明,她在1978年致蔣祖林和李靈源的信中說:“可是我的讀者的確是少了,也不那么熱心了。這只能說我的文章已落后了,已不能抓住人心,叫人為我拍案了。”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11卷,第261頁。明知落后卻仍然一意孤行,這種看似扭曲的心態必須從時代環境、知識結構與作家隱秘的心結來綜合看待。1975年丁玲從秦城監獄被釋放,來到山西嶂頭村并在此開始《在嚴寒的日子里》的創作。在此期間,負責丁玲案件的人宣布了對她審查的結論,“把1957年定的‘自首變節上升為‘叛徒了”。
蔣祖林:《丁玲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490頁。丁玲一輩子視黨性為生命,她甚至認為:“一個人失去了政治生命,就等于沒有了生命。”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年譜長篇》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5頁。因此,這份審查結論帶給丁玲的沉重負擔可想而知。據陳明記載,丁玲要把“《在嚴寒的日子里》這本書寫出來……證明丁玲還是個好黨員,還是黨的兒女”
陳明:《我與丁玲的五十年——陳明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第252頁。。在這樣的心態指使下,丁玲做出不合時宜甚至有些偏激的表述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丁玲這一時期對文學的理解以及人物的塑造還受到特定時代知識結構和情感心理的影響。她在致蔣祖林和李靈源的信中說:“樣板戲也的確給我許多啟示和激勵。我從那些作品中也吸收了許多經驗。”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11卷,第153頁。這種知識結構的直觀呈現就是《在嚴寒的日子里》的農民幾乎清一色的是好的、新的、革命的。道德品質和階級立場中的瑕疵被整體性地移除。當然,對農民形象的提純復壯也與丁玲在北大荒的經歷息息相關。在丁玲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北大荒進行改造時,底層的勞動者不以政治面貌而以實際表現對待她,以至于她不無激動地回憶:“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眾對我的了解和信任,是醫治我心靈上隱痛的良藥。”
鄭笑楓:《丁玲在北大荒》,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20頁。應該說丁玲的情感是真實的,這種和人民的親近感與特定的知識結構和作家心境共同化合成為了丁玲的創作與表述。不得不說,其中既有某種真誠的信仰也有為達到政治目的的人生表演。
“作品中現實生活的變化,既體現著政策的力量,同時又以其復雜與微妙,指出了政策與生活的某種不吻合。”
王中忱、尚俠:《丁玲生活與文學的道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頁。考察丁玲如何將生活的資源納入到黨的政策和意識形態的要求,也是診斷知識分子精神氣候的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從《五四指示》《中國土地法大綱》到《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政策處在時時的變動中,丁玲通過學習土改文件不斷調整著自己對于這場運動的看法。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獨特的經歷和知識儲備也為她獨特地把握文件的精神內涵提供了思想基礎。從理性的層面上看,丁玲始終認為生活大于政策。從來源上看,“政策從哪里來,政策從群眾的斗爭生活里面總結出來”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8卷,第167頁。。從實踐方式上看,“只有把從書本上看到的,講話中聽來的帶到群眾生活中去……有了群眾實踐的經驗,然后再回過來經歷一個反芻,消化理論。”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8卷,第246頁。因此,丁玲始終強調要深入生活,到群眾中去落戶,并且在生活中完整地理解政策的內容。她反對通過政策和理念的框架去尋找內容,并且認為:“到生活中去尋取合乎框框的材料的創作方法,是不容易提高,不容易達到理想的。”
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第20頁。生活往往有政策所不能包含的詩意和動人心魄的力量,因此如果土改小說僅僅滿足于一般化的政策和意識形態的要求,那么“這里面是找不到所謂詩的東西,文學的東西,找不到創作。”
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第22頁。從感性的層面來說,丁玲始終要求用自己的感情去體悟和把握政策,這更多地依賴于作家的直覺和生活經歷。因此,當顧涌第一次出現時她就感覺給他的階級定位發生了偏差。而黑妮僅僅是一瞬間的回眸就觸動了她童年刻骨銘心的回憶,以至于這個人物被主流評論界批評時也念念不忘為她辯解。丁玲正是以敏感而細膩的情感體驗去理解帶有宏觀性和全局性的政策文件,才發現了整齊劃一的文件背后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而在丁玲備受爭議的新時期,她仍然以溫婉細膩的筆觸寫下了《牛棚小品》,其中女性特有的筆觸讓王蒙也備受感動。可以說,進入新時期的丁玲,其情感訴求中仍然蘊含著個性的追求。當然,在七十年代末,丁玲在創作《在嚴寒的日子里》期間曾給蔣祖慧、周良鵬寫過一封家信,在信中她說自己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是“怎樣把黨寫好,怎樣把黨的路線寫好,怎樣能寫成一本文藝作品”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11卷,第187頁。。而她在隨后還表述了“作家就是政治化的人”的觀點。探究這種極端政治化的表達原因,有學者指出:“為了消極地保護自己,為了避免在自己徹底平反問題上再起禍端……在許多政治問題上開始不僅自覺地‘順著說,而且還常常說的過分、夸大。”
秦林芳:《丁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59頁。應該說這是持平之論。關于丁玲三十年代在南京是否自首變節的爭論,始終是她黨員身份的道德污點。如果說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因為有陳云和任弼時的保護而讓這個心結顯得不那么明顯的話,七十年代末她的黨員身份的恢復受到周揚和張光年等人的阻撓,這個污點就是最為直接的障礙。因此對意識形態和黨的政策的無條件服從就是趨福避禍,保護政治生命的直觀體現。不得不說,扭曲的背后也有諸多的無奈。
二、誰來啟蒙與誰接受改造
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精神癥候直接影響了丁玲對小說人物的選擇以及對人物所代表的價值取向的判斷。“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頁。改造的中心就是逐步去除知識分子的中心化并且置換知識分子與工農兵之間啟蒙與改造的位置。相較于左翼文學大眾化、通俗化的訴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政策的形式引導作家寫什么、怎么寫以及明確什么樣的故事、主角、結構是可以被接納的。這要求作家對既往的寫作視角、身份姿態、階級立場作出明確的檢討,真正服務于工農兵群眾。當然,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處于大動蕩、大調整中,中國共產黨出于革命的需要對廣大知識分子葆有必要的尊重與寬容。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認為:“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5頁。因此,四十年代知識分子去中心化本身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戰時寬松的環境為知識分子發揮自身能動性提供了必要的余地。“在貶損現實主義的某些個人主義傾向(在中國人的眼光中就是自我沉溺)的同時,他們繼續期望對觀察與批判的重視,能夠平衡政治教條的頤指氣使。”
[美]安敏成:《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姜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5頁。從丁玲個體來看,作為地主階級的叛逆兒女,童年的生活經歷使得她對階級判斷不僅注重血統和出身,更關注個體的作風與經歷,因此階級就不僅是一個身份的名詞更是一個實踐的名詞。而對待群眾,丁玲在1938年明確表述:“只求能適合群眾,而絕不取媚群眾。”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7卷,第23頁。而她在到達延安初期創作的《在醫院中時》《“三八節”有感》所表現的敏感的批判意識和鮮明的性別意識,也是丁玲知識分子傲骨的直觀體現。雖然在學習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丁玲也明確表示要向群眾“投降”,但是批判的警惕心理作為一種隱性的心理結構并未完全被祛除。因此,《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誰來啟蒙與誰接受改造就呈現出某種更為矛盾和吊詭的意味。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首先塑造了一個近乎于“妖”的知識分子形象文采,以致于丁玲不得不在俄譯本序言中對這個形象引起的困惑作出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有幾篇文章就是批評這些書呆子的。”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9卷,第48頁。文采的形象事實上是毛澤東同志在四十年代關于知識分子論述的負面集合體。他的身上既有主觀主義的“傲”,認為群眾一旦發動了就有“左”的危險;也有宗派主義的“狠”,對于同一革命陣營的張裕民、程任、楊亮、胡立功有著本能的不信任感;更有黨八股與洋八股的作風,“能一連嘮叨上六個小時,把農民折騰個夠”。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9卷,第48頁。吊詭的是,這個需要被改造的知識分子典型在實踐中逐步改變著自己的作風,并悄悄地扮演了“啟蒙”農民翻身的角色。在第38章“初勝”中,“雖說他們也訴說了許多種地人的痛苦,給了許多諾言,但文采總覺得不放心。他一時又沒有更多的辦法,只好模仿著一個地主,厲聲問道……”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6頁。文采通過模仿地主與農民一問一答,啟迪著貧農的階級覺悟,促成了王新田、郭富貴等人向地主江世榮要地。而當王新田拿著江世榮的“獻地”回來時,文采又進一步啟迪他們,“咱們是要和他算賬,咱們不要他獻地。地是咱們的嘛,他有什么資格,憑著什么說獻地?”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199頁。因此文采身上集合了兩種相反的特征,他既是“被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又是催生農民由“翻身”向“翻心”的“啟蒙者”,吊詭的集合隱含著丁玲對知識分子曖昧的判斷。與文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作組的另一個知識分子楊亮。從丁玲的日記和諸多創作談中我們可以發現楊亮事實上是丁玲土改工作經驗的直觀投射。1983年丁玲在致施大畏、丁國聯的信中說:“楊亮怎么成了隊伍中拖拖拉拉的一個小兵了呢?他只能是短小精干、堅實。”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5頁。這封信從側面反映了丁玲對這個形象的喜愛。與文采相比,楊亮的最大特點是敢于深入群眾,放棄了對群眾的主觀預想和偏見,并且在實踐中不斷調整自己的工作作風。在婦聯主任董桂花心里,她覺得楊亮“為人真對勁。開始當他進來的時候,她有一點怕他,怕他召集大會……現在呢,她只要出去‘串門子,他就是這么說的。只要去同別人敘道,就像他同她談話一樣,這個她準有。”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62頁。同時,楊亮對群眾的力量并不畏懼,相反他認為只有徹底發動群眾才能動搖農村的傳統秩序,因此“他提議,根據要紅契失敗的經驗,再進行一次有把握的勝利的戰斗,用小小的勝仗來鼓舞士氣”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178頁。。不可忽略的是,楊亮這個形象也是政策與現實之間妥協的產物,他既是讀過書的小知識分子,同時又是貧農出身,“他自己是個窮人,窮人家里就是他的家”。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61頁。因此,在他扮演群眾啟蒙與發動者的角色時就擁有了一個穩固的階級背景。這種身份與立場的嬗變也從側面反映了丁玲對知識分子走向的判斷。通過這一個對照組的呈現,我們可以窺測丁玲在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觀。知識分子和工農兵仍然可以和諧互助、相互促進,知識分子一方面需要改造自己高高在上的貴族作風,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在革命中扮演更為重要的啟蒙角色,這兩者并行不悖。這也印證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表述:“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頁。顯然,這一段時期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仍然處在相對和諧的“蜜月期”。當然小說中呈現的知識分子的力量顯然也是有限的。當群眾的力量被徹底發動時,知識分子也就自愧不如了,小說中的胡立功更是明確地說道:“這要是換上咱們來辦成么?”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194頁。
“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1頁。毛澤東的這段論述確立了工農在知識分子面前的優越感。然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要反映農民由“翻身”走向“翻心”的心路歷程。因此,她在小說中一方面揭示群眾驚人的革命力量,也在另一方面呈現了革命所具有的二重性。革命改天換地的力量與投機革命的破壞性經常呈現出交叉與重疊,道德立場與階級立場在現實中也并非完全統一,革命的無私性與個體的利益糾纏也經常發生矛盾。這種二重性的描寫恰恰是農民“翻心”道路艱難的呈現。丁玲雖然在小說中預設了窮人與富人的二元對立,但她對于窮人內部的壓迫尤其是借革命之名行壓迫之私的舉動有著本能的警惕。在第五十四章“自私”中,趙功全因為分配給自己的地有被沖垮的危險,硬要和錢文虎換地。遭到拒絕后他說:“你憑什么不給我?你還想仗著你叔伯哥哥的勢么?”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293頁。“你來斗爭咱啦,要分咱的地,好!還是要給你叔伯哥哥報仇啦!”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293頁。在趙功全身上,道德立場和階級立場是分裂的。他出身貧農,卻借助自己的階級優越感強行索要錢文虎的好地,遭到拒絕后又攻擊對方階級出身力圖達到自己的目的。革命與偽革命、反抗與壓迫之間并非涇渭分明,相反它們在人性和欲望的驅使下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滲透。丁玲在這一章的呈現反映了她對土改冷靜而細膩的觀察。革命的無私與個體的利益沖突也是丁玲觀察土改的一個重要維度。在無私與有私之間,丁玲并非計較誰對誰錯,而是客觀呈現了人性本身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區工會主任老董是個肯干事不怕難的老黨員,然而面對暖水屯轟轟烈烈的分地運動,他也有了私人的打算,“他做幾十年長工,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有三畝葡萄園子,他很想要,他還可以抽空回家耕地,他哥哥也能幫他照顧。可是這事萬一區上同志不贊成呢?說他自私自利,說他落后呢?”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125頁。不同于后來革命小說中主人公大公無私的表現,丁玲對公私的呈現其實也是對欲望和利益的有限度肯定。這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主人公的道德圓滿性,卻讓人物更加真實自然地存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也是丁玲小說中不斷呈現的形象。然而這些女性在革命斗爭中的主動性與在家庭中的溫順馴良經常呈現出難以調和的矛盾。羊倌的老婆周月英在斗爭地主錢文貴時比任何男性還要積極,然而回到家中被羊倌毆打辱罵她卻毫不反抗。相反,“她卻慢慢的安靜了。她會乖乖的去和蕎面,她做扁食給他吃。”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75頁。“她送他到村子外,坐到路口上,看不見他了才回來,她一個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和寂寞。”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75頁。女性的尷尬處境實際上呈現了土改過程中階級解放與人的解放的不平衡性,這是由土改整體的意義決定的。土地改革要求清算地主、富農的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貧與富之間的階級對立就具有了壓倒一切的力量。而同屬于貧農陣營的夫妻矛盾就不得不讓位于階級解放。丁玲敏銳地發現了階級解放與人的解放之間存在的某種抵牾,卻又因為服從于土地改革的整體意義而并沒有對男權文化做出行之有效的批判。因此,在文本中最終呈現的是階級解放收編個人解放。可以說,這是丁玲在自己的情感體驗與意識形態的要求之間做出的必然妥協。
1979年初刊于《清明》雜志的《在嚴寒的日子里》,啟蒙者與改造者的形象發生了大幅度的變化。這是由徘徊時期的政治氣候、丁玲對于樣板戲的借鑒以及她急于恢復黨籍的個人心態共同決定的。知識分子被丁玲從小說中全部移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單純而整齊的貧富對立。扮演啟蒙者角色的是長工出身并且在實踐中成長為堅定的黨員干部的李臘月。他在國民黨軍隊即將卷土重來、土改勝利果實有可能受到嚴重威脅時,運用村莊的廣播進行戰前動員啟發百姓的仇恨意識和斗爭意識。他說,“我們要相信黨,相信老百姓。我們窮人多,天下窮人都是富人的對頭。我們抱成團,只要我們大家一條心,我們就不怕他們,我們就治住他們。”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365頁。李臘月的動員將窮人與富人的二元對立突出得更加明顯,這樣人物的階級屬性和階級陣營就更加清晰分明。為了加深這種階級對立,作者甚至將1956年《人民文學》初刊前八章中地主家兒子的名字趙厚、趙康改成了趙富、趙貴,以此來凸顯自己的價值立場。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注重呈現農民的二重性不同,《在嚴寒的日子里》窮人與富人在知識水平、道德修養、階級立場方面涇渭分明。性別的差異、個人的恩怨、利益的考量被無產階級的復仇火焰所壓倒,整部小說也成為了階級斗爭的簡單傳聲筒。可以說,這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是丁玲在徘徊時代扭曲心理的典型呈現。它的出現更多地是為了治療丁玲的心靈創傷而并非藝術的深化拓展。
三、文本的修改與知識分子的土改想象
啟蒙與改造身份的置換也制約了知識分子的土改想象,無論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還是《在嚴寒的日子里》,丁玲都對文本進行了大量的修改,修改過程的本身就是知識分子調整自身定位的直觀反映。《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9月初版于東北光華書店,1949年5月由新華書店出版并改名為《桑干河上》。據龔明德考證:“這個文藝叢書本的出版時間后于東北初版本,但從有關內容考察,它卻更接近于丁玲的手稿,甚至可以說它才是真正的初版本。”
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頁。隨后經歷較多修改的有1951年的北京校訂本和1955年的大連修改本,1979年版本沿用大連修改本并且修改了序言。《在嚴寒的日子里》在1956年的《人民文學》刊發了前八章,并在1979年《清明》雜志刊登了重寫的前二十四章。這兩部小說被譽為丁玲土改小說的姊妹篇,它們以1946年開始的晉察冀土地改革為空間背景,在時間上也前后連貫。前者描寫了農民翻身斗地主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光輝歷程,后者則呈現了國民黨卷土重來、護地隊捍衛土改成果并最終犧牲的過程。共同的歷史背景與固有的思想資源不斷被歷史喚起,并且隨著語境的變化被不斷地重構。增補與刪改的過程是歷史經驗與現實緣起共同決定的。因此,探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在嚴寒的日子里》的創作與修改可以更好地呈現知識分子對于土改想象的嬗變歷程。
愛情始終是人類永恒的話題。革命戰爭與土地改革期間,由于作家肩負的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太過沉重,如何處理這種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抒寫就成為了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這既依賴于作家對人性的考量,又必須時時刻刻考慮政策的要求。1949年版的《桑干河上》丁玲設計了黑妮與程任的戀愛。丁玲始終對黑妮有著惺惺相惜的感覺,這源于“潛意識里喚起她自己童年生活境遇的某種回憶(她也是飽嘗世態變遷的地主的女兒),她以這種情感創造出錢文貴的女兒(以后又改為侄女)黑妮”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第361頁。。然而,正是由于這種情感的投射,丁玲將黑妮塑造成為了一個帶有“仙女”色彩的形象。在創作的過程中,彭真和蔡樹藩批評丁玲的小說有同情地富的思想,因此“她才變得小心謹慎,中規中矩,時時以政策條文作為尺度了”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第372頁。。在這種左右為難的處境下,丁玲在1949年版的《桑干河上》第五十五章中設計了一個黑妮與程仁不歡而散的場景,“老頭子攤開兩只手望著他,不知說什么好,黑妮卻把臉回過一邊去,好像不是這伙人一樣”。
丁玲:《桑干河上》,北京:新華書店,1949年,第362頁。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從創作到出版,周揚的態度始終保持冷淡并且百般阻撓。據胡學常記載:“周揚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程仁和黑妮的戀愛是反階級的。但毛澤東說它好,周揚是錯誤的,又由艾思奇、蕭三等人向宣傳部作出保證,這才得以正式出版。”
胡學常:《胡風的1949》,《百年潮》2004年第5期。因此,丁玲對程仁和黑妮愛情的處理更像是為求保險過關的無奈之舉,而文本的字里行間仍然透露著對這段戀愛的同情。隨著這本書的出版并獲得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丁玲奠定了自己在共和國文藝界的地位。她在1955年的大連修改本中又對這段戀愛做出了調整,“老頭子攤開兩只手望著他,不知說什么好,黑妮看見程仁那樣的親熱的笑著,臉刷的一下就紅了,她不知道怎么樣才好,只好把臉回過一邊去,裝出好像不是這伙人一樣”。
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93頁。黑妮對程仁的欲迎還拒、面帶嬌羞最終讓這對苦命鴛鴦的愛情瓜熟蒂落。即使反階級,丁玲也將愛情擺放在了名正言順的位置。《人民文學》1956年發表了《在嚴寒的日子里》的前八章。丁玲對主人公李臘月和蘭池的戀愛仍然念念不忘,描寫的內容相較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糊里糊涂的一伸手就把她圍著,緊緊地抱著她,她一點聲音也沒出,等他手一松,卻刷的站起來跑了。”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529頁。“像夢一樣的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他看著她那發愁的眼睛,真想一下把她抱過來,像個小孩似的親親她。”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330頁。值得注意的是,李臘月和蘭池的戀愛有著更為一致的階級身份。前者是長工出身并且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后者則是貧雇農。因而兩個主人公的戀愛擁有了更加理直氣壯的身份屬性。丁玲對男女主人公身份的調整也是在意識形態容許的范圍內做出的微妙調整,愛情悄悄地發生了階級前提的變化。1979年丁玲大幅度修改《在嚴寒的日子里》,對臘月和蘭池的戀愛做了大幅度的“潔化”處理,露骨的愛情描寫被丁玲全部移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炙熱的階級仇恨。“壓力許久,才猛地用兩只手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胸前面,顫聲說:‘蘭池,我們的事干不完呵!我們要記住,祖祖輩輩過的牛馬不如的日子,我們要為人民舍身拼命翻過這世界,我們要一輩子跟定共產黨鬧革命呵!”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348頁。由此觀之,愛情在丁玲土改敘事中的變化經歷了反階級到階級純化到逐步被壓抑這一過程。這樣的發展歷程在進入新時期之后顯得與主流文學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也備受爭議。黨性和階級性一直是丁玲揮之不去的隱秘心結。惟其遭受侮辱,作家就更加地珍惜它。丁玲急于用《在嚴寒的日子里》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因此采取放逐個人化的階級敘事也就成為消極避禍的最佳手段。
“丁玲一再說,農民要翻身,首先要翻心,翻不了心就翻不了身。所謂翻心,就是覺醒,覺悟,就是改變千百年來的形成的歷史觀念,下定決心跟黨走。”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第372頁。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要反映中國農民思想的變化。要實現真正的“翻心”,首先要克服歷史代代相承的“變天”思想,也要克服在現實中逐步形成的自私自利的小生產者屬性。因此,如何敘述農民從物質上的翻身走向精神上的翻心,就成為了土改想象不可回避的問題。丁玲在1979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說:“我不愿把張裕民寫成一無缺點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寫成了不起的農會主席。他們可以逐步成為了不起的人,他們不可能一眨眼就成為英雄。”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9卷,第98頁。1949年版的《桑干河上》,丁玲塑造了具有革命兩重性的農民形象。在第九章中,地主江世榮去女巫白娘娘家找張裕民時,“張裕民也想說句笑話,說家里炕太冷,來這里找個睡處,可是一想不妥當,便半真半假的說:‘……別人都說白娘娘的白先生靈驗,咱來找白先生瞧瞧……”
丁玲:《桑干河上》,第38頁。這一段描寫使張裕民身上流氓無產者所帶有的痞性暴露無遺,這也印證了文采對他的基本判斷。然而這樣的描述挫傷了張裕民作為暖水屯支部書記的道德品質和階級覺悟,因此在1955年的大連修改本中,丁玲將這段話改成了“張裕民也就半真半假的笑說道‘……別人都說白大嫂的白先生靈驗,咱來找白先生瞧瞧……”
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2頁。帶有葷段子性質的調侃從文本中被移除,人物的道德品質也更加圓滿。縱觀整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作者筆下的人物在真實的人和意識形態要求的人之間仍然保持著相對的張力。《桑干河上》的人物經歷了斗爭地主之后都在物質上翻了身,然而翻心的歷程卻仍然任重而道遠,這也成為了丁玲創作《在嚴寒的日子里》的契機。據陳明回憶:“我們認為土改不僅僅是農民物質上的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翻心,翻身不翻心,土改的成果就不會鞏固。這就是為什么丁玲離開石家莊以后,還打算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里》。”
陳明:《我與丁玲的五十年——陳明回憶錄》,第94頁。客觀上說,雖然丁玲有這樣的創作構想,然而從1956年《人民文學》刊登的前八章來看,農民翻心的歷程仍然顯得艱辛而坎坷。以農民干部劉子明為例,他在尋找江山青的道路上躲躲閃閃,被老江質疑“劉子明!我在這里,看你這樣兒!你躲躲閃閃干什么事啊!險些把你當壞人打了。”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499頁。而當江山青遭到趙康暗算,劉子明“又以為自己給打死了,他全身麻木,癱做一堆”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501頁。。劉子明這樣的貪生怕死顯然與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有著不小的距離,猶豫畏懼的表現并沒有充分揭示貧農的階級覺悟。因此1956年《人民文學》刊登的《在嚴寒的日子里》前八章揭示了農民要想真正從翻身走向翻心,必須走過艱難的歷程。在1979年重寫的《在嚴寒的日子里》中,劉子明的形象被大幅度調整,當梁山青遭到趙貴暗算,“劉子明立刻清醒過來,他大怒地沖上去,扭住趙貴,咬牙切齒地罵道:‘你這該死的!”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323頁。因此,連趙康也心虛地感受到:“你看劉子明剛才那樣子,比殺了他親生父親還眼紅,恨不得一口咬死他。”
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2卷,第325頁。1979年版的《在嚴寒的日子里》強化了農民的階級意識,丁玲在地富與貧農之間做了一個徹底的切分。無論是思想覺悟還是道德水準,農民與地富都顯得黑白分明、截然不同,變天思想與自私自利的心態也被堅定的黨性和階級性取代。當然這一版的《在嚴寒的日子里》農民實現翻心并非一個漸變的過程,而是從一開始就完成了突變,因此作品的真實性和藝術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了。徘徊時期的政治氣候與丁玲急于恢復黨籍的焦躁心理共同促成了這個帶有“樣板戲”特征的未完成長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