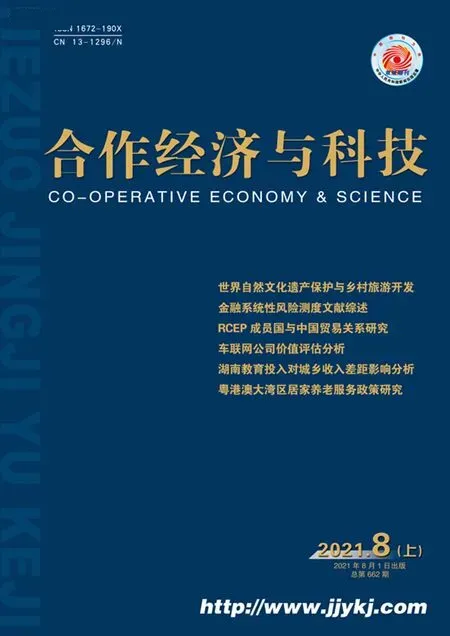談企業財務造假手段
□文/潘玉瑤 周 雪 孫 濤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會計學院 上海)
[提要]近年來,財務造假事件頻出,擾亂了市場秩序,急需整頓。本文以上市公司獐子島為例,通過舞弊三角論、COSO內部控制框架體系以及舞弊后帶來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同時對其公司的特殊產品進行存貨盤點,認定存貨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以及存貨應如何計提跌價準備等,對獐子島公司進行分析。
一、獐子島簡介
(一)公司基本概況。1958年,獐子島企業成立,主營產品為各類海產品,如蝦夷扇貝、海參、海膽、海螺等。后來逐漸發展成為育苗、貿易、養殖、加工、海上運輸等經營范圍的一體化海洋食品公司。但是,獐子島最主要的產品是蝦夷扇貝,這才有了后來三次扇貝“跑了”的故事。雖然近幾年扇貝頻“逃”,但它確實曾是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也被視為水產養殖業的名片。
(二)獐子島舞弊事件始末。獐子島第一次扇貝“出逃”始于2014年,當時獐子島公司在10月30日晚間發布公告稱公司的蝦夷扇貝絕收。至此,導致前三季度的業績發生巨大的轉折,從預計凈利潤0.44~0.76億元直接變為虧損約8.12億元。2018年2月,獐子島公司基于2017年檢測的蝦夷扇貝存貨不存在減值風險的結果上修改了公告,聲稱扇貝“餓死”,財務業績再次修正,存貨核銷和計提后,凈利潤直接虧損了7.25億元。兩次離奇的扇貝事件引起了證監會的關注,2018年2月9日,證監會正式以涉嫌違規披露信息為由對獐子島公司進行了立案調查。即使被證監會調查,獐子島公司的扇貝依然“出事”,2019年一季度,獐子島第三次發布了關于“扇貝跑了”的公告,公司再次陷入業績虧損狀態,約4,314萬元。累計影響凈利潤14.35億元。經過三次扇貝事件,獐子島公司于2019年7月公司收到證監會下達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
二、基于舞弊三角理論探討獐子島舞弊行為的原因
舞弊三角理論是用來分析企業舞弊動機的常用工具,三角分別指的是“壓力”、“機會”、“自我合理化”這三個核心要素,三要素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舞弊動因結構的整體。
(一)壓力。壓力是舞弊三角理論的第一個層次。壓力通常是指企業進行財務造假的動機。關于本文中獐子島公司的財務造假動機,我們總結了以下幾點:
1、退市。2014年、2015年獐子島凈利潤均為負數,若2016年和2017年凈利潤為負,按照深交所規定,連續虧損三年將被暫停上市,連續虧損四年將被終止上市,這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該公司是想通過利潤調節避免退市,進而繼續進行融資和套現行為。
2、經營不善,成本收益失衡。從表1以及結合2015~2018年年報數據我們得到,2012年開始獐子島公司業績只有小幅下滑,但到了2014年,業績跳崖式暴跌,幾乎所有主要財務指標都是下降的,其中凈利潤比上年減少了1326.83%,虧損了接近12億元;緊接著2015年企業依然處于虧損的狀態;2016年賬面數據是扭虧轉盈了,可是公告顯示,2016年年報中獐子島公司通過虛減營業成本、虛減營業外支出的方式,虛增資產1.31億元,虛增利潤1.31億元,虛增利潤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158.15%。2016年報中利潤總額為8,292.53萬元,凈利潤為7,571.45萬元,追溯調整后利潤總額為-4,822.23萬元,凈利潤為-5,543.31萬元,業績由盈轉虧;2017年賬面顯示虧損7.23億元,但公告顯示,獐子島通過虛增營業成本、虛增營業外支出和虛增資產減值損失的方式,使得2017年年度報告虛減利潤2.79億元,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38.57%,追溯調整后,業績仍為虧損。2019年公司又進入虧損的狀態,并且下滑幅度達到1341.79%,與2014年巨額虧損幅度相當。(表1)

表1 2014~2019年主要財務數據一覽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2014~2019六年中,除2018年業績為小幅盈利(并且不知道是否為事實盈利)外,其他5年都是虧損狀態,包括2016年被調查證明了的實際虧損,連年的虧損說明公司經營出了問題。并且從2014年至今,獐子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逐年增高,尤其是2018年、2019年更是高達88%,進一步說明,經營不善導致資金周轉不靈而不得不融資舉債。除了基本的利潤、資產負債率等財務數據,重大資產出售和股權質押也可以看出獐子島公司由于經營不善業績不佳而不得不“瘦身保命”。可以看出,不管外在還有多少因素的影響,公司經營不善導致虧損的責任不可推脫。從不合理的業務管理到業績虧損,經營不善必然是最大的問題。
3、股東個人利益。2011年獐子島業績下滑前夕,吳厚剛以實現激勵管理團隊為由,減持1.79%的股份,套現3億元。獐子島的前高管曾表示,吳厚剛實際用于激勵團隊只花了1億元左右。那么,剩下的2億元有極大的可能被吳厚剛拿去作為別的用途,甚至用于個人用途。而在2014年冷水團事件后吳厚剛曾表示,自愿承擔1億元災害損失,補給獐子島。2011~2016年減持3.96億元,這種操作背后與股東個人利益脫不了干系。此外,吳厚剛除了從獐子島“賺錢”,遠不止減值套現,獐子島作為一個家族企業,裙帶關系嚴重。吳厚剛成為董事長之后,陸續安排自己的多個親戚參與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并且多占據重要職位。綜上所述,吳厚剛作為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他的財務造假動機明顯。(表2)

表2 吳厚剛歷年增減持情況一覽表
(二)機會
1、市場監管制度不完善。深交所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各項監管制度和法律法規跟不上發展的速度。此外,由于匯集了眾多行業領域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信譽品質參差不齊,對各行各業的監管就變得更為復雜和困難,而且長期以來,交易所一線監管手段較為單一,這些都為財務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機。
2、農林漁牧業的特殊性。財務造假重災區的農林漁牧業,利用消耗性生物性的特殊性,即資產數量大、受自然環境影響大、風險高、難以監測和監管等特點,使得行業整體的財務造假案例層出不窮。如,本文案例獐子島公司,三次宣告虧損都是借扇貝業務餓死凍死等借口。正是因為扇貝的生長與自然環境關系密切,不受人為控制且難以檢測其生長狀況,扇貝不會按常態生長到預期水平的狀況也很常見。加上存貨盤點困難,扇貝這類生物資產的成本并不能可靠計量,預期生長水平及成長標準只能由企業自身進行評估,因此隱藏著巨大的資產操縱風險。受虛增營業成本、虛增營業外支出和虛增資產減值損失影響,獐子島公司2017年年度報告虛減利潤27,865.09萬元,占當期披露利潤總額的38.57%。
獐子島利用扇貝存貨的特殊性,以“洗大澡”式的盈余管理虛減2017年度利潤,以便能在未來年份轉回,增加利潤,避免退市。由此可見,消耗性生物資產很容易成為企業財務造假的庇護傘。
3、外部審計制度不健全。第一,大華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獐子島連續8年密切合作的事務所,對該公司如此大的財務舞弊,早期卻沒有發現,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制度的疏漏,給企業財務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機。第二,由于生物性資產的特殊性,事務所審計受生物性資產種類繁雜、數量龐大、養殖地生態環境復雜風險高等因素的影響較大,由此導致生物資產審計困難,因此,審計范圍受限,給獐子島公司財務造假提供了重要渠道。
4、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不健全。獐子島作為一個上市公司,高層家族化嚴重,管理層串通舞弊,不遵守職業道德,而且大股東權力集中,內部審計沒有很好地發揮防線作用。一旦企業的內控防線崩塌,公司的經營和自我約束力也將全線崩潰。
(三)自我合理化。自我合理化是舞弊操作的重要條件,財務造假公司通過編造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用來掩蓋舞弊本質。除了三次扇貝“跑了”的托辭,獐子島還有以下的掩飾理由:
1、環境波動、自然災害、氣候異常風險。獐子島每年年報上面都會披露水產養殖的風險。扇貝養殖周期長,通常為3年,由于蝦夷扇貝生長在海底,不易監測,扇貝等幼苗的養成只能聽天由命,環境好的時候生長的好,環境不好時可能變成海底“墓場”。恰巧這幾年的養殖環境都不好,如2014年的高溫期的異常低溫加變溫、2017年的高溫期提前且延續時間長、2017年降水和徑流銳減,海水中的鹽分變少,減少了養殖海域的生物硅藻等的餌料數量,這樣的環境顯然不適合扇貝生長。由于這些自然環境的災害,為獐子島的造假提供了合理的庇護。
2、先天不足。獐子島稱公司進苗的資金緊張,而且市場上買不到好苗,很多苗在投放前已經死了。但是,有人反映,公司高管吳厚計認識育苗老板,有的島民還會通過他購買苗種,可是價格會貴上一點。說明公司內部高管的進苗人脈網是很廣的,不然也不會做起了“中介”,買不到好苗實在不具有說服力。顯然在苗種這里,所謂的先天不足也是借口罷了。
3、水土不服。獐子島對于“扇貝跑了”更為奇特的解釋還有“思鄉心切”之說。據說蝦夷為日本北海道的舊稱,蝦夷扇貝系日本北海道引進的異域品種。由于扇貝類的幼苗苗種高度依賴異地輸入,養殖苗種容易形成環境應激,會有扇貝“思鄉心切”、順洋流集體大遷徙之說。這樣的理由令投資者們震驚。
4、會計審計因素。每年年終上市公司總要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報審計、發布審計報告,審計要進行存貨盤點的話只能打撈盤點,導致虛弱狀態的扇貝被撈起來后便死了。不得不說,審計這次成了背鍋俠。
三、上市公司可能舞弊的手段
近年來,股票市場“黑天鵝”頻飛,上市公司財務造假層出不窮,從早期安然公司、世通、施樂等國際名企到銀廣廈、新大地丑聞事件的曝光,市場監督加強的同時,財務造假卻愈發“狡猾”,手段越來越高明。從這些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例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多種財務舞弊手段。
(一)利用會計政策和會計差錯更正對財務造假。最簡單的財務舞弊手段一般是利用會計中不同的財務規則。如,存在多種計價及計提跌價準備方式的固定資產或者存貨這類資產往往會被不當利用。如,企業可以隨意變更固定資產的使用年限、預計凈殘值和折舊方法,從而在年報中多提折舊減少利潤或少提折舊增加利潤。有些公司則通過改變發出存貨的計價方法來調節利潤,采用不同的計價方法會對當期利潤產生不同影響。
還有的企業會利用會計差錯更正,虛增利潤。例如,公司可以將補提資產減值準備作為前期會計差錯更正追溯調整,從而為企業制造盈利。康美藥業就是個例子,2019年4月30日康美藥業發布的“前期會計差錯更正”顯示,貨幣資金科目由之前的341.51億元調減為42.07億元,調整“差錯”金額高達299.44億元。
(二)虛增(減)收入。不管是虛構交易,偽造憑證來增加企業收入,還是通過不合理的關聯交易定價來增加收入,亦或是僅僅通過變更收入確認節點來改變收入金額,這些都是通過改變收入來達到造假目的的手段。
收入提前確認是常用手段,例如大智慧公司,其在2014年2月合同尚未履行完成的情況下,請第三方公司渤商所,配合其提前將項目驗收,提供虛假的項目合作驗收確認書,由于驗收日期倒簽為2013年12月31日,借此2013年虛增15,677,377.4元的收入。
(三)虛增(減)資產。常用的手段有資產評估增值入賬,常見于房地產企業;不良資產或潛虧長期掛賬,資產狀況不良但是一直未處理,從而達到粉飾資產狀況的目的;不計或少記(多計)各項資產減值準備,獐子島公司就是典型的多計提存貨減值準備,“洗大澡”的盈余管理方式在當年度加大虧損,等到來年追溯調整轉回增加利潤,避免退市;虛增(減)應收賬款等。
其他造假手段還包括虛增(減)所有者權益;虛增(減)成本費用,例如輝山乳業案例,其對外宣稱自供苜蓿草,通過自己種植將苜蓿草的成本降低為每噸92美元,但是實際卻是長期從外部第三方購買苜蓿草,每噸均價在300美元以上,隱瞞實際成本,虛增了利潤;虛減(增)負債;例如2018年宜華健康由于預計負債計提不充分被質疑涉嫌財務造假,違規的會計處理,例如2008年蓮花味精將接收的4,167萬元的政府補助直接沖減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等等。
四、總結
類似于獐子島這種由于生物資產的特殊性而導致的財務造假案例繁多,財務造假重災區的農林牧漁業的審計監督需要進一步完善。此外,各大行業由于其行業的特殊性,財務造假的手段越來越隱蔽,例如互聯網行業,由于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很多資產和處理手段已經不再是傳統的方式。互聯網金融行業存在審計證據收集難度大、信息科技風險、審計監督體系不健全、信息技術可控性、穩定性風險、數據泄露與侵權風險、系統性風險等問題,所以這就更需要審計機構和相關人員提高風險識別能力,鑒別企業造假行為。當然,最重要的防范手段還是要從企業自身的內控抓起,更要從法律層面加以完善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