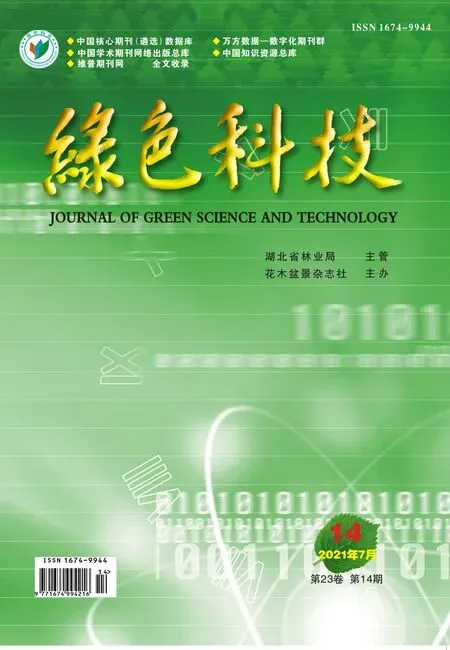高質量發展下長三角地區綠色協調發展水平測算
董 潔,李 勁,趙明濤
(安徽財經大學 統計與應用數學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1 引言
201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求長三角城市群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同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探索生態優先、綠色協調的高質量發展路徑。長期以來,生態環境惡化、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束縛著長三角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綠色協調發展成為社會關注熱點。
目前針對高質量發展方向研究較多。王永昌[1]提出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陳騰[2]結合“五大發展理念”理論,建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體系。對于綠色生態的研究,郭永杰[3]采用熵值法和障礙度模型對寧夏縣域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研究。黃娟[4]從協調發展出發對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進行研究。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緊密結合五大發展理念,以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作為研究,依據2015~201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了高質量發展下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之間綠色生態和協調發展的差異性,結合時間和空間分析,從橫向和縱向研究了26個城市的綠色協調發展的趨勢,從而為城市的高質量發展和綠色協調發展出謀劃策。
2 數據來源和評價體系
2.1 數據來源
2015~2019 年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6—2020)》《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6—2020)》,其余數據通過二次計算可得。
2.2 評級體系
根據前人研究和相關文獻建立以下評價體系,由正(指標值越大,系統協調度水平越高的效益型)、反(指標值越大,系統協調度水平越低的成本型)兩方面考慮[5],表1中“+”為正向指標,“-”為負向指標。

表1 長三角地區綠色生態和協調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3 長三角地區綠色生態發展水平分析
3.1 熵權-TOPSIS綜合評價法
TOPSIS 模型是對原始數據進行歸一化之后,通過余弦法反映各方案差距的一種方法,同時本文引入熵值法對決策矩陣進行加權。步驟如下:

(2)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ei和效用值,并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構造加權的規范矩陣C,利用熵值法對7個指標權重進行。
(3)確定正負理想解(即指標最優值和最劣值),并計算各評價單元與指標最優值和最劣值之間的距離[7]。
(4)計算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值G:
3.2 結果分析
3.2.1 綠色生態指數的時序分析
從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的時間序列角度,研究2015~2019年每年長三角地區綠色生態發展水平均值,可得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綠色生態發展水平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在2016年長三角城市群綠色生態發展水平較前一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在2016年長三角城市的面板數據庫中,可以看到,長三角城市群工業廢水和廢氣排放量有所上升,造成城市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下降。
3.2.2 綠色生態指數的空間分析
從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的空間角度,如圖1所示,長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截面差異明顯,以2015、2017、2019年為例,2015年杭州綠色發展水平最低,安慶、金華水平較高;2017年杭州等地的綠色水平開始升高,安慶、金華等地勢頭較弱,此時舟山綠色發展水平最為落后,無錫、馬鞍山等地后來居上;而到2019年,南通處于最低水平,無錫、馬鞍山等地綠色生態水平居高不下,杭州的綠色生態水平實現反超,排名名列前茅。

圖1 近5年長三角城市綠色生態發展水平指數
如圖1所示,2015~2019年間,南通市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綜合指數雖然有上漲趨勢,但一直處于較低狀態,無錫、杭州、馬鞍山指數處于較高狀態且上漲幅度大。根據 26 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均值大小,可將其分為三類,見表2。

表2 綠色生態水平下城市分類
從整體均值上來看,第三類為南通、鹽城等地,其綠色生態發展處于最低水平,除上海以外其余7個城市都是非中心城市,綠色生態理念普及度不高,工業污染程度高;處于第二類的城市是省會或省會周圍城市,工業污染的處理技術更加先進,可以有效利用資源;第一類的城市綠色生態水平較高,地域為經濟中心,多以商業、文化發展為主,積極落實相關政策,做到了資源的高效利用。
4 長三角地區協調發展水平分析
4.1 因子分析
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通過研究協調發展系統變量的基本結構,利用少數幾個因子來反映協調發展系統的主要信息[8]。
(1)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令協調發展體系中5個指標為變量Bi,則Bi=μi+ai1F1+…+aimFm+εi,Fi稱為公共因子。
(2)根據相關系數矩陣進行相關性檢驗,再進行因子旋轉最后得出因子得分函數。
(3)各城市協調發展水平綜合得分:
4.2 結果分析
4.2.1 協調發展指數的時序分析
從協調發展水平的時間序列角度,研究2015~2019年每年長三角地區協調發展水平均值,可得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協調發展水平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在2017年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水平較前一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在2017年長三角城市的面板數據庫中,可以看到,長三角城市群產業升級和城鎮化有所下降,造成城市協調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下降。
4.2.2 協調發展指數的空間分析
從綠色生態發展水平的空間角度,如圖2所示,長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間協調發展各有不同,但單個城市的發展處于規律性較強,以2015、2017、2019年為例,2015年南通協調發展水平最低,杭州、蕪湖、馬鞍山水平較高;2017年南通的協調發展水平仍仍處于最低,但較之前有所提升,杭州、蕪湖、馬鞍山等地協調水平穩步提升,處于較高水平;到2019年,26個城市協調 發展情況與之前大致相同,蘇州、南京、常州等地協調發展水平開始飆升。

圖2 近5年長三角城市協調發展水平指數
由圖2可知,從單個城市之間來看,在2015~2019年間,大部分城市協調發展呈平穩上升態勢,少數城市如金華等地再發展過程中略顯遲緩,甚至有下降趨勢。根據 26 城市綠色發展水平均值大小,可將其分為三類,見表3。

表3 協調發展水平下城市分類
從整體均值上來看,第三類為南通、金華等地的協調發展處于最低水平,這5所城市皆遠離省會,在地理位置上稍顯劣勢,在城鎮化發展和經濟發展上起點較低;處于第二類的城市是省會周圍城市,享有充分的地理優勢和資源供給,城鎮化推進力度大,產業升級速度快;第一類的城市協調發展水平較高,地域為省會以及靠近經濟中心,經濟發達,工業體系完善,產業結構和升級在穩步推進,城鄉一體化效果顯著。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2015~2019年面板數據,測算26個城市綠色生態和協調發展水平,研究結論表明:從時間上來看,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綠色生態發展水平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但在2016年略有下降,同樣26個城市的協調發展水平整體為上升趨勢,但在2017年有所下降,說明長三角地區的綠色協調發展之路漫長而曲折。從空間上來看,長三角地區綠色生態與協調發展水平呈現從經濟中心到偏遠地區衰退的態勢,尤其是區域化和城鎮化發展不均導致了26個城市協調發展水平差異明顯。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將綠色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積極改善生態環境。工廠等地區力求降低廢氣廢水的排放強度,減少資源浪費消耗;政府建立完善的立法保障,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同時還有引導群眾建立綠色生態的理念,努力構建資源高效利用的生態和諧綠色城市。
(2)加強城鄉協調、產業協調,倡導產業升級;發揮沿江沿海城市群的輻射作用,帶動內陸城市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力求開拓長三角地區分工協作、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