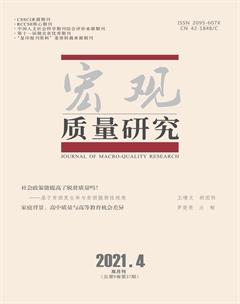知識深度和廣度、社會聯結與企業高質量創新
楊震寧 侯一凡 耿慧芳



摘 要:以2017年國家科技部創新調查中的720家制造業企業為樣本,研究了知識深度和廣度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影響,并將社會聯結作為調節變量研究其作用機制。實證結果表明: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知識廣度越高,越有利于企業高質量創新;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的相互作用會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產生影響;企業具有的機構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企業具有的市場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正向調節知識廣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研究結論搭建了知識基礎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之間聯系的橋梁,同時豐富了企業技術創新理論,在實踐上為企業進行知識管理和創新管理提供了借鑒與啟示。
關鍵詞:知識深度;知識廣度;社會聯結;企業創新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韋倩和李珂涵,2019)。創新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葉建亮等,2019),也是企業在激烈競爭中存活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然而,中國的創新效率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存在較大差距(陳勁,2018),中國創新正處于“低質低效”的雙低困境(諸竹君等,2020),在重視創新速度和數量的同時,提升創新的質量顯得尤為重要。除此之外,由于創新面臨著資源和環境的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企業應當通過更加廣泛的方式搜尋和利用知識資源,以彌補企業內部技術和市場資源的不足(Chesbrough,2006),因此關于知識獲取、知識整合、知識分享、知識基礎等相關知識理論深刻地影響了企業的創新水平與競爭能力。知識基礎理論認為,企業現有的知識存量限制了其理解和將新知識應用于重大創新的范圍和能力(Hill和Rothaermel,2003),因此對于知識基礎的討論,也是對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和水平的探索。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共同構成知識存量和知識基礎(Cohen和Levinthal,1990;McGrath和Nerkar,2004;West和Iansiti,2003),它們作為知識基礎的兩個不同維度,揭示了企業擁有的整體知識的結構和內容(Zhou和Li,2012),是企業最為重要的競爭資源(Miller等,2007),在企業的創新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最終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績效(Grant和Rober,1996),創新的成功和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Wu和Shanley,2009)。探索知識深度和廣度在企業創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知識深度和廣度來提高企業高質量創新水平已成為創新管理領域的重要問題。
知識深度和廣度是知識基礎的兩個維度,揭示了企業擁有的整體知識的結構和內容(Zhou和Li,2012)。知識深度是指企業對特定技術或應用領域的熟悉程度(Wu和Shanley,2009),它對企業意義重大,企業要形成并發展核心競爭力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在少數專業技術領域發展深厚知識(Prahalad和Hamel,1994)。近年來,知識深度仍然是一個熱點話題,部分學者就知識深度持積極態度,認為知識深度在促進企業知識重組(Fleming和Sorenson,2004)、“結構式創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Henderson和Clark,1990)、知識創新(唐青青等,2018)和突破性創新(Laursen和Salter,2006)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主體的知識深厚程度高不一定會帶來積極的作用,甚至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Zhang和Fuller,2007;Cristina和Carlos,2008)。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結論既說明了問題的復雜性,也體現了對于連貫性結論的需求和相關深度研究的需要(Jin等,2015)。除知識深度以外,構成知識基礎的另一個維度是知識廣度。知識廣度是指企業擁有專業知識的科學和技術領域范圍(Wu和Shanley,2009)。目前對知識廣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積極作用方面。企業所擁有的多元化知識范圍越廣,越有利于滿足企業發展對異質性信息的需要(Kogut和Zander,1992),可以提高企業的知識吸收能力(付敬和朱桂龍,2014)、技術合作能力(Zhang和Fuller,2007)和技術創新績效(楊震寧等,2016)。然而,知識深度和廣度作為知識基礎的兩個維度,除了可以單獨對主體產生影響,也存在共同作用于主體的可能性,那么在兩者共同作用于企業時,是發揮積極還是消極作用呢?對于這個問題,已有學者主張知識廣度和深度之間達到平衡可以對企業創新產生積極影響(Katila和Ahuja,2002;Laursen和Salter,2006)。
企業創新研究的另一個相關方面是社會聯結。社會聯結與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等概念具有相似性。社會聯結定義為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穩定的社會系統(Wellman和Berkowitz,1988),或者可以定義為人際關系網絡中的對個體在社會中發展有影響的關系型資源(Burt,1992)。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企業置身于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在新的創新環境下,越來越多的企業打破了最初的“封閉式創新模式”下的良性循環邏輯,形成了開放式創新的新邏輯,尋求外部社會資源,嘗試采取各種方式與外部主體開展交流與合作、建立社會聯結,來彌補企業內部知識基礎的不足(Arora和Gambardella,2010)。隨著組織邊界的逐漸模糊,知識得以跨組織流動,企業除憑借自身的能力搜索、吸收外部知識之外,利用外部社會聯結來增加自身知識儲備、提高知識基礎的深度和廣度,從而獲取更多創新資源、縮短創新周期、降低創新風險,成為另一種創新路徑(Lichtenthaler,2011)。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將重心從創新數量向創新質量轉變(趙玉林等,2021)。創新質量的概念最早由Haner(2002)提出,指的是對組織內各領域實現創新結果過程的評價以及對創新潛力和結果的比較,是對綜合創新績效的一種表述,具有特殊的動態特征。從創新質量角度對創新進行評價時,可以將創新分為高質量創新和低質量創新,學者在使用專利申請量對創新質量進行衡量時,普遍認為發明專利可以代表高質量創新,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設計專利相對來說技術含量較低,不能很好地代表高質量創新(余明桂等,2016;田軒和孟清揚,2018;白旭云等,2019;吳堯和沈坤榮,2020;王靖宇等,2020)。對于高質量創新的界定,趙玉林等(2021)認為高質量創新指的是先進技術、核心技術以及具有高應用價值和經濟效益的創新;周陽敏和桑乾坤(2020)認為高質量創新指的是以速度快、主體包容性強、自主性高為特征的創新;呂越等(2021)認為高質量創新意味著創新由簡單模仿向自主研發的轉變、由重視速度向質量和效益傾斜、由資源和資本導向轉為創新驅動發展。
目前研究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對企業創新作用的文獻主要有幾種情況:一是只討論知識深度或知識廣度中的一方(唐青青等,2018);二是將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同時討論,并探討新知識和原有知識之間的一致性作用(劉巖和蔡虹,2011);三是研究不同層次的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組合對其他因素的作用機理(盧艷秋等,2017)。然而,現有相關研究普遍存在三個特點和共性:一是主要圍繞“吸收能力”視角展開(Cohen和Levinthal,1990;劉巖和蔡虹,2011;鄒波等,2015;唐青青等,2018);二是利用專利數據對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進行測量(Ahuja和Katila,2001;Wu和Shanley,2009;劉巖和蔡虹,2011);三是對企業創新進行研究時,往往以創新績效、創新效率、突破性創新、知識創新等為研究對象,較少結合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發展階段和時代要求對高質量創新、創新質量等加以研究。可以發現,現有研究缺乏從更廣泛的視角對知識深度和廣度與企業創新的關系進行探索,并在知識深度和廣度之間建立聯系研究其對于企業創新的綜合作用,同時對于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測量不夠豐富。
基于上述理論背景和現實背景,本文認為有必要從一個新的視角對知識深度和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的關系進行探討。在開放式創新的環境下,知識搜尋、知識積累、知識管理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王紅麗等,2011),社會聯結作為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蘇敬勤和林海芬,2011),可以打破組織邊界,促進知識的跨組織流動,對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產生深刻影響,同時對于企業創新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經濟由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階段,也對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創新在數量上的提升并不能夠客觀反映創新競爭力(張志強等,2020),創新的高質量發展才是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的綜合體現(張古鵬等,2011),是創新研究更值得關注的議題。知識深度和廣度作為知識基礎的兩個維度,用于衡量企業內部所具有的知識特征,社會聯結衡量企業外部所具有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因此,將企業內部知識基礎、外部社會聯結、企業高質量創新納入一個研究框架中加以討論,形成知識基礎、社會聯結和企業高質量創新的一個完整邏輯,打破企業邊界的束縛討論知識與創新,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可能存在的貢獻在于:其一,以知識基礎、社會聯結、企業高質量創新為研究變量,探討企業內部所具有的知識特征與企業外部所具有的社會資源的作用機理,以及知識特征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影響機制,豐富了企業技術創新理論、知識基礎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其二,對知識基礎、社會聯結和企業高質量創新都進行了細分,討論具體的細分因素對于不同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具體影響,研究更加具體。其三,不僅研究知識深度和廣度這二者分別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影響,還探討知識深度和廣度之間的平衡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影響,形成知識基礎-社會聯結-企業創新之間一個完整的關系鏈條。其四,問卷數據和二手數據相結合,以問卷數據為主,并通過二手數據進行驗證。另外,本文所采用的制造業企業創新活動調查數據通過問卷形式獲取,問卷既結合了經典量表,也進行了特色性更新,具有研究特色。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 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
知識深度是指企業對特定技術或應用領域的熟悉程度(Wu和Shanley,2009),它對企業意義重大,企業要形成并發展核心競爭力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在少數專業技術領域發展深厚知識(Prahalad和Hamel,1994)。
關于知識深度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創新型企業通常習慣于從少量的資源中深入汲取知識和想法,懂得深入使用關鍵性資源并與其保持良性溝通的企業往往具有更高的創新能力(Laursen和Salter,2006)。第二,企業專注于某一領域的深厚知識使其更容易識別和搜尋外界對自身有用的相關知識,有利于知識的積累和知識存量的增加,可以提升企業在專業領域的技術水平,提高創新績效(McFadyen和Albert,2004)。第三,當企業完成了某一領域深厚專業知識的積累后,會在實踐中加以利用和改進,即對這些知識進行重新組合,形成自己需要并且適合自己的新知識,從而促進企業創新和再創新(Xu,2015)。第四,當企業經過多次對專業領域知識的搜尋、吸收、重組后,會形成嫻熟吸收和利用相關知識的能力,提高利用專業知識的效率,降低知識的搜尋和利用成本(唐青青等,2018)。由于高質量創新是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的綜合體現(張古鵬等,2011),由以上分析可知,知識深度對于企業創新能力、創新績效均具有促進作用,可以說知識深度對于企業高質量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企業的知識水平并不是越深越有利于創新,過于深厚的知識基礎可能還會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產生反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企業所擁有的知識層次越深,越難從中繼續挖掘和吸取有用知識,對新知識的搜尋難度越大,原有知識越來越難以運用于新的途徑,會導致創新機會的減少和產生創新突破的可能性降低(劉巖和蔡虹,2011),難以在以往創新的基礎上產生更加高質量的創新;第二,某一方面過于集中的知識可能會導致核心能力僵化和路徑依賴,不利于企業產生新穎的想法,阻礙開拓性發明和創新(Cristina和Carlos,2008),開拓性發明受到阻礙即意味著高質量創新受到制約;第三,企業過度專注于某一特定的專業和技術領域,會使企業難以靈活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不利于技術創新績效的提升(劉巖和蔡虹,2011),創新績效是創新質量的表現形式之一(張古鵬等,2011),從而不利于企業高質量創新。綜合以上文獻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
(二) 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
知識廣度是指企業擁有專業知識的科學和技術領域范圍(Wu和Shanley,2009),它可以反映企業異質性知識的水平維度(Luca和Atuahene-Gima,2007)。
不同于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倒U型關系,多數學者認為知識廣度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的影響是正向的。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其一,擁有廣泛知識基礎的企業對許多領域的知識都有所涉獵,多樣性知識對于企業解決正常或異常的日常運營問題至關重要(Henderson和Cockburn,1994),這些知識中的一部分可以幫助企業鎖定“資源位置”并確定“資源質量”(Salavisa等,2012),一旦企業在某些方面遇到問題,這些知識就可以快速整合各種資源,為企業提供多種選擇(Jin等,2015)。其二,從競爭優勢的角度考慮,學者Peteraf(1993)提出,聘用具有深度專業知識的專家本身并不太可能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現有企業更需要的是從新的和小的企業中學習并獲取大量的補充知識,而創新就是對現有知識進行不斷重新組合的過程(Fleming和Sorenson,2004)。其三,如果一個企業具有多樣性的知識庫,在與合作伙伴交流時,則可以將新知識與已有知識建立聯系,從而簡化對于新知識的吸收和消化,有利于企業嘗試更多路徑以探索新領域(Kauffman等,2000),增強對于新知識的識別能力(Arora和Gambardella,2010)、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及對隱性知識的汲取能力(Moore,1958);同時,通過將新知識與已有知識進行整合,可以提高自己對于知識的“架構能力”(Henderson和Cockburn,1994),最終促進創新能力的提升。高質量的創新需要這種對知識和資源的吸收、整合、利用能力(Guan和Liu,2016)。其四,知識廣度較高的企業會有強烈的意愿和充分的能力與其他企業建立技術合作關系(Zhang等,2007),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潘清泉和唐劉釗,2015)。其五,不同來源的知識對于企業不同方面的高質量創新產生的積極作用可能是不同的,科學型知識和市場型知識對于探索式管理創新的積極作用更大,從供應鏈合作伙伴處獲取的知識則對利用式管理創新具有更大的積極影響,多樣性的知識有利于企業進行多種形式的創新(余傳鵬等,2020)。由以上分析可知,知識廣度對于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提升均具有積極作用,同時對于企業整合和利用資源、形成競爭優勢、進行多種形式的創新方面亦有重要影響。由于高質量創新是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的綜合體現(張古鵬等,2011),可以由此推出,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綜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三) 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平衡與企業高質量創新
大多數研究表明,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對于企業創新都是必要的,但是有學者提出,由于企業資源稀缺性的限制以及追求知識深度和廣度的行為具有自我強化機制,因此知識深度和廣度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Katila和Ahuja,2002)。一方面,企業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企業探索知識深度和廣度的行為會爭奪資源,若是投入過多資源在知識廣度的拓展上,則會在知識深度的挖掘方面投入較少的資源,一定程度上損失知識深度在企業高質量創新方面帶來的積極作用(Jin等,2015)。另一方面,知識和創新行為具有自我增強和路徑依賴的特點,沒有協調好知識深度和廣度之間的平衡會使得企業很容易陷入自我增強和路徑依賴這兩種陷阱,從而對企業創新產生負面影響(Levinthal和March,1993)。因此,企業需要實現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這兩個維度的平衡(Jin等,2015)。綜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的平衡與企業高質量創新存在正相關關系。
(四) 社會聯結的調節作用
社會聯結定義為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穩定的社會系統(Wellman和Berkowitz,1988),或者可以定義為人際關系網絡中對個體在社會中發展有影響的關系型資源(Burt,1992)。企業通過社會聯結可以進行資源交換和知識分享(Reagans和Mcevily,2003),從而促進產品創新(Tsai和Ghoshal,1998)和新產品開發(Yli-Renko等,2001),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效率(谷磊等,2019),是企業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基礎性因素(周小虎和馬莉,2008)。企業通過社會聯結可以產生一種集聚效應,推動技術外部性和知識溢出,從而提高企業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陳智和吉亞輝,2019)。在社會聯結的分類方面,可以分為產業界內的社會聯結(企業與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其他企業)和產業界外的社會聯結(企業與政府、大學、科研機構)(戴勇和朱桂龍,2011);或者可以分為橫向關系聯結(企業與客戶、供應商)、縱向關系聯結(企業與競爭對手、其他企業)和社會關系聯結(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中介組織、政府部門、行業協會、金融機構、風險投資機構)(張方華,2005)。
本文對社會聯結的分類,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張方華(2005)、戴勇和朱桂龍(2011)以及楊震寧和趙紅(2020)的定義,將企業的社會聯結分為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機構聯結包括高校、政府或公共科研機構、咨詢公司和私立研發機構以及專業行業協會,市場聯結包括設備、原材料、零部件或軟件供應商、客戶或消費者以及市場競爭者或同行其他企業。
本文認為,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倒U型關系。當企業所具有的知識深度較低時,意味著企業對于本行業的知識了解得不夠深厚和透徹,此時通過建立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可以幫助企業了解本行業的初級和中級知識,這些知識中的大多數對于企業來說是新穎的,沒有與企業原有專業知識構成過多重疊,因此增加了企業的知識深度(Jin等,2015)。但是,企業一定時間內所能吸收的知識是有限的,在企業知識深度處于中低水平時,社會聯結帶來的豐富專業知識不能很快被企業吸收,與企業自己從外界獲取的專業知識量并沒有顯著不同,反而因為知識的重疊導致吸收效率變低(唐青青等,2018),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知識深度較低時對企業高質量創新所產生的正效應。企業的知識積累到一個較高水平時,企業自己獲取、學習和吸收的知識存在重復和冗余,知識的新穎性降低,有效吸收的知識變少(潘清泉,2015)。這時候通過建立社會聯結,可以從其他主體中吸收前沿知識,借鑒其他主體解決冗余知識的思路,同時在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的幫助下對所需專業知識的搜尋范圍擴大,更容易搜索到企業所需的特定深度知識,深度和專業知識搜索的成功率有所提高(唐青青,2018),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知識深度過高對企業高質量創新所產生的負效應。綜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倒U型關系。
本文認為,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正向調節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前面已經分析到,知識廣度對企業高質量創新有正向促進作用:第一,知識廣度可以帶來異質性信息,對于企業解決日常運營問題至關重要(Henderson和Cockburn,1994);第二,創新一直被認為是已有知識和新知識的重組(Katila和Ahuja,2002),知識廣度越大,企業重組和整合不同知識的機會就越大(Fleming和Sorenson,2004);第三,知識廣度越大,捕獲信息的區域就越廣,信息轉化為新想法、新思想和新觀點的可能性就越大(Jin等,2015);第四,當企業的知識廣度較高時,可以從研發、制造、營銷和金融等其他領域的聯系中獲得各種互補的知識和信息,從而開展創新活動,降低創新成本(Narula,2001)。當企業建立了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后,獲取知識的區域將變得更加廣闊,更容易獲得異質性知識和其他領域的互補知識,有利于企業將廣度知識轉化為創新的想法,促進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創新績效的增長,從而推動企業高質量創新。可以發現,社會聯結可以增強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綜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5: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正向調節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綜上所述,本文的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三、研究設計
(一)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17年國家科技部關于制造業企業的創新調查所獲取的截面數據,調查方式是發放問卷,對象是科技部選取的具有典型創新行為和活動的來自全國43個城市、30個細分制造業領域的1407家企業,內容是制造業企業過去三年間所進行創新活動的基本情況,問卷填寫人員為對本企業創新活動較為了解的相關中高層管理者。刪除成立時間以及企業年齡等變量中存在不合理數據的企業樣本、刪除本文所需條目中存在缺失值的樣本后,最終保留720家樣本企業的數據。同時,將這720家企業的名稱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數據庫中的企業名稱進行匹配,確認了問卷中相關條目的真實可靠性。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二)變量測量
本文選取企業高質量創新作為因變量。從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兩個維度來衡量企業高質量創新,這么做是因為:本文所基于的調查問卷的對象是制造業企業,新產品和新工藝的產生和開發非常適合衡量制造業企業的創新績效(楊震寧和趙紅,2020)。產品創新績效通過問卷條目衡量,將產品創新績效分為三個等級——僅對企業而言是新的、只在中國大陸是新的、在世界范圍都是新的。工藝創新績效通過問卷條目衡量,基于過去三年企業推出工藝創新的次數將工藝創新績效分為四個等級——0次、1~4次、5~10次、10次以上。除此之外,企業的專利申請數量可以反映企業的創新能力(顧海峰和卞雨晨,2020),而發明專利相較于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而言,由于獲取難度更大、技術含量更高,所以可以更好地反映企業的創新能力、創新水平以及創新質量,可以更好地代表企業的高質量創新(余明桂等,2016;田軒和孟清揚,2018;白旭云等,2019;吳堯和沈坤榮,2020;王靖宇等,2020)。因此,為了證明模型及結果具有穩健性,本文將發明專利申請數量作為替代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Aggarwa,2020;王泓略等,2020;李波等,2020)。
本文選取知識深度、知識廣度、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平衡作為自變量。對知識深度的測量借鑒Jin等(2015)、劉景東和黨興華(2013)、張志鑫和梁阜(2019)的測量方式,將知識深度分為三個方面——企業對本行業的了解程度、企業對本行業技術知識的掌握程度、企業對本行業綜合知識的掌握程度。對知識廣度的測量借鑒Jin等(2015)、劉景東和黨興華(2013)、張志鑫和梁阜(2019)的方法,將知識廣度分為三個方面——企業所擁有的市場廣度、與企業建立聯系和知識交換的客戶類型多樣性、企業中技術人員的技術背景多樣性。
對于兩變量之間的平衡關系的研究,已應用于開放式創新(Ferrary,2011)、跨國組織學習(Russo和Vurro,2010)、創新組織(McCarthy和Gordon,2011)、全面質量管理(Luzon和Pasola,2011)等多個領域,管理學界已有相關成果:He和Wong(2004)在研究組織靈活性時,通過構造乘積項來建立起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之間的平衡,從而探討兩種創新戰略之間的平衡對于因變量銷售增長的影響。Cao等(2009)同樣構造了二者乘積項來研究探索式創新和利用式創新之間的平衡對公司績效的影響。Jin等(2015)構建了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乘積項來表示其平衡效應,在研究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單獨作用的同時,還探討兩個維度之間的平衡對于探索式創新績效和利用式創新績效的影響。本文借鑒以上學者的研究方法,即構造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乘積項來表示這兩個維度之間的平衡。
本文選取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市場聯結)作為調節變量。借鑒張方華(2005)、戴勇和朱桂龍(2011)以及楊震寧和趙紅(2020)對社會聯結的分類并做出適當調整,將企業的社會聯結分為高校,政府或公共科研機構,咨詢公司和私立研發機構,專業行業協會,設備、原材料、零部件或軟件供應商,客戶或消費者以及市場競爭者或同行其他企業7項。
本文選取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產總額、所有制類型、細分行業、所在地區作為控制變量。通過對企業從業人數的測量來衡量企業規模,并將企業規模分為三個等級——300人以下、300~2000人、2000人以上;用企業的成立時間來衡量企業年齡,即用問卷調查的年份2017減去企業成立年份并取自然對數;將企業資產總額分為三個等級——4千萬以下、4千萬~4億、4億以上;將所有制類型分為八類——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其他內資公司、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并采用啞變量來衡量;細分行業,分為30個細分制造業領域,并采用啞變量來衡量;所在地區,根據企業注冊地來確定其所在城市,并采用啞變量來衡量。
(三)模型選擇
本文數據為截面數據,變量除調節變量外基本均為離散數值,因變量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是有序整數,因此本文采用Stata15.1對變量進行有序邏輯回歸(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構建層次回歸模型。除此之外,本文使用發明專利數量作為替代因變量進行穩健性分析時,模型選擇分為三步:首先,考慮到發明專利數量為非負整數,適合采用泊松回歸或者負二項回歸進行分析;其次,由于因變量的方差大于期望,即存在“過度分散”,適合采用負二項回歸而不是泊松回歸進行分析;最后,很多企業過去三年間的發明專利數量為0,存在很多“0”值,適合采用零膨脹負二項回歸(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ZIP)進行分析(陳強,2014)。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5.1對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發現,各自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均小于0.8,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Rockwell,1975)。同時,對自變量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各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0,再次證明了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問卷由同一人完整填寫,可能會存在同一來源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問題(Podsakoff等,2003),因此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的方法來檢驗是否存在此問題,即對本文所采用的所有問卷測量條目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Harman,1967)。結果表明,旋轉后的第一主成分所解釋的方差比例為21.675%,低于40%,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三)回歸分析
表3為以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作為因變量進行有序邏輯回歸的結果。模型1~模型5為以產品創新績效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6~模型10為以工藝創新績效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
在模型1中,知識深度一次項的系數為正且顯著(系數=1.742,p < 0.01),二次項的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126,p < 0.01),表明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曲線拐點約為6.91;在模型6中,知識深度一次項的系數為正且顯著(系數=1.271,p < 0.01),二次項的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082,p < 0.01),表明知識深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曲線拐點約為7.75,綜合模型1和模型6的結果,H1得到驗證,即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這與劉巖和蔡虹(2011)、潘清泉和唐劉釗(2015)、唐青青等(2018)所得結論一致。
在模型2中,知識廣度的系數為正且顯著(系數=0.296,p < 0.01),表明知識廣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知識廣度每增加一個單位,企業產品創新績效的變化幅度為1.34倍(通過e系數求得,下同);在模型7中,知識廣度的系數為正且顯著(系數=0.357,p < 0.01),表明知識廣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知識廣度每增加一個單位,企業工藝創新績效的變化幅度為1.43倍,綜合模型2和模型7的結果,H2得到驗證,即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與劉巖和蔡虹(2011)、潘清泉和唐劉釗(2015)、曾德明和陳培禎(2017)、唐青青等(2018)、Jin等(2015)所得結論一致。
在模型3中,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074,p < 0.01),表明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的平衡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存在負相關關系,知識深度和廣度的平衡程度每提高一個單位,企業產品創新績效的變化幅度為0.93倍;在模型8中,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044,p < 0.05),表明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的平衡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存在負相關關系,知識深度和廣度的平衡程度每提高一個單位,企業工藝創新績效的變化幅度為0.96倍,綜合模型3和模型8的結果,結論與假設方向相反,H3未得到驗證。Jin等(2015)的文章也研究了知識深度和廣度的平衡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將創新績效分為利用式創新績效和探索式創新績效,結論為二者平衡對利用式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探索式創新績效的影響不顯著,可見,對創新績效的不同研究視角會導致這個結論具有差異,也顯示出平衡性研究結論的穩健性還有待加強。
在模型4中,機構聯結與知識深度二次項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133,p < 0.05),市場聯結與知識深度二次項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135,p < 0.05),表明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即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隨著社會聯結的增強而削弱;在模型9中,機構聯結與知識深度二次項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系數=-0.064),市場聯結與知識深度二次項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系數=-0.138,p < 0.05),表明企業具有的市場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但機構聯結對知識深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之間的調節效應并不顯著,綜合模型4和模型9的結果,H4得到部分(四分之三)驗證。假設未得到完全驗證的原因可能是將社會聯結和企業創新都進行了細分,填寫問卷的企業處于不同的發展時期,大多數企業雖具有社會聯結,但部分企業可能對于其細分因素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有不同的側重,比如有的企業具有很強的機構聯結和較少的市場聯結,對于機構聯結的相關問卷條目可以進行熟練和精確填寫,而對于市場聯結的相關問卷條目只能進行粗略估計,類似地,部分企業可能對于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有不同的側重,因此這個假設大部分可以被驗證,少部分未得到有效驗證。
在模型5中,機構聯結與知識廣度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系數=-0.029),市場聯結與知識廣度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系數=-0.039),方向與假設相反且不顯著,表明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對知識廣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在模型10中,機構聯結與知識廣度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系數=-0.038),市場聯結與知識廣度構成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系數=-0.031),方向與假設相反且不顯著,表明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對知識廣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綜合模型5和模型10的結果,H5未得到驗證。
由于H5沒有得到有效驗證,因此本文借鑒Jin等(2015)所采用的對調節效應的檢驗方法,試圖通過更適合檢驗調節效應的方式來進一步驗證H5。具體方法是,將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分為兩組,低于平均值的樣本劃分為低值組,高于平均值的樣本劃分為高值組,以和上文相同的方式進行有序邏輯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關于社會聯結對知識廣度和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調節作用(即H5),模型給出了不同于表4的解釋。對比模型11和模型12,可以發現隨著企業機構聯結程度的增加,知識廣度與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系數的顯著性得到提高;類似地,對比模型15和模型16,可以發現隨著企業市場聯結程度的增加,知識廣度與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系數的顯著性得到提高,說明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正向調節知識廣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但社會聯結對知識廣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的調節效應并未得到驗證,因此H5得到部分(二分之一)驗證,假設未得到完全驗證的原因可能與上文對H4的分析類似。
綜上,可以發現,H1和H2可以得到完全驗證,這與目前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H3未得到驗證,可能是由于對于兩變量之間平衡的研究較少,對于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平衡的研究更少,因此缺少理論支撐,另外也可能是由于問卷填寫企業的特性導致,如受訪企業均是制造業企業、均是國內企業等。H4和H5得到部分驗證,這兩個假設用來驗證調節效應,未被完全驗證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文將社會聯結細分為機構聯結和市場聯結,將企業高質量創新細分為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假設用于驗證機構聯結與產品創新績效、機構聯結與工藝創新績效、市場聯結與產品創新績效、市場聯結與工藝創新績效這四種調節效應,可能太過于具體,受訪企業在填寫問卷時,存在側重于某一方面的情況,也存在企業未對這些問題進行細致劃分的可能性,導致問卷填寫存在偏差,使得調節效應的兩個假設大部分得到驗證,但未被完全驗證。
(四)穩健性檢驗
(1)替換因變量:為了進一步驗證所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發明專利申請數量作為替代因變量進行零膨脹負二項回歸,此數據通過問卷獲得,并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數據庫進行驗證,結果如表5所示。可以發現,對于所有假設的驗證結果均與表3一致,表明本文的回歸結果比較穩健,具體結果此處不再贅述。
(2)分樣本檢驗:考慮到研發投入可能會對企業創新產生影響(楊震寧和趙紅,2020),本文以研發投入的中位數為分界點,將研發投入分為高、低兩組,再次進行主效應檢驗調節效應檢驗,以處理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由于以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為因變量的檢驗結果相似,為簡便起見,此處僅以產品創新績效為因變量做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可以發現,對于所有假設的驗證結果均與表3一致,本文的回歸結果比較穩健,具體結果此處不再贅述。
(3)改變回歸方法:本文改變表3所用的有序邏輯回歸方法,采用OLS回歸方法對主效應和調節效應再次進行驗證,由于以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為因變量的檢驗結果相似,為簡便起見,本文僅以產品創新績效為因變量做回歸,回歸結果均與表3一致,表明本文的回歸結果比較穩健。限于篇幅,此次不展示具體回歸結果,若讀者感興趣,可聯系作者索取。
五、研究結論、啟示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探討了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關系,并加入了企業社會聯結作為調節變量,提出了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社會聯結和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關系的相關假設,得到以下五個結論:
第一,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當企業具有的知識深度比較低時,隨著知識深度的提高,專注于某一領域的深厚知識使其更容易識別和搜尋外界對自身有用的相關知識,有利于知識的積累和知識存量的增加,提升企業在專業領域的技術水平;同時將專業知識在實踐中加以利用和改進,對這些知識進行重新組合,形成自己需要且適合自己的新知識;并形成嫻熟吸收和利用相關知識的能力,提高利用專業知識的效率和創新能力,使得創新績效得到提升,最終有利于企業的高質量創新。然而,當知識深度的提高達到一定程度之后,若知識深度繼續增加,則會加大新知識的搜尋難度,同時可能會導致核心能力僵化和路徑依賴,不利于企業產生新穎的想法,最終導致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的降低,不利于企業的高質量創新。
第二,知識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企業的知識廣度越高,涉獵的領域越廣,其對于新知識的識別能力、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和架構能力越強,有利于新知識的吸收,從而使得自身所擁有的知識類型具有多樣性和異質性,提高企業應對各種情況和危機的能力,最終有利于企業的高質量創新。
第三,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的相互作用會對企業高質量創新產生影響。當企業想要提高創新質量時,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將知識深度和廣度控制在合理范圍,并使二者達到平衡。知識深度不能過高,否則會降低知識廣度帶來的正效益,使得總體效益降低,因此要找到本企業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能夠帶來最佳價值的最優平衡點。
第四,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倒U型關系。具體而言,企業具有的機構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企業具有的市場聯結負向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和工藝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可以發現,市場聯結可以調節知識深度與企業工藝創新績效之間的倒U型關系,而機構聯結卻不能,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特征的不同。對于工藝創新而言,其重點在于運用新的方式方法來提高企業的生產水平和生產效率,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通過建立市場聯結可以了解市場情況,明白自己的產品在哪些工藝上需要進行細小的調整和改變才能更加適應市場的需求,促使企業獲取工藝改進方面的知識,從而提高企業的工藝創新績效。
第五,企業具有的社會聯結正向調節知識廣度與企業產品創新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知識廣度可以為企業進行日常運營和產品創新帶來異質性信息,促進對不同知識的重組和整合,并且可以從研發、制造、營銷和市場等領域中獲得各種互補的知識和信息,這對于新產品的研發和舊產品的改進至關重要,最終促進企業產品創新績效的提升。
(二)研究啟示
本文豐富了企業技術創新理論、知識基礎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對于企業進行知識管理和創新管理提供了借鑒與啟示,具體體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企業要合理運用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不同點和特色來推動企業的高質量創新。企業在創新初期要深入學習專業領域的知識,提高自身的專業能力,聚焦于自己擅長的領域,不斷鉆研,精益求精。隨著專業水平的提高,企業不能固步自封,當自身所在領域呈現出飽和狀態時,要勇于吸收更多領域的異質性知識,減小核心能力僵化帶來的副作用,將多樣性的知識運用于自己所在的領域,在必要時候可以適當進行轉型,提高企業的適應能力和靈活性。與此同時,企業需要結合自身情況,調整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之間的平衡,尋找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最優平衡點,利用知識深度和知識廣度的綜合作用促進企業高質量創新。
其次,企業要合理運用社會聯結所具有的調節效應。若企業處于發展初期,知識深度和廣度都比較低,此時可以充分提高自身社會聯結的質量和水平,強化知識廣度對于高質量創新的提升作用,雖然可能會一定程度上減緩知識深度對于高質量創新的提升速度,但是知識深度和廣度對于高質量創新的積極作用均處于不斷提高的狀態。若企業處于發展后期,知識深度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知識深度的繼續提升可能會損害高質量創新,這時候企業依然要充分利用社會聯結的作用來減緩知識深度對于高質量創新的負向作用,同時推動知識廣度對于產品創新績效的積極作用。
最后,企業要注重創新的質量,促進高質量創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可見高質量創新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從傳統的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再到創新驅動,以高質量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在我國的發展藍圖中占據著決勝制高點。在這種時代要求下,企業僅追求創新效率、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是不夠的,應該注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培養核心技術并減少核心技術“空心化”,重視高質量的發明專利的產出,不斷加強高質量創新。
(三)未來展望
雖然本文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啟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對于平衡性的研究,所得結果與假設和Jin等(2015)的研究結果相反,希望未來研究可以探索出更多的衡量平衡效應的方法。除此之外,我們的研究僅描述了知識深度和廣度與企業高質量創新之間的靜態關系。然而,從更現實的角度來看,這些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知識廣度和深度發展的演化路徑,從而尋找知識深度和廣度之間的最佳平衡。第二,本文對于知識深度和廣度的測量是基于特色性的問卷數據,是對被采訪者的主觀評估,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希望在未來研究中可以獲取到更加客觀的數據再次進行驗證,并且,本文對知識深度和廣度進行測量時為了更加準確地測量深度和廣度,將每個變量分成三個方面,每個方面又包含多個小問題,意味著將每一個條目賦予了等權重,這種方法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還有待商榷,期望未來研究能夠給予回答。第三,本文使用的是問卷數據、橫截面數據,由于水平所限,未能找到合適的方法解決內生性問題。另外,調節變量可能不是一個典型的外生變量,很有可能也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希望未來的相關研究能夠更好地解決本文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參考文獻:
[1]白旭云、王硯羽、蘇欣,2019:《研發補貼還是稅收激勵——政府干預對企業創新績效和創新質量的影響》,《科研管理》第6期。[Bai Xuyun,Wang Yanyu and Su Xin,2019,R&D Subsidies or Tax Incentiv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Quality,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6.]
[2]陳強,2014:《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Chen Qiang,2014,Advanced Econometrics and Stata Application,Higher Education Press.]
[3]陳勁,2018:《國家創新藍皮書:中國創新發展報告(2017—20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Chen Jin,2018,National Innovation Blue Book: China'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2018),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4]陳智、吉亞輝,2019:《中國高技術產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期。[Chen Zhi and Ji Yahui,2019,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Based on Chinas Spatial 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2.]
[5]戴勇、朱桂龍,2011:《以吸收能力為調節變量的社會資本與創新績效研究——基于廣東企業的實證分析》,《軟科學》第1期。[Dai Yong and Zhu Guilong,2011,Research on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th Absorptive Capacity as Moderator——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Guangdong Enterprises,Soft Science,1.]
[6]付敬、朱桂龍,2014:《知識源化戰略,吸收能力對企業創新績效產出的影響研究》,《科研管理》第3期。[Fu Jing and Zhu Guilong,2014,Effect of Knowledge Sourcing Strategy,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Output,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3.]
[7]谷磊、呂沖沖、楊建君,2019:《社會資本對西部地區創新產出與創業水平影響的研究》,《管理學刊》第3期。[Gu Lei,Lv Chongchong and Yang Jianjun,2019,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Innovation Output and Entrepreneurship Level in the West China,Journal of Management,3.]
[8]顧海峰、卞雨晨,2020:《內部控制、董事聯結與企業創新——基于中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證據》,《管理學刊》第6期。[Gu Haifeng and Bian Yuchen,2020,Internal Control, Board Interlock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on GEM in China,Journal of Management,6.]
[9]李波、楊先明、楊孟禹,2020:《土地購置行為影響企業創新嗎?——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經濟管理》第5期。[Li Bo,Yang Xianming and Yang Mengyu,2020,Does Land Acquisition Behavior Affect Enterprise Innovation? Eve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5.]
[10]劉景東、黨興華,2013:《不同知識位勢下知識獲取方式與突變創新的關系研究》,《管理評論》第7期。[Liu Jingdong and Dang Xinghua,2013,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Modes and Radical Innovation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Knowledge Potential,Management Review,7.]
[11]劉巖、蔡虹,2011:《企業知識基礎與技術創新績效關系研究——基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的實證分析》,《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第10期。[Liu Yan and Cai Hong,201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Base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 Test in China's Electrical & Electronic Industry,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10.]
[12]盧艷秋、肖艷紅、葉英平,2017:《知識導向IT能力、知識管理戰略匹配與技術創新績效》,《經濟管理》第1期。[Lu Yanqiu,Xiao Yanhong and Ye Yingping,2017,The Effects of Matching Between Knowledge Oriented IT Capabilit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erformance,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1.]
[13]呂越、田琳、呂云龍;2021:《市場分割會抑制企業高質量創新嗎?》,《宏觀質量研究》第1期。[Lv Yue,Tian Lin and Lv Yunlong,2021,Does Market Segmentation Hinder the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1.]
[14]潘清泉、唐劉釗,2015:《技術關聯調節下的企業知識基礎與技術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管理學報》第12期。[Pan Qingquan and Tang Liuzhao,2015,The Impact of Knowledge Bas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12.]
[15]蘇敬勤、林海芬,2011:《管理者社會網絡、知識獲取與管理創新引進水平》,《研究與發展管理》第6期。[Su Jingqin and Lin Haifen,2011,Managers' Social Network, Knowledge Acquirement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roduction Level,R&D Management,6.]
[16]唐青青、謝恩、梁杰,2018:《知識深度、網絡特征與知識創新:基于吸收能力的視角》,《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第1期。[Tang Qingqing,Xie En and Liang Jie,2018,Knowledge Depth,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Perspective,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1.]
[17]田軒、孟清揚,2018:《股權激勵計劃能促進企業創新嗎》,《南開管理評論》第3期。[Tian Xuan and Meng Qingyang,2018,Do Stock Incentive Schemes Spur Corporate Innovation,Nankai Business Review,3.]
[18]王紅麗、彭正龍、谷峰、陸云波,2011:《開放式創新模式下的知識治理績效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第6期。[Wang Hongli,Peng Zhenglong,Gu Feng and Lu Yunbo,2011,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Knowledge Governance within Open Innovation Based on Outside Sources,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6.]
[19]王泓略、曾德明、陳培幀,2020:《企業知識重組對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知識基礎關系特征的調節作用》,《南開管理評論》第1期。[Wang Honglue,Zeng Deming and Chen Peizhen,2020,A Research on Knowledge Recombin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derate Effect of Knowledge Elements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Nankai Business Review,1.]
[20]王靖宇、劉紅霞、劉學濤,2020:《公益捐贈與企業創新質量——基于慈善立法的自然實驗》,《宏觀質量研究》第5期。[Wang Jingyu,Liu Hongxia and Liu Xuetao,2020,Public Don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Quality——A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arity Legislation,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5.]
[21]韋倩、李珂涵,2019:《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創新研究——第一屆中國制度經濟學論壇綜述》,《經濟研究》第2期。[Wei Qian and Li Kehan,2019,The Summary of the 2th China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orum,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
[22]吳堯、沈坤榮,2020:《最優金融結構與企業創新產出質量》,《宏觀質量研究》第2期。[Wu Yao and Shen Kunrong,2020,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of Firm Innovation Output,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2.]
[23]楊震寧、吳劍峰、喬璐,2016:《企業研發伙伴的多樣性、政治嵌入與技術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經濟管理》第1期。[Yang Zhenning,Wu Jianfeng and Qiao Lu,2016,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versity of Corporate R&D Partners,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1.]
[24]楊震寧、趙紅,2020:《中國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制度環境、“競合”關系與創新績效》,《管理世界》第2期。[Yang Zhenning and Zhao Hong,2020,Chinese Enterprises' Open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Management World,2.]
[25]葉建亮、朱希偉、黃先海,2019:《企業創新、組織變革與產業高質量發展——首屆中國產業經濟學者論壇綜述》,《經濟研究》第12期。[Ye Jianliang,Zhu Xiwei and Huang Xianhai,2019,The Summary of the 1st China Forum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Scholars,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2.]
[26]余明桂、范蕊、鐘慧潔,2019:《中國產業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中國工業經濟》,第12期。[Yu Minggui,Fan Rui and Zhong Huijie,2019,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12.]
[27]余傳鵬、林春培、張振剛、葉寶升,2020:《專業化知識搜尋、管理創新與企業績效:認知評價的調節作用》,《管理世界》第1期。[Yu Chuanpeng,Lin Chunpei,Zhang Zhengang and Ye Baosheng,2020,Specialized Knowledge Search,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Appraisal,Management World,1.]
[28]張方華,2005:《知識型企業的社會資本與技術創新績效研究》,《浙江大學》。[Zhang Fanghua,2005,Knowledge-based Firm's Social Capital and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Zhejiang University.]
[29]張古鵬、陳向東、杜華東,2011:《中國區域創新質量不平等研究》,《科學學研究》第11期。[Zhang Gupeng,Chen Xiangdong and Du Huadong,2011,Research on Inequalit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Quality in China,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11.]
[30]張志強、喬怡迪、劉璇,2020:《中關村科技園區創新質量的時空集聚效應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第11期。[Zhang Zhiqiang,Qiao Yidi and Liu Xuan,2020,Study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Quality of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11.]
[31]張志鑫、梁阜,2019:《知識搜索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知識基礎的曲線調節作用》,《中央財經大學學報》第8期。[Zhang Zhixin and Liang Fu,2019,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 Curve Moderating Effect of Knowledge Base,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8.]
[32]趙玉林、劉超、谷軍健,2021:《研發投入結構對高質量創新的影響——兼論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協同效應》,《中國科技論壇》第1期。[Zhao Yulin,Liu Chao and Gu Junjian,2021,The Effect of R&D Investment Structure on High-Quality Innovation ——Also on the Synergy of Promising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1.]
[33]周陽敏、桑乾坤,2020:《國家自創區產業集群協同高質量創新模式與路徑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第2期。[Zhou Yangmin and Sang Qiankun,2020,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Model and Path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2.]
[34]周小虎、馬莉,2008:《企業社會資本、文化取向與離職意愿——基于本土化心理學視角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Zhou Xiaohu and Ma Li,2008,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genized Psychology,Management World,6.]
[35]鄒波、郭峰、熊新,2015:《企業廣度與深度吸收能力的形成機理與效用——基于264家企業數據的實證研究》,《科學學研究》第3期。[Zou Bo,Guo Feng and Xiong Xin,2015,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Firms' Breadth and Depth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64 Firms' Data,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3.]
[36]諸竹君、黃先海、王毅,2020:《外資進入與中國式創新雙低困境破解》,《經濟研究》第5期。[Zhu Zhujun,Huang Xianhai and Wang Yi,2020,FDI Entry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Double Low Dilemma of Chinese Innovation,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5.]
[37]Aggarwal,V. A.,2020,Resource Congestion in Alliance Networks: How a Firm's Partners' Partners Influence the Benefits of Collaborat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41(3),627-655.
[38]Ahuja,G. and R. Katila,2001,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Firms: A Longitudinal Stud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2(3),197-220.
[39]Arora,A. and A. Gambardella,2010,Ideas for Rent: An Overview of Markets for Technology,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3),775~803.
[40]Burt,R. S.,1992,Structural Hole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1]Cao Q.,E. Gedajlovic and H. Zhang,2009,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 Contingencies, and Synergistic Effects,Organization Science,20(4),781-796.
[42]Chesbrough, H. W.,2006,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Manag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127(3),34-41.
[43]Cohen,W. M. and D. A. Levinthal,1990,Absorptive Capabi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5(1),128–152.
[44]Cristina,Q. and A. B. Carlos,2008,Innovative Competenc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Research Policy,37(3),492-507.
[45]Ferrary,M.,2011,Specialized Organizations and Ambidextrous Clusters in the Open Innovation Paradigm,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9(3),181-192.
[46]Fleming,L. and O. Sorenson,2004,Science as a Map in Technological Search,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5(8/9),909-928.
[47]Grant and M. Robert,1996,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17(S2),109-122.
[48]Guan,J. and N. Liu,2016,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in Knowledge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 A Patent Analy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of Nano-energy,Research Policy,45(1),97-112.
[49]Haner,U. E,2002,Innovation Quality——A Conceptual Framewor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80(1),31-37.
[50]Harman,H. H.,1967,Modern Factor Analysi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1]He,Z. L. and P. K. Wong,2004,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Organization science,15(4),481-494.
[52]Henderson,R. M. and K. B. Clark,1990,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5(1),9-30.
[53]Henderson,R. and I. Cockburn,1994,Measuring Competence? Exploring Firm Effects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5(S1),63-84.
[54]Hill,C.W. and F. T. Rothaermel,2003,The Performance of Incumbent Firms in the Face of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8(2),257-274.
[55]Jin,X.,J. Wang and S. Chen,2015,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nowledge Base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the Organizational Slack Regulating,Management Decision,53(10),2202-2225.
[56]Kauffman,S.,J. Lobo and W. G. Macready,2000,Optimal Search on a Technology Landscap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43(2),141-166.
[57]Katila,R.G. and Ahuja,2002,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5(6),1183-1194.
[58]Kogut,B. and U. Zander,1992,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 Science,3(3),383-397.
[59]Laursen,K. and A. Salter,2006,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7(2),131-150.
[60]Levinthal,D. and J. March,1993,The Myopia of Learning,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4(2),95-112.
[61]Lichtenthaler,U.,2011,Open Innovation: Past Research, Current 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5(1),75~93.
[62]Luca,L. M. D. and K. Atuahene-Gima,2007,Market Knowledge Dimensions and Cross-Functional Collaboration: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Routes to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Journal of Marketing,71(1),95-112.
[63]Luzon,M. D. M. and J. V. Pasola,2011,Ambidexterity and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Management Decision,49(6),927-947.
[64]McCarthy,I. P. and B. R. Gordon,2011,Achieving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in R&D Organizations: A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Approach,R&D Management,41(3),240-258.
[65]McGrath,R. G. and A. Nerkar,Real Options Reasoning and a New Look at the R&D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Pharmaceutical Firm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5(1),1-21.
[66]McFadyen,M. A. and A. C. Albert,2004,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Creation: Diminishing Returns of the Number and Strength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7(5),735-746.
[67]Miller,D. J.,M. J. Fern and L. B. Cardinal,2007,The Use of Knowledg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in Diversified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2),307-326.
[68]Moore,E. C.,1958,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Philosophy of Science,107(4),617-618.
[69]Narula,R.,2001,R&D Collaboration by SM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Face of Globalisation,Research Memorandum,24(2),153-161.
[70]Peteraf,M. A.,1993,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Based View,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4(3),179-191.
[71]Podsakoff,P. M.,2003,Mac 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8(5),879.
[72]Prahalad,C. K. and G. Hamel,1994,Strategy as a Field of Study: Why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5(S2),5-16.
[73]Reagans,R. and B. Mcevily,2003,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48(2),240-267.
[74]Rockwell,R. C.,1975,Assessment of Multicollinearity: The Haitovsky Test of the Determinant,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3(3),308-320.
[75]Russo,A. and C. Vurro,2010,Cross-boundary Ambidexterity: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Fuel Cell Industry,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7(1),30-45.
[76]Salavisa,I.,C. Sousa and M. Fontes,2012,Topologie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the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Complementary Assets through Formal and Informal Ties,Technovation,32(6),380-399.
[77]Tsai,W. and S. Ghoshal,1998,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1(4),464-476.
[78]Wellman,B. and S. D. Berkowitz,1988,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9]West,J. and M. Iansiti,2003,Experience,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The Evolution of R&D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Research Policy,32(5),809-825.
[80]Wu,J. F. and M. T. Shanley,2009,Knowledge Stock,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on the United States Electromedical Device Industry,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62(4),474-483.
[81]Xu,S.,2015,Balancing the Two Knowledge Dimensions in Innovation Effort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among Pharmaceutical Firms,Journal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32(4),610-621.
[82]Yli-Renko,H.,E. Autio and H. J. Sapienza,2001,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Based Firm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2(6/7),587-613.
[83]Zhang,J. and V. Fuller,2007,Technological Knowledge Base, R&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Alliance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Research policy,36(4),515-528.
[84]Zhou,K. Z. and C. B. Li,2012,How Knowledge Affects Rad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 Base, Market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ternal Knowledge Sharing,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33(9),1090-1102.
Knowledge Depth and Breadth, Social Connections and High Quality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Yang Zhenning1, Hou Yifan1 and Geng Huifang2
(1.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2017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y survey database, patent database and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knowledge depth and breadth on high-quality innovation of companies, and uses social connection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study its mechanis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exis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epth and high-quality corporate innovation; (2)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breadth and high-quality corporate innovation;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depth and knowledge breadt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high-quality corporate innovation; (4) Institutional connections will negatively regulate the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epth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market connections will negatively regulate the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epth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5) Social connections of the companies will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breadth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knowledge-based theor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enrich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 practice.
Key Words:Knowledge Depth; Knowledge Breadth; Social Connection; Corporate Innovation
責任編輯 郝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