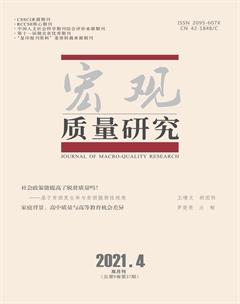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的總體思路與主要任務研究
盛朝迅 徐建偉 任繼球



摘 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是破解產業鏈安全瓶頸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動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建設制造強國的重要抓手。建議按照“質量為先、點鏈協同、企業主體、有限目標、分類施策”的方針,加強產業鏈鏈主企業和專精特新隱形冠軍企業培育,強化“要素—平臺—制度”三維支撐,探索建立新型技術攻關突破機制、創新產業政策支持機制、優化產業鏈上下游和跨領域協作機制、構建產業基礎再造國企支撐機制、完善國內國際協同創新機制,構建有利于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的創新服務體系和制度環境,加快推動重大基礎裝備、關鍵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高端工業軟件等產業基礎技術的突破和升級,努力構建和再造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產業基礎體系。
關鍵詞:產業基礎; 新型舉國體制; 產業鏈現代化; 新發展格局; 體制機制保障
一、引言
產業基礎是產業發展的基石、制造強國的根基和實現產業鏈現代化的前提,決定著產業發展的自主可控水平、長遠競爭能力和整體發展高度。長期以來,受產業發展模式、路徑、支持政策、要素條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約,我國產業發展主要采取加工組裝和終端品制造模式切入全球產業鏈,促進了產業規模和制造水平的快速提升,成為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202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連續11年位居全球首位,接近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總和,生產了全球超過50%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甲醇、燒堿和平板玻璃,60%的家電,70%的化纖、手機和計算機,85%的稀土冶煉產品,有20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然而,相較于我國體量龐大的終端產品制造能力,我國產業基礎研發制造能力相對薄弱,總體自給率只有30%-40%左右,在高端基礎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先進生產設備、關鍵基礎材料等方面的對外依存度甚至高達90%-100%,幾乎完全依賴從美歐日進口,“卡脖子”問題日益突出。
毫無疑問,這種模式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但也造成兩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難以滿足構建新發展格局和現代化發展的新要求。一是產業升級滯緩。產業發展如同一條河流,上游的基礎能力決定著下游產業發展高度和產業升級的能力。無數產業發展實踐表明,產業升級的過程是一個從加工組裝、中低端產品制造到高端研發、關鍵零部件制造躍遷的過程,也是從產業鏈中下游向上游躍升的過程。我國制造業在產業鏈上中下游布局的不均衡、基礎能力薄弱的現狀,導致了在全球產業鏈中分工地位低下的困境和產業鏈升級的滯緩。唯有不斷強化產業基礎領域攻關突破,樹立產業基礎領域競爭優勢,才能打破這種“分工鎖定”,實現產業升級。二是關鍵環節受制于人。在全球化分工邏輯下,各國依據比較優勢進行分工,產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得到緩解,正常的供應能夠得到基本保證。但在貿易摩擦和大國博弈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在基礎領域和核心技術上的優勢成為經濟制裁的工具和“武器”,頻頻采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斷供”等非經濟手段,使得我國高技術領域產業安全矛盾凸顯。
為此,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做好頂層設計,明確工程重點,分類組織實施,增強自主能力。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進一步明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這可以說抓住了推動產業升級和科技自立自強的牛鼻子,對于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設制造強國、破解產業鏈安全瓶頸、構建新發展格局、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等都具有非常重要而又深遠的現實意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舉措。那么,到底如何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明確具體路徑和實施方案,科學設定階段性的戰略目標,謀劃具體舉措,是全社會共同關心的重大議題。本文擬從概念分析入手,從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相結合的視角,提出未來一個時期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的總體思路、主要路徑、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建議。
二、產業基礎的基本概念與主要特征
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首先要明確“工程”的對象,即什么是產業基礎,摸清楚產業基礎的特征和發展規律,才能夠做到有的放矢。
(一)概念內涵
關于產業基礎的內涵,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工業四基拓展說”,認為產業基礎的概念來源于“工業四基”,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條件變化,其內涵和外延需要進一步拓展和補充,既包括傳統“工業四基”,也包括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基礎軟件(許召元,2019),還包括信息化條件下的自動控制和感知硬件、工業核心軟件、工業互聯網、工業云和智能服務平臺等“一硬、一軟、一網、一臺”以及芯片、工業軟件、操作系統、數據庫、人工智能、算法等產品或技術,甚至可以拓展至產業技術公共服務平臺、檢驗檢測平臺、基礎設施、質量標準、能源動力(羅仲偉、孟艷華,2020)等基礎支撐。
第二種觀點是“產業支撐能力說”,認為產業基礎是保障和推動產業發展的能力,這一觀點不再強調產業基礎與“工業四基”的直接對應關系,而是從更為宏觀和抽象的視角將產業基礎理解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支撐,這些基本支撐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可以具體到產業的基礎性要素,也可以是提供基本生產資料的基礎產業部門(羅仲偉,2020),甚至包括科技創新基礎能力、支撐保障基礎能力、產業競爭基礎能力、可持續發展基礎能力、產業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等(干勇,2020),以及基礎產品、基礎技術、創新體系、基礎文化、基礎教育和人才、基本政策等較為寬泛的范疇(中國工程院,2019)。
我們認為,以上兩類觀點從不同角度對產業基礎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分析,是研究不斷深入和深化的具體表現。“工業四基拓展說”側重于從研究對象的角度深化和拓展產業基礎的范圍和邊界,“產業支撐能力說”側重于從產業功能角度論述提升產業基礎能力所需要的諸多要素和條件。從實際經驗看,聚集某一領域某一環節推動基礎領域攻堅突破,往往是低效的,甚至是無效的,必須從系統、聯動、協同的角度,統籌謀劃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為此,必須結合新時代、新形勢對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的要求,重新提煉和概括“產業基礎”的概念和內涵,增強制造業底層整合能力。
對此,我們界定,“產業基礎”是產業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支撐,是為產業發展提供基礎技術、材料和零部件支撐,能夠決定生產制造方式的基礎單元,以及為其形成提供支撐的基礎要素、公共服務體系和平臺、制度環境的集合。產業基礎包括核心層和支撐層兩個層面,核心層是指支撐產業發展的基礎性環節和底層技術,包括基礎裝備、基礎零部件、基礎工業軟件、關鍵基礎材料等四個方面,可以稱之為“產業四基”;支撐層是指支撐核心層技術突破的條件和保障,主要包括重大科學裝置和創新平臺、底層基礎要素、質量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等(見表1)。其中,核心層是從產業鏈角度定義的,主要是指能夠劃分到具體產業門類的基礎產業,是顯性的、被較多關注的產業基礎領域;支撐層是從支撐條件角度定義的,主要是指支撐核心層發展的各種要素、公共服務體系和制度環境,是處于產業發展底層、較少被政策和公眾關注的基礎領域。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構成產業基礎的全部內容。由此可見,產業基礎是一個內涵、外延十分豐富的概念,既包括支撐產業發展的基礎產業和底層技術,也包括與之相配套的基礎要素、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平臺、配套政策和制度環境,是基礎產業、基礎要素、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體系和制度環境的有機統一。
(二)主要特征
產業基礎特別是核心層的“產業四基”,作為支撐產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礎部門,往往具有底層性、戰略性、寡占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等特征。
一是底層性。正如地基處于建筑物的底層不容易為外界所看見一樣,產業基礎一般處于產業鏈的上游、前端或中間投入品的生產環節,屬于產業發展的底層架構,并不直接與位于終端的消費市場和消費者發生經濟技術聯系,因此,市場顯示度較低。比如,X86/ARM架構是全球計算機芯片行業的基礎,Linux開源體系是很多軟件服務的基礎,TCP/IP協議是萬維互聯的基礎,RSA算法是金融加密系統的基石。這些技術都非常重要,但往往不為大眾所熟知。
二是戰略性。主要指產業基礎部門在產業發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決定產業競爭力和控制力的關鍵所在。由于產業基礎部門掌控著整個行業的關鍵知識和技能,具有無法替代的競爭優勢地位,是整個產業命運的真正決定者和行業“大廈”的根基。本部門的技術改進或停滯,會極其顯著地影響下游用戶的產品質量和產出狀態。比如半導體產業的高端芯片制造、極紫外線(EUV)光刻機生產、光刻膠等關鍵材料生產環節,雖然產業規模體量不大,但卻掌握著關鍵核心技術,把控著行業發展的“命門”,是整個產業鏈最關鍵的環節。一旦發達國家實施“斷供”,我國數萬億元的產業發展都將受到極大的沖擊。離開了產業基礎發展產業,就好比在沙灘上建高樓,既不安全,也不牢靠。
三是寡占性。由于產業基礎領域專業性比較強,大多數從事產業基礎領域生產的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比較單一,供應鏈關系相對穩定、固化,具有分工鎖定、行業進入門檻高、技術突破難等特征。因此,往往會出現“贏者通吃”的局面,即該產品和技術的供應僅由少數幾家企業掌握,形成完全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先發企業在某一領域一旦形成了先發優勢,后發追趕者追趕超越的難度將異常大。在全球市場也是如此,德國很多隱形冠軍企業全球市場占有率都超過50%,在世界范圍內做到極致,受到業界的廣泛認可。
四是系統性。產業基礎包括關鍵核心技術、基礎裝備和核心零部件、基礎材料、基礎工業軟件、質量基礎設施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創新服務體系、要素支撐和制度環境等,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既關乎基礎科學,也涉及推廣應用。這些產業基礎的具體內容相互支撐,缺一不可,只要某一個環節出現瓶頸和薄弱項,就會遭遇“卡脖子”的困境,整體產業基礎實力的突破就會變得很難,產業競爭力提升也會受到限制。因此,提升產業基礎能力是一項系統性工程,絕非某一環節、某一領域、某一技術突破所能完成,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要有頂層設計、系統謀劃和統籌推進。
五是動態性。指產業基礎的范圍會根據技術條件或時代背景的變化而動態調整,不同時代產業基礎的內涵、外延也不盡相同。在農業經濟時代,基礎產業部門是農具生產和種子培育,基礎要素是土地和農民,基礎設施也是圍繞農業生產的農田水利和倉儲設施等;在工業經濟時代,核心基礎零部件和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工業四基”取代農具生產和種子培育成為基礎產業部門,相應地,資本、技術、企業家和工人在要素中的重要性上升,基礎設施也隨之改變;在信息經濟時代,軟件和數據的重要性上升,基礎裝備、核心零部件、基礎工業軟件、關鍵基礎材料等“產業四基”取代“工業四基”成為最重要的基礎產業部門,其要素條件和基礎設施也相應調整(見表2)。未來,產業基礎的內涵、外延還會調整。
三、當前我國提升產業基礎能力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制約
近年來,隨著全社會對產業基礎的重視程度增加和國家工業強基工程的持續實施,我國在部分基礎材料、部件、裝備和技術領域開始取得技術突破、產品質量持續提升、市場化推廣應用不斷加快,部分“卡脖子”問題有所緩解。但是,總體而言,我國在基礎領域的突破仍集中在點上,關鍵零部件、元器件和關鍵材料自給率僅有30~40%,基礎不牢、底子不穩、“卡脖子”的問題仍然非常突出,總體上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一)核心領域“卡脖子”
1.部分重大基礎裝備質量性能差距明顯
裝備產業是國際競爭最激烈的領域,也是發達國家最具競爭優勢、對我國技術封鎖最嚴和市場打壓最狠的領域。如,德國裝備制造商在32個細分裝備領域的16個領域居于世界第一,掌握著這些領域的主導權。我國在部分重大基礎裝備領域仍然存在突出短板,產品性能、環境適應性、使用壽命、質量可靠性等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部分領域甚至存在技術和供給空白。根據中國工程院的研究,我國在高檔數控機床、機器人、集成電路及專用設備、飛機和航空發動機、高性能醫療器械等15類產業上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大或巨大中國工程院:《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制造強國戰略研究(三期)綜合報告》,2019年1月。]。如高端數控機床,85%的國內市場被日本的發那科、牧野和馬扎克、德國的DMG和哈默、美國的哈斯等跨國企業控制,95%的數控系統依賴西門子等跨國企業。關鍵集成電路裝備具有精度靈敏度高、技術難度大、成本投入高、市場格局固化等特點,國內企業在國際上幾乎沒有競爭優勢,前道光刻機等嚴重依賴進口傅翠曉:《國內外集成電路裝備現狀分析》,《新材料產業》2019年第10期。]。國產機器人在快速響應性、功率密度、穩定性、工作精度、發熱噪音等指標上差距較大,在過載等較為復雜工況環境下性能下降明顯。納博特斯克RV減速器產品的平均壽命一般可達10000小時以上,在設定的工作壽命時間內可嚴格保持精度和剛度不下降,而國產產品壽命均低于6000小時邱海霞等:《我國激光技術醫療應用和產業發展戰略研究》,《中國工程科學》2020年第3期。]。
2.關鍵核心基礎零部件對外依賴嚴重
在產品內分工日益深化的情況下,“卡脖子”技術往往來自于關鍵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礎零部件和元器件是發達國家維護其全球競爭力和分工地位的關鍵所在,始終掌握著大量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把持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和控制權。基礎零部件“卡脖子”是我國產業發展的“隱痛”。如,高端基礎芯片領域,國內商用化研發剛剛起步,高端存儲器主控芯片訂單集中在美國的Marvell和Microchip,消費類低端主控芯片主要由臺灣慧榮(SMI)和群聯(Phison)瓜分。模擬芯片領域,國內模擬廠商的自給率不到20%,在高端領域低于5%。工程機械領域,大型盾構機刀盤主軸承合金元素、雜質含量控制、鍛件滾子熱處理技術,超大直徑密封結構設計、制造及表面處理技術等尚未突破。機器人領域,我國減速器70%以上的市場份額由外資品牌占據,哈默納科和納博特斯克占有絕對領先地位,智能機器人發展所需的視覺、力覺、激光、聲吶等傳感器也主要依賴進口余江:《鑄造強國重器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規律探索與體系構建》,《中國科學院院刊》2019年第3期。]。這些“卡脖子”短板很多是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老大難”問題,既關系到戰略性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也制約著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提升和現代產業體系建設黃群慧:《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人民日報》2019年12月31日。]。
3.工業軟件和控制系統等“軟約束”突出
我國在基礎領域不僅硬件短板突出,軟件差距更加明顯,可謂“體不強、心不健”,以工業軟件、控制系統等最為突出。工業軟件行業壁壘高、項目經驗壁壘高、品牌壁壘高“三高”并存。目前,國內工業軟件市場被國外企業壟斷,國產工業軟件發展嚴重滯后,絕大多數無法與國外工業軟件抗衡,只是在生產管理類軟件的低端市場和生產控制類軟件的細分行業偶爾占優勢,難以突破歐美軟件企業構建起來的生態圈,進入大中型企業核心應用領域的難度很大。目前,關鍵核心工業輔助設計、工藝流程控制、模擬測試等軟件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國外企業軟件,工業操作系統、工業軟件開發平臺等重要國產工業基礎軟件更是全產業鏈缺失,運行于國產工業操作系統的國產工業控制應用軟件幾乎是空白。控制系統也是如此,我國大部分控制系統在高可靠性、高穩定性、高環境適應性,以及數字化、智能化、集成化等方面競爭力不足,相比國外先進產品存在較大差距。目前,我國重大工程的關鍵裝備、核心裝備、主體裝備絕大部分被國外控制系統所壟斷,尤其是用于廣大離散型工廠自動化的PLC系統,西門子、三菱、歐姆龍等跨國企業占據領先地位。
4.關鍵基礎材料受制于人、風險較大
材料從研發到成熟應用往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周期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幾十年。盡管我國原材料工業對下游需求滿足程度不斷提高,但在一些關鍵領域依然存在“無材可用、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的現象,重大裝備制造、重大工程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及國防軍工等領域所需的部分材料產品仍嚴重依賴進口。工信部的調研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的關鍵基礎材料32%仍為空白,52%依賴進口。在石化行業中,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等領域的高端專用材料、部分關鍵單體以及高規格電子化學品進口依存度偏高。在鋼鐵行業中,我國仍有鋼鐵短板材料70項,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先進軌道交通、海洋工程及高技術船舶、電力裝備、汽車、能源石化、高檔機床、信息技術等8個用鋼領域,高端軸承鋼、高性能模具鋼、超高強度不銹鋼、航空發動機及燃氣輪機用高溫合金等“卡脖子”問題突出。在有色金屬領域,航空用鋁合金板帶和型材、航空用鈦合金型材、航空緊固件用鈦合金絲材、高純難熔金屬單晶材料、數控硬質合金和金屬陶瓷刀具等存在明顯短板,精深加工能力尤其不足。在復雜的國際貿易摩擦形勢下,如果高端原材料產品和技術裝備進口受阻,將給上下游產業和重大工程戰略以及國防經濟安全造成連鎖反應。
(二)支撐領域有短板
1.重大科技設施和創新平臺不完善
我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與先進科技強國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需求也還有較大距離,一些領域或重要方向的設施布局仍為空白,設施體系的完整性、總體規模、技術水平等都還有較大提升空間中國科學院:《科技強國建設之路:中國與世界》,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2月。]。我國基礎共性技術創新體系不健全,原來一些面向行業服務的研究院所改制后,共性技術研發和服務平臺缺失,部分行業甚至空白。雖然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平臺建設進入提速期,但是平臺建設的參與者、主導權、運營模式、激勵機制等一系列問題仍有待探索突破。在研發組織上,跨學科、大協作、高強度、開放式的協同創新基礎平臺尤其缺乏。盡管國內成立了眾多技術創新戰略聯盟,致力于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并向全行業擴散,但是受制于研發投入、知識產權、利益分配等問題,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2.產業基礎要素存在嚴重供給瓶頸
產業基礎能力提升首先面臨人才制約,即創新型、技能型、復合型人才緊缺。一是基礎領域的領軍型人才匱乏,全球頂尖的基礎研究團隊、戰略性領域的“帥才”“將才”數量偏少。目前,國內缺乏能夠心無旁鶩、長期穩定深耕基礎理論的研究人才隊伍,難以產生重大原創性的理論和思想成果。二是高層次高素質的工業技術人才結構性供給不足問題突出于清笈:《大力推進高素質人才隊伍建設 支撐機械工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教育部網站2017年2月14日。]。基礎領域的知識復雜性、嵌入性高,涉及大量緘默知識、專利和know-how(技術訣竅)。我國基礎人才培養與實際需求脫節,普通高校培養本科生的專業目錄按寬口徑通才教育模式設置,特色工科專業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四基”專業技術人才的供給缺口。以軸承專業為例,一個綜合性、寬口徑的機械工程專業的本科生軸承課時只有數十個小時,人才培養“不精不深”、教育實踐環節薄弱劉云:《工業“四基”人才長期匱乏:反思工科教育的不精不深》,《光明日報》2014年9月2日。]。其次是產業基礎數據積累不足。工業軟件和控制系統長期依賴于國外產品,導致國內海量的關鍵工藝流程和工業技術數據信息未能得到有效整理、儲存,面臨著毀損、流失乃至被竊取的風險。此外,產業基礎領域受限于資本回收周期長、風險大等特點,資本關注度低,金融機構往往繞道而走、避而不投。
3.質量基礎設施服務支撐能力不足
由于質量技術基礎的基礎性、技術性、專業性較強,社會對其戰略性作用認知度不高。據研究,中國、德國、法國、英國和奧地利標準化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達7.88%、27%、23%、12%和25%。我國國家質量技術基礎的概念提出相對較晚,建設仍顯薄弱,對經濟增長貢獻偏低,還不能完全滿足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計量方面,一些領域缺乏計量基準、計量標準以及相關的測量方法和技術。標準方面,標準體系不夠合理,標準交叉重復的現象仍然存在,實質性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的能力和水平不高,新興產業領域的技術規則制定權幾乎由西方國家掌控。認證認可方面,目前還沒有一項國際通行的認證認可標準或認證認可制度是由我國率先提出的,在國際新認證制度建設和引領方面能力不足。檢驗檢測方面,我國現有高性能檢測系統和儀器絕大多數都是進口品牌,檢驗檢測機構較為分散,基礎研究滯后,技術儲備能力較弱。
(三)體制機制制約較為突出
1.基礎領域長效支持政策不足
與長期過度重視和依賴進口形成對比,我國對基礎領域重視不夠、投入不足,基礎能力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被忽視、讓之于人的領域。在產業政策上,“重生產輕研發”“重主機輕部件”“重引進輕自主”導向明顯,對市場顯示度高的整機及成套設備高度重視、大力支持,對顯示度低的核心技術和零部件重視不夠甚至忽略,如技術引進政策以引進成套設備生產設備為主,大量進口基礎材料和核心基礎零部件,對基礎領域的技術引進非常不足。在科技戰略上,傾向于投資試驗發展和應用研究,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割裂的問題比較突出。目前,我國鋼鐵行業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投入比例大致為2∶10∶88,相比歐美日等國家存在明顯差距。在企業組織上,國際上從事產業基礎能力建設的主要是中小企業,而我國中小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獲得的政策支持力度較小,在創新投入、融資貸款、項目招標等方面障礙重重、困難多多,其發展生態難言樂觀。
2.關鍵共性技術供給機制有待完善
產業關鍵共性技術具有基礎性、關聯性、系統性、開放性等特點,屬于競爭前技術,能夠在一個或多個行業中廣泛應用并產生深度影響。目前,基礎共性技術研究被削弱甚至缺位對于整體創新造成嚴重影響,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研究→產品開發→產業化構成的技術創新體系存在重大斷鏈環節。國際上,美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聚焦基礎共性技術開發,建立了數以百計的工業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學技術中心,最有名的半導體制造技術聯盟(SEMATECH)對促進美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功不可沒。我國原來一些面向行業服務的研究院所改制后,其“營利性”與產業共性技術研究的“公益性”存在矛盾沖突,逐漸放棄了對共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的跟蹤研究,高水平的、適于產業共性技術的研究越來越難以組織。一些共性關鍵技術研發項目力量分散,融通合力難以形成,許多研發活動往往因項目完成而終止,研究團隊因項目完成而解散,沒有形成持續穩定的技術創新攻關機制,對產業共性技術研發能力積累和創新能力提升造成一定影響。
3.部門領域融合發展機制缺失
基礎裝備及部件、基礎工藝、基礎原材料乃至基礎質量設施是互為基礎的。基礎領域突破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領域鏈條化的創新主體協同才能得以實現。在技術積累薄弱、歷史欠賬較多的背景下,通常難以單點攻破。我國基礎領域發展不協調,整機、系統、成套設備與工業基礎發展相互脫節、嚴重割裂,不同行業、各個主體間缺乏供需互動、創新協同和資源整合,導致產業鏈上下游被嚴重分割。比如,軸承、緊固件、彈簧、模具等基礎零部件的質量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與所使用的材料和制造工藝密切相關,因此,很難拋開材料和工藝問題成功實現零部件質量的實質性突破喬標:《提升工業基礎能力的五大難題及對策建議》,《賽迪智庫專報》2017年第64期。]。再如,行業交叉領域的技術研發短板明顯,甚至存在空白。由于機械和電子信息產業融合發展不夠,機電一體化貌合神離、存在諸多制約,且上述問題不同程度存在于數控系統、汽車電子等諸多領域。另外,一些企業沿襲“大而全、小而全”的發展路徑,缺乏有效分工基礎上的高效合作,也對融合發展造成制約。
4.產學研協同發展機制不暢
基礎領域的企業和科研機構缺乏產學研深度聯動,創新成果轉化率低,科技產業“兩張皮”現象突出。一方面,企業研發機構覆蓋率低,對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方向選擇、投入支持不夠,沒有能力實現核心零部件和關鍵基礎材料突破。另一方面,科研機構考核機制嚴重偏離市場需求,既存在關鍵核心技術攻堅組織方式不合理的問題,也存在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與單位短期利益平衡的問題,無法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產學研脫節問題比較嚴重余江,陳鳳等:《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規律探索與體系構建》,《中國科學院院刊》2019年第3期。]。此外,國內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存在過度對標甚至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如近年來廣為詬病的“SCI指揮棒”問題,以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攻關卻嚴重不足,導致許多科技創新成果“水土不服”。現實中還存在產學研“虛假合作”“表象合作”的情況,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對本職、主業不夠專注,很多科研項目都提出了技術研發突破、成果轉移轉化、產業化能力建設等多元目標和要求,過度分散的目標設置導致在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上的投入不足,很多專家學者在產業化領域的探索也很低效甚至無效。
5.基礎產品推廣應用體制尚不完善
基礎領域的技術和產品精度、穩定性、可靠性等要求高,需要在應用中不斷調整、擴充、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基礎產品,無不是通過不斷試錯來打磨升級技術,經過數十年“用”中沉淀后,獲得行業認可。國外基礎產品供應商在國內市場占有率高、競爭力強大,導致國內基礎領域的技術和產品突破沒有足夠的市場空間來推廣應用,國內企業產品性能提升和迭代升級的機會嚴重缺失。由于核心技術和產品商用生態遲遲未能建立,國內一些基礎產品即使在技術上實現了突破,質量性能和產品壽命等方面符合使用要求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一些部門采購或企業招標過程中仍然存在“國民歧視”現象,下游用戶會以各種借口拒絕使用或人為設置障礙抬高市場門檻,常常以沒有業績為由或通過直接提高技術指標要求等方式剝奪國產基礎產品的投標資格。此外,國外一些客戶由于慣性路徑依賴等原因,也會對生產制造商提出采購國外基礎產品的要求,不愿意承擔使用國產基礎產品帶來的風險。
四、我國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的總體思路與主要路徑
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是“十四五”及未來一個時期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和制造強國建設的基礎性、全局性工程,是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破解產業鏈安全瓶頸約束,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高點的務實舉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長遠戰略性工程,必須高度重視、系統設計、統籌謀劃、切實加以推動。
(一)總體思路
“十四五”及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的基本思路是: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質量為先、點鏈協同、企業主體、有限目標、分類施策”的方針,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提升產業基礎能力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為目標,加快培育產業鏈鏈主企業和專精特新隱形冠軍兩大主體,強化“要素—平臺—制度”三維支撐,構建協同發展的政策體系,加快突破“卡脖子”瓶頸約束,創造更多的“從0到1”原創技術和產品,努力實現能力再造、體系再造和制度再造,積極構建和再造具有世界先進水平、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產業鏈現代化和新發展格局的產業基礎體系。要聚焦并明確工程重點,調動部門、企業、行業協會等各方力量,使產業基礎薄弱問題力爭3年至5年得到初步緩解,5年至10年得到明顯解決,并在若干領域形成備胎和反制“卡脖子”約束的非對稱制衡能力。
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籌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與產業鏈現代化。產業基礎和產業鏈是相互關聯、相互支撐的重要概念,產業基礎是產業發展和制造強國建設的根基,也是提升產業鏈水平的前提。產業鏈現代化為產業基礎能力提升提供豐富的應用需求,產業基礎高級化則為產業鏈現代化提供必要的技術保障,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必須系統謀劃,統籌推進。因此,推動產業基礎再造不能僅僅考慮產業基礎技術的攻關突破,還需要推動配套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強化企業主體培育,夯實創新領軍人才、工匠人才和企業家等要素支撐,促進產業鏈的協作聯動,推進政策環境的改革創新等,是一項非常大的系統工程。要大力促進產業基礎能力“點式突破”與全產業鏈“鏈式創新”相結合,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基礎上,著力推動產業鏈上下游產品設計、材料開發、工藝開發、裝備制造、示范應用推廣等企業和機構協同聯動,構建國產首臺(套)、首批次產品大規模市場應用的生態系統,解決國產化技術和產品不愿用、不敢用的難題。
二是堅持企業主體與政府引導相結合。在“市場失靈”和面臨發達國家掣肘的“卡脖子”領域,僅僅依靠市場創新和固有的資源稟賦,企業自主創新很難取得成功,政府必須要予以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取代企業成為產業基礎技術攻關的主體。由于新興基礎領域技術迭代快、創新活躍,政府選方向往往都不準。因此,要發揮好企業和企業家作用,讓企業成為產業基礎再造和資源要素集聚的主體,依靠市場機制來識別產業基礎再造中的機會,發現和抓住真正的機遇。大力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有效發揮國有企業在攻克“卡脖子”問題和補短板中的中堅作用,更好地發揮中小企業作用,引導民營企業突出主業,專注細分市場,掌握獨門絕技。政府主要聚焦單純依靠市場力量無法解決的難題,更多在暢通信息、優化環境和創造條件上下功夫,進一步深化改革,優化基礎能力提升的政策體系,完善支撐產業基礎發展的要素市場和平臺設施,強化有效的正向激勵,形成有利于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的產業生態,使廣大微觀主體進一步釋放活力,提升復雜競爭環境下的適應能力和發展能力。
三是注重有限目標、分類施策。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不是基礎技術全面開花,而是要根據產業基礎技術的重要性、影響的經濟規模和“卡脖子”的程度等分類施策。第一類是影響的經濟規模大、技術攻關難度也大的“卡脖子”技術,比如芯片、核心傳感器等,是未來數字經濟、智能經濟時代制高點競爭的關鍵和基石,影響的經濟規模超過數十萬億元甚至上百萬億元級,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亟需解決的關鍵核心技術,必須采取新型舉國體制集中力量予以攻克。第二類是影響的經濟規模較大,但攻克的難度并不大,即所謂的“崴腳脖子”技術,由于市場空間較大,企業從事此類技術攻關仍然有利可圖,因此,主要交給相關市場主體去攻關,政府采取適當的引導和支持即可。這類技術一般國內已經有一定基礎和比較優勢,但可靠性和穩定性比較差,需要強化政策配套,進一步夯實產業基礎,為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和產業鏈升級提供支撐。第三類是影響的經濟規模較小,但技術攻關難度較大的“卡脖子”技術,這類技術研發往往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發達國家業已構建了很強的專利池和產業發展“護城河”,想要追趕突破可能性微乎其微,重點是實施“備胎”打造計劃,通過多元化采購或自研的方式打造備胎,不追求產品和性能的絕對領先,只是作為戰略儲備。比如部分關鍵零部件技術攻克難度巨大,除美國以外還有第二供應來源,應該積極尋求與第二技術來源的技術合作。第四類是市場規模較為小眾、攻克難度也比較小的“卡脖子”技術,這類技術一般不會成為發達國家遏制中國的“標的物”,即使采取“斷供”措施,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影響也相對可控,不宜作為政策支持的重點。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的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應該是面向未來的新時代戰略性工程,其主要目標在短期內應聚焦“補短板”,但不應僅僅局限于“補短板”。因為,產業基礎的短板光靠補是補不完的,傾注過多資源“補短板”的機會成本比較高,發達國家有可能在“補短板”的時候產生技術進步而再次領先,又會產生新的短板,總是被動防守就永遠無法領先。一代科技革命,一代產業基礎。“十四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由孕育興起向突破發展演化升級的關鍵過渡期。全球范圍內5G、人工智能、物聯網、生命科學、量子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術快速興起,重大技術創新及其應用醞釀爆發,將會引發產業體系深刻變革。我國能否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脫穎而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是關鍵。因此,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不能局限于“補”的思路,必須樹立“創”的思維,即努力在和發達國家處于同發水平,并事關國家安全的領域和經濟社會發展亟需突破的重點領域打造自己的殺手锏,形成局部領域領先的優勢,獲取和發達國家談判的砝碼和反制“卡脖子”約束的非對稱制衡能力,努力“鍛造長板”,在換道超車和搶占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前沿中形成自己獨特的戰略優勢。為此,必須瞄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科技產業競爭方向,夯實支撐智能經濟、數字經濟、生物經濟、綠色經濟和空天海洋經濟創新發展的產業基礎,重構和再造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需要的產業技術基礎、人才支撐體系、基礎設施體系和政策支持體系,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把握先機。
四是堅持自主可控與開放合作相結合。必須承認和牢記,真正的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必須強化自主發展,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形成自主發展能力。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美國、德國、日本、法國、韓國、以色列等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強國仍然是我們學習和合作的對象,部分國家單方面挑起的貿易和科技爭端不會打亂我們科技、創新和產業領域開放合作的進程。封閉的結果必然是落后。越是在部分國家鼓吹逆全球化浪潮、大行霸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當下,我國越是要以開放的胸襟、虛心包容的態度積極拓展深化與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產業和技術合作交流,統籌利用好“兩種市場、兩種資源”,打造基礎領域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盛朝迅,2021)。此外,產業基礎領域的發展,本身具有開放性的訴求。由于產業基礎領域市場空間有限,一國市場有“天花板”,僅僅靠國內市場很難做大做強,必須拓展國際市場空間。比如德國之所以產業基礎領域實力強、隱形冠軍企業多,主要得益于其堅定走開放的全球化之路,產品生產以出口為主、經濟外向度高。因此,產業基礎的產品經營、研發和服務是專業化的,但其市場開拓必須是全球化的,在世界范圍內做到極致,受到全球業界的廣泛認可。
(二)主要路徑:新型舉國體制
如前所述,產業基礎領域所具有的底層性、戰略性、寡占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等特征決定了僅靠市場力量無法完成產業基礎的再造與升級,而現有的政策支持體系由于部門分割、力量分散、政策體系不健全等因素導致難以發揮合力,造成產業基礎領域長期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較大的現實。因此,必須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彌補市場失靈和系統性協調的失敗。
這其中,最主要的路徑就是探索新型舉國體制,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和發揮市場機制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結合起來,在國家層面建立多部門協作機制和合作大平臺,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支持建設企業創新聯合體,探索“揭榜掛帥”等新的政策支持方式,鼓勵、引導金融資金以市場化方式參與支持重大專項研發,形成部門、地方、全社會參與的格局。
在國際上,舉國體制早有先例。最典型、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共有2萬多家美國企業、200多所大學、80多個研究機構參與了阿波羅登月計劃的研發和實施,高峰時期雇傭的人數高達30多萬人。在產業基礎領域,日本在碳纖維、半導體材料、顯示材料等關鍵基礎材料領域的研制上也采取了舉國體制的辦法,主要通過政府不遺余力的政策支持和行業組織的統籌協調推動產業發展,使得日本在全球碳纖維市場上占據了超過50%的市場份額,其中,PAN 基碳纖維占全球總產量的70% 以上,瀝青基碳纖維占全球總產量的 90%,掌握了絕對的控制能力。我國在載人航天、原子彈、氫彈等“兩彈一星”研發上也采取了舉國體制的做法。近十年來我國探月工程與高鐵產業的持續性技術創新,亦展現了舉國體制的突出核心技術攻關優勢。
然而,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調整和新的全球科技競爭格局要求,繼續沿用過去由國家組織動員、高效調動有限資源、固定人員和團隊、按照既定技術路線進行集中力量攻關的傳統舉國體制的做法,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必須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的新路徑、新模式。
首先,傳統舉國體制“動員制”的運作模式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傳統以政治動員為中心的舉國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制度情境的產物,其所依賴的治理機制與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原則存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依靠特定機構來“選人”,不如依靠市場機制來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主要體現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成為新型舉國體制運轉的突出要求,也是新型舉國體制“新”字的本質特征,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兼顧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新的、市場化的方式和體制機制來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意味著在基于新型舉國體制開展重大科技項目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時,要充分尊重市場規律,最大限度尊重與激發市場各類創新主體、企業和科研團隊的技術創新活力與潛能,優化制度環境與營商環境。
其次,新型舉國體制要著力攻克的技術對象和時代對技術的要求發生根本性變化。從實踐看,我國過去通過發揮舉國體制實現追趕的主要是在壟斷程度和技術成熟度較高、應用市場有限、規模效應要求不明顯的領域,技術路線相對明確,如“兩彈一星”等,主要解決“有和無”的問題,對技術的經濟性和市場化應用要求不高,主要需求是國家戰略需求和國防安全考慮。但在電子信息、醫藥、新材料等技術進步快、市場開放度較高、競爭激烈的領域,通過建立傳統舉國體制實現并跑、領跑的難度較大。政府采購支持只能支持產業發展初期的產品市場應用,如果技術經濟性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大規模的市場化應用的高昂成本將會使產業發展失去競爭力。可以說,傳統舉國體制下的技術創新以單一科技目標為主,100次實驗有一次取得成功就算取得突破。而新型舉國體制下的技術創新則要兼顧技術經濟性和產品商業化應用,至少要保證99%以上的合格率,確保產品性能穩定和使用壽命長久。特別是,當一個國家科技發展逐步進入“并跑”“領跑”階段后,很多產業技術進入“無人區”,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技術路線圖可以參考,通過發揮舉國體制實現跨越的更是少見,更多的是加強面向顛覆性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激勵大量中小企業去試錯,建立以創新型企業為主體、產學研聯合的新型舉國體制。此外,戰略前沿的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不僅投入大、風險高,還需要強大的基礎研究和工業基礎支撐,對于基礎研究的要求更高,必須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
最后,傳統舉國體制難以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開放性、生態化、智能化的要求。新型舉國體制下的技術創新是多學科交叉的產物,對于產業技術研發生產與創新迭代的開放性提出更高要求。以高端芯片為例,芯片的研發創新過程是基礎研究能力與應用開發能力的高度互嵌,需要產學研融通結合,既需要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等多基礎學科的綜合基礎研究,又需要IC設計、晶圓制造、封裝和測試過程中的多工序協同,以及基于基礎理論的研發創新與基于工藝創新的應用開發創新的雙元創新能力,需要開展跨部門、跨團隊、跨領域、跨學科的聯合。但這種開放合作不是基于“挑選冠軍”或“動員式”的合作,而是基于市場化機制上的“揭榜掛帥”,誰有能力誰揭榜,誰有能力誰參與協同攻關。與此同時,新型舉國體制下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往往需要建立龐大的產業生態體系。如果要突破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封鎖打壓,則意味著我們必須能夠獨立完成芯片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等所有環節,突破EDA設計軟件、光刻機等關鍵核心技術,還要構建類似WinTel、GooArm聯盟的龐大軟硬件產業生態體系。為此,需要在重點領域支持以龍頭企業為主體成立企業技術創新聯盟或企業技術創新聯合體,以龍頭企業需求為導向,貫通產學研各方和產業鏈上下游力量進行協同攻關,構造良好的產業生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智能化數字化成為時代發展的主題,由于數字技術具有高度的滲透性,數字技術與生物技術、制造技術、材料技術等加速融合,并逐步成為科學研究與應用開發的底層技術,產業發展和技術突破的邊界日益模糊,各產業發展的底層融合加快,基礎研究、應用開發與技術商業化的時空距離進一步縮短,各種網絡型科技平臺和組織應運而生,科技成果轉化的商業化鏈條也更加動態便捷。為此,需要高度重視數字技術的數字化智能化賦能效應,加快構建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需要的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新型數字治理體系,為新型舉國體制下的科技項目組織和治理賦能夯基。
五、重大舉措建議
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是對產業基礎及其所涉及的體制機制環境、重大共性服務平臺、要素保障支持條件等進行系統謀劃和布局,重點解決多部門協調失靈和系統失敗等問題的系統性政策安排。需要聚焦我國提升產業基礎能力面臨的要素、平臺、制度等方面的瓶頸制約,堅持以企業為主體,強化“要素—平臺—制度”三維支撐,夯實產業基礎再造的微觀基礎和制度基礎。
(一)堅持企業主體,加快培育產業鏈鏈主企業和專精特新隱形冠軍企業
企業是提升產業基礎能力的重要載體。對于提升基礎能力而言,最為關鍵的是產業鏈鏈主企業和大量專精特新隱形冠軍企業這兩類主體。德國在發展數控機床等基礎裝備產業時就注重推動龍頭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協同發展,通過推動大中小企業聯合創新,促進數控機床的功能和型號不斷更新迭代,從而保持了持續的競爭能力。我國要圍繞基礎裝備、基礎零部件、基礎工業軟件、關鍵基礎材料等“產業四基”,大力培育聚焦基礎產品和技術研發生產的企業群體。
(二)強化要素培育,催生一批支撐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的高端要素
從要素層面看,高素質科技創新人才是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提升產業基礎能力的關鍵要素。產業基礎能力提升對人才的供給結構和質量素質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為此,需要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弘揚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大力培養具有科學探索精神的基礎領域創新型人才、掌握先進制造技術的工程師人才、技能型工匠人才和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人才。一是培養潛心科研、熱愛探索的科學家和創新人員。通過體制機制創新,賦予其技術路線決策權、項目經費調劑權、創新團隊組建權,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 二是加大頂尖人才引進力度,大力吸引杰出的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創業。三是打造新時期大國工匠。四是改革高技能人才培養模式。實施高等教育“強基計劃”,建設一批未來技術學院和現代產業學院,加快培養高端芯片及軟件、新材料、先進制造等緊缺人才。此外,也要暢通數據、技術、資金等要素向產業基礎領域有序流動機制,夯實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的要素支撐。
(三)加快平臺建設,構建完善的產業基礎能力提升服務體系
從平臺層面看,重點是加快構建支撐產業基礎發展的基礎性平臺和基礎設施,加大力度支持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智能標準生產設施、技術研發轉化設施、檢驗檢測認證設施、職業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完善科研成果中試、產品創制試制和模擬應用場景等成果工程化應用平臺,夯實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新一代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支撐能力,構筑良好的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體系。
(四)完善體制機制,再造有利于基礎能力提升的制度基礎
推動產業基礎再造,亟需優化制度供給,加快建立完善新型技術攻關突破機制、產業政策長效支持機制、產業鏈上下游和跨領域協作機制、質量提升保障機制、軍民融合協作機制、國企產業基礎再造支持機制和國內國際協同創新機制,為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營造良好環境。
參考文獻:
[1]陳家建,2013:《項目制與基層政府動員——對社會管理項目化運作的社會學考察》,《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Chen Jiajian, 2013,The Project Syste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Official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Project-oriented Ope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
[2]陳勁、陽鎮、朱子欽,2020:《“十四五”時期“卡脖子”技術的破解:識別框架、戰略轉向與突破路徑》,《改革》第12期。[Chen Jing,Yang Zhen and Zhu Ziqin, 2020, TheSolution of"Neck Sticking" TechnologyDuringthe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IdentificationFramework,StrategicChangeandBreakthrough Path, Reform,12.]
[3]干勇,2017:《三基產業技術基礎發展及創新》,《中國工業評論》第1期。[Gan Yong,2017,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ree basic industries, China Industry Review,1.]
[4]賀俊,2017:《產業政策批判之再批判與“設計得當”的產業政策》,《學習與探索》第1期。[He Jun,2017, Rethinking of the Arguments against the Industry Policy and the "Properly Designed" Industrial Policy, Study & Exploration,1.]
[5]黃群慧、余永澤、張松林,2019:《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中國工業經濟》第8期。[Huang Qunhui, Yu Yongze and Zhang Songlin,2019,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hina Experience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8.]
[6]黃群慧,2020:《“十四五”時期深化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重大挑戰與戰略選擇》,《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Huang Qunhui, 2020, Major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in Deepening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eriod, Journal of the CCPS (CAG),2.]
[7]江小涓、孟麗君,2021:《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與更高水平雙循環——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管理世界》第1期。[Jiang Xiaojuan and Meng Lijun,2021, Mainly Inner Circulation, Outer Circulation Empowerment and Higher Level Double Circulation: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Practice, Management World,1.]
[8]劉志彪,2019:《產業基礎高級化:動態比較優勢運用與產業政策》,《江海學刊》第6期。[Liu Zhibiao,2019, Advanced Industrial Foundation: Application of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dustrial Policy, Jianghhai Academic Journal,6.]
[9]羅仲偉、孟艷華,2020:《“十四五”時期區域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區域經濟評論》第1期。[Luo Zhongwei and Meng Yanhua,2020, Regional Industrial Base Advanced and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Daring the 14th Five-Year Period,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1.]
[10]盛朝迅,2019:《推進我國產業鏈現代化的思路與方略》,《改革》第10期。[Sheng Chaoxun,2019,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Reform,10.]
[11]盛朝迅,2020:《統籌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經濟日報》7月22日。[Sheng Chaoxun,2020,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 Economic Daily, July 22.]
[12]盛朝迅,2021:《新發展格局下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展的思路與策略》,《改革》第2期。[Sheng Chaoxun,2021,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Saf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form,2.]
[13]王詩宗、楊帆,2018:《基層政策執行中的調適性社會動員、行政控制與多元參與》,《中國社會科學》第11期。[Wang Shizong and Yang Fan,2018, Adaptive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s Policy: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Multipolar Involve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1.]
[14]王一鳴,2020:《百年大變局、高質量發展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管理世界》第12期。[Wang Yiming,2020,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Management World,12.]
[15]許恒、張一林、曹雨佳,2020:《數字經濟、技術溢出與動態競合政策》,《管理世界》第11期。[Xu Heng,Zhang Yilin and Cao Yujia,2020,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Dynamic Coopetition Policy, Management World,11.]
[16]余江、陳鳳、張越、劉瑞,2019:《鑄造強國重器: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規律探索與體系構建》,《中國科學院院刊》第3期。[Yu Jiang, Chen Feng, Zhang Yue and Liu Rui,2019, Forging Pillar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Mechanism Explor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Breakthrough of Core and Key Technologi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3.]
[17]張偉、于良春,2019:《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的國有企業改革路徑選擇研究》,《經濟研究》第10期。[Zhang Wei and Yu Liangchun,2019, Path Selection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under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0.]
[18]ITC,2005, Innovations in Export Strategy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Quality Assurance Challenge.
[19]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2019,Quality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Xu Chenggang,2011,The Foundation Institution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4,1076-1151.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Idea and Main Tasks of Implementing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Reengineering Project
Sheng Chaoxun, Xu Jianwei and Ren jiqiu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foundation re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crack the security bottleneck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construct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lead to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hile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grasper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industries as well as build the country into a manufacturing power. Reflecting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point-chain coordination, enterprise subject, limited targeting, classified practicing', the study results suggest that steps be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ajor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professional-elaborate-specialized-innovative hidden-champion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the three-dimensional support of 'elements-platform-system',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vanced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mechanism and an innovative industrial policy support mechanism, to optimize the upstream-downstream and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buil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pport mechanism for industrial foundation reengineering project,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to build an innovative service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basic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Meanwhile, it is also advised to accelerate the breakthrough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ies, such as those in major basic equipment, key basic components, key basic materials and high-end industrial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to strive to build and re-create an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at the advanced level of the world.
Key Words:Industrial Foundation; New National System; Industrial Chain Moderniz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Guarantee
責任編輯 郝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