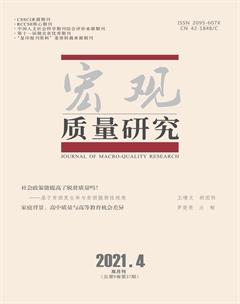新農人發展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彭超 段晉苑 馬彪



摘 要:新農人發展質量需要從科學的角度構建指標體系進行評價,并探究發展質量的影響因素。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維度對新農人發展質量進行系統評價,研究發現:現階段新農人發展質量仍然不高,尤其是需要在協調和開放兩方面進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新農人善于利用互聯網經營涉農產業,但目前電商發展對新農人發展質量貢獻并不大。基準回歸和分位數回歸結果均表明,新農人進入涉農產業的時間、第一桶金來源、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產業發展定位和主營產品銷售模式等因素是當前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關鍵因素。根據實證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加速補齊新農人文化素質短板,實施學歷提升行動;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農技推廣人員、科技特派員和人才及企業孵化基地、“雙創”社團負責人等發揮職業優勢,形成創業就業導師機制;鼓勵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深度合作,創立農產品品牌,打造優勢產品,放大農產品品牌溢價效應;提升新農人對農產品電子商務的認知水平,充分發揮電商對新農人的賦能作用。
關鍵詞:新農人;高質量發展;影響因素;熵權法;分位數回歸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鎮和非農領域就業,大批農村本土人才出村進城。在這種情況下,農村普遍出現了“空心化”“389961留守”等現象。“誰來種地?”“誰來養豬?”“誰來興村?”等問題已經成為農業產業發展、農村社會繁榮的重要制約因素。近年來,一方面,部分留在農村本地的能人,因為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而成為新產業新業態帶頭人;另一方面,部分農民工、大學生、科研人員、退伍軍人等,返鄉下鄉創業創新。這些創業創新群體多數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帶頭人,一般掌握了新技術、樹立新理念、從事新產業、融入新平臺、選擇新業態,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新作用,所以經常被冠以“新農人”的稱謂。新農人為農業農村注入了發展新動能,本身就構成了鄉村人才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在鄉村產業振興、生態振興、文化振興、組織振興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的重要參與力量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先行者。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農人已不再是一種身份或社會地位的象征,而是作為一種職業標識而存在(郭智奇等,2012;陳傳波等,2019)。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經營主體而言,新農人接受新事物、新技術的能力較為突出,其更善于利用互聯網思維從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流通,標準化程度往往較高。
國內學者對新農人的研究大多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對新農人的概念進行界定。廣義上的新農人主要是指農業全產業鏈上的具有互聯網思維的農業經營者、監管者和研究者等(阿里研究院,2015),狹義上的新農人則是指依托于“互聯網+新媒體”向市場出售高質量農產品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課題組,2016)。由于本研究重點關注的是鄉村人才振興背景下的新農人發展質量問題,因此本文結合現有研究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將新農人定義為能夠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工具進行高質量農產品生產和銷售并且能夠起到帶動、引領以及示范作用的農業經營管理主體。為進一步明晰新農人這一概念在政策制定、行業發展以及學術領域的發展脈絡,本文嘗試從新農人的內涵界定、基本特征、產生背景、制約因素等方面進行綜述。
新農人的概念最早出現于2013年前后(張新蕾、劉福軍,2019),此后關于新農人內涵的討論開始逐年增多,現有文獻大都將研究重點落在“新”上,探討新農人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相比新在何處。總體來看,學者們比較集中地從生產方式、經營業態、互聯網基因以及市場化思維等四個方面界定新農人的內涵,提出了新農人即農業新業態、農村新細胞、農民新群體(汪向東,2014;郭艷平、譚瑩,2016)。其特征包括:按照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方式進行生產(杜志雄,2015),運用“互聯網+農業”的生產方式從事農業等。這些研究雖然提出了部分新農人的基本特征,但沒有廓清新農人的群體范圍,盡管強調了新農人的互聯網基因和綠色生態理念,但看不出新農人的成長軌跡和發展趨勢。對此,部分研究開始探討新農人的產生原因,并總結出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動機:一是資本驅動,隨著一批成功的農業企業和農產品品牌的出現,大量社會資本進入農業領域,進而催生出一批對“三農”事業發展有熱情、有理想的農業經營主體(郭艷平、譚瑩,2016;張永軍、張靜,2016);二是問題驅動或者需求驅動,新農人產生初期正是我國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時期,也是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要求日益提高和需求越來越多元化的時期,很多新農人進入農業的目的是探索扭轉食品安全頻發態勢,按照符合自身食品安全和質量要求來進行農業生產,甚至有的新農人就是為了滿足自身家庭和親朋好友家庭的農產品需求才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杜志雄,2015;郭艷平、譚瑩,2016;劉家富等,2019);三是技術驅動,隨著農業機械化、智能化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物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在農業領域應用場景不斷增加和日益成熟,一批成長在網絡時代、掌握互聯網學習技能、具備互聯網思維的人投身“三農”領域,成為推動農業生產經營邁入信息化時代的先鋒力量(張新蕾、劉福軍,2019);四是情懷驅動,隨著我國生態環境問題愈發嚴峻和城市生活壓力的日益增大,一批秉持著綠色生態理念,期待“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城鄉創業者,或返鄉、或下鄉、或在鄉踐行生態農業的理念,將生活追求與“三農”事業融為一體,希望利用自身優勢為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做出貢獻(汪向東,2014)。此外,還有部分文獻從新農人的示范引領作用和發展制約因素兩個方面展開研究。這一方面的文獻認為新農人在促進我國農業轉型升級、引領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改變傳統農業流通模式、推動農產品營銷方式創新、促進農民創業就業以及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領作用(歐陽國輝、郭佳,2017),但與新農人在引領帶動等方面展現出的優勢相比,現階段新農人的發展不僅要面臨土地、金融資本、人力資源以及基礎設施的制約(張雪占,2018;謝艷華,2019;嚴愛玲等,2020),還要面臨難以融入鄉村熟人社會的現實問題(張新蕾、劉福軍,2019)。
通過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國內學者已在新農人產生的背景、動機、典型特征以及發展制約因素等方面進行了充分研究,但關于新農人發展質量的評價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則較為匱乏。實際上,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物”的現代化,還是“人”的現代化。2019年《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提出,要培養一支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高素質農民隊伍。高素質農民是現代農業的生產者、現代設施和現代流通體系的運營維護者,也是現代治理體系的參與者(彭超,2021)。而新農人是高素質農民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質量該如何科學評價?發展質量又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在鄉村人才振興的背景下廓清上述問題顯得尤為重要。上述問題的答案不僅關系到對新農人整體狀況的評估,還關系到農業農村投資是否可持續,更關系到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發揮。基于此,本文將參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中高質量發展的定義構建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體系,結合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員問卷,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維度創新性地對新農人發展質量進行科學系統評估并就其影響因素進行更為客觀的實證分析。
本文余下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將構建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在第三部分中,將會描述數據來源、指標評價方法與測度結果;第四部分是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因素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評價新農人發展質量,有助于更為清晰全面地了解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尤其是新農人的發展情況。構建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體系需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是科學性,即要求評價指標體系中所選取的指標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出新農人發展質量的綜合情況;二是系統性,即要求評價指標體系中所選取的指標之間具有一定邏輯關系,具有整體不可分割性;三是可操作性,即要求評價指標體系中涉及新農人發展質量的指標在計算方面具有一致性,便于模型計算和分析(彭超、張琛,2019)。鑒于此,本文參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中高質量發展的定義來構建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體系。具體而言,高質量發展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更明確地說,高質量發展就是經濟發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M] . 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p109-p113.]。這一定義沿用在新農人發展質量上同樣契合。換言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在新農人發展上到底體現得如何,可以作為新農人發展質量的評價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評價新農人發展質量是本文的邏輯起點,但仍需在構建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體系之前給出新農人在本文中的界定,以進一步明確研究對象。綜合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本文將具有互聯網思維、綠色發展理念、注重生態環境效益,致力于提供高質量農產品的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定義為新農人。這部分群體既包含城鎮生活經歷但返鄉就業、創業的農民工、大學生、退役軍人等,又包括一直生活在鄉村從事農業經營活動但生產觀念和思維方式發生明顯轉變的原住農民。為此,本文結合關于新農人發展情況的大樣本調查,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維度對新農人發展質量進行全面、科學和客觀的評價。對新農人而言,創新主要體現在科技創新、人才創新、品牌創新、業態創新,協調主要體現在產業協調、要素協調,綠色主要體現在產品綠色、生產體系綠色,開放則體現在業務開放等方面,共享則集中體現在帶動小農戶和貧困人口方面(鄧悅等,2021)。各維度指標的具體選取情況如表1所示。
(一)創新維度
創新是新農人發展的動力來源。新農人是天然的創新主體。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農業科技創新步伐明顯加快,成果轉化和推廣不斷加強。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實施報告(2018-2019),2019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到59.2%,超過了土地、勞動、資本等傳統要素貢獻率之和。對新農人所在的農業經營單位而言,科技發展質量能夠積極影響其生產經營活動,使新農人所在的農業經營單位更加注重生產技術發展,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加強質量管控,通過生產優質產品提升新農人品牌效應及市場競爭力(胡元木、紀端,2017)。鑒于此,本文選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擁有的國家專利數量、注冊商標數量作為衡量科技和人才創新的指標。品牌創新主要的衡量指標是注冊商標數量。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下,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起決定性作用,人力資本存量越高的勞動者獲得高收入的機會越大(Welch,1970;Yang,2004),受過高等教育或具有豐富技能的勞動者也更能為企業做出貢獻。通常意義上,勞動力質量對勞動力人力資本的邊際效應能夠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Schultz,1971;朱焱、張孟昌,2013)。對本文而言,高級技術人員數量、本科學歷工作人員占比、碩士員工數量以及博士員工數量反映的則是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人力資本質量。業態創新主要是新農人采納新業態的情況。農產品電子商務作為互聯網服務“三農”的典型代表,為農產品產銷銜接提供了新的渠道,深刻地改變了農村地區的產業業態(薛巖等,2020;彭超、馬彪,2019)。新農人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經營主體相比而言,最大的不同在于新農人善于利用互聯網思維從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流通(阿里研究院,2015)。本文選擇自建電商平臺數量、電商平臺銷售的主營產品數量作為業態創新的衡量指標。
(二)協調維度
協調發展是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但人們在討論農業發展時,往往習慣聚焦農業要素投入、技術進步、市場流通等方面,恰恰忽視了人的主體因素(朱啟臻、楊匯泉,2011)。新農人協調發展不僅要求產業融合、主體協同、要素互通,還要求新農人與各類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各類農業服務主體、農產品加工主體、流通企業等協同融合,對產品的自產、外購等方面進行協調,新農人對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和配置都會影響協調的質量。對應于問卷,本文選取涉農產業營業總收入、精深加工的自產農產品比重、長期雇用工作人員數量作為協調發展的衡量指標。
(三)綠色維度
綠色生產方式、產品類型、產業標準是新農人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區塊鏈等信息技術的不斷完善(程虹等,2020),城鄉居民獲取高品質農產品的渠道日益增多,消費者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優化農產品生產方式構建農業生產“三品一標”體系已成為各類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農產品生產質量的重要抓手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于印發《農業生產“三品一標”提升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農辦規〔2021〕1號)]。標準化生產作為高質量農業生產的基礎,與綠色農產品、有機農產品,地理標志農產品和食用農產品達標合格證制度“三品一標”認證共同構成了實現農產品優質優價的必要途徑。
(四)開放維度
整個經濟體系層面的開放,主要是國家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對新農人而言,其立足的基點多數是內需。當然,很多新農人所在的企業等有進出口業務和國際合作。出于強調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和城鄉雙向開放的目的,本文先立足對內開放。主要是指標體系當中,能夠反映開放程度的變量。主要選取了有合作關系的科研單位數量、使用的第三方電商平臺數量。第三方電商平臺主要是指獨立于買賣雙方,由第三方建設為買賣雙方提供農產品交易的電子商務平臺,例如淘寶、京東、拼多多等。自建電商平臺則是指由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自主搭建的農產品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擁有獨立域名,可在線推廣增加品牌權重,創造品牌價值。
(五)共享維度
新農人作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之一,其對小農戶的輻射帶動能力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以及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具有重要影響。早在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明確提出要支持新型經營主體成為建設現代農業的骨干力量,充分發揮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在農業機械和科技成果應用、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引領作用。以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帶農支農效果衡量新農人的生產經營情況,有助于從被帶動者的視角側面反映新農人的發展質量。本文選取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帶動小農戶進入涉農產業鏈條的數量、帶動的貧困戶數量以及帶動的貧困人口總量等三個指標測度新農人的帶農支農質量。
三、數據來源、指標評價方法與測度結果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員問卷。其中,一部分學員問卷來自“鄉村振興帶頭人計劃”,該計劃是由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浙江大學全球農商研究院、云集共享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合作開發的新農人培訓項目;另一部分學員問卷來自同期在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舉辦的“新農人”培訓班。截至2020年9月,共舉辦新農人培訓班8期。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員問卷累計發放1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129份,問卷有效率為94.1%。
(二)新農人發展質量的綜合評價方法
如何客觀、科學、全面地確定新農人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的權重是本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個體的福利狀態往往難以用線性組合的形式直觀反映,目前廣泛采用的層次分析法、等權重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線性賦權法存在著較大局限性。基于現有指標權重評價方法的局限性,本文將熵權法運用到新農人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的權重計算中。熵權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原理是根據各指標的變異程度,利用模糊評價矩陣和輸出的信息熵計算出各指標的熵值,并基于熵值對指標權重進行修正,進而得到最終的權重值。采用熵權法計算權重能夠有效避免由于主觀因素導致的偏誤問題,目前已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應用(Zou et al.,2016;張琛等,2017)。熵權法的具體計算步驟為:
(三)測度結果
根據上述計算步驟,本文最終得出了新農人發展質量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及各項指標的權重。在測度新農人發展質量的20項指標中,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中博士員工數量、碩士員工數量、帶動的貧困人口總量、擁有國家專利數量、涉農產業營業總收入、帶動小農戶進入涉農產業鏈條的數量、有機產品數量以及帶動的貧困戶數量8項指標的權重相對較高,超過了全部指標權重之和的一半。其中,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中博士員工數量的權重最高,約為8.2%,充分說明了高素質人才對新農人發展質量的重要作用。
從高質量發展的五個維度看,反映新農人創新質量的8項指標累計權重最高,約為42.2%。這實際上是新農人“新”的題中應有之義,創新成為新農人發展質量的首要綜合維度。排在第二個大類的是綠色維度,反映新農人綠色質量的4項指標累計權重為19.1%。綠色生態是新農人返鄉下鄉和本土創業普遍的發展形態,也是新農人對接市場的需要。可喜的是,同為三個指標,新農人的協調質量和共享質量當中,共享質量權重較高,累計權重達到18.6%,協調質量的3項指標累計權重為13.1%。開放維度上的2項指標累計權重為6.9%。當然,以上維度的累計權重大小與指標數量有關。但是,即使是在指標數量相近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區分大小。
值得說明的是,雖然新農人善于利用互聯網經營涉農產業,但目前電商發展質量在新農人發展質量綜合評價體系中的權重系數并不高,電商的增收效應仍有較大上升空間。總體而言,運用熵權法計算新農人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權重后,并未發現冗余指標,即研究所選取的評價指標較為合理。權重測度的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四、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因素分析
(一)變量選取
為了研究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因素,探尋提升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可行路徑,本文將采用實證分析的方式對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因素予以探究。實證分析中,因變量為依據熵權法計算所得的新農人發展質量總得分,自變量則是在綜合考慮已有研究和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選取新農人稟賦特征、以往經歷、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產品定位、市場定位以及商業模式5個方面的18個變量。各變量的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
根據表3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基于熵權法得到的新農人發展質量平均總得分僅為0.127,處于較低水平,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發展質量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從解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男性新農人比重較大,青壯年居多,進入涉農產業的時間在8年左右,超過三分之一的新農人擁有黨員身份,半數以上的新農人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新農人與傳統農業經營主體相比較而言,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在新農人的過往經歷方面,外出打工仍是最主要的非農經歷,53.4%的新農人曾有過外出打工經歷,曾有公職人員和經紀人工作經歷的新農人比重僅為3.5%和11.9%。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產品定位方面,近半數的新農人將產業定位在綠色生產上,占比約為40.4%,將產業定位在有機生產的新農人占比為22.5%。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市場定位方面,超過90%的單位定位為中高端市場,定位在低端市場的單位只有9.1%。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最終產品采取的商業模式方面,接近半數的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采取的是自營店鋪直銷和對接店直銷,約有22.4%的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采取的是由超市和其他店鋪代銷,37.4%的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采取的是經紀人或采購商上門收購。
(二)基準回歸
本文的實證分析包含兩個部分,即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因素的整體效應與分層效應。其中,整體效應以均值回歸為基礎。在分層效應中,考慮到均值回歸無法反映整個條件分布的結果,為此本文將采用分位數回歸法進行估計。分位數回歸能夠研究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條件分位數關系,其結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因素的群體異質性,對基準回歸進行有效補充(Koenker and Bassett,1978)。
表4報告了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均值估計結果。鑒于新農人發展質量總得分處于0-1之間且部分樣本的新農人發展質量得分存在歸并現象,(2)列采用Tobit模型進行估計,作為列(1)OLS模型的對照。此外,考慮到Tobit模型的擾動項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為保證Tobit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列(3)采用歸并最小絕對離差法(Censore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s)進行估計。綜合模型(1)~模型(3)的估計結果可知,反映新農人稟賦特征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變量通過了各自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其中新農人的性別和文化程度與發展質量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女性新農人相比,男性新農人發展質量總得分更高,新農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其發展質量總得分也越高。在過往經歷方面,新農人進入涉農產業的時間和第一桶金是否來源于非農產業積累均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新農人進入涉農產業的時間越長,對農業生產經營的情況越了解,來自內心的工作動力和職業使命感越強(李群等,2020),發展質量總得分也越高。新農人第一桶金來源于非農產業積累的發展質量總得分要高于第一桶金源于其他途徑的發展質量總得分。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產業發展定位方面,發展定位是否為有機生產和發展定位是否為綠色生產均通過了各自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與新農人發展質量總得分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在新農人主營產品的銷售模式方面,是否采用自營店鋪直銷和對接店直銷的商業模式、是否采用由超市和其他店鋪代銷的商業模式以及是否采用由經紀人或采購商上門收購的商業模式等三個變量均通過了各自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其中是否采用自營店鋪直銷和對接店直銷的商業模式以及是否采用由超市和其他店鋪代銷的商業模式與新農人發展質量總得分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主營產品通過直銷或超市和其他店鋪代銷的商業模式有助于提升新農人發展質量。值得注意的是,是否采用由經紀人或采購商上門收購的商業模式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自營店鋪、對接店、超市和其他店鋪對待銷產品的標準較高,“倒逼”新農人嚴格管控主營產品的質量,而經紀人或采購商上門收購對待銷產品的要求則相對較低,反而降低了新農人的發展質量。
(三)分位數回歸
考慮到新農人發展質量得分的異質性,本文選取0.10、0.25、0.50、0.75和0.90五個經典分位點,基于分位數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了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因素的分層效應,具體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分位數回歸結果可以得出,除反映新農人稟賦特征的文化程度、進入涉農產業的時間和第一桶金是否來源于非農產業積累等三個變量在不同分位點下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外,其余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各項指標均存在異質性。新農人性別在75%分位點和90%分位點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估計結果為正,這說明性別對不同程度發展質量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男性新農人對較高水平發展質量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新農人年齡在50%分位點、75%分位點以及90%分位點均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估計結果顯著為負,這說明年齡對不同程度發展質量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且對發展質量的負效應在中、高水平上表現得更為明顯。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產業發展定位是否為有機生產、是否為綠色生產只在50%分位點通過了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估計結果為正,這說明現階段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已逐漸成為評判產業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吉亞輝、陳智,2019)。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產業發展定位是否為有機生產、是否為綠色生產是決定新農人發展質量由低到高的轉折點,對發展質量為中等收入水平的新農人而言,將產業發展定位為綠色、有機有助于發展質量升級和產品附加值提升。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是否采用自營店鋪直銷和對接店直銷的商業模式、是否采用由超市和其他店鋪代銷的商業模式在75%分位點和90%分位點通過了各自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估計系數為正,這一結果表明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商業模式對中、高水平發展質量起到了顯著性促進作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是否采用由經紀人或采購商上門收購的商業模式在25%分位點、50%分位點和75%分位點通過了各自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估計系數為負。這一結果表明,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的主營產品由經紀人或采購商上門收購對中、高水平的發展質量起到了較為明顯的負向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維度構建新農人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基于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1129份學員問卷對新農人發展質量的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并探究新農人發展質量的影響因素,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新農人發展質量仍然不高,新農人發展質量總得分仍處于較低水平,存在較大提升空間;第二,在總體發展質量中,創新和綠色發展質量較高,共享居中,協調、開放處于比較低的水平;第三,雖然新農人善于利用互聯網經營涉農產業,但目前電商發展質量在新農人發展質量綜合評價體系中的權重系數并不高,反映新農人電商發展質量的3項指標累計權重僅為12.5%,電商的增收效應并未得到充分體現;第四,基準回歸和分位數回歸結果均表明新農人進入涉農產業的時間、第一桶金來源、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產業發展定位和主營產品銷售模式等因素是當前影響新農人發展質量的關鍵因素。
為提升新農人發展質量水平,實現新農人的高質量發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補齊新農人文化素質短板,以新農人需求為導向,實行“農學結合”彈性學制,遵循“因需施教”原則,實施學歷提升行動。二是積極引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領辦人,農技推廣人員、科技特派員和企業孵化基地的負責人下到村組田間地頭,與農民面對面交流、手把手教學,實現從理論灌輸向專業服務轉變。三是重點支持新農人在農產品精深加工、冷鏈物流和科技研發等方面的建設,促進產銷銜接,鼓勵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深度合作,創立農產品品牌,打造優勢產品,放大農產品品牌溢價效應。四是提升新農人對農產品電子商務的認知水平,強化農產品電子商務在新農人所在農業經營單位中的業務地位,充分發揮農產品電商在降低交易成本、拓寬銷售渠道和提高流通效率等方面的優勢。
參考文獻:
[1]程虹、王華星、范寒冰,2020:《我國傳統企業如何通過“平臺化”促進高質量發展?——基于“良品鋪子”的案例研究》,《宏觀質量研究》第4期。[Cheng Hong, Wang Huaxing and Fan Hanbing, 2020, How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 Through Platformization? A Case Study Based on BESTORE,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4.]
[2]陳傳波、閻竣、李睿,2019:《新型職業農民對接城鎮職保的試點經驗分析——以上海、蘇州、威海和成都為例》,《農業經濟問題》第7期。[Chen Chuanbo, Yan Jun and Li Rui, 2019, Pilot on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to Dock Urban Vocational Insurance: Cases from Jinshan, Suzhou, Weihai and Chengdu.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7.]
[3]陳智、吉亞輝,2019:《中國高技術產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Chen Zhi and Ji Yahui, 2019,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Based on Chinas Spatial 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Province Panel Data,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3.]
[4]鄧悅、吳忠邦、蔣琬儀、汪禹同,2021:《從內生式脫貧走向鄉村振興:山區脫貧質量分析》,《宏觀質量研究》第2期。[Deng Yue, Wu Zhongbang, Jiang Wanyi and Wang Yutong, 2021, From Endogenous Poverty A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in a Mountain Area,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2.]
[5]杜志雄,2015:《“新農人”引領中國農業轉型的功能值得重視》,《世界農業》第9期。[Du Zhixiong, 2015,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New Players in Agriculture for Its Role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orld Agriculture, 9.]
[6]郭艷平、譚瑩,2016:《新農人成長的影響因素及政策路徑》,《農業經濟》第4期。[Guo Yanping and Tan Ying, 2016, Development of New Players in Agriculture: Determinants and Policies, Agricultural Economy, 4.]
[7]郭智奇、齊國、楊慧、趙聘、白瑜,2012:《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問題的研究》,《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15期。[Guo Zhiqi, Qi Guo, Yang Hui, Zhao Pin and Bai Yu, 2012,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hine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15.]
[8]胡元木、紀端,2017:《董事技術專長、創新效率與企業績效》,《南開管理評論》第3期。[Hu Yuanmu and Ji Duan, 2017, Technology Expertise of Directors,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Nankai Business Review,3.]
[9]李群、栗憲、張宏如,2020:《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師徒指導關系對新生代農民工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一個雙調節的中介模型》,《宏觀質量研究》第5期。[Li Qun, Li Xian and Zhang Hongru, 2020, The Influence of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Mediation Model with Double Moderation,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 5.]
[10]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課題組,2016:《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新農人發展調查》,《中國農村經濟》第4期。[Research Group of Department of Rural Economic System and Manage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2016, 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arm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Chinese Rural Economy, 4.]
[11]歐陽國輝、郭佳,2017:《傳統村落文化保育中的“新農人”介入研究》,《湖南社會科學》第5期。[Ouyang Guohui and Guo Jia, 2017, Research on the Intervention of "New Farmer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5.]
[12]彭超、馬彪,2019:《農產品電商發展瓶頸及解決路徑——來自河北省邯鄲市的調查》,《農村工作通訊》第3期。[Peng Chao and Ma Biao, 2019, Bottleneck and Sol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Development—A Survey from Handan City, Newsletter About Work in Rural Areas, 3.]
[13]彭超、張琛,2019:《農村人居環境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宏觀質量研究》第3期。[Peng Chao and Zhang Chen, 2019,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ournal of Macro-quality Research,3.]
[14]彭超,2021:《高素質農民培育政策的演變、效果與完善思路》,《理論探索》第1期。[Peng Chao, 2021, The Evolution, Effect and Improvement About the Policy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Farmer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1.]
[15]汪向東,2014:《“新農人”與新農人現象》,《新農業》第2期。[Wang Xiangdong, 2014, New Players in Agriculture and Its Phenomenon, New Agriculture, 2.]
[16]薛巖、馬彪、彭超,2020:《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電子商務:業態選擇與收入績效》,《農林經濟管理學報》第4期。[Xue Yan, Ma Biao and Peng Chao, 2020, New Players in Agriculture and E-commerce: Business Type Selection and Incom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4.]
[17]謝艷華,2019:《“互聯網+”背景下新農人成長的瓶頸及化解》,《農業經濟》第5期。[Xie Yanhua, 2019, Bottlenecks and Solutions of New Farmers' Grow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gricultural Economy, 5.]
[18]嚴愛玲、江宏、鄭書莉,2020:《鄉村振興視域下的互聯網金融對新農人創業績效的影響——基于安徽省調研數據的分析》,《南京審計大學學報》第5期。[Yan Ailing, Jiang Hong and Zheng Shuli, 2020, The Impact of Internet Financ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New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Anhui Province, Journal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5.]
[19]曾億武、郭紅東,2016:《農產品淘寶村形成機理:一個多案例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第4期。[Zeng Yiwu and Guo Hongdong, 2016,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ro-Taobao Village: A Multiple-Case Study,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4.]
[20]張琛、黃博、孔祥智,2017:《家庭農場綜合發展水平評價與分析——以全國種植類家庭農場為例》,《江淮論壇》第3期。[Zhang Chen, Huang Bo and Kong Xiangzhi, 2017,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Family Farm: A Case Study of Planting Family Farm in China, Jianghuai Tribune,3.]
[21]張永軍、張靜,2016:《新農人——逐夢農業藍海》,《農村經營管理》第10期。[Zhang Yongjun and Zhang Jing, 2016, New Players in Agriculture: Pursue Dream in Agriculture Blue Sea, Rur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10.]
[22]張新蕾、劉福軍,2019:《我國新農人發展研究綜述》,《云南農業大學(社會科學)》第2期。[Zhang Xinlei and Liu Fujun, 2019, The Research Summary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Farmers, Journa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
[23]張雪占,2018:《基于流通視角的新農人培育路徑探究》,《農業經濟》第4期。[Zhang Xuezhan, 2018,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New Farm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ircul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y, 4.]
[24]朱焱、張孟昌,2013:《企業管理團隊人力資本、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第11期。[Zhu Yan and Zhang Mengchang, 2013, Enterprise Management Team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ccounting Research,11.]
[25]朱啟臻、楊匯泉,2011:《誰在種地——對農業勞動力的調查與思考》,《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Zhu Qizhen, Yang Huiquan, 2011, Who are Engaging in Agriculture?——Investigations and Recogni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1.]
[26]Koenker, R. and G. Bassett,1978,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 46(1):33-50.
[27]Schultz T. W.,1971,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53(4):553-559.
[28]Welch, F.,1970, Education in P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35-59.
[29]Yang, D. T., 2004, Educa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During Rural Reform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4(1):137-162.
[30]Zou, Z., Yi, Y., and J. Sun, 2006, Entropy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Weight of Evaluating Indicators in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for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 Sciences, 18(5):1020-1023.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Peng Chao1,Duan Jinyuan1 and Ma Biao2
(1.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2.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evaluated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velopment quality need to be explored.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th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s made in this study, which reveals that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s still not high enough, and, especially, the coordination and openness are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Although new farmers are good at using the Internet to manage agriculture related industries,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o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s very much limited. The results of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new farmers'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period of time when new farmers ente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e source of the first pot of gol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units where the new farmers belong, as well as the sales mode of their major products. As shown by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concrete actions to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new farmers'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o support the full functioning of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leaders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personn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enterprise incubation bases, as well as those in charge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ssociation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form a tutor mechanism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and to encourage new farmers in the agricultural business units in having deep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s and of superior products, and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brand premium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TEPS NEED TO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gnition level of new farmers on e-comme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o fully utilize the power of the e-commerce in empowering new farmers in their businesses.
Key Words:New Farmer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Quantiles Regression
責任編輯 鄧 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