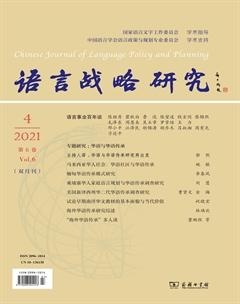語言事業(yè)百年談
陳獨(dú)秀 瞿秋白 魯迅 陳望道 錢玄同 黎錦熙 毛澤東 周恩來 吳玉章 羅常培 王力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胡喬木 呂叔湘 周有光 習(xí)近平
[編者按]為迎接建黨100周年,本刊特設(shè)“語言事業(yè)百年談”欄目,遴選杰出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友好人士有關(guān)語言事業(yè)的語錄,呈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上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引領(lǐng)拉丁化新文字運(yùn)動、新中國成立后領(lǐng)導(dǎo)文字改革、改革開放后倡導(dǎo)構(gòu)建和諧語言生活的歷史脈絡(luò),為推進(jìn)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滋養(yǎng)和啟迪。(整理者:北京華文學(xué)院 趙春燕)
1921~1949年
陳獨(dú)秀
新制拼音文字,實(shí)為當(dāng)務(wù)之急。……有人譏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shí)想做倉頡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dāng)然不是什么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yuǎn)古一直到現(xiàn)在無數(shù)倉頡造成的;今后需要許多倉頡來研究制造新的文字。
現(xiàn)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zhì)太過分,離開實(shí)際語言太遠(yuǎn)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種地方語作標(biāo)準(zhǔn),現(xiàn)在國語真正未成立之前,應(yīng)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語作標(biāo)準(zhǔn)語來過渡。(《〈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及說明》,1929年3月)
瞿秋白
中國話的發(fā)展顯然沒有日益分化的趨勢,而只有日益同化的趨勢,但是離著統(tǒng)一的時期還很遠(yuǎn)。……中國言語的真正的統(tǒng)一,必須經(jīng)濟(jì)上的發(fā)展形成了統(tǒng)一的經(jīng)濟(jì)機(jī)體,方才可能。而現(xiàn)在的經(jīng)濟(jì)情形只是圍繞著各個大城市,形成比較大的區(qū)域,以及各自的普通話。(《中國文和中國話的現(xiàn)狀》,1932年8月)
一切寫的東西,都應(yīng)該拿“讀出來可以聽得懂”做標(biāo)準(zhǔn),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話。至于革命的大眾文藝,尤其應(yīng)當(dāng)從運(yùn)用最淺近的新興階級的普通話開始。……這是要新興階級的先進(jìn)分子,領(lǐng)導(dǎo)著一般勞動民眾去創(chuàng)造新的豐富的現(xiàn)代中國話。(《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xué)月報》1932年6月第1期)
魯 迅
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幾個讀書人在書房里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xiàn)在在碼頭上,公共機(jī)關(guān)中,大學(xué)校里,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fā)達(dá),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門外文談》,《申報·自由談》1934年8月)
因?yàn)闈h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shù)的人民,永遠(yuǎn)和前進(jìn)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jī)。……我想,新文字運(yùn)動應(yīng)當(dāng)和當(dāng)前的民族解放運(yùn)動,配合起來同時進(jìn)行,而進(jìn)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jìn)文化人應(yīng)當(dāng)肩負(fù)起來的任務(wù)。(《幾個重要問題》,載《魯迅最后遺著》,莽原書屋,1936年)
陳望道
我們反對立刻廢除漢字的過左的主張,也反對把漢字看做萬古不變、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靈物崇拜的頑固主張。我們認(rèn)為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它是跟著社會經(jīng)濟(jì)政治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漢字本身自有它存在的歷史價值,既用不到廢除也決不會廢除。(為上海新文字研究委員會修改的《拉丁化中國字運(yùn)動新綱領(lǐng)草案》,1939年7月)
語言文字問題是我們社會生活上的基本問題。靠著語言文字,我們才可以經(jīng)營社會生活。我們對于語言文字理解得正確不正確,處理得適當(dāng)不適當(dāng),往往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上發(fā)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希望社會生活逐漸進(jìn)步,趨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確和適當(dāng)。(《“中國語文學(xué)會”成立緣起》,《文匯報》1947年2月14日)
錢玄同
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biāo)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yè),我們當(dāng)然應(yīng)該竭力去進(jìn)行。但這種根本改革,關(guān)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dá)到目的的。……但現(xiàn)行漢字在學(xué)術(shù)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經(jīng)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圖補(bǔ)救的方法!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才來改革!(錢玄同、黎錦熙、楊樹達(dá)、陸基在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上的提案《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1922年)
國語文學(xué)是活的文學(xué),國語是活的語言,所以現(xiàn)在應(yīng)該用天然的活語活音作為國語國音,而且還應(yīng)該定一種活語活音作國語國音的基本,而再旁搜博采許許多多別種活語活音以輔助之增益之,使國語國音豐富到不可限量。所以現(xiàn)在定用北京語北京音作國語國音的基本,這是咱們的主張。(《給黎劭西的信——樵歌的跋》,《語絲》1926年10月23日第102期)
黎錦熙
漢字革命,為的是文學(xué)的革新和文化的增進(jìn)與普及,是學(xué)術(shù)上的問題,是教育全部的問題,不但是通俗教育,平民教育的問題。漢字革命,為的是要使?jié)h語脫離漢字,得到一個“真切的表現(xiàn)”。……用改革文字的手段來保存語言,整飭語言,提高語言,修飾潤色語言。(《漢字革命軍前進(jìn)的一條大路》,《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1922年8月)
所謂“不統(tǒng)一”的國語統(tǒng)一又怎么講呢?國語統(tǒng)一,并不是要滅絕各地方的方言,因?yàn)榉窖允鞘聦?shí)上不能滅絕的,是有歷史關(guān)系的,而且在文學(xué)上也是狠有價值的。用滅絕方言的手段來強(qiáng)迫國語的統(tǒng)一,這又是二千年前李斯丞相所干的勾當(dāng),是終于沒有效果的。(《全國國語運(yùn)動大會宣言》,1926年1月)
1949~1978年
毛澤東
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寫的按語,1955年12月)
(漢語拼音方案)在將來采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么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以采取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凡是外國的好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xué),就是要統(tǒng)統(tǒng)拿過來,并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20日)
文章要有中國氣派、中國風(fēng)格。中國文字有自己獨(dú)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樣嚴(yán)格要求有主語、謂語、賓語。你們的文章洋腔洋調(diào),中國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同吳冷西、田家英講到如何寫文章時的談話,1958年10月26日)
周恩來
當(dāng)前文字改革的任務(wù),就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現(xiàn)在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是在過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種拼音方案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這個方案,比起歷史上存在過的以及目前還在沿用的各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來,確實(shí)更加完善。……漢字在歷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這一點(diǎn)上我們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至于漢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yuǎn)不變呢?還是要變呢?它是向著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xiàn)在還不忙作出結(jié)論。(《當(dāng)前文字改革的任務(wù)》,《人民日報》1958年1月13日)
吳玉章
我國使用漢字,已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要改變成為拼音文字,自然不是很短時間所能完成的。而且,即使在開始實(shí)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個新舊文字并用的過渡時期。……因此,在漢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適當(dāng)?shù)卣砗秃喕F(xiàn)在的漢字,使它盡可能減少在教學(xué)、閱讀、書寫和使用上的困難,就有迫切的需要。(《關(guān)于漢字簡化問題》,《人民日報》1955年4月7日)
要使?jié)h族人民,普遍使用一種共通的語言,這是一件移風(fēng)易俗的大事。這是一項(xiàng)長期的艱巨的工作,不能強(qiáng)迫命令,急于求成。……應(yīng)當(dāng)本著科學(xué)的實(shí)事求是的精神,……把推廣普通話的工作,作為一種科學(xué)實(shí)驗(yàn),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在第四次全國普通話教學(xué)成績觀摩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64年8月17日)
羅常培
語言是人們用來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標(biāo)準(zhǔn),才能使人們正確地互相了解。……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是個很復(fù)雜的問題,因?yàn)椴坏歉鱾€民族形成的方式可以頗有不同,而且各個民族原來的“語言生活”也是多種多樣。這里只能極概括地說明。
詞典是進(jìn)行規(guī)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詞匯是語言的建筑材料,現(xiàn)在在語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亂情形一大部分是在詞匯方面。(羅常培、呂叔湘《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1955年10月)
王 力
在文字改革前途上也的確存在著許多困難,需要全國知識分子共同討論,共同尋求妥善的解決方法。只要是善意的、企圖解決文字改革的困難的意見,都應(yīng)該受到歡迎。甚至懷疑文字改革和反對文字改革的言論,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都應(yīng)該予以發(fā)表。(《關(guān)于文字改革問題應(yīng)該經(jīng)常展開辯論》,《文字改革》1957年第10期)
簡化漢字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因?yàn)榉斌w字難寫,難認(rèn)。有些知識分子低估了簡化漢字的作用,以為多寫幾筆沒有什么關(guān)系;有些人寫慣了繁體字,一時改不過來,因此產(chǎn)生了抵觸情緒,甚至有人認(rèn)為簡化漢字破壞了“六書”(據(jù)說“六書”是造字的原則),從根本上反對簡化。這些都是沒有替六億人民的利益著想。(《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wù)》,《文字改革》1960年第3期)
1978~2012年
鄧小平
現(xiàn)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nèi)容重復(fù),新的語言并不很多。重復(fù)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shí)事,多做少說。〔《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diǎn)》,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江澤民
語言文字工作,我講三點(diǎn)意見:一、繼續(xù)貫徹國家現(xiàn)行的語言文字工作方針政策,漢字簡化的方向不能改變。各種印刷品、宣傳品尤應(yīng)堅(jiān)持使用簡化字。二、海峽兩岸的漢字,當(dāng)前可各自維持現(xiàn)狀,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將來去討論。三、書法是一種藝術(shù)創(chuàng)作,寫繁體字,還是寫簡化字,應(yīng)尊重作者的風(fēng)格和習(xí)慣。可以悉聽尊便。(《江澤民總書記對語言文字工作作出三點(diǎn)指示》,《語文建設(shè)》1993年第1期)
胡錦濤
建設(shè)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體系,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推廣和規(guī)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繁榮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化事業(yè)。(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
胡喬木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了名之后可以貫徹新的方針,說服大家適當(dāng)放慢文改腳步,并說明文改的內(nèi)容擴(kuò)大了,名副其實(shí),……改了名,表示文改工作進(jìn)了一步,有利于開展工作,適合國家和社會需要。現(xiàn)在嘛,名不副實(shí),檢字法、漢字信息處理、語言規(guī)范化等等,文字改革就包括不了。〔《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領(lǐng)導(dǎo)成員的談話》,1985年7月2日,載《胡喬木談?wù)Z言文字》(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
呂叔湘
語言的研究不應(yīng)局限于語言本身,也要研究人們怎樣使用語言,研究語言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語言研究》創(chuàng)刊號題詞,1981年)
中國的詞典事業(yè)可憐得很,在國際上比較起來,簡直太不象樣。這么一個文明古國,詞典事業(yè)是如此之不發(fā)達(dá)!……法國的面積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論人口,法國人口五千萬,我們是他們的二十倍。他們的詞典兩萬多種,我們不知道出到了兩千種沒有,相形之下實(shí)在是難為情。……所以說,詞典工作大有可為,夸大一點(diǎn)說,是不朽的事業(yè)。(在《漢語大詞典》第二次編委會上的講話,1980年11月)
周有光
1982年“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國際標(biāo)準(zhǔn)”(ISO 7098)。漢語的字母從“民族形式”到“國際形式”,從“國內(nèi)使用”到“國際使用”,從“國家標(biāo)準(zhǔn)”到“國際標(biāo)準(zhǔn)”,一座使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化通向國際舞臺的橋梁建成了。(《新時代的新語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
人類學(xué)中有一個“失去了的環(huán)節(jié)”(missing link):猿和人之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還沒有找到。文字學(xué)中也有一個“失去了的環(huán)節(jié)”:意音文字和字母之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還沒有找到。(《比較文字學(xué)初探》,語文出版社,1998年)
2012年~
習(xí)近平
一個國家文化的魅力、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過語言表達(dá)和傳遞。掌握一種語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國文化的鑰匙。學(xué)會不同語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進(jìn)而客觀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處。(習(xí)近平在同德國漢學(xué)家、孔子學(xué)院教師代表和學(xué)習(xí)漢語的學(xué)生代表座談時的講話,2014年3月)
語言相通是人與人相通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語言不通就難以溝通,不溝通就難以達(dá)成理解,就難以形成認(rèn)同。在一些有關(guān)民族地區(qū)推行雙語教育,既要求少數(shù)民族學(xué)習(xí)國家通用語言,也要鼓勵在民族地區(qū)生活的漢族群眾學(xué)習(xí)少數(shù)民族語言。(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wù)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tuán)結(jié)進(jìn)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fā)現(xiàn)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tǒng),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fā)展。(致信祝賀甲骨文發(fā)現(xiàn)和研究120周年,2019年11月)
要認(rèn)真做好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國家統(tǒng)編教材。要在各族干部群眾中深入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特別是要從青少年教育抓起……(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內(nèi)蒙古代表團(tuán)審議時的講話,2021年3月5日)